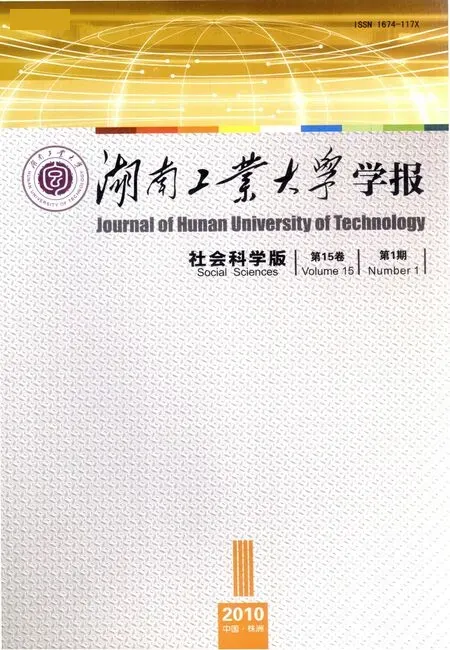援道入儒 外道内儒
——汪曾祺品人散文中的立人理想
2010-04-07刘长华
刘长华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沙410081)
援道入儒 外道内儒
——汪曾祺品人散文中的立人理想
刘长华①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沙410081)
汪曾祺品人散文是散文史上值得关注的存在。其文学世界里的主人公群体主要是由“热爱”与“天真”两类文化性格组成,从中充分传达出作者一种“印象”和“直觉”的品人观。这是汪氏“援道入儒、外道内儒”的立人理想的体现,和传统“儒道互补”的内涵不同,从中隐含了其对诉诸西方资源改造国民的反思与拒绝,并包涵了其寻根思想之精义,具有一定文学思想史的考察价值。
汪曾祺;品人散文;立人理想
众所周知,沈从文的立人思想鲜明而有特色。其立人思想的具体内涵就是将湘西文化中的“自然”“生命”等特质,即金介甫所说的“心理健康与尊严”。[1]灌输给被封建正统文化、现代都市文明“阉寺”了的国民,以实现民族精神的现代性“重造”。他的弟子汪曾祺在立人思想这一文化阵地上也是有过作为的,并且不是简单接手沈氏衣钵,而是另辟道路,标识出了自己的独异与清晰。本文拟从当前研究相对薄弱以至于付之阙如的领域——汪氏的品人散文入手展开探讨,以期获得某些认知。
一 、人物审美性格:“热爱”与“天真”
汪曾祺被人冠以“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自是其身上所表露出的文化性格、生活情趣等与传统密切相连的鲜明气质。“品藻人物”便是这些特点之中的突出表征。在汪氏的创作世界里,品人之类的篇什所占比重是不下半数,关涉的对象涵盖了古今中外、尊卑老幼,主人公的出场方式有追忆,有纪实,有道听途说,有据史征引……一切表明品人是汪氏的用力、用心之所在。既为“品人”,其重心无疑主要是落在被品之人的审美性格之中,譬如魏晋时人品人时,他们关注的是人物的“清”与“神”之气质。[2]汪曾祺在品谈沈从文时曾说:“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对工作、对生活充满兴趣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正是沈先生的气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在品谈沈从文,文中的沈氏又在品谈别人,俨然台上台下都是戏,这充分地见证了两人的精神血缘。事实上,上述两类人物恰在汪氏笔下出现最多,特性也最明白。这也就成了汪氏散文中最为“凸显”的个性。
“热爱”一词,汪氏将它对应为“生活”。首先,这种“热爱”对应的是入世情怀。虽然汪氏的品人散文中没有描述过业儒形象,甚至对“国子监”(《国子监》)某些行为有所诟病,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对入世者的称颂。在《笔下处处有人》中,汪氏就以遮掩不住欣赏的口吻说:“宋士杰是一个好人。他好在,一是办事傲上。在旧社会,傲上是一种难得的品德。一是好管闲事。”《地质系同学》中写道:“我的地质系的同学,年龄和我不相上下,都已经过了七十了。他们大概是离、退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会是离而不休、退而不休。他们大概都还在查资料、写论文,在培养博士生、硕士生,不会是听鸟养花,优游终老的。”所以,于文末汪氏感慨系之:“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多好的知识分子”。入世情怀还可形象地表述为“铁桥”和尚冲破清规戒律,对世俗生活的珍爱和与女人间的欢娱情爱(《三圣庵》)。其次,这种“热爱”表现为仁爱心肠。汪氏对沈从文品与写的份量最多,质量也是最为上乘之一,以至于标识了新文学领域里的某种高度。在对沈的品评中不乏这样的语句:“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他的书,除了自己看,也是借给人看的”(《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甚至在汪氏看来,仁爱之心是沈从文写作成功与否的关键:“首先要有一颗仁者之心,爱人物,爱这些女孩子,才能体会到她们的许多飘飘忽忽的,跳动的心事。”(《沈从文和他的〈边城〉》)戏剧家谭富英在病危时,拒绝贵药,并说:“这药留给别人用吧!”至此,汪氏不禁嘘欷:“重人之生,轻己之死。如此高格,能有几人?”(《马·谭·张·裘·赵》)。哲学家金岳霖的一些行为很耐人寻味,“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金岳霖先生》)金先生“变相”地“慈爱”小孩。汪氏的父亲“为人很随和,没架子。他时常周济穷人,参与一些有关公益的事情。”(《我的父亲》)最后,这种“热爱”就是笔下人物对业务的全身心投入。《马·谭·张·裘·赵》中不仅盛赞他们技艺的精湛,而且嘉言了他们的治艺之精勤:马连良“在做角色准备时是很认真的。一招一式,反复琢磨。”裘盛戎被汪氏揽入记忆深处:“睡得很晚,晚上他一个人盘腿坐在床上抽烟,一边好像想着什么事,有点出神,有点迷迷糊糊。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后总觉得盛戎的许多唱腔、唱法、身段,就是在这么盘腿坐着的时候想出来的。”如上人物专注业务,不是孤芳自赏,而是益于世道人心的。
“热爱”是一种积极心态,是基于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应对。在巨大的生存关系网络中,个人与自我关系的处理是重要节点,也是鸿蒙以来人们一直思考的课题。汪氏的意见是正如上文所提“热爱”的同时,却不能失却“天真”。“天真”便是他对处理个人与自我关系问题上的回答。
具体说来,这种“天真”应涵括两个方面。一是指真实做人,不为世俗名利所束缚。汪氏笔下的人物往往机心稀薄、俗念浅少,而且这些人物占据了其品人散文的主角。乃师沈从文就是“赤子其心”。金岳霖是“很有趣的”,所以不恃身份和小孩逗乐。杨慎在“保山是仍然保持诗人气质,放诞不羁的。‘所至携倡伶以随’。”(《杨慎在保山》)潘天寿的脾气很“倔”,“文革”中他也“不识时务”,亦是如此(《潘天寿的倔脾气》)。这些人物为人处世都坦荡真如,没有戴着面具糊人、骗人,更遑论包藏祸心害人,符合人的真正本质。第二,它是指以艺术生活来滋润人性。艺术家、作家、文人、学者等是汪氏谈得最多的,他们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斗争和社会利益冲突之间的交集,人性在艺术中得到了转移与升华。与之同时,有些人虽然不是文化人,但他们的性情充满艺术色彩,散发着奇谲遐思,也是汪氏所“津津乐道”的。比如他回忆:“我父亲这个孩子头儿带着几个孩子,在碧绿的麦垅间奔跑呼叫,为乐如何?”(《我的父亲》),“我的祖父本来有点浪漫主义气质,诗人气质的”(《我的祖父祖母》),比如他写家乡曾经“拉皮条”的“薛大娘”给“蒲三爷”拉拢女人,拉的就是她自己。“薛大娘不怕人知道了,她觉得他干熬了十一个月,我让他快活快活,这有什么不对?”(《一辈古人》),这完全不同于世态常情。
不难看出,如上的“天真”都充分标识了对人性、对自我的尊重。当然,最好是“天真”的“热爱”,“天真”被纳入或化合在“热爱生活”的范畴之内。这正如汪氏在《金岳霖先生》中的文末所写:“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哲学家予人的符号意义就是“超凡脱俗”,而汪氏将其设计为带着一脸好奇,深入市井,汲食人间烟火,意象本身是荷负着象征功能的,“为人天真”与“热爱生活”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的寓言,这正是汪氏所希冀的理想人性。
二 、品人艺术风格:“印象”或“直觉”
在《短篇小说的本质》一文中,汪氏如是说:“悬定一个尺度,很难。小说的种类将不下于人格;而且照理两者的数量(假如可以计算)应当恰恰相等;鉴别小说,也如同品藻人物一样的不可具体说。但我们也可以像看人一样的看小说,凭全面的、综合的印象,凭直觉。”汪氏在不经意间阐发了“品人理论”,是其品人实践的积淀与升华。尽管只言片语,但“微言大义”,因为从方法论的意义角度来看,甚至可以说在整个新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于一般意义上的现当代作家品人实践中胜出。基于传统基因和整合沈从文等人的文学批评所给予的影响,按照“印象”或“直觉”的总体要求,汪氏在具体实践和行文表达中渗透着鲜明的品人艺术个性。
第一,涵泳着生活情趣是其品人内在意向。“印象”或“直觉”对象的生命本质就在于讲究情趣或审美。魏晋时期“品藻人物”之风大兴,就是以超越现实苦难、政治压抑、功利追求为趋向的;“京派”文人力倡“印象主义”文学批评,亦是部分出于对社会批评等大行其道的反拨。不过,这些行为于外在形态上显得抽象、玄妙。汪氏不落故常,继承他们对美追随的同时,却将艺术的脚根踏在生活大地上,真正生动地诠释了“诗在生活”的理念。他的品人触角延伸在日常生活里的百姓人家,如《闲市闲民》、《美国女生——阿美利加明信片》、《我的祖父祖母》、《一辈古人》、《继母》、《道士二题》、《罗汉》等就是典型例证。与之同时,他笔下的文化名流、知识精英都是生活的儿女,血液中流淌凡人性情。闻一多先生上课抽烟,开讲时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闻一多先生上课》)。语言学家唐兰和照顾自家生活的女孩产生感情,向其写情词(《唐立厂先生》)。作家林斤澜不顾口忌,美食是来着不拒,同时也“吃喝很平民化的”(《林斤澜!哈哈哈哈……》)。在《金岳霖先生》中,金岳霖一举一动完全散发着无比的生活气息,让人感到热情与快乐。就是有些“问题人物”如于会泳,是“不讲人情的”,但汪氏将其冠冕堂皇的政治嘴脸通过某些细节加以反讽的方式让人忍俊不禁。汪氏品人从涵泳着生活情趣的内在意向出发,使得这些人物在其文字里“活”出了“神采”或“风骨”,生活的亲切、诗意的享受以及特别是人性的健康都得到了充分的传达。我们想,此才是汪氏所看重的。
第二,“于新奇而不猎奇处见精神”是其品人的出彩技巧。人生是一轴长卷,岁月浩荡,变幻万千,所以,汪氏说“品藻人物”是“不可具说”的。“不可具说”中却往往说出了神韵。汪氏凭藉个性与自由的性情,总能抓住被品之对象身上的某一闪点或某些侧面,从中开掘出耐人寻味的韵采。唐兰本是研究古汉语,他却自告奋勇地教词选,他教词的特点就是:“讲是不讲,不讲是讲”(《唐立厂先生》);吴宓在讲“红楼梦”时候给女同学搬座位,表现出了“贾宝玉精神”(《吴雨僧先生二三事》);孔子在汪氏眼里不是一个峨冠博带的“正人君子”形象,而是诗意盎然的“诗人”,因为他“编选了一本抒情诗的总集——《诗经》”,并在《论语·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所表现出的“潇洒自然的生活态度是很美的。”(《我的创作生涯》);刘文典讲庄子,开场白就是:“《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西南联大中文系》)……不难看出,其中的“韵采”就表征为被品人物身上某些亮点的“脱颖而出”。如是而为在“无目的”中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方面,被品人物在一些“点”或“面”中显得更为有血有肉,别有风采,一方面被品人物因这些陌生化效果在读者心中留刻下的痕迹更鲜明。这些人物性格正如上文所说本来就涵泳着“生活情趣”,这就是所谓的“于新奇而不猎奇处见精神”。
第三,优雅而灵动的品人姿态。品人是主体对客体的情感投入和凝结,表露着主体的情感色彩、文化身份、言说姿态。汪氏拓印在品人文字里的是优雅与灵动。首先,被述说者较少与苦难生活、卑劣人性有交集。中国近现代是由苦难所主宰的历史,诉说苦难和批判人性是最重要的诗学。而汪氏笔下似乎都没有苦大深仇感,亦不怨天尤人,而是浸润在“生活情趣”中,追求情调、与人为善,就是“于会泳”这些人物,汪氏也将他们的生存悲剧归为有些荒诞而又强势的政治使然。所以,汪氏品人的行文思路、文字表达中就没有那种执着苦难而产生的凝滞、困厄之感。其次,述说时的情感处于“出”与“入”之间。“怨恨”被人归纳为典型的中国现代情绪。[3]在传统的沉重负累和现代性的迅猛推进之间挣扎便是文化转型期的现代中国的最根本特征,现当代作家因而很少具有公正缓和的语气来写作。汪氏品人亦是带着强烈的情感,用着真实的感情说着想说的话,所以,笔下人物才生动传神。不过,汪氏比一般作家更“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4]情感的流露都寓含在对人物的描述和品味之中,都由他们的行动和思想折射出来,汪氏的抒情温文敦雅。最后,述说时的用语既妥贴又充满灵动。既为品人,予人评价就理属必然。裘盛戎的艺术表演是:“粗豪和妩媚是辩证的统一。”(《裘盛戎二三事》),潘天寿是“倔脾气”(《潘天寿的倔脾气》),闻一多“炽热而又严冷的目光审视着现实”能表达着他的“内心世界”(《闻一多先生上课》),铁凝的作品很“清新”(《铁凝印象》)……如上结论完全是“知人之言”,审美眼光和思辨能力达成完美统一。
三 、立人理想:援道入儒和外道内儒
汪氏为何选择“热爱”与“天真”这两种类型的人物性格特征为其审美表象?为何又只看重“印象”或“直觉”是其品人的主要方法?这一切都导源于他“援道入儒、外道内儒”的立人思想。
首先,其笔下的人物审美品格正是“儒”、“道”文化内蕴的映射和凝结。第一,“热爱”一词的意义在汪氏散文中正和儒文化构成对称。通过梳理,我们知道,汪氏所意指的“热爱”主要包含了“入世情怀”、“仁爱心肠”、“投入业务”三个方面的内容。返观儒家文化的价值体系,包含如下取向:讲求进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力主人道,“仁者,爱人”;倡导钻研,“业精于勤”。汪氏笔下的“热爱”所涵括的范畴完全与它们构成契合的对应关系,这也就清楚地表明儒家文化是汪氏的价值诉求之一。第二,汪氏赋予“天真”一词是与道家文化内涵紧密相联。道家文化视功名如鄙屣,反对繁文缛节,在山水自然中舒放着艺术心态,于为人处世上确保着全真性情。从“真实做人”、“艺术心态”这两种类型的人格气质在汪氏笔下主人公身上的所呈现的生动与趣味来看,它们正是从道家文化中生发而成,彰显着道家文化的某些魅惑与神采,汪氏对道家文化亦有“所欲也”的“内心需要”因此一览无余。第三,“热爱”与“天真”的交融在汪氏的品人世界里圆满地表征着“援道入儒、外道内儒”的立人思想。儒家、道家文化在汪氏这里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统一的。这正如他自己所说:“作家的思想是一个复合体,不会专宗哪一种传统思想”(《我的创作生涯》)。“儒”“道”两者究竟如何“复合”,无疑,这又是一个丰富多维的话题,汪氏选择的路径即我们所归纳的:援道入儒、外道内儒。这是因为总体看来,在汪氏所品之人物,机心稀薄、俗念浅少,保持着道家的“真”或“奇”的风貌;或者表面上冷眼看人间,俨然道家作派,内心深处却燃烧着一股浓浓的爱意,爱惜羽毛、坚守人格、关爱民瘼、体恤他人……换言之,他们要不是以“天真”的心灵在“热爱”生活,要不就是因为“热爱”而显示出非同寻常的“天真”,一切仅仅是程度深浅而已。上升到思想史角度来观照,汪氏是以道家的“守真”、“性灵”来冲淡儒家因执着社会和过分追求功利而导致的主体异化、物化之苦,同时,以儒家的进取心、责任感为旨归来矫正道家的绝对个性主义和自由散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一句话被汪氏在文章中反复引述,他很欣赏曾子所表达的“潇洒自然的生活态度”(《我的创作生涯》),句中所描述的意境正是“援道入儒、外道内儒”思想的最感性、最有说明力的诠释。其次,汪氏品人姿态行为本身就体现了“援道入儒、外道内儒”的人格思想。“风格即人格”。孔子品人时,言语公允执中,是其“中庸”思想的反映;魏晋时人崇尚“贵无”主义,故品人时放言无忌或好作玄秘;鲁迅是战斗情怀,品人时因此有时在深刻中不免尖刻。汪氏的品人艺术特色给人印象就是:既生动有趣又不粗俗浅薄,既有厚实的内容又不失形式的灵动,行文的散漫灵动是其品人姿态最直观显现。这些正是“援道入儒、外道内儒”的人格理想如实外化,也无形中注解了散文最能展露作者真情实感的通行说法。而且正是从“援道入儒、外道内儒”出发,所以,汪氏才会说:“我对生活,基本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人类是有前途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没有那么多的失落感、孤独感、荒谬感、绝望感。”所以,他“愿意把这些朴素的信念传达给人”。(《我的创作生涯》)
汪氏“援道入儒、外道内儒”的立人思想,更让人们能辨别他与沈从文之间的歧异。通过对这种形象所阐发出来的思想进行解读,将获取汪曾祺在文学思想史上几个新的认识:
其一,它隐含了汪氏对整体历史语境援引西方资源对国民性改造的反思与拒绝。“国民性”改造是20世纪的大课题,各种阶层都有过他们的方案甚至举措。知识界的主导思路就是西方的人文主义。对个性、对自我的尊重与张扬就是这种人文主义的关键内容。问题是,这种个性、这种自我很容易滑向绝对利己主义,造成人际的紧张、内心的枯寂,鲁迅“先知”般洞察到了这点,所以呼唤“大独”。不过,这仅也是一种乌托邦,几千年来被集体意识完全所麻痹的民族不可能一夜之间觉醒。鲁迅小说里因而出现了启蒙被消解、意义轮回的主题与叙述心态上的焦灼。既然西方的人文主义难以避免给人心灵带来“失落感、孤独感、荒谬感、绝望感”(《我的创作生涯》),那么,如何补救或者规避,同时又不重蹈传统对个性的压抑与泯灭的老路?其实,这种悖论与困惑一直是新文学若隐若现的抒写线索和悲剧基调。从鲁迅、巴金、丁玲、路翎等到当代的李存葆、路遥、贾平凹等人一些作品都有所体现。汪氏选择的是“传统创造性转化”的思路,即我们所归结的“援道入儒、外道内儒”。其目的也正如上文所说的“以道家的‘守真’、‘性灵’等来冲淡儒家因执着社会和过分追求功利而导致的主体的异化、物化之苦,并以儒家的进取心、责任感为旨归来矫正道家的绝对个性主义和自由散漫”。这种创造性转化自然也就暗含了整体历史语境援引西方资源对国民性改造的反思与拒绝,这种立人思想就是所谓汪氏的“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我的创作生涯》),而不是文艺复兴特别是后期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人道主义。汪氏这种立人思想在整个新文学坐标系中独一无二。
其二,它道出汪氏的“寻根思想”之精义。汪氏属于“寻根”文化一派,这是公论。但是,稍作深究,汪氏“寻”的是哪般“根”呢?答案可能会五花八门,有说是寻“风俗”的,有云是寻“民族美德”,甚至干脆语焉不详地说寻“传统文化”的……因为问题本身是文学思想史没有解决的。其实,汪氏自己说得好,“写风俗,不能离开人”(《汪曾祺·文论卷》,还说过:“在中国,不仅是知识分子,就是劳动人民身上也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些人没有读过老子、庄子的书,但可能有老庄的影响。”(《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从这些话语中可以得出,寻“风俗”实际在寻“人”,寻“人”时讲到了老庄,而老庄是反对俗德的。所以,汪氏寻“传统文化”的精义就在于“援道入儒、外道内儒”。
同时,需提醒的是,这种“援道入儒、外道内儒”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互补”有所差异。传统的“儒道互补”在后来就主要体现为“补儒家之偏”和“补儒家之缺”,没有把“道家”真正意义上地放在外在情形之上,而主要是士大夫放逐于庙堂之外,落魄于江湖之中时安身立命的技巧或者一种庸俗的官宦哲学,不是建立在汪氏所处的对现代性人格反思的语境之上。有人在探讨彼得拉克时说:“他对于古代充满热情的研究的情形可以而且应该引发一种仿超意识”。[5]“援道入儒、外道内儒”,强调了“道家”时刻以外表方式出现,和“儒家”共生同存、不可分割,主体永远保持着生活的乐趣,说到底就是“自由”要分足“责任”的地盘,而且是第一印象,它的主体对象是整个国民,而不是一群“进就儒,退就道”的士子。
[1]金介甫.沈从文传[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254
[2]宁稼雨.《世人新语》与人物品藻的范畴演变[J].文艺理论研究,2005(6).
[3]刘晓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8.
[4]王国维.王国维文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36.
[5]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8.
Introducing Daoism into Confucian ism,Daoism Outside and Confucian ism W ithin——OnWANG Zeng-qi’s People Cultivation Philosophy in His Personality Comment Prose
L IU Changhua
(Literature College,Hunan NormalUniversity,Changsha Hunan 41008,China)
WANG Zeng-qi’s personality comment prose is remarkable in the prose history.The protagonists in his literaryworld are of two cultural types:"lovable"and"naive",which show the author’s unique personality comment idea of"impression"or"intuition".Wang’s people cultivation idea of"introducing Daois m into Confucianis m,Daois m outside and Confucianism within"differs fromthe traditional"complementation of Confucianis m and Daois m"and isof some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study of literary ideology history,in which are his ideas of introspection and refusal of refor ming people through resorting to western resources hidden and the real meaning of seeking ideological root included.
WANG Zeng-qi;personality comment prose;the idea of cultivating people
I206.6
A
1674-117X(2010)01-0104-05
2009-04-28
刘长华(1978-),男,湖南隆回人,湖南师范大学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