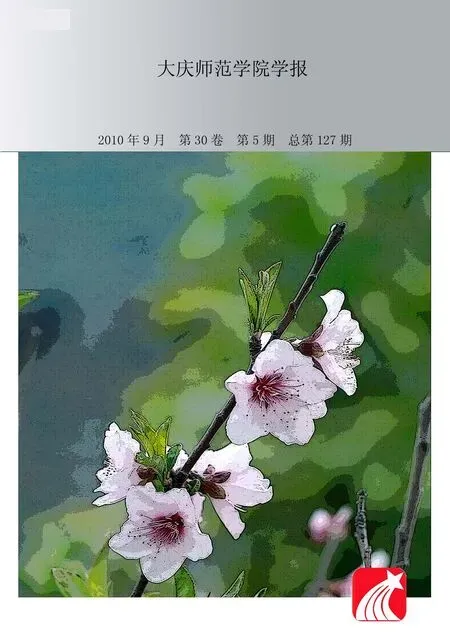试论自然地理环境对屈原创作的影响
2010-04-06唐海宏
唐海宏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甘肃 成县 742500)
自古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不但很不平衡,而且文化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同时,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形成又都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而自然地理环境又进一步通过物质生产、文化环境以及技术系统等形式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包括文化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文化创造的基础,而文学创作、文学作品也无不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一、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各要素对文化发展具有影响作用
在先秦《周礼·考工记》中有涉及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影响的论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橘踰淮而北为枳,鸲鹆不踰济,貉踰汶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另外,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声音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主上之情欲,故谓之俗。”班固在这里说明了人的性情、气质的形成,发展,变化受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地域差异使人的个性、气质乃至文学创作也具有鲜明的地域性。
在西方也有相似的看法。黑格尔将人类发展的地理条件分成三种类型,阐明了不同地形条件对人们生产、生活和性格的影响。一是“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原和平原”,这里的居民中“没有法律关系的存在,因此,在他们当中就显示出了好客和劫掠的两个极端”。二是“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所流过的地方”,这里土地肥沃“在这些区域里发生了伟大的王国,并且开始筑起了大国的基础”,“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便跟着发生了”。三是“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1]他恰如其分地估价了地理环境对文化发展的作用状况。
现代,童庆炳在其《文学理论教程》中也提道:“在同一时代和同一民族的不同地域中,由于环境条件的不同,民俗风情的不同,反映在文学风格上,可能形成不同地域的特点。”[2]张岱年曾说过:“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的意识或精神的基础。”[3]同时他又说:“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物质条件,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3]
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很多情况下自然地理环境是通过作用于人文地理环境整体或其他要素,进而作用于文化要素的,因而可以说,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各要素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作用是地理环境作用于文化发展的最初根源。同样,作为个体的人的作家也一样会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其创作亦然。
二、自然地理环境对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风格语言的影响
(一)自然地理环境对屈原作品思想的影响
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屈原出生于楚地的归国(即现在湖北省西部的秭归县)。在《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注》引宋忠说:“县故归乡,《地理志》曰:归子国也。……‘归’即‘夔’,归乡盖夔乡矣。”
据上面这些记载,屈原较为准确的出生地即秭归或秭归周边地区。秭归及其周边的自然地理环境,一是地形复杂,多由高山、丘陵、平原等地貌组成,使得自然景观奇幻多变;二是地形多为山区丘陵,素有“七山一水两分田”的美誉。同时郦道元在《水经注·江水注·三峡》中写道:“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迭嶂,隐大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崦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而且其出生地正好处在巴蜀与荆楚的交界处,其西有《华阳国志》记载“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谨,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的四川盆地;其东有“两湖熟、天下足”,“极目楚天舒”的洞庭、江汉平原。而其地又以产盐著称,虽然地形以高山峡谷为主,日照时间短,但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当地居民质朴、刚毅而坚贞不屈的性格。
我们可以说正是这伟岸、雄拔的高山,造就了屈原坚忍的意志。这些反映在作品中则是他百折不回的爱国精神和探索精神。像《哀郢》说道:“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晁吾以行。”《抽思》中写道:“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唯郢都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识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离骚》则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随俗则存,矢志则亡。他又何尝未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无奈他独立不迁、禀性难移;“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不能舍也”、“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悔兮,岂余心之可惩”一篇之中,何啻三复斯言!在这里诗人反复诉说、反复吟唱的是深切的乡土之爱,及植根于其上的爱国主义激情。作为楚文化的代言人,屈原不同于战国时的游士,他没有周游列国以求一用。从他的出身、所属阶级和他所受的儒家文化的熏陶来说,去国远游自是一种精神的背叛、文化的背叛。这就使其作品更具有深邃的思想,而这深邃思想正是自然地理环境所赋予。
(二)自然地理环境对屈原作品内容的影响
王逸《离骚经序》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从这则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楚地的社会习俗,这也说明了楚文化对屈原的影响。那么自然地理环境对屈原的作品内容有影响吗?回答是肯定的。
在屈原的众多作品中无不涉及到自然风物。如《橘颂》中写道:“后皇嘉树,橘来服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离骚》写道:“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茞?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九歌·山鬼》则有:“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辟荔兮带女萝……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作品中对自然地理环境的描述也无不带有浓浓的楚地特征。同样在《九歌·山鬼》中作者还写道:“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涉江》则有“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难怪乎沈从文曾深有感触地说道:“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两千年前中国会产生一个屈原,写出那么一些美丽神奇的诗歌,原来他不过是一个来到这地方的风景记录人罢了。屈原虽死了两千年,《九歌》的故事还依旧如故。”[4]这里自然地理环境对屈原作品内容的影响可见一斑。
诚如南朝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勰指出:“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馀者,晓会通也。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鉴风人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5]正是这些形形色色变化无穷的自然景物、自然环境赋予了屈原作品取之不竭的内容,使他的作品深深地植根于楚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当中。
(三)自然地理环境对屈原作品风格的影响
魏徵《隋书·文学传》序中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义,理胜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明代屠隆在《鸿苞集》中认为:“周风美盛,则《关雎》、《大雅》;郑、卫风淫,则《桑中》、《溱洧》;秦风雄劲,则《车邻》、《驷》;陈、曹风奢,则《宛丘》、《蜉游》;燕、赵尚气,则荆、高悲歌;楚人多怨,则屈骚凄愤,斯声以俗移。”日本的青木正儿这样论述中国南方气候环境对作家的影响:“南方气候温暖,土地低湿,草木繁茂,山明水秀,富有自然资源。所以,南方人生活比较安乐,有耽于南国幻想与冥思的悠闲。因而,民风较为浮华,富于幻想,热情,诗意。而其文艺思想,则趋于唯美的浪漫主义,有流于逸乐的华丽游荡的倾向。”[6]以上这些都说明了自然地理环境对作家的作品风格有着重要的影响。
再联系到屈原的作品我们就可以看出其作品绮丽浪漫的想象是多么的瑰丽了。如屈原在听了灵氛之吉占遨游天界一段:“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蘼以为粻。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扬云霓之晻蔼兮,鸣玉鸾之啾啾。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乎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驾八龙之蜿蜿兮,载云旗之委蛇。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娱乐。陟陛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而《九歌》“筑室兮水中,茸之兮荷盖。荪壁兮柴坛,菊芳椒兮成堂。桂栋兮兰撩,辛夷楣兮药房。罔辟荔兮为帷,擗蕙櫋兮既张。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这种奇丽的想象将作品的浪漫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离骚》中关于神游一段的描写,诗人朝发苍梧,夕至县圃,他以望舒、飞廉、鸾凰、凤鸟、飘风、云霓为侍从仪仗,上叩天阍,下求佚女,想象丰富奇特,境界仿佛迷离,场面宏伟壮丽,有力地表现了诗人追求理想的精神。
这里屈原驰骋想象,糅合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编织幻想境界。我们可以说这是屈原故乡——荆楚大地(西有巫山、荆山耸峙,北有秦岭、桐柏、大别诸山屏障,东南围以幕阜山地,恰似一个马蹄型巨大盆地。在这里,长江横贯平原腹地,汉江自秦岭而下,逶迤蜿蜒,源出于三面山地的千余条大小河流,形成众水归一,汇入长江的心状水系,形成了其独特而优越的地理环境)赋予了他创作的灵性。家乡的山林溪谷,河湖沼泽无不给诗人以无穷的想象,这些想象又融入作品中则表现为瑰丽、奇幻的浪漫风格。
在自然地理环境赋予他无穷想象的基础上,屈原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风格,而且还广泛采用神话神巫故事,同时也运用了许多寓言,这样使他的作品不但委婉、清丽而且更富于浪漫。
(四)自然地理环境对屈原作品语言的影响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中指出:“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鈋鈍,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 阮籍《乐论》:“故八方殊风,九州异俗,乖离分背,莫能相通;音异气别,曲节不齐。”这里他们分别论及了南北方自然地理环境对语言及人的气质的影响和殊风异俗造成学术的音异气别曲节不齐。这些地理环境决定和限制了各个地域不同的人文环境,进而影响到了语言。
而楚文化不同于黄河流域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追求对称和工稳,而是更跳跃、更激情,它具有非常鲜明的楚地域文化特征,它激越而又有序,笃实而又灵动,浪漫而又实际。在精神文化方面,楚文化有“巫”、“道”、“骚”三大精萃。道学的睿智妙论、巫学的奇思幻想、骚学的斑灿文采,使得作为精神文化的楚文化光芒熠熠。这在语言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作品《离骚》基本上是四句一章,字数不等,亦多偶句,形成了错落中见整齐,整齐中又富于变化的特点;同时大量地吸收了楚地方言,虚字也运用十分灵活,又常以状词冠于句首,造句颇有特点。再以作品《招魂》为例,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每隔一句用一个“些”字做语尾。而用“些”字又是楚国巫觋禁咒语的旧习。这正是诗人把民间流行的习惯语言引入到自己的创作中的最好例证。我们可以总结出在语言上屈原的作品是不同于《诗经》的四言,而变为以六言(不记语气词“乎”)为主的杂言。而“些”、“乎”的运用更应证了黄伯思“书楚语,作楚声,征楚地,名楚物”的观点。
可以说,孕育于楚地自然地理环境的楚地方言,经屈原的铸炼形成了或优美如《九歌》,或雄浑如《离骚》,或瑰丽如《天问》,或神奇如《招魂》,或隽秀如《九章》的丰富多样的文学典范。屈原通过各种形式、风格的语言,或吟,或咏,或歌,或诵,抒写着自己各种不同的思想情绪。从而形成了屈原“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的语言风格。
总之,正如沈从文所说:“湘西的神秘,和民族的特殊性大有关系。历史上‘楚’人的幻想情绪,必然孕育在这种环境中,方能滋长成为动人的诗歌,想保持它,同样需要这种环境。”[7]而屈骚就是楚地的自然地理环境、自然风情陶冶下的产物,它最终成为楚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为楚地浪漫感伤的文学风格的形成定下了基调。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94-97.
[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59.
[3]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24-30.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四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387.
[5]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417.
[6]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思想史[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3.
[7]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一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