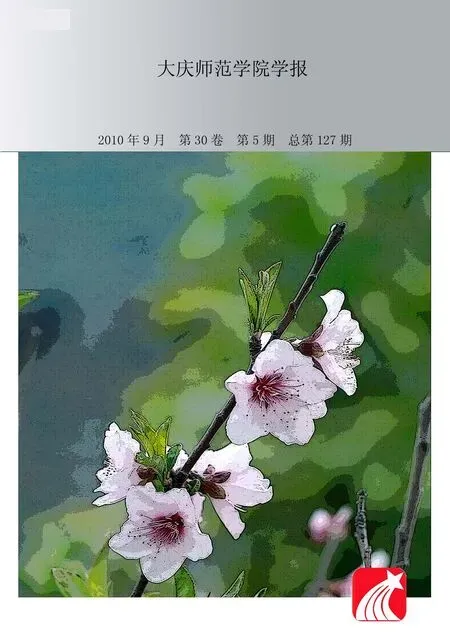《桃花源记》的桃花流水原型
2010-04-06邓福舜
邓福舜
(大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712)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生动地描写了桃花溪水形象。桃木意象和溪水意象的描写受到了魏晋传奇的影响,而魏晋传奇常表现为灵异变化的故事,故使其桃花溪水意象赋予了一种原型意义。陶渊明对这种原型意象的使用,使《桃花源记》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一种原型意义。
一桃木形象最初进入人类的文化视野乃始于上古的辟邪巫术。王充于《论衡·订鬼》卷中引《山海经》佚文云:
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约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主领阅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茶,都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
《战国策·齐策》载苏代说孟尝君云:
今臣来,过于淄上,有土偶人与桃梗相与语。……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地,土则复西岸而。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
先秦之神话还有以桃木震邪刿之举,此风亦延至民间,成为风俗。以桃木刻削人形,以驱凶魅,言桃木有辟邪驱凶魅之功能。
为何桃木具有驱邪避鬼之功能?《太平御览》引《典术》云:“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压伏邪气者也。桃木之精生在鬼门,制百鬼,故今作桃人梗着门以压邪,此仙术也。”作为五木之精的桃木,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驱邪的功能大概来源于此。《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夸父逐日的神话,言:“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邓林即桃林。桃木乃夸父这一逐日英雄所化,故桃木亦感染了夸父的无穷力量获得了旺盛之生命力。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云:“桃性早花,易植而子繁,故字从木、兆。十亿曰兆,言其多也。”从生殖崇拜的角度说明桃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量和旺盛的生殖力量。在中国文化的漫长发展演变过程中,桃木已经由一个具体的自然事象变成了蕴涵丰厚文化内容的原型意象。
魏晋时期,桃木崇拜在整个社会有深广的影响,其蕴涵的文化意义延续了前代的传统。
曹操《致太尉杨文先书》:“谨赐足下锦裘一领,八角桃杖一枝。”宗懔《荆楚岁时记》:“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晋书·礼志》:“岁旦,常设苇索、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之门以禳恶气。”
这种桃木崇拜观念不仅波及了政治生活、宗教文化、社会生活,也影响到文学创作。
《桃花源记》开篇写:“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面对桃木渔人甚异之,写出了渔人的感受,也写出了桃木的神异性。
从桃木的分布结构来说,是“夹岸数百步”,桃树的夹岸而生所呈现的形式结构就具有一种象征意义。至迟在魏晋际已有桃符。桃符乃分列于门之两侧,以避鬼魅邪刿不入门径。进入桃花源世界的门径是“山有小口”。小口即是桃花源世界之门,而渔人所行之溪水则象征进入桃花源世界之途径,分列于溪水两侧之桃木正是桃符的象征。因此,这种桃木分列的形式结构的表现,其深刻的文化意蕴乃在显示一种神秘的护佑与辟邪功能。应该说,诗人陶渊明在无意中使用了桃木崇拜的典型结构模式,而这种结构模式所蕴含的原型意义,又恰好能够引发人们对和平、安宁、幸福生活的联想。桃木分列的形式结构,还具有开合自如抵御邪刿的功能。武陵人能够得以自由地进入桃花源世界,本意不为寻觅桃花源世界,因为缘溪捕鱼、忘路之远近。不为寻觅,毫无机心,才可以一睹桃花源世界的真容。《桃花源记》结尾写武陵人将桃花源世界的秘密上报太守,而太守派人寻访,“遂迷不复得路”。故事的这种结局正表现了桃林的辟邪功能,“落英缤纷”的桃林真正显示了驱灾避祸的神力。桃源中人因“先世避秦时乱”,至今五百余年,居于桃花源世界,长久地与外界隔绝。只有隔绝,才能分离出一片独立自足的天地和家园,而这一家园又长久地存在,不受丝毫的干扰和破坏,就在于“山有小口”的这种宗教性灵异性的门户的庇佑,而能起到这神庇佑作用的,主要在于象征平安、幸福、长寿的桃林。
有了桃林的庇佑,就有了桃花源世界的长久存在。桃花源世界究竟是一个现实的人间世界,还是一个超现实的神仙世界,古来意见不一。实际上,陶渊明是以亦隐亦仙的世界来模塑他的理想社会。作为一个灵异传说、桃花源世界也更类于一个神仙的世界。桃花源中人何以成仙,桃花源世界何以能得以长久存在,从原型意义来说,桃木的延年益寿的功能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桃木具有益寿功能,在上古就被誉为“不死之树”。《山海经·东荒经》云:“东方有树,高五十丈,叶长八尺,名曰桃,其子径三尺三寸,和桃羹食之,令人益寿。”《汉武帝内传》云西王母“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须臾,以玉盘盛仙桃七颗。大如鸭卵、形圆,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颗与帝,三颗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辄收其核,王母问帝,帝曰:‘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中夏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桃木具有灵异的功能,是道家修炼食谱之中物。食之可以延年益寿。《抱朴子·仙药》说:“(桃)久服之身轻有光明,在晦之地如月初。”《神农经》甚至言:“玉桃服之长生不死,若不得早服,临死服之,其尸毕天地不朽。”
桃木具有长寿功能,食之可以成仙,这在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西游记》中多写王母设蟠桃宴会以宴众仙。土地神向孙悟空介绍蟠桃:
有三千六百株:前面一千二百株,花微果小,三千年一熟,人吃了成仙了道,体健身轻;中间一千二百株,层花甘实,六千年一熟,人吃了霞举飞仙,长生不死;后面一千二百株,紫纹缃核,九千年一熟,人吃了与天地齐寿,日月同庚。[1]
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中,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写桃花,而且将这一理想社会称之为桃花源,似乎不是偶然的。不论陶渊明是否有意以桃花作为一种长寿的象征来写,作为一种文学意象,一旦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原型崇拜的创作模式,他的文学意象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这种原型的丰富意义。翻检魏晋人的记载灵异变化题材的笔记小说,一些神话故事常常能够照见《桃花源记》的影子。有些作品竟然与《桃花源记》极为类似。
《搜神记》记载这样一则故事:
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时,好刻木作羊卖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绥山多桃,在峨眉山西南,高无极也。随之者不复返,皆得仙道。故乡里谚云:“得绥山一桃,虽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数处。
葛由成仙得道处多桃木,时人以为,其成仙原因乃在多桃之故。而且随之者普遍可得成仙,没有贵贱贤愚之区别。可以想见,近桃、食桃对于成仙得道、久视长生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
《述异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武陵源在吴中山,无他木,尽生桃李,故称桃李源,上有石洞,中多乳水,世传秦末丧乱,吴中人于此避难,食桃李者皆得仙。
我们不应该怀疑,《述异记》所记故事与《桃花源记》有一种渊源的关系。它与《桃花源记》有五处相类者:(1)是桃李意象的使用和描写。文中记为桃李,而陶记为桃木;(2)是皆有水意象的描写,本记为“中有乳水”,而陶记为溪水;(3)是岩穴意象,陶记写“山有小口”,山口内别有洞天,即为桃花源世界。本记为“上有石洞”,未明言避难者即居于洞中,但石洞意象所传达之灵异意蕴不言自明。最为相类者,山中有居者与桃花源世界有人居住不仅相同,而且其来源与目的都完全相同。皆是来源于秦末战乱,居住之目的都是为了避难。最后,《述异记》与《桃花源记》甚至所用语词都惊人地相似。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一文,是受到了魏晋间记载灵异变化、仙道飞升题材的笔记小说之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时间、人物、背景的表现、叙述和描写,甚至所使用的文学意象也受到了仙道文学中文学意象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决定着陶渊明使用何种意象,甚至还决定了陶渊明在使用这些意象的时候必然会赋予作品一种原型意义。陶渊明是在这种隐含的原型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升华,进而表现他所要表现的桃花源式的社会理想。
二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也写到了流水意象,虽然流水意象在《桃花源记》中没有给予更为充分的重视,但是,流水意象是陶渊明创造桃花源世界的背景环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应该说,在桃花源世界中,不能没有流水,在《桃花源记》中,也不能没有流水意象。
宋苏轼已对《桃花源记》中写水意象引起重视:
旧说南阳有菊水,水甘而芳,民居三十余家,饮其水皆寿,或至百二三岁,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见五世孙者,道极险远,生不识盐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龙蛇,饮其水故寿,近岁道稍通,渐能致五味,而寿益衰,桃源盖此比也欤!使武陵太守得此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尝意天壤之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余在颍州,梦至一官府,人物与俗间无异,而山川清远,有足乐者,顾视堂上,榜曰仇池,觉而念之,仇池武都氐故地,杨难当所保,余何为居之,明日以问客,客有赵令町德麟者曰,公何为问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盖云,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神鱼人不见,福地语真传,近接西南境,长怀十九泉,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他日,工部侍郎王钦臣仲至,谓余曰,吾尝奉使过仇池,有九十九泉,万山环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2]
《桃花源记》中溪水的描写在构成整个桃花源世界过程中具备何种作用、何种功能,这不仅是一个文学的问题,更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在中国文化长河中,水与中国文化的复杂因素相融合,已经构成了非常丰富而复杂的文化意蕴。应该说,《桃花源记》中的溪水同样具有一种原型意义。
在《桃花源记》一文中,之所以称桃源世界为桃花源,说明所叙述故事与水有关。“源”乃水之初起之处也。桃花源世界本有象征意义。其象征的意义就是发源于桃木意象和水意象。
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水被赋予了丰富的原型意义,水是生命的源头,《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巫咸北的女子国妇人入黄池浴,出即怀妊。《史记·殷本记》载:“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梁书·东夷传》:“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长发委地。至二三月,竟入水则妊娠,六七月则产子。”中国古代的女性生殖崇拜常与水有关,女性生殖是生命诞生起始的过程,这一过程都应该有水在发生作用,表现了水为生命源头的文化意蕴。
两汉魏晋之际的志怪类笔记小说,表现洞穴神仙、灵异变化类的笔记小说也常常与水有关。
《搜神后记》载:
会稽剡县民袁相、根硕二人猎,经深山重岭甚多,见一群山羊六七头,逐之,经一石桥,甚狭而峻,羊去,根等亦随渡,向绝崖。崖正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水流下,广狭如匹布,剡人谓之瀑布。羊径有山穴如门,豁然而过。既入,内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著青衣,一名莹珠,一名洁玉……
《搜神后记》:
南阳刘驎之,字子骥,好游山水。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闭一开。水深广不得渡。欲还失道,遇伐薪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囷中皆仙方灵药及诸杂物。驎之欲更寻索,不复知处矣。
又云:
长沙醴陵县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樵,见岸下土穴中水逐流出,有新斫木片逐流下,深山中有人迹,异之。乃相谓曰:一人便以笠自障,入穴。穴才容人。行数十步,便开明朗然,不异世间。
在这些记载灵异变化题材的故事之中,都有水的存在,也都有洞穴的存在,在流水与洞穴的尽头,将发生一种灵异故事。水环绕或者展延于洞穴之外,洞内皆有与世俗迥异的洞天世界。水是生命之源,水具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量。这是这些灵异故事中运用水意象的关键所在。“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万物之本源也,清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3]《管子·水地篇》将《桃花源记》与这些灵异变化题材的故事进行比较,无论在叙述模式还是故事情节方面都有相当大的一致性。灵异传说故事中的水具有神话的象征意义。无可否认,《桃花源记》的水同样也是有原型象征意义。
这种原型意义首先表现在水是生命源泉的意义。水是万物之源,桃花源之所以能够存在,正因为有溪水的存在。没有溪水,就没有桃花源。这是水的原型意义给予我们这样的一种启示,溪水两侧之所以能够“落英缤纷,芳草鲜美”,就是因为有水的滋润,无论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和生物学的角度,都会启发我们做如此的理解。从桃花源的结构形式来说,水是一种导引,直通“山有小口”的桃花源世界之门。因此,溪水就是水路,不由溪水,无以探索桃花源世界。其象征意义在于,没有溪水,也就没有桃花源世界。《桃花源记》的描写,正是印证了《桃花源记》所蕴涵的这种原型意义。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
正是这条溪水,灌溉了溪水两侧的桃花,水的滋润,使桃花源世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其象征意义正是借水的原型意义隐喻了桃花源世界的充沛活力。同时,不由水源,无以达到桃花源世界,其意在隐喻溪水乃是桃花源世界的发源之动力。没有溪水的存在,就不会有桃花源世界的存在。
正因为水是生命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发动者,因此,水对于桃花源世界又是保护者。水使桃花源世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具有生机活力的事物又是具有自我保护性功能的事物。因此,毫无疑问,水对于桃花源世界来说,也隐喻为一种庇佑的力量。上引《搜神后记》原相、 根硕故事以及南阳刘驎之故事中的水的描写都具有一种庇佑功能。其中刘驎之故事写“水深不得渡,欲还失道。遇伐薪人间径,仅得还家”,后“欲更寻索,不复知处矣”。无疑是以流水意象来隐喻这种神异世界的庇佑功能。《桃花源记》如是说: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末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渔人从水道入,又从水道出,于水道处“志之”,但是,寻访桃花源时,都“遂迷,不复得路”。以水道志之,后却失道。深层的文化意蕴正是隐喻水所蕴涵的一种庇佑功能,正是有水的这种庇佑功能,才使桃花源世界能够遗世独立,成为福地洞天,不致遭受世人的骚扰。
《桃花源记》一文的创作,是在魏晋记载灵异变化传说故事大力发展的文学背景中产生的。陶渊明所创作《桃花源记》,无疑受到了这些灵异变化故事的影响。应该说,《桃花源记》是借鉴了民间灵异变化传说故事经过文人化的改制加工创作出来的,它本身就具有神话传说的特点。因此,桃花流水意象不是一般的文学模写性意象,而是具有深厚的文化原型意义的文学意象,这种原型意象的使用,使《桃花源记》具有更为深隐隽永的艺术韵味。
[参考文献]
[1]黄周星.西游记:定本西游证道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3.
[2]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等.陶渊明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管子[M]// 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