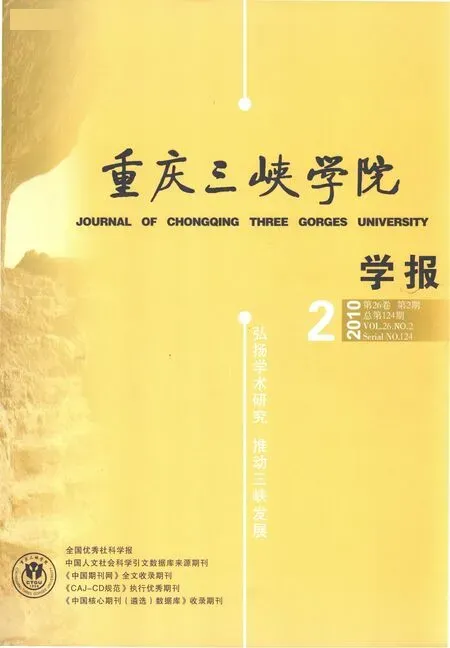菲利普·罗斯《幽灵作家》的元小说特征解读
2010-04-04雷术海
雷术海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国际贸易与外国语分院,浙江湖州 313000)
菲利普·罗斯《幽灵作家》的元小说特征解读
雷术海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国际贸易与外国语分院,浙江湖州 313000)
《幽灵作家》是美国当代文学大师菲利普·罗斯的一部重要作品,通过分析其元小说特征,指出叙述者利用想象实现视角越界,进行叙述操纵是为自己塑造一个陷入艺术和生活矛盾张力中的影子,表达了对小说和现实关系的思考。
菲利普·罗斯;幽灵作家;元小说;特征
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无疑是美国当代最为瞩目的一位作家。自1959年出版中短篇小说《再见,哥伦布》以来,他已出版了23本小说和6本非小说,在美国文坛驰骋了50多年,并且现今的他依然以每年一本书的速度勤奋地创作,其最新作品的出版日期已经排到了2011年。他是唯一一个活着时其全部作品就被收入“美国文库”的作家,无愧于美国当代文学大师和“文坛活着的神话(Living Literary Legend)”之美誉。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备受关注和热议,美国文学批评家欧文·豪曾说:“许多作家需要终其一生刻意追求的那些东西——独特的声音、稳妥的节奏、鲜明的主题——菲利普·罗斯似乎马上就全部得到了”。[1]罗斯的作品题材丰富,寓意深刻,常常涉及当代美国社会特别是犹太移民中最敏感最尖锐的问题,如同化、异化、民族身份的认同等。罗斯在小说叙述技巧上的大胆试验表现在他对作品中人物、事件的回旋和对他本人经历的巧妙虚构上,从而体现出某些“元小说”特征。1979年,“内森·祖克曼”首次出现在罗斯的《幽灵作家》一书中,此后近30年,这个角色果真就如幽灵一般,在罗斯的众多作品中挥之不去,美国文学界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他”是罗斯自身在作品中的影子的推测。本文通过分析其代表作品《幽灵作家》的元小说叙事特征,挖掘小说反映的关于艺术和现实的哲理思考。
一、元小说特征
元小说又称“自我意识”小说,通过小说创作的实践探讨小说创作理论、小说与现实的关系,有意识、有系统地注重其作为人工制品的身份。最早把“元小说”作为文学术语进行讨论的是美国小说家兼批评家威廉·H·伽斯,1970年他在《小说与生活中的形象》(Fiction and the Figures of Life)中提出了“元小说”概念,并指出它是“小说的小说”。[2](15-18)元小说就是对小说创作与叙述形式的反思探究与自我关照。英国学者马克·柯里在其著作《后现代叙事理论》中将这种写作手法称为“理论小说”或“叙事学的叙事”。不同于传统小说用单纯语言构建文本世界,元小说喜欢虚构文本,强调形式创新,其行文方式如天马行空。可以说,文本在元小说那里已经成了一场语言的狂欢与虚构的游戏。
英国著名批评家帕特里夏·沃(Patricia Waugh)明确指出了元小说的特征与本质,他说:“元小说是一个专有名词,指一种为了凸显关于小说与现实之间关系的问题而自觉地、有系统地把注意力放在小说自身作为人造物品(artifacts)的身份上的小说写作……这种小说不仅分析研究叙述小说的基本结构,而且探究文艺小说文本的外部世界可能存在的虚构性”。[3]美国学者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中认为:“元小说(metafiction)以另一种方式悬置正常意义……当作者在一篇叙事之内谈论这篇叙事时,他(她)就好像是已经将它放入引号之中,从而跃出了这篇叙事的边界。于是这位作者立刻就成了一位理论家,正常情况下处于叙事之外的一切在它之内复制出来……‘小说’是一种假装。但是,如果它的作者们坚持让人注意这种假装,他们就不再假装了。这样他们就将他们的话语上升到我们自己的(严肃的,真实的)话语层次上来”。[4](228-229)这表明,“‘元小说’的作者特意设置了小说的叙述框架……故事是小说叙述框架之内的一个层次,由叙述者和其他人物构成,在小说叙述框架之外和作者之间则存在另一个层次,即超故事层。在超故事层里,作家的理念和有意识的操作在起作用”。[5](157)作家操纵叙述者在故事层内叙述的进程中论及虚构本身,以直接或含蓄的方式提醒读者小说真假共存的叙述结构和亦真亦幻的小说世界。元小说特征有二:一是将小说创作策略的探寻寓于文本之中,二是强调文本的虚构性。
为了营造虚构的文本,元小说家们喜欢玩弄语言游戏,正如马克·柯里所说,元小说是“一种由新一类的文学教师、作家和批评家写出的东西”。[6](55-56)“他们清楚怎样讲故事,但他们的叙事却在自我意识、自觉和反讽的自我疏离等不同层面上返回叙事行为本身”。[6](70)元小说以其内容的鲜明自我意识与形式的不确定性,构筑了文本的虚构特征。
二、《幽灵作家》的元小说特征解读
(一)鲜明的自我创作意识
《幽灵作家》讲述了叙述者“我”(年轻作家内森·祖克曼)到伯克郡去拜访一位著名的犹太老作家并在那里邂逅了年轻女作家爱美·贝丽特。这是一个关于作家讲述他们自己创作经历的故事。《幽灵作家》最能呈现其元小说创作特征的是,“我”在书房中构思了一个故事,让爱美在“我”的操纵之下把她自己想象成尚存人世、隐姓埋名的著名的《后楼》日记作者——安妮·弗兰克,同时“我”有意放弃小说反映现实生活的努力,不时暴露故事的虚构性,诸如:“我”告诉读者,《后楼》日记的第一段“记的日期是在爱美诞生前一年多”,[7](119)“这就是她的故事……她说的都是真心话,但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7](132)“我不断被拉回到我躺在黑暗的书房里在她和洛洛夫夫妇身上构思出来的小说中去”,[7](137)等等。另外,罗斯和叙述者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在纽瓦克犹太社区度过童年时光,作为文坛新秀又都面临着艺术创作和生活真实的矛盾,由于信仰偏差与父辈的关系危机重重……这类作品在叙事人称上多以第一人称“我”为主,它采用元小说的表达模式,既照应了后者以小说的实践反思小说艺术的审美取向,又吻合了元小说创作和批评并举的特点。因为叙述人“我”可以灵活多变地游走于多重身份之间,既是故事里的人物,又充当作家的代言人,有时候甚至就是作家本人,传递关于其作品的某些信息,直接对叙述本身发言,对叙事进行思考和质疑,小说因此得以不断反思和调整自身,仿佛具有了一种能动的“自我意识”。
(二)强调小说的虚构性
小说的故事层主要围绕着“我”面临的问题和问题的解决展开,并通过“我”与作家之间的接近关系(自传体优势)充当作家的代言人,在超故事层里不时巧妙地提醒读者小说的虚构性。事件发生在1956年,“我”由于创作了一部被认为污蔑了犹太人形象和声誉的小说而遭到来自家庭内外众多的指责和疏远,虽然“我”为自己辩解,否定艺术的现实模仿性,但得不到众人的理解。是屈从纽瓦克敌视创作和想象的压力,选择作父母的孝子还是坚持自己的艺术原则,带着这样的困惑,“我”来到洛洛夫的家寻求支持,受到他和夫人霍普的热情接待并在那里邂逅了年轻姑娘爱美。洛洛夫对年轻一代毫不避讳他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例如注意力的不集中、想象力的匮乏、生活上的话题,洛洛夫坦言:“我写了三十年的幻想小说,却什么也没有遇到”,[7](15)而他写作的方式居然是颠倒句子“我写了一个句子,把它颠过来,看了一下,又把它倒过去,接着吃午饭,吃过午饭又回来写另一个句子,接着喝茶,把新句子颠过来,接着把这两个句子再看一遍,又把它们都倒过去……”,[7](16)甚至哈佛大学还要保留他改了二十七稿的原稿,他的沮丧和自嘲恰恰暴露了小说创作的人为性和虚构性,小说只是言语的结构体和语言文字的游戏,“我”似乎就此找到了自我辩解的依据,激发了对他“女儿式的喜爱,这个人了解生活,了解儿子,而且表示称许”。[7](51)和他一起生活了三十年的霍普抱怨他“不要生活,他就是从不要生活中产生他的动人的小说的”。[7](152)进一步揭示了小说和生活的脱节,艺术不是现实而是现实的代用品。
“我”并不满足于从洛洛夫身上获得的关于小说故事身份的信仰,“我”还要利用自己的特权来构思一个故事,用这个故事来说明小说的虚构性。在第二部分“内森·迪达勒斯”,“我”从祖克曼摇身变成了“迪达勒斯”,“迪达勒斯”原是希腊神话中建造迷宫的建筑师和雕塑家,意即“能工巧匠”,“我”即将要向“你”揭示“我”的小说的“编写”手法,告诉“你”“我”的素材或灵感来自何处,我是如何一步步形成自己的思路、操作写作、虚构出关于爱美的传奇故事的。接着“我”开始煞有介事地向“你”表明这个过程。首先,爱美娇小的身躯和大脑袋发育得不成比例,行为举止的成熟和衣着打扮的孩子气,使“我”感到神秘莫测,对她的身份感到好奇,接着洛洛夫向“我”介绍她是他的学生,文学爱好者,称赞她杰出的散文文体,霍普证实了十一年前,爱美作为欧洲难民曾得到洛洛夫的帮助,来到美国学习并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这“使我想起了我们幼时住在新泽西州时吃饭时常常听到的‘欧洲挨饿的儿童’。如果爱美是其中之一,那么我在她身上看到的发育不全的现象就不言自明了,尽管她的成熟是很显眼的,她的美貌有些严厉。我心里在想,这个有个怪性格的黑发姑娘很可能是犹太人,在欧洲所遭到的苦难要比挨饿苦得多”。[7](49)这就为爱美预设了一个二战遭迫害的犹太难民身份。当晚,“我”在书房留宿时发现了一张写了“柔情、勇气、爱和蔑视”出自肖邦乐曲的卡片,于是“我”推测这是会弹钢琴的爱美写给洛洛夫的,“我”对这似乎暗含着与老夫妇有某种微妙关系的字条不免进行了推理,层层铺垫出爱美和安妮在年龄、背景、写作才华和与父亲的亲密关系等方面的相似,给了“我”创作的灵感,使“我”决定让爱美在“我”的操纵下,把她自己当成从集中营的死灰中“复活”却隐姓埋名的安妮,而“我”则隐入幕后,从容地观察着一个幻想着自己是安妮的名叫爱美的人的故事。
(三)转换叙述视角
由于想象的介入,叙述者在这个构思的故事里变换了叙述视角,由第一人称限制视角索性全部转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这种视角越界可以使叙述者更方便地探视人物的内心世界,像局外人那样叙事并对叙事进行思考和质疑,满足他的要求。为了突出真实性,叙述者假意追求细节,煞有介事地将故事编造得像真的一样,他会突然就故事的可靠性作一番辩解。例如,当爱美只向洛洛夫宣布她是安妮时,“我”写到:“接着是她的故事中洛洛夫肯定会认为不大可能的部分,但她本人则认为没有什么可奇怪的”,[7](113)对于爱美没有在战后按照一家人的约定去瑞士寻父,叙述者辩解道“这也并不是那么说不通。一个身体虚弱的姑娘,没有钱,没有签证……会去作这样的长途跋涉吗?”[7](114)就在读者快要落入叙事圈套时,“我”又突然主动暴露故事的虚构性,例如前文提到的爱美和安妮实际年龄的不相符,《后楼》日记的第一段“记的日期是在爱美诞生前一年多”,以及“我”公开承认“都是虚构”。[7](149)最后,故事临近结局时,爱美明确地告诉“我”,她没有经历过战争。她不是安妮,她没怎么读过《后楼》日记。[7](148)也许,叙述者在爱美的眼中根本就是无足轻重的,小说在追求文学写实的同时又颠覆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在建构幻象的同时又揭露这种幻象并最终让它倒塌,这一切都是为了使读者意识到小说不是现实的摹本,而只是作家编撰的故事。
(四)凸显艺术与生活的矛盾
“我”操纵下的爱美是一个分裂的人,因为“我”让她陷入了不可救药的幻觉之中。全世界都以为安妮已经被纳粹杀害了,其实她还活着,改名为爱美,从欧洲来到美国,作为洛洛夫的寄女,在他家中长大独立,直到有一天,她偶尔得知父亲奥托还健在并出版了她躲藏在阁楼时写的《后楼》日记,可是她却没有与父亲相认。表层原因似乎是,她发现自己已经成为犹太民族的圣徒,阁楼成了千万人参观的圣地,人们如潮水般涌向剧场看《后楼》的演出,因此她担心作品巨大的力量可能会因为写作者尚在人间而受到削弱,她想:“要是大家知道《后楼》是一个活着的作家写的作品,它就永远不会有更大的意义,只不过是……孩子们晚上临睡前可以同《瑞士家庭鲁宾逊》一起阅读的东西”。[7](127)看来她只有选择继续“死亡”,悖论式地通过失去身份完成身份的确认。然而,“我”操纵下的爱美梳理出的是一个文学价值超越政治意义的《后楼》,一个具有强烈恋父情结的女孩在孩童时代就制定的成为伟大作家的伟大计划和她已在日记里表达出的非凡的写作才华。她在书上做了记号,“……她做记号的大部分地方,都是那些她不能相信自己还是个小孩子时候居然能写出的章节。乖乖,多么流畅,……”。[7](119)这完全是“我”的理念在起作用,因为恰恰是“我”自己“……更多关注的是《后楼》日记如何记载了一个年轻作家的迅速成长过程,而不是书中所揭露的战争的恐怖”。[9](32)“她是个了不起的年轻作家。她才十三岁,真不容易。这就像看一部加速的影片,一个胎儿迸出了一张脸,看着她长大懂事。你一定要读。突然她发现了思索,突然有了性格刻画,人物速写,突然有一件错综复杂的曲折事件,叙述得那么动人,好像改了十几稿一样”。[7](147)显然,安妮杰出的文学才华正是爱美所渴望的,引起了她的共鸣,同时,安妮曾经失败地向父亲宣布独立,这无疑也引起了爱美强烈的认同,她正处于对父亲/洛洛夫一往情深而不能实现的挫败中。这样,爱美同样面临着在艺术和生活中做出选择的困境:如果选择做安妮,继续“死亡”,她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可是她只能永远做父亲的小女孩,任何要宣布独立的企图都要流产;如果选择做现实的爱美,她认为自己完全有权利成为父亲/洛洛夫年轻的妻子,但她当最出名的作家的梦想便宣告结束了。
前文已经指出,这里的“叙述者出面”就是“作家出面”,因此我们在超故事层里需要考虑的是叙述者通过他所叙述的故事所要传达的意思:其一,洛洛夫“颠倒句子”式的写作实践和“我”在书房构思故事的叙述策略清楚地表明,通过元小说的操作模式,“我”颠覆了艺术追求历史真实以反映现实的创作主张。正如拉康所言,现实之物是不能用语言/符号代表的,所以任何描绘无法再现历史和社会的现实。《幽灵作家》通过小说实践揭示了小说的虚构肌质和故事身份。我们稍加留意便会发现贯穿小说始终的对照片、电影、替身、扮演、化装、面具、幻觉、人工制造、妄想等的刻意强调以及有意识运用“仿佛”、“似乎”、“好像”等猜测性词语,渲染出了一个虚幻的对象世界和夸大的假面舞会。其二,“我”所构思的关于陷入艺术和生活矛盾张力中的爱美的故事实际也是“我”自己以及那些不得不在两者中择一而取的作家们的故事,爱美是“我”的影子,她在美国自立奋斗的经历,对艺术的追求,对洛洛夫情感上的依恋,要艺术还是要生活的焦虑引起了“我”的认同并引发了“我”对两者不等同关系的思考,小说结局处,洛洛夫为“我”的伯克郡之行郑重其事地“主持了坚信礼”,[7](157)也完成了“我”对所受不公正职责的应答。
[1]欧文·豪.父辈的世界[M].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2]格非.小说叙事学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3]帕特里夏·沃.元小说:自觉意识小说的理论与实践[M].刘雁滨译.台湾:骆驼出版社,1995.
[4]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5]刘俐俐.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M].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7]菲利普·罗斯.幽灵作家[M].董乐山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8]Hendley, W. Clark. An Old Form Revitalized:Philip Roth’s Ghost Writer and the Bildungsroman[J].In Studies in the Novel. 1984(Vol.16),98.
[9]Furman, Andrew. What Drives Philip Roth?[A].In Contemporary Jewish American Writers and the Multicultural DilemmaL: the ruturn of the exiled[C].Ed. Andrew Furman.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0.
On the Metafiction Characteristics ofGhost Writerby Philip Roth
LEI Shu-ha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Foreign Language, Huzhou Vocational & Technological College,Huzhou, Zhejiang 313000, China)
Ghost Writeris one of very important works of American contemporary literary master Philip Roth.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ts metafic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narrator realizes the cross-border of narrative angles by using imagination, and that narrative manipulation is to form a shadow trapped in art and life contradictive tension for the narrator himself. It deals with the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ction and reality.
Philip Roth;Ghost Writer; metafiction; features
I106.4
A
1009-8135(2010)02-0096-04
2009-12-14
雷术海(1975-),男,河南商城人,浙江省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国际贸易与外国语分院讲师。
(责任编辑:郑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