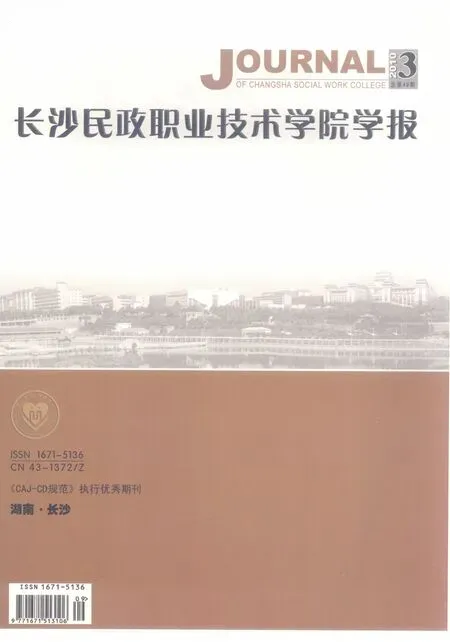山寨文化中“模仿”的特点
2010-04-04陈金美廖海兵
陈金美 廖海兵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山寨文化中“模仿”的特点
陈金美 廖海兵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山寨文化中的模仿具有平民性、媚俗性、相似性、创造性、游戏化的特点。模仿者皆为平民身份;对原型符号价值的追求使得模仿具有媚俗性;原型与摹本的外形、构造和功能等极为相似,但也存在差别;在模仿的形式上,摹本增加新元素,超越了原型;从创造者的心态看,模仿具有游戏化的特性。
山寨文化;模仿;特点
2008年岁末,“山寨”一词狂飙突起。它已经从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衍生为社会文化现象。而“模仿作为山寨文化的基本内核”[1]已成为共识。模仿作为一种行为以及行动的本能,其历史几乎和人类一样久远。而随着时代和技术的发展,山寨文化中的“模仿”出现了平民性、媚俗性、形似性、创造性和游戏化的特点。
一、平民性
平民性主要体现在模仿主体的身份上。在“山寨”盛行的当今,有多少山寨文化产品,就有多少个模仿者。尽管模仿者无数,但他们在多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1)个人收入相对不高;(2)没有显赫的家世和社会背景;(3)遭遇过生存困境和话语霸权;(4)渴望诉求利益和表现自我。根据这些描述,山寨文化创造者的身份轮廓进一步清晰起来。他们大多绝非达官豪商、专家学者、明星贵人,也并非出自名门望族。根据200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山寨文化创造者更多来自产业工人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或者说,他们处在占据我国总人口多数的社会基层,如生产山寨手机的中小厂主、发起山寨春晚的四川北漂——老孟、制作山寨《百家讲坛》的自由职业者——韩江雪、拍摄山寨《红楼梦》的在读大四学生——陈维实、模仿周杰伦的福建小艺人——周财锋、手拿山寨火炬进行传递的山村农民等。他们有着不同的遭遇:或者饱尝生存之苦,或者缺乏文化关怀,或者倍受各种歧视。但他们都用一种独特的方式 (模仿)把自己的构想和理念付诸于现实,从底层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反叛之声。他们是基层群体的急先锋,紧扯着低成本模仿的福祉,积极投身于文化产品的生产中。这样,笼罩于文化头上的神秘乌云不断散去,精英与民众的距离被骤然拉近,文化创造不再是某些人的“专利”。草根民众在高雅艺术和通俗文化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只要愿意,平民也可成为“导演 ”、“制片人 ”、“摄影师 ”、“主演 ”、“主讲者 ”、“设计师”、“明星”等角色。然而,在古代社会里,由于经济、教育及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艺术创作更多为贵族阶级所垄断。到了近代,模仿生活和教化世人成了知识分子的专利,民众被迫游离在文化的边缘,得势的文艺精英们更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设置距离,把自己塑造成完美的“救世主”。进入到当代,这种现象并无多大改观,精英文化仍为少数文化精英所把持,而貌似大众自己的大众文化也好不到哪里去。“大众文化的从业者既是文化人,更是唯利是图的商人”[2](p27)。机械复制只能是文化媒介人和资本家生产文化产品和利润的工具。
二、媚俗性
媚俗性集中体现在山寨文化创造者 (以下称创造者)所模仿的对象上,从实物到人物,再到精神产品,模仿的内容非常广泛,如NOK IA手机、康师傅方便面、雕牌洗衣粉、999皮炎平、百度、谷歌及雅虎网络搜索引擎、北京奥运会火炬、“神七”登月舱、鸟巢、刘翔、周华健,还有电影《幸福像花儿一样》、央视春晚、央视《百家讲坛》、电视剧《红楼梦》等等,无不成了创造者模仿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对照山寨产品,我们便会发现山寨文化产品的原型 (模仿对象)有一个突出特点:它们都是早已为大众熟知或当下流行的“经典”。正如中山大学李宗桂教授所言,“山寨文化的很多产品,都是对先进产品的模仿”[3],“先进产品”是创造者眼中所谓的“经典”,更是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所提出的“媚俗物”。在消费社会里,消费者与物品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费者“不再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4](p3)。这使得消费物品因其符号功能而逐渐弱化、丧失了实用功能,一切消费品成了一堆摆设,成为一个个的“媚俗物”。媚俗物的流行能为人们提供空幻的期许和自欺欺人的精神慰藉。它那强大的符号功能让消费者对此趋之若鹜,顶礼膜拜。上列的品牌物品摆放于此,它吸引消费者的不仅是其客观实用性,更是其昂贵的品牌、著名的商标以及它们所共同暗示的时尚、尊贵、富有和高人一等。由于品牌一旦确立就难以超越,再加上低端消费者无力购买价格较高的名牌产品,创造者只得通过对现成的媚俗物进行改造,重新生产出意义和快感。这样,既满足了他们的实用需求,更给予了自己极大的精神安慰。创造者对这些品牌或经典的模仿实际上是对它们所代表的文化符号的追求,其行为本身就带有一种媚俗性。仅凭这点,山寨文化中的模仿在源远流长的模仿史上是独树一帜的。模仿对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被加以修正和更新。以前,原型或者是与自然相应的主体的内心结构;或者是神秘原始的自然;或者是至高无上的上帝;或者是万物基始的理式。它们作为形上之物,看不见摸不着,受世人模仿和景仰,具有无比的崇高性和神秘性。而现今的山寨文化创造者极力模仿形下之物,舍本求末,其媚俗性不言而喻。
三、形似性
形似性主要体现在原型与摹本关系的处理上,山寨文化从外形、结构、功能和商标、风格等方面模仿品牌、明星和经典。首先,从外形、构造、功能看,山寨商品和品牌商品极为相像,但创造者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在它们之间保留着极其微小的差异。比如,一些山寨手机外观与品牌机酷似,功能接近甚至超越了品牌机,但其价格、质量 (手机自身和售后服务)的差别就能让消费者识别它们各自的身份。再如“NOKLA”与“NOK IA”、“康帅傅 ”与“康师傅 ”、“营养干线 ”与“营养快线”、“慢严舒柠”与“慢严舒宁”之间在标贴上差之毫厘,可质量也许就失之千里。其次,虽然山寨明星在原型的发型、体形、招牌动作和神态上极尽模仿之能事,但他们的学识修养、歌唱水平和商业价值与原型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差距。譬如,山寨周杰伦的长相尽管与周杰伦很像,但他们做广告的价格真是天壤之别了。再说,作为山寨文化代表之一的山寨《百家讲坛》,它模仿央视《百家讲坛》的风格,主讲人口述、话外音、插图和背景,五脏俱全,可二者的制作成本及质量相去甚远。由上可知,在创造者对原型的模仿过程中,他们使得摹本与原型在形式上建立了一种再现与被再现的关系。山寨文化中的模仿就在像与不像、是与不是、叛逆与顺从之间游离,获得了一种形似的特征,即山寨文化在商标、外形、功能、动作和风格上无限地接近或靠近原型,同时又在模仿和照搬中刻意凸显自己独特之处。正如北大学者张颐武所指出,“‘山寨’产品一面制造混淆和相似,一面却也表现差异和区别。……‘山寨’有模仿秀等文化潮流的影子,但它并不期望惟妙惟肖地变成被模仿的对象,而是一种刻意的‘像但不完全是’的姿态和风格”[5]。或者说,山寨文化的模仿追求的不是神似,而是形似。这种形似化处理既是商家善于打法律擦边球的结果,更是草根受众那种豪奢消费欲望与自己经济实力极不相称的矛盾心态的表达。
山寨版文化的模仿力求形似,而历史上其他的模仿呢?传统现实主义的艺术家模仿自然或生活,不求惟妙惟肖地模仿客观世界的外形,而重在模仿一种超越外部世界的精神实质,即神似,给读者以道德教化或精神鼓舞。模仿作为现代主义的一种创作手段,它要求艺术家全面模仿传统作品中特有的风格甚至习性,务必在形式上达到一种“陌生化”的效果。福克纳式的长句、劳伦斯别具特色的自然意象、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风格等就是这方面突出的例子[6](p451)。后现代主义的拼贴是一种对传统风格或习俗的空心 (缺乏嘲弄)模仿,是诸多历史碎片的无序组合,更是一盘“历史大杂烩”[7](p454)。其中除了一堆文本、文字、精神分裂者的语言,一无所有。这无疑将形式的模仿发挥到了极致。
四、创造性
从模仿的形式来看,模仿可分为客观性模仿和创造性模仿两类。前者主要以柏拉图的镜式模仿为代表,后者主要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并得到全面继承和进一步发展。而山寨文化中的“模仿”就属于创造性模仿。这种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山寨文化的生产者往往整合很多不同名优产品的长处,再根据草根消费者的需求,增加新的功能,或者在外形上讲究变化,力求新颖,从而打造出一种新的商品。这一点在山寨机上表现尤为突出。山寨手机的生产厂家针对中国年轻消费者的“特殊需求”,增加了大屏幕、大喇叭、大容量、超长待机、双卡双待、验钞、电棍、游戏机等功能,甚至利用先进的拼装技术,把八个低音炮喇叭、四个摄像头、高倍率望远镜、全球卫星定位系统都拼接到一部手机上。网络上正炒得火热的“桔子手机”除了高仿苹果 iPhone外,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还实现了两个重要超越:一是超长待机时间,二是支持双卡。另一方面,根据个人需求、地域特色、外在背景和现实条件,在材质、风格等方面力求变化,仿造出新产品,实现对模仿对象的超越。比如说,山寨鸟巢的制作者们根据北京鸟巢的外形,分别采用不同的材质如沙石、核桃、竹子,因地制宜,生产出不同版本的鸟巢 (沙盘鸟巢、山核桃鸟巢、竹鸟巢)。大四学生陈维实利用家中的被单、桌子等做道具,根据演员自己对角色的理解,拍出风格迥异的山寨版《红楼梦》。“山寨的模仿里有自己的创造,照搬中有新的元素和想象的延伸”[8]。模仿暗含着创新,创新又隐藏在模仿中,山寨文化的特殊性就是巧妙地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模仿中带着几分草根智慧的创新,既符合模仿自身的规律,更有市场的需求必然。这更为山寨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把模仿当作照镜子,开辟了机械式模仿的先河。到了古罗马时期,艺术家的模仿更趋于逼真,尤其是造型艺术已没有古希腊的那种神性的刻意美化,像奥古斯都、庞贝、尼禄这些大人物的肖像酷似原型,贴近现世的模仿观占据主流。当代的机械复制就是这类模仿得到进一步强化的结果。比起它们,当代山寨文化的模仿在创新上确实前进了一步。然而,根据创新模式理论 (创新可分为跟进创新、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三个阶段)进行判断,山寨文化还只是停留在跟进创新或集成创新的阶段。可以说,山寨文化中的创造性处在一个低级阶段,还有待于日后的完善和发展,最终要向原始创新阶段迈进。
五、游戏化
游戏化的形成与山寨文化创造者当下的心态和心理诉求是密切相关的。“新时期初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乐观、生气勃勃、理想主义的情绪,伴随着生存境遇的危机和个体在转型期间的失落、无奈,形成一种普遍的怀疑精神和非理性主义。‘一场游戏一场梦’、‘潇洒走一回’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游戏’心态”[9]。另外,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工作压力
越来越大,人际交往愈发荒漠化,人们自由支配的时间和自由活动的空间特别是精神沟通的心理时空受到限制,在身心方面都很容易感到疲劳,从而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放松身心和享受娱乐的强烈需求,尤其是在俏皮中长大的年轻草根一代。因此,“游戏”心态定会在人们的行为中刻上烙印,娱乐需求必然构成他们行动的内驱力。山寨文化创造者正是用一种调侃、游戏甚至致敬的心态模仿原作,并在对原作的解构、拼贴、戏谑和嘲讽中,真正体验到自由、解脱和精神胜利的快感。正如席勒所言:“人只有在‘游戏’时 (摆脱自然和理性的强迫)才是自由的”[10](p414)。山寨《红楼梦》中那简单的道具 (被单当华服)以及家人搓麻将的穿帮镜头令网民忍俊不禁,其实这更可看作是对新版《红楼梦》脱离民众欣赏趣味的嘲讽。山寨歌曲《说句心里话》中那汉语式的英文歌词、很不地道的美声唱法以及《阿甘正传》的背景画面无不让人捧腹。山寨诺贝尔奖和山寨熊猫通过对社会事件与诺贝尔奖的嫁接和对松狮狗的“易容”,表达了草根大众渴望获得诺贝尔奖和一睹“国宝”风采的美好情怀,更是人们对当前一些社会现象的一种无奈和失望情绪的发泄。山寨文化中的“模仿”融入夸张、解构、拼贴和嫁接等后现代主义手法,寓严肃于轻松之中,达到嘲讽社会百态和追求快乐的目的,获得一种啼笑皆非的效果。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山寨文化中的模仿也可称作戏仿,这种游戏化特点与人们当下的“游戏”心态和强烈的娱乐诉求是契合的。另外,网媒的推动使得这个特点更会显现出来。
[1][8]刘瑞生.中国刮起“山寨风”:山寨成最流行网络新词[N].人民日报,2009-02-19.
[2]叶志良.大众文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3]李宗桂.何必跟山寨文化过不去?[N].人民日报,2008-12-07.
[4][法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 [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张颐武.“山寨”的活力和限度[J].新西部,2009,(3).
[6][7][美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M].上海:三联书店,1997.
[9]汪方华.通俗电视剧接受中的独特心理机制 [J].现代传播,2005,(1).
[10]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C913.4
A
1671-5136(2010)03-0015-03
2010-04-25
陈金美 (1952-),男,湖南南县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化哲学;廖海兵(1980-),男,湖南衡南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