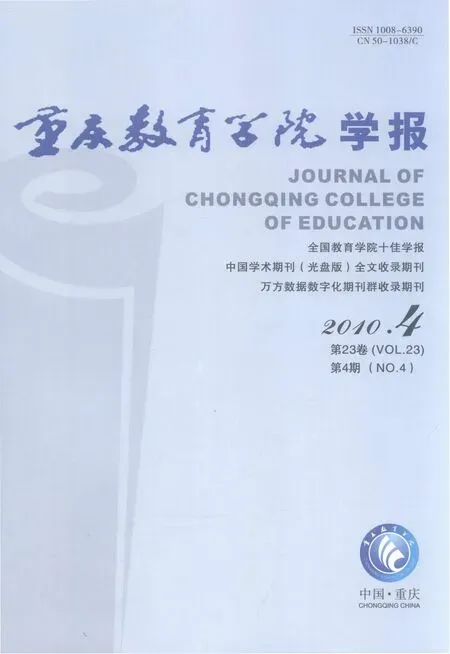我国群育思想之变迁及其对当代高校的启示
2010-04-04韩荭芳
韩荭芳
(西南大学 教育学院,重庆 400715)
一、群育思想的发轫——先秦时期
(一)孔子的群育思想
春秋时代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在其言行著录中便有记载许多关于群育思想的论据。如“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礼之用,和为贵”、“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等等。[1]显而易见,我国的群育思想在二千多年前就有之。孔子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体系是从“泛爱众而亲仁”开始的。孝敬长辈爱人,推己及人,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这是人类最自然高尚的情感。“移之以事君则忠,资之以事长则顺,施之于闺门则夫妇和,行之于朋则朋友信”。将心比心,同样的原则推己及人,这种顾“群”的观念及群性教育的思想本身就是群性教育的重要内容。
(二)孟子的群育思想
孟子承孔子仁礼学说之衣钵,衍生出自己的群育思想,孟子认为,人之所以超出自然,异于禽兽,在于人心中的四个“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2]“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对社会尊老爱幼、诚信和睦、照顾幼小的写照。另外孟子认为,实行了“仁政”,就会出现举世同心、天下太平,这也说明了实行群育的重要性。
(三)荀子的群育思想
战国时期,荀子由自然的法理推出:“古之所谓士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不能生养人者,人不亲也。”[3]在他的著述中明确提出了“合群多力”、“丧群必亡种”,提倡“善群”、“能群”等“群性”观念。在荀子看来,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 “群”,而“群”的关键在于“义”和“分”即道德和秩序,群体表现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征服自然并使人得以生存。
荀子的群育思想有别于孔孟所理解的群体,前两者更多地带有人伦的色彩,荀子明确提出的 “合群”论超越孔孟“敬天”、“畏天”的态度。
二、群育思想的发展——民国时期
1898年,严复翻译了英国H.Spencer的《群学肄言》,用群学来解释政治学、社会学。这是社会学导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群”文化揉合的标志性事件。
(一)群育成为国民政府教育方针
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和实施方针,同年4月由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行。基于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民国政府提出“德、智、体、群、美”的“五育”教育方针,群育成为民国时期各级各类教育的指导方针。1931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许多条款涉及群育,如初等教育要“使儿童个性群性在三民主义教育指导下平均发展”,高等教育之“训育应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养成德、智、体、群、美兼备之人格”。[4]从此,群育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得到深入而广泛的探索,并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提出的群育,从教育的角度,强调要培养共和健全之人格,强调群育是促进健全人格发展的需要,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二)著名教育家对群育思想的推崇
1.蔡元培的群育思想。蔡元培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1912年他从 “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人格”的观点出发,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成为制定民国元年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础。“群性之发展,自人道主义而达于动物之爱护;各性之发展,由居住身体而达于思想之自由,然对于群之义务、对于己之权利有并行不悖之规道焉。”他认为,个体与社会是相连的、不可分离的,个性和群性是人性的两个方面,促进个性与群性发展离不开教育。另一方面,个性的发展与群性的陶冶是相辅相成的,对“群之义务”、“己之权利”都要顾及。换言之,个性与群性,两者不可偏颇,不能相互抵触,而是要均衡发展。[5]
2.潘光旦的群育思想。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1899-1967)是最早提出通才教育的教育家之一。他提出了“德、智、体、群、美、富”的“六育”主张,他认为,“六育”是整体并进、各方面协调发展的,在教育实践中对任何一方面的施教,都不是孤立地、单一地进行的,都相互关联到其他方面。其中,“群”、“富”两方面是在过去的教育中很少提及的。潘光旦就这两方面作了特别解释:所谓“群育”就是培养协作精神及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能力;所谓“富育”就是培养吃饭能力,并在生计上富裕的能力。这六个方面在教育上是一个整体,是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他指出:现代教育误入专业化、技术化歧途,不能将学生培养成为“健全的、完整的人”,为此要全面实施“六育”。可见,潘光旦的“完人教育”思想中包含群育,在他看来,如果不实施群育,教育就不完整。[6]
3.梅贻琦的群育思想。梅贻琦(1889-1962)于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德、智、体、群、美”诸育并举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群育是他“五育观”中有特色的部分,与通才教育相应。为加强群育,他大力扶持各种集体活动和社团活动,他自己也经常参加,借各种机会增进团体生活精神。1935年,梅贻琦在对学生讲话时强调:“平时因课务甚忙,求抽出时间使师生常常聚会,很不容易。大家借此机会晤面亲近,表现出团体生活精神,且集合唱歌听讲,于陶冶性情,增进知识两方面,同时可以得到。”梅贻琦认为“群育”既是指个体要在群体中接受教育,也是指个体要与群体和睦相处;既是指“己”要与群合(合群),也是指“己”在治学和修养方面要有足够的“慎独”功夫。总之,“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7]
(三)民国时期高等学府实施群育的实例
1913年-1918年,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大礼堂入口处的横匾上就写“德、智、群、美”几个大字。可见,“群育”已列为当时学校教育目标之一。1927年11月,南洋大学成立了群育委员会,设立群育处,并改学监股为群育处,聘焦斐瞻为群育主任。南京大学张其昀在《南高的学风》一文中大加称赞“南高”的精神是德育、智育、美育、群育四个方面的完美结合。1928年,张学良兼任东北大学校长时,他认为中国急需“促成国家现代化,而消弭邻邦的野心”的实用人才。培养这种人才不仅要有以爱国思想为核心的德育,以研究高深学术为内容的智育,养成群体精神的群育,爱美、审美、求美、创造美的美育,更需要促进身心发达的体育。因此他主张智、德、体、美、群五育并重。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亦提倡“德、智、体、群”四育。认为民众教育的内容……所以智、德、体三育之外,应当加一个群育。智、德、体、群育须同时平均发展。在我们素来散漫的中国人尤须注重群育。[8]
这些实例,说明我国近代大学教育非常重视群育,旨在促进个人的群性或社会化发展,培养受教育者有益的社会行为与生活态度,使之能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互助合作,适应生活环境,以达到和谐共处。同时也是从三个方面来践行群育,一是从理论方面,阐释群育的思想内涵,倡导五育均衡发展;二是有组织地开展群育活动,设立了群育处等组织机构;三是群育成了高校办学理念之一。
三、群育思想对当代高校人才培养的启示
(一)实施群育的可行性和客观基础
国际教育委员会于1996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报告中提出,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和学会做人,其中的“学会共处”就是指培养在人类活动中的参与、合群和合作精神。当前我国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依然将中国传统的群育思想发扬光大,鲜明提出“德智体群美”目标。例如,台湾教育目标提倡“德智体群美”,其中群育特别强调通过课外集体活动及公益活动进行群育,学习为社会服务的技能,树立为社会服务的思想;香港“五育”目标是:培育青少年的品德、智能、体格、合群和美好生活;新加坡教育目标分为“德、智、体、群、美”五个方面,其群育则包括群众观点、集体主义、互助合作、宽容大度等内容。[9]
近年来为了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在全国推行了“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要在思想政治与道德素养、社会实践与志愿者服务、学术科技与创新创业、文化艺术与身心发展、社团活动与社会工作、技能培训等6个方面引导和帮助大学生完善能力结构。在这六方面中,社会实践与志愿者服务、社团活动与社会工作、技能培训等,便属“群育”范畴,每个人及群体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其他人及其群体的存在和发展,他们互为条件,互动共生,相互依存和发展。追求和谐、自由、公平、互惠、文明的人际关系环境,是人的本性需要,是人的幸福之源,也是人生的重要目的。继承和发展群性和群性教育,有利于促进人的个性和群性协调发展,有利于促进个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当代高校有必要实施群育,健全人格的培养
德国教育家纳托普认为,真正的教育在于使人变为社会的人,有些人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所受的教育没能与社会很好的融合,而在长大后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因此,纳托普特别注重个人与社会同一性以及通过教育使人明了社会的真相和处世的方法,即注重“群育”。
当前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激烈冲撞,现存的价值规范体系、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也受到猛烈冲击。人类越来越生活在人性化的人群之中,因此,群性教育已成为重要的一环。目前在校的大学生,基本上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生的,独生子女居多,在成长、发展历程中,比较注意自己的个性张扬,往往缺乏与社会、与他人的合作意识,对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义务缺乏应有的负责态度。网络世界的发展令现代许多人生活在网络虚拟“群”中,缺乏过现实团体生活的愿望和能力,容易将年轻人拉向非群性化轨道。
学校应通过学生社团、集体活动等多种形式,让学生有群处的机会,学会与人沟通交流,学会正确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培养其群策群力的团队精神,激发其先公后私、尊重他人的心态,舍弃自我中心观念,培养学生乐群、合群、爱群、治群、为群的良好道德素养和个性品质,相互理解和沟通,有助于互帮互助、互惠互利。通过交往可以对他人的兴趣、爱好性格习惯能力知识水平、价值观念等有较为深入的把握,为双方的互动合作沟通交流消除误解创造条件,有利于他们在互动过程中做出正确的角色期待、意义解释和人际反应,也有利于对双方“和而不同”,产生一种“群体共生效应”,从而将人的群性发展为人的社会性。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南怀瑾.孟子旁通[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梁啓雄.荀子简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5]蔡元培.蔡元培全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6]刘述礼.梅贻琦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7]陈学恂.中国教育史研究(现代分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8]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
[9]向春.中国传统群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高等教育研究,20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