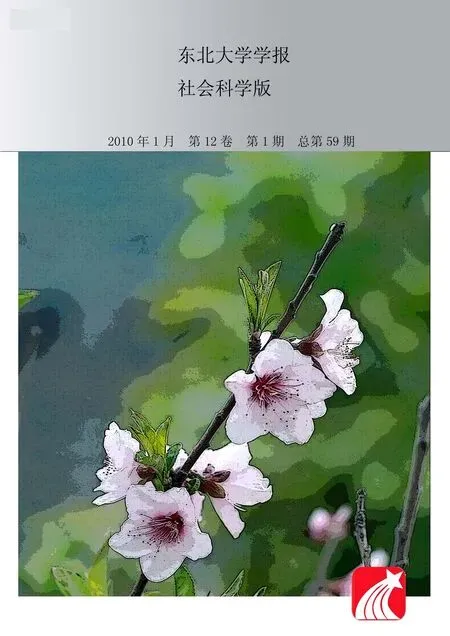科学认识的模式
----以微血管减压术的发展为例
2010-04-03张今杰徐志欣
张今杰,徐志欣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
科学认识是人类面对复杂而神秘的自然界时所采取的一种理性行为,也是人类对自然界进行认知的成果。“人类在创造自身生存条件的活动中,为了能够反作用于自然界,包括人类自身,首先必须发现自然的奥秘,认识自然的规律性,并因此获得自由。一切科学认识和科学发现都是复杂的人类活动。”[1]97人类在长期的科学认识活动中,总结出了一些普遍而有效的规律或者模式。现代西方的科学哲学中不少流派的代表人物都竞相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理论来证明这一点。如托马斯·库恩的“范式论”、卡尔·波普尔的“否证论”、伊姆雷·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他们的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科学认识进步的规律或模式。医学的发展和进步同样遵循一定的模式。本文试图以医学中微血管减压术的产生、发展和成熟并最终成为治疗窦性心动过缓的一种新术式作为实例,说明科学认识发展的模式。
一、 微血管减压术的临床实践
微血管减压术是现代临床医学中的一种常用的术式。“微血管减压术(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简称MVD) 是指应用显微外科操作技术,将走行于三叉神经、面神经等颅神经根部并对神经进出脑干区造成病理性压迫的血管推移垫开,以解除血管对神经的压迫,治愈相应临床症状的一种术式。”[2]人们早在上世纪40年代在尸体解剖时就发现,在三叉神经痛(trigeminal neuragia,简称TN)和面肌痉挛的患者中的颅内小脑延髓池里存在动脉血管对颅神经的接触或压迫,这种压迫的出现几率较高。美国的Gardner在1962年首先报道用微血管减压治疗面肌痉挛。当时的微血管减压的治疗效果还不是十分确切,1966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的Jannetta教授将显微外科技术成功用于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HFS)的手术治疗,并将这一手术命名为微血管减压术。Jannetta手术效果比Gardner明显提高,Jannetta也提出微血管减压术的原理。他认为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的病因学是三叉神经(第五颅神经)和面神经(第七颅神经)的出根区/入根区(root exit/entry zone)存在桥小脑角的动脉血管压迫,导致三叉神经和面神经受到刺激引起的临床症状。他认为将压迫血管推开减压后,受累的神经去掉压迫,神经功能恢复正常后临床症状将自动消失。手术治疗原理采用“插入法”,解除血管对神经的压迫,其关键步骤是判明责任血管后,将血管充分游离之后再将其推移离开面神经,将适当大小的Teflon棉放置在责任血管和脑干之间。Jannetta的微血管减压术的原理由于其治疗效果的相对确切(创伤小、治愈率高、手术并发症发生率低,特别是其完全保留血管、神经功能的特性),逐渐被世界各地神经外科医师所接受。另外,磁共振血管造影(MRA)及磁共振血管断层造影(MRTA)除提供清晰的神经血管图像外,还可以分辨责任血管的形态来源走行及与神经压迫的关系。因此,“随着手术经验的积累和神经影像学的发展及锁孔技术的应用,MVD技术已经是治疗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的首推治疗方法”[3]。
美国的Steven教授等人对美国1996—2000年全国性的住院患者采用追踪随访性研究,结果显示,“采用MVD治疗三叉神经痛患者1326例,面肌痉挛237例,舌咽神经痛27例,总死亡率只有0.3%,有神经方面并发症1.7%,术后脑脊液(CSF)漏0.4%,0.7%的患者需呼吸机,3.4%的TN患者同时接受了三叉神经感觉根切断术”[4]。这些研究数据显示对于药物及其他方法难以控制的TN患者实行MVD治疗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国内左焕琮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用微血管减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由于中国的此类病人数量巨大,我国的微血管减压术已经十分成熟,治疗效果也十分满意。
二、微血管减压术的发展所遵循的科学认识模式
从微血管减压术的提出、完善到正式成为一种新的术式的过程来看,微血管减压术作为人类对自身这样一个认知客体所进行的认识的取得遵循了一定的模式,总起来说,它经历了几个前后关联的发展阶段。
1. 医学实践中遭遇难题
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是临床上十分常见的疾病,50~60岁的中老年人发病率最高。三叉神经痛是一种在面部三叉神经分布区内反复发作的阵发性剧烈神经痛,被人称为“天下第一痛”。三叉神经痛是神经外科常见病之一,也是国际公认的疑难杂症之一。由于其发病机理长期未能明确,药物治疗时一般是服用镇痛剂,只能暂缓疼痛,且有副作用。而手术治疗则大多对神经有一定的破坏,会引发其他方面的疾病,而且容易复发。
面肌痉挛即面部一侧抽搐(个别人出现双侧痉挛),精神越紧张、激动痉挛越严重,直至发展为口眼歪斜。面肌痉挛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原发型面肌痉挛,一种是面瘫后遗症产生的面肌痉挛。两种类型可以从症状表现上区分出来。原发型的面肌痉挛,在静止状态下也可发生,痉挛数分钟后缓解,不受控制;面瘫后遗症产生的面肌痉挛,只在做眨眼、抬眉等动作时产生。我国民间治疗面肌痉挛的方法繁多,面肌痉挛治疗时间都较长,如贴膏药治疗、服中药治疗、针灸等常规治疗,但大多传统口服药物只是单纯地通经活络,祛风化淤,只会见效,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这些常规治疗方法在缓慢治疗的同时,也给病人带来了许多不便。病人往往得长期生活于痛苦之中。
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成为了困扰人类多年的难治之症,不过,随着微血管减压术的出现,这个难题就有了解决之道。
2. 临床医学的实验尝试
临床医学历史悠久,“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公元前377)创立医学形成学派,坚持把疾病看做是一种要服从自然法则过程,强调用细致的观察来研究疾病,因而对许多疾病进行了描述,并提出了适当的治疗方法,是现代临床医学的开端”[5]。人们认为,我们今天也只有从临床现象的观察到病理规律的把握,再从病理规律的掌握到新术式的采用,以及这些过程的循环往复中,才能不断地推进医学的发展和完善。
早在上世纪的上半叶,就有多种开颅手术应用于三叉神经痛的治疗,包括三叉神经节减压术,圆孔、卵圆孔减压术,三叉神经感觉根切断术,硬脑膜减压术,三叉神经根减压术等。根据1934年美国的Dandy的报道:“经枕下开颅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215例,在三叉神经出根区(root exit zone,简称REZ)意外发现了神经根被动脉瓣压迫66例(30.7%),静脉压在神经根30例(14%),提出了微血管压迫(MVC)这一概念,并且将其推广到面肌痉挛的发病原因中,进而提出,MVC是颅神经疾病一个不可忽视的致病因素。”[6]1959年美国的Gardner对18例TN患者采用枕下开颅小脑桥角探查术,发现有6例血管压迫神经根,将压迫神经根的血管剥离开减压后,疼痛消失而治愈,并提出了“短路”(short circuit)学说。Gardner指出:“使用脱脂海绵解除这些血管压迫获得良好的临床疗效 。”[7]正是这些医学研究人员通过不断的临床医学的实验尝试,才有了微血管减压术的渐趋完善,这个实验尝试过程也并不是独立进行的,而是始终与科学认识的其他过程相伴而行的。
3. 科学假说的提出
人类往往在经过一系列的实验尝试过程之后,会对所研究的问题提出一些尝试性的假说。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定义,科学假说是指根据已有和新的科学事实对所研究的问题作出的一种猜测性陈述。它是将认识从已知推向未知,进而变未知为已知的必不可少的思维方法,是科学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一对科学假说的规定中,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科学假说具有猜测、假设的性质,还不属于被实践所验证了的科学事实;二是科学假说又不同于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而是以已知的科学知识和新的科学事实为基础,是在这些基础上提炼出的科学问题,并在多种科学知识基础上运用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类比和想象等方法,形成解答问题的基本观点。波普的证伪原则告诉人们,“一切科学理论都只是猜测和假说,它们不会被最终证实,但却会随时被证伪,证伪的过程使用试错法的程序:假说—事例—(更完善的)假说”[8]。因此可以说假说是通向理论的必要环节,科学假说是科学理论的可能方案。科学假说带有或然性,微血管减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的原理最初仅仅是一种假说。
在对微血管减压术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在对面肌痉挛的患者进行微血管减压治疗的时候,在国际上首先观察到一种临床现象:面肌痉挛的患者中有一部分合并有窦性心动过缓(窦性心率慢于每分钟60次),而且在大多数这些患者的微血管减压术中可以见到与面肌痉挛同侧的迷走神经或者延髓腹外侧也存在颅内动脉血管的压迫。术中对个别患者同时进行了迷走神经或延髓腹外侧的减压,术后观察到患者的心率明显增加。研究人员选择了部分合并有窦性心动过缓的面肌痉挛患者,对这些压迫血管同时进行减压,观察这些患者的术后心率变化。结果发现这些窦性心动过缓的患者的面肌痉挛症状多数发生于右侧脸部,术后近期(约一周)和术后远期(1年)的心率无统计学差异;术前的心率和术后近期及远期的心率比较均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研究人员于是提出假说:面肌痉挛合并窦性心动过缓的原因是颅内动脉血管对迷走神经颅内段或者延髓腹外侧的压迫导致延髓内的疑核或迷走神经背核,迷走神经颅内段受到刺激,迷走神经的兴奋性增高。支配心脏的心迷走神经具有负性的变时变传导作用,因此引起心率变慢。窦房结主要受右心迷走神经的支配,因此具有明显的右侧优势。这只是研究人员对这种现象提出的假说,并没有得到证实。
4. 实践的检验
把假说运用于实践,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事实和这个假说相符合,并且没有任何已知事实和它矛盾,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假说接受为理论,它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所以,我们必须把假说放到实践中去接受大量实践事实的考验,或者用科学实验去证明(证实)或反驳(证伪)它。在假说与实验之间的关系问题上,20世纪初不少科学家已经注意到:不停地提供材料的实验和不停地进行解释的假说之间不断的斗争,推动着科学认识不断前进。“在这一对立中,一方面,假说的提出和验证要有实验根据;另一方面,实验的设计和进行实验的解释又必须依赖于假说。”[1]101
无论在验证假说还是导致新理论的情况中,科学实验毫无例外都是科学认识的源泉和检验真理的标准。有一类实验不是对某些客体或自然现象本身进行实验观察,而是先设计与该客体或自然现象相似的模型,用它们模拟原型,如用动物去模拟人,通过对模型的实验来间接研究原型的性质和特点。如动物实验就是医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和手段,是指在医学研究中给予动物某种实验处理后观察动物反应及其规律性变化,并将结果推论到人的过程。它在人类的疾病调查和防治研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模型实验大大扩展了人们进行经验研究的可能性,它是一种间接的经验。为了进一步得到更多的证据来证实前面提出的假说,研究人员也进行了动物实验。开颅对猫的迷走神经或延髓腹外侧进行一定程度的压迫,实验动物分左右侧和对照组,结果发现压迫右侧延髓腹外侧后心率有明显的下降,而且这种下降效果在一定时间内得到保持。实验结果支持研究人员提出的假说。
任何假说都应具备解释功能和预见功能。根据上述假说,神经受到动脉血管的压迫会导致功能的异常。但为什么这种情况只在三叉神经和面神经发生,而没有在其他部位出现呢?许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有人认为,如果其他部位的血管压迫神经,而血管和神经的情况也大体相同的话,也应该会引起相应的临床症状。于是人们继续进行检验,后来发现对第9颅神经微血管减压后有治疗舌咽神经痛的效果,并且已经逐步应用于临床。但是在对其他部分的血管和神经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表明,上述假说并不成立,这是什么原因呢?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能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血管对神经的压迫主要发生在桥小脑角,因为在颅内甚至全身只有这个部位有潜在的腔隙,并且血管神经十分丰富,大部分的颅神经都在此经过。椎基底动脉的主干和分支也走行在这个区域,而且血管的走行变异较大。因此这里血管对神经的压迫相对来说是常见的。近年来人们又发现偏头痛的病因可能也与血管压迫有关系。对引起偏头痛的主要神经(眶上神经、耳颞神经和枕大神经)的减压在部分偏头痛患者中取得了成功。对于全身其他部位血管压迫临近神经的情况则大不一样。在四肢和体腔,由于动脉血管和神经一般都是走行比较规律,变异不大,周围多是软组织,缺乏束缚,故很少引起对神经的压迫症状。而颅腔容量较小,被颅骨固定,潜在腔隙小,其中走行的神经血管比较丰富,走行变异较大,此部位的颅神经出颅部位神经裸露,行程较远,位置相对固定,容易形成血管对神经的压迫。
回过头来再分析颅神经的解剖特点,就能发现这种压迫现象其实应该是一种必然要存在的现象。颅神经一共有12对:视神经、嗅神经、动眼神经、滑车神经、三叉神经、外展神经、面神经、听神经和前庭神经、舌咽神经、迷走神经、副神经、舌下神经。前面我们已经对迷走神经有所分析,就不再赘述,这里再分析一下其他11对颅神经:视神经和嗅神经本身位于前颅窝底,没有伴行的较大的动脉血管,动眼神经、滑车神经、外展神经细长柔软,动脉血管难以对之形成张力性压迫,因此临床目前没有发现动脉对这些神经的压迫症状。三叉神经和面神经相对短粗,行程固定,因此容易被变异的动脉血管压迫出现临床症状。舌咽神经行程也相对固定,长度中等,舌咽神经应该也可以出现动脉血管的压迫症状,舌咽神经已经在临床被证实有压迫症状,并且微血管减压有一定的治疗效果。副神经的部分神经根行程较短,此部分神经根可能出现压迫症状,在痉挛性斜颈的患者术中切断部分副神经根可能就是这个原因。舌下神经行程相对较长,难以出现压迫症状。迷走神经的颅内行程不长,直径中等,动脉血管能否造成压迫迷走神经的症状呢?按照前面的一般推理,应该是可以出现的。
5. 术式的推广应用
我们认识自然界的奥妙,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人类不断探索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是为了将认识到的真理用于指导实践。任何科学认识,都来源于实践,并最终回到实践。对此,列宁曾作出深刻的概括:“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9]。也就是说,认识的目的是为了实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那么,科学家们所提出的这种在微血管减压术应用中通过了实践检验的假说真的能指导我们的实践吗?
研究人员结合此假说的原理和窦性心动过缓病症的特点,认为这种术式完全可以用于治疗窦性心动过缓。在临床上,尽管大多数窦性心动过缓(如心率不低于每分钟50次),没有症状,并不需要治疗,只有少数有心输出量不足的患者才需要植入起搏器治疗,但专家们认为,许多没有面肌痉挛的单纯窦性心动过缓的患者也可能是由于颅内动脉血管压迫引起的,如果他们出现心输出量不足的情况,如果能够通过减压增加心率,增加心输出量,就有可能避免心脏起搏器的植入。因此,人们相信对迷走神经或者延髓腹外侧的微血管减压将来可能成为一种治疗有症状的窦性心动过缓的手段,成为一种应用性很强的新术式。
现代医疗器械的进步为这种新术式的应用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许多新的技术已应用于MVD。其中有关神经内镜的报道较多,神经内镜可用于桥小脑角的探查,也可辅助显微镜用于MVD。因显微镜有所谓的“死角”,内镜可作为辅助手段,用以显示脑池,寻找变异的血管,显示压迫神经的血管。减压结束后,内镜可用来确立手术的完整性。在一些病例中内镜可用以辅助电切和电凝静脉,对血管神经的高倍数放大在探查桥小脑角时尤显重要。虽然神经内镜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关内镜的图像融合技术、握持装置、防雾装置、冲洗装置也有待进一步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手术的成功率,但是,“随着这些问题的克服及显微镜与内镜融合技术的不断发展,神经内镜的使用会越来越广泛”[11]。相关医疗器械的进步为这种新术式的推广应用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由此可见,微血管减压术治疗窦性心动过缓是大有可为的。
三、 科学认识发展的一般模式
人类对自然界及自我的认识是全方位的,微血管减压术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的方面。从微血管减压术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科学认识的发展不是随机的,而是遵循一定的模式。这些模式在实践中被科学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
那么科学认识发展的源头是什么呢?早期的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始于观察所得的经验材料,科学认识最后又必须回到经验中进行检验。波普尔则强调“观察渗透着理论”。他说:“我们的日常语言是充满着理论的,观察总是借助于理论的观察。”[12]在他看来,客观的、无先入之见的观察以及观察陈述是不存在的,一切科学观察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是渗透着理论的观察,因此观察并不是科学的真正起点。科学开始于问题,始于科学研究和生活中所遇到的难题。“应当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13]科学理论就是一种解决问题的猜想,而观察乃是对这种猜想的检验和反驳。在这里,波普尔把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倒转了过来,成为逻辑实证主义过渡到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关键人物。波普尔的观点虽有偏颇之处,但总体上来说有一定的合理性。
面对难题,科学家共同体会提出一系列相互竞争的科学假说,任何科学认识最先都仅是一种假说,而假说则是一组模型化的解释命题。科学家们借助于这种模型化的解释命题,把他们对于对象的认知模拟出来。这种模型所描述的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整体性的相似关系。正因为有这种相似关系,这种理论模型才可能在科学实践中成功地解释和预言科学现象。理论模型是科学家们建构出来的,但这种建构并非纯粹是理性的,而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
科学家们建构出来的假说无疑带有一定的虚构性,但是这种虚构性将会在与公认的实验事实的比较中不断地得到矫正,并且不断地向着与真实世界的一致性逼近。在科学认识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并存着相互竞争的假说系统,分别描绘出相互竞争的几个不同的可能世界,这些可能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相似性程度决定了人们对这些假说的取舍态度。人们一般都会选取相似性程度较高的假说,并对其进行经验和实验的检验,不断进行修补和完善,一步步增加其真理性的程度。也就是说,这种相似性不是两个系统之间的固定不变的关系,而是会随着我们对世界的深入理解和认知而不断增强。当假说系统在解释和预测科学事实的实践中不断经受住考验时,人们就会承认和接受它为一种正确的理论,同时将其应用于科学研究和生产、生活的实践中。
微血管减压术的产生、成熟和发展及推广为我们呈现了科学认识发展的一个典型范例。在临床医学中,医学研究人员通过微血管减压术的实践中所偶然发现的迷走神经被压迫的症状,提出了迷走神经被压迫的假说,并通过相关患者的手术和动物实验初步检验了这种假说,然后将此假说作进一步的推广应用,试图将微血管减压术作为治疗窦性心动过缓的一种新术式。
四、 结 语
科学认识不是理论系统与真实世界之间的绝对的一致性的表征,而仅是理论模型与实在世界之间一定程度上的相似关系。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入,这种相似关系最终将逐渐地趋向模型与世界之间的一致性关系。也就是说,科学真理将是关于世界的理论模型与实在世界之间的相似关系的一种极限,这是科学认识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微血管减压术这样一个临床医学技术发展的案例本身给我们展现了科学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科学的发展需要经过实验尝试、提出假说、实践检验和推广应用等环节。这个科学认识发展的程序,既不是纯量变的“积累式”,也不是纯质变的“革命式”,而是把量变和质变统一起来的科学认识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刘大椿. 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2]Jannetta P J. Microsurgical Management of Trigeminal Neuralgia[J]. Arch Neuro, 1985,42:800.
[3]Hainess S J, Jannetta P J, Zorub D S. Microvascular Relations of the Trigeminal Nerve: An Anatomical Study with Clinical Correlation[J]. Neurosurgery, 1980,52:381-386.
[4]Kalka anis, Steven N. M D, Eskandar, et al.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Surgery in the Unites States, 1996 to 2000: Mortality Rates, Morbidity Rates, and the Effects of Hospital and Surgeon Volumes[J]. Neuro-surgery, 2003,52:1251-1262.
[5]黎松强,张学先. 解“李约瑟难题”看现代科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63.
[6]Dandy W E. Concerning the Cause of Trigeminal Neuralgia[J]. Am J Surg, 1934,22:447-455.
[7]Gardner W J, Miklos M V. Response of Trigeminal Neuralgia to “Decompression” of Sensory Root: Discussion of Cause of Trigeminal Neuralgia[J]. JAMA, 1959,170:1773-1776.
[8]赵敦华. 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227.
[9]列宁. 哲学笔记[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181.
[10]余源培,吴晓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导读:上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142.
[11]王召平,种衍军,朱广廷,等. 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的现状与进展[J]. 中华现代外科学杂志, 2005(5):438-439.
[12]波普尔. 科学发现的逻辑[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6:31.
[13]波普尔. 猜想与反驳[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