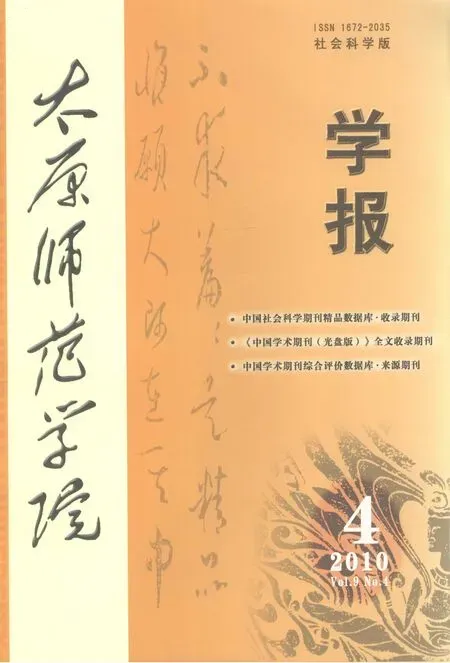论大众传媒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的关系
2010-03-22王欣
王 欣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7)
论大众传媒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的关系
王 欣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7)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从宏大叙事的价值观转向个人化、私人化,女性主义文学得到迅猛发展,堪称是女性文学思潮的绚烂期,同时也是大众媒体逐渐占据社会主流话语地位的时期。以图书、杂志、影视、网络四种大众媒体主将与女性文学的关系为例,以发掘它们在推动女性文学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和在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女性文学;大众传媒;关系;双刃剑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的发展现状及其特征
女性文学的命名,也可称为“女性写作”,广义指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狭义指由女性作家创作的,具有女性风格的,凸显女性意识的作品。对女性文学的定义存在多方争论,我们仅以戴锦华的观点为参考。在她看来,女性文学呼唤并要求着两个东西:一是性别立场,一是文学。两者都不可或缺,但也不能简单地互相替代与等同。[1]根据戴锦华提供的两个标准,我们可以对女性文学进行谨慎而宽泛的定义:女性文学是女性作者关于性别关系的想象与建构。
女性文学从20世纪80年代的“浮出历史地表”,到90年代的“概念性女性写作”,到世纪之交美女作家的“众声喧哗”,发展起起伏伏,在文学界也掀起了一阵阵波澜。我们以20世纪90年代作为切入点,不仅考虑90年代是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绚烂期,而且更想考察大众媒体逐渐占据社会主流话语地位的背景对女性文学发展的影响。
我们将根据代表性女作家的创作特征简单地把她们分为以下三个类别,以此来概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中所彰显的女性意识。
王安忆、池莉、方方、铁凝、张抗抗、迟子建、张欣、范小青——温和派女性主义——以女性作为描写对象,凸显启蒙话语下对“人”的关注;林白、陈染、海南、徐小斌、徐坤、虹影——激进派女性主义——建立女性话语系统,提出明确的反父权和男权意识;卫慧、棉棉、魏微、戴来、朱文颖、金仁顺、安妮宝贝——70后女作家——超越男女性别论争,彰显性别魅力和确立女性主体地位并行不悖。
二、大众传媒对女性文学发展的影响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认为:文学活动是一个循环的整体,由客观世界、创作者、作品、接受者四个要素组成,四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然而这四个环节之间还由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贯穿——传播媒介,只有这样,四个要素才能成为一个循环的整体。
1.大众传媒兴起及占据主流话语的背景
21世纪初,大众文化以其广泛的触角遍及工业化国家并渗入经济文化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以商业化、物品化为特点,并借助强大的大众传媒,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大众文化的视域下。[2]在信息渠道单一的时代里,文学具有显著的权威话语权,并一度引导社会文化舆论的方向。而现代商业社会,大众媒体包括电影、电视、网络、手机等高科技信息传播媒介以其高速便捷并包含巨大信息量的传播方式契合现代社会信息爆炸的特征,逐渐取代文学并取得了至高无上的话语权。
2.大众传媒对女性文学发展的影响
以此为背景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文学批评,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而大众传媒在塑造女性形象和彰显女性意识的过程中,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女性文学在大众传播中处于怎样的地位以及发展的困境是什么?我们以女性文学与四种大众媒介的关系为研究的切入点,尝试作出分析。
其一,大众媒体的分类。在传统社会,文学作品大多需要口口相传,即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传播,或者印刷成图书进行有限的销售,而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我们来到了科技主宰生活的新世界。借助声色光影,各种科技媒介日益深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这就是大众传播,具体指传播组织通过现代化的传播媒介——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电影、杂志、图书等,对极其广泛的受众所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而我们就是“大众”,分布广泛、互不相识的广大受众。大众媒体面对的受众广泛,传播对象是一对多,即一种媒介面对大量人群,传播信息量密集,因此传播效果比较显著。更重要的是,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无孔不入,不仅作为传播信息的渠道和媒介,同样也担当了塑造社会文化和生活观念的责任。我们在本文中选取图书、杂志、电视、电影、网络等五种媒体作为研究对象,前两种是传统媒体,在商业社会功能有所异化,后三种是新兴媒体,在商业经济的推动下,在大众媒体和人们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影响力不可小觑。
其二,“女性作家畅销书排行榜”的出版策划。图书作为传播时间最长久的印刷媒体,具备以下优势:第一,信息容量大。一本厚厚的图书,有足够大的空间来阐述详细的内容,因此范围广泛、层次丰富、分析深刻是其独特的优势。第二,保存时间长。图书是印刷品,便于保存,方便日后随时进行翻阅查询。第三,受众的主动性大,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主观能动性,随意选择任何一部分进行阅读。
“畅销书”的概念来源于美国。在1895年美国书商杂志社创刊,并刊登了第一个对图书的销量进行统计排行,以作为读者选购图书的参考,这就是世界公认的最早畅销书排行榜。而在我国,1995年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进行每月一次的畅销书调查,并刊登于同期的《中国图书商报》。自此国内的畅销书排行榜纷纷面世,拉开了图书出版市场新的较量。从女性文学“私人化写作”的发端,引起图书出版市场的注意,贩卖女性隐私成为商家的噱头,创造了巨大商业效益,同时也验证了在男权社会中女人是“风景文化”、“娱乐文化”。
如70后美女作家与商家联合,运用多种惊人的手段策划个人作品出版,取得轰动效应。新写实作家池莉的小说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在“飞利浦·真的咖啡之十本好书”评选的颁奖典礼中,与《挪威的森林》、《山居笔记》、《上海的金枝玉叶》等书一起位列其中。她的《生活秀》被读者评选为最受欢迎的十本好书之一。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来来往往》两年卖了20多万册,《小姐你早》也有十多万的印数。王安忆等都成为知名畅销书女作家,频频举办新书发布会,成为广大女性心目中的“明星”、“榜样”、“生活顾问”。
其三,文学杂志对女性文学的推手作用。杂志的媒体功能与图书相比,发行周期比较短,但由于内容容量有限,发行量小,所以更小众化,内容专业化专门化,图文并茂,印刷精美,面对的都是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精英人群。在文学界,纯文学期刊对女性文学的发展起到推手,甚至堪称伯乐的作用。当然,大众传媒的商业性也使文学期刊向大众文化投诚,获得商业效应的同时降低了文学性。
1998年《作家》第7期推出“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也称“新新人类小说”,她们的亮相标志着新一代女性作家的诞生。各种文学期刊主办的女性文学研讨会,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花城》杂志社主办的林白《守望空心的岁月》研讨会,《钟山》杂志社主办的王安忆《长恨歌》研讨会等。2000年起,《百花洲》改版成为国内首家大型女性文学双月刊,成为一本女性文学“自己”的刊物。在文学期刊普遍面临危机的情况下,《百花洲》以特别的识见和勇气,对杂志进行全面彻底改造,无疑对女性文学的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改版后的《百花洲》开辟了一批富有特色的栏目,诸如“第一视点”、“金蔷薇”、“我的女性观”、“佳作推荐”、“现实与虚构”、“双桅船”等,推出了一大批的作家、学者,既有对女性文学理论的探讨,又有精彩的原创作品,兼顾了各层次的读者。[4]
其四,女性文学与影视剧改编的成功联姻。电视在大众媒介中占据半壁江山,是当代社会的告知者、劝说者、娱乐者、教育者和沟通者。不仅由于其娱乐性强,视听兼备,图声并茂,而且节目即时性播放,受众门槛低,是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家庭获得信息的渠道。电影由于其高品质、视觉性、逼真性的大银幕影院效果,吸引了中高端受众,但现在大众可借助网络下载,受众面也越来越宽泛。影视文化的输出同时有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持,经费充足,逐渐取得大众文化的霸权地位,对文学的影响也日趋深远。
厦门大学的朱水涌教授认为,“由于90年代商品经济的冲击,文学不得不从贵族化的精神高地上走下来。80年代几亿人同看一部短篇小说的现象,在当下已没有可能。文学为求生存不得不考虑受众问题,而影视传媒恰恰是21世纪辐射最广的媒体。作家选择这条合作的道路,是当下的文学‘大众化’,是一种历史性的‘谋合’”[5]。
由于影视剧的受众群中女性占了多半边天,所以女性作家的作品频繁被改编为影视剧就顺理成章,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池莉的《小姐你早》及据此改编的电视剧《超越情感》广受欢迎,随后其多部作品《来来往往》、《生活秀》也都改编为收视火爆的明星电视剧。
《沧桑花楼》的剧本,开出同时期国内剧本120万元的最高价。纯文学作家王安忆《长恨歌》更是多家媒体抢拍的目标,广州女作家张欣作品不仅多部改编,本人更兼职编剧,直接参与其中,这些作品都受到了大众的热烈欢迎。
其五,读图时代到“读网时代”的飞跃。网络媒体超越了性别、地域、种族等界限,面对众生人人平等,为女性提供了和男性同等的写作权利,发表自己的言论和心声。同时,由于其匿名性、即时性、双向或多向互动性,人们都可以通过网络即时交流,在21世纪以来受到最大的欢迎,对文学的影响也可见一斑。多媒体功能集于一体,音乐、图像、动画、色彩相结合,中国从“读图时代”进入“读网时代”,对女性文学的发展也影响深远。
安妮宝贝最初的作品《告别薇安》发表在国内最大的社区论坛——“天涯”,小说连载点击率居高不下,风头强劲,受到出版市场的关注。木子美借着70后美女作家的春风,以性和身体作为噱头,在网上连载个人性日记,得以成名一时。随着网络的盛行,由翟永明和周瓒等主持的女性诗歌网站和荒林主持的女性文化网站,也借助网络发出女性独立的声音。池莉、王安忆、严歌苓、张欣等女作家的作品也都搬上了网络,大众可以随时进行在线阅读。
三、大众传媒对女性文学的“双刃剑”作用
1.大众传媒对女性文学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
其一,作家明星化。商业效应给女性作家冠上明星的光环,以王安忆、池莉、张欣等为代表的一批女作家,成为广大女性心目中的偶像,特别是白领阶层为主的知识分子,她们在商业社会中获得经济独立的同时,追求精神的主体地位,追逐享乐,而女作家作品中生活在城市中的女性,她们面对生活苦难的韧性和坚强,她们的生活姿态,都受到广大女性的推崇。明星的光环也促进了作家作品的销量大增,知名度升高。
其二,读者广泛化。借助大众传媒的作用,女性作家的作品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不仅是知识分子纯文学的关注,更拥有了更多的普通读者。同时由于影视媒介的推手作用,在收视率爆红之后,广大受众更想阅读作家的文本,借以拥有更多的想象空间。正如踏入影视圈数年之久的知名作家刘恒所说,“作家辛辛苦苦写的小说可能只有个人看,而导演清唱一声听众可能就达到万人”。由此可见,影视魅力对观众的影响,作家也希望借助于大众传媒向更多的观众传播自己的思想和艺术观念。文学作为人学,终于从高高在上的殿堂走下来,走向了广泛的民间和广大的大众。
2.大众传媒视野中女性的符号性和商业性
其一,作品商业化。作品的商业化表现一方面是以70后美女作家和网络作家为代表,作品问世之初就在商业浪潮中翻滚,利用营销策划手段,为自己作品叫卖,以女性、私人化为卖点,女性被作为“多功能玩偶”的符号。70年代女作家更突出的特质是物质的实用主义、精神的虚无主义,面对男权社会的文化反抗已经基本消失,留下最多的是在消费社会中寻求利益。
另一方面,由于迎合商业社会的需求,更多是广大读者的愿望,女作家纯文学的创作也逐渐有了转变。例如池莉的作品虽取得广泛的市场成功,但缺乏自我的超越性。在商业机制的促动下,对日常生活的描写转换为模式化的写作,新的作品基本与以前的作品雷同。这是一个作家转向畅销通俗作家的标志。
其二,看与被看。“身体写作”不仅作为建构女性话语空间和主体性的符号,也将女性置于被看的尴尬境地,被男性和女性来窥视。这也是身体写作的一个误区,有些作品将女性的身体当作抢占市场的招牌,被强有力的商业包装和改造,消费性凸显,越来越媚俗。商业社会衡量的标准是男性的尺度和男权的视域,女性从看的地位转到了被看。“被称为‘美女作家’的新一代女性写作者则是自觉接受商业流行话语的诱导,其倾心打造的肉体狂欢早已经丧失了身体写作的革命意义,沦落为一种主动趋奉男性窥视欲望的消费话语”。[5]
四、余论
美国学者戴安娜·克兰在《文化生产:媒介与都市艺术》一书中提出了文化产品在生产流通过程中,需要经过“多阶段过程的组织过关”理论。具体来说,在整个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产品面临两个独立的“把关系统”,第一个系统涉及接受某种文化产品,第二个系统涉及评价这些文化产品,并为“被选中者”提供进入更严格的传播系统的途径,以使之获得广泛的传播。参照这一理论,我们不难理解大众传媒在女性文学发展过程中是如何发挥“把关人”的作用的。针对图书杂志的出版行业,我们可以说文学期刊的编辑是“首轮把关者”,出版商是“二度把关者”。文学期刊决定哪些作家和作品可以面世,出版商决定着哪些作家和作品可以流行。有影响力又最看重经济效益的出版商有自己独立的销售系统、明确的读者定位、对市场和读者具备一流敏感性,所以他们的选择对文学作品的传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对影视行业来说,“把关人”的作用创造了许多文学的市场神话。鉴于影视传媒自身的娱乐性和消费性,他们对文学作品的选择和把关完全体现了对大众趣味的倾斜。这些现象不能不让我们担忧,在大众文学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中,如何能使纯文学生存下去,坚持对读者和未来文学的发展产生影响,是我们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1] 戴锦华.犹在镜中[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6.
[2] 李灵灵.矮化与误区:商业传媒背景下的文化共谋——大众文化视野看9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7,(3).
[3] 郭庆光.传播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 邓利.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5] 荒林,王光明.两性对话——20世纪中国女性与文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冯自变】
2010-05-16
[个人简历]王 欣(1984-),女,河南南阳人,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
1672-2035(2010)04-0083-03
I206.7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