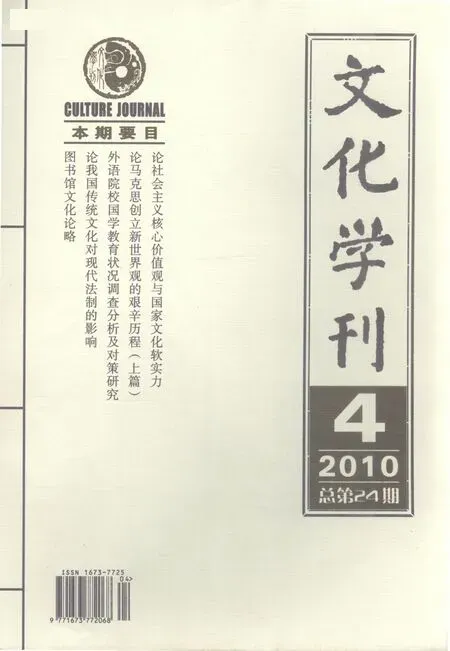藏族成文立法的演变及特点探议
2010-03-22刘艺工
刘艺工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
藏族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具特色的法律文化传统。成文立法是藏族传统法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并形成了一系列显著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藏族传统立法仍然在藏区存在。民主改革后,虽然形式上的藏族传统法制已经不存在,但传统的法制观念仍然在藏族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力。改革开放后,传统藏族法制中的“赔命价”还一度在藏区复活,并与国家法律发生冲突。因此,系统研究藏族法律传统对于更好地理解传统藏族法律文化和保持藏区的和谐稳定均有重要的意义。
一、藏族成文立法的演变
传统的藏族法制包括历代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颁布的各类法律和民间以部落为基础形成的部落习惯法。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颁布的各类法律多为成文法,部落习惯法多为不成文法。
藏族成文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赞普时期,历史上的藏族成文法包括赞普时期颁布的《法律二十条》、《六大法典》、吐蕃《三法》和元、明、清时期西藏地方政府组织有关人员编写的《三典》等。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以前,藏族已经有十几个部落,部落中没有文字,当然也不会有成文立法。到了松赞干布时代,他用武力统一了西藏全境。在松赞干布的授命下,西藏学者根据印度梵文创制了藏文,为成文立法创造了条件,成文法开始出现。
但即使进入松赞干布创制成文法的年代,习惯和习惯法在吐蕃社会中也仍然影响巨大,甚至发挥着比成文法更加有效的实际作用。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早期立法的粗陋与简单。从有关文字记载看,这些立法的规定内容单一,可操作性不强,其具体实施还离不开习惯的补充与支撑;二是由于西藏地广人稀,居住分散,经济、文化均非常落后,立法的传播和人们对立法的理解都需要较长的过程;三是统一伊始,各部落间的融合尚需时日,各地区的特殊性与地域性依然较强,统一立法的实施必须以地方习惯来加以辅助。[1]
松赞干布时期,由印度传入的佛教取代了藏族的原始苯教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信仰,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持。佛教中,最基本的教义是提倡“十善”,即不杀、不盗、不淫、不嫉妒、不忿恨、不愚痴、不谎言、不巧辩、不挑拨、不恶骂。吐蕃王朝立国的7世纪初期,松赞干布便命令吞米桑布札、噶尔东赞域松等大臣,依据佛教“十善”的精神,制定了法律二十条,于公元629年颁布,在全国施行,开吐蕃立法之先河。
《法律二十条》的内容为:1.杀人者偿命,争斗者罚金;2.偷盗者,除追还原物外,加罚八倍;3.奸淫者断肢,并流放异地;4.谎言者,割舌或发誓;5.要虔信佛、法、僧三宝;6.要孝顺父母,孝敬侍养;7.要尊敬高德,不与贵族及贤俊善良人争斗;8.敦睦亲族,敬事长上;9.要帮助邻里;10.要出言忠信;11.要做事谨慎,未受委托,不应干涉;12.要行笃厚,信因果,忍耐痛苦,顺应不幸;13.要钱财知足,使用食物与货物务期适当;14.要如约还债;15.要酬德报恩;16.要斗秤公平,不用伪度量衡;17.要不生嫉妒,与众和谐;18.勿听妇言,自有主张;19.要审慎言语,说话温雅,讲究技巧;20.要处世正直,是非难判断时,对神发誓。
松赞干布在位时期还颁布了《六大法典》,包括:(1)“六六大计法”;(2)度量衡标准法;(3)伦常道德法;(4)敬强扶弱法;(5)判决势力者法;(6)内库家法。内容涉及行政区域的划分、军事行动的管理制度、大臣等官员的地位和义务、农牧管理方面的法律、以道德伦理为基础的法律规范、度量衡标准、君王在审判中的权威等。松赞干布去世后,后世赞普还颁布了《以万当十万之法》、《王朝准则之法》、《纯正大世俗十六条及戒十恶法》及《三法》等。所谓《三法》是指《狩猎伤人赔偿律》、《纵犬伤人赔偿律》和《盗窃追偿律》。《三法》共有两万余字,内容相当丰富,是吐蕃时期重要的律例文献。《三法》已脱离格言形式的教义和道德规范,将吐蕃狩猎、游牧生产方式下形成的法律关系以规范性的律令加以调整,其中涉及禁止性、义务责任性、许可性和引导性的规范内容有所增加。[2]
所谓《三典》是元、明、清时期西藏地方政府组织有关人员调查整理的三部影响较大的法典,即《十五法典》、《十六法典》和《十三法典》。[3]
元朝后期帕摩主巴政权曾制定《法律十五条》,原文虽已亡佚,但从此后藏巴汗政权的《十六法典》中可见其原貌。目前的史料尚无《十五法典》详细内容的记载,但《续藏史鉴》和《西藏王臣记》等史料记载了其篇名。即1.英雄猛虎律;2.懦夫狐狸律;3.地方官吏律;4.听讼是非律;5.逮解法庭律;6.重罪肉刑律;7.警告罚锾律;8.使者脚钱律;9.杀人命价律;10.伤人抵罪律;11.狡诳洗心律;12.盗窃追偿律;13.亲属离异律;14.奸淫罚锾律;15.半夜前后律。
明朝建立以后,在藏区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继续对各教派的大喇嘛加以怀柔,以期发挥蕃僧“化道愚顽、阴助王化”的作用,同时设置藏族地方统治机构,建立土司制度,加强对藏区的管辖;通过土官朝贡和赏赐制度强化了与藏区僧俗贵族的联系;继续实行唐以来的“茶马互市”,实现汉藏两地资源互补。明朝末年,帕摩主巴政权被推翻,彭措南杰建立了第悉藏巴地方政权,又称噶玛政权。社会变革带来社会关系的变化,使法制的变化不可避免。因此,噶玛丹迥旺布下令由地方长官贝色利用藏族传统法律资源、伦理道德资源、宗教禁忌,并直接参照吐蕃王朝法律和《十五典》,制定了《十六法典》。在立法体例上,《十六法典》直接继承了《十五法典》的传统体例,甚至许多律名都是从《十五法典》中直接照搬而来。清代为西藏地区制定的《十三法典》又是以《十五法典》和《十六法典》为蓝本,有一脉相承的关系。[4]《十六法典》与《十五法典》的主要区别是:在《十五法典》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法条“异族边区律”。该法对生活在西藏周边地区各民族的杀人赔偿、牲畜伤人、截获分配、狩猎规则、劫掠习俗、盗窃追赔、审判程序等行为和活动制定相关的法律予以规范和调整。[5]明朝后期藏巴汗政权制定的《十六法典》,是藏族法制史上内容最为丰富,体系最为完整的法律,是清代藏族地方政权制定《十三法典》的蓝本。[6]
清朝前期,康熙帝平定西藏,结束了蒙古准噶尔部的统治,巩固了西南边疆,这时藏区法制的任务主要是惩办杀人、放火、抢劫、偷盗,处理男女通奸和借贷纠纷案件,维持社会秩序。与此相适应,西藏地方制定了包括刑事、民事法律规范在内的《十三法典》。《十三法典》是在集西藏政教权力于一身的五世达赖喇嘛的授命下完成的,他命令第巴索南饶丹借鉴吐蕃、元代及帕摩主巴等时期立法的经验制定法典。索南饶丹按照五世达赖喇嘛所规定的立法宗旨,将藏巴第悉噶玛丹迥旺布时期制定的《十六法典》进行了综合调整,删去第1条英雄猛虎律、第2条懦夫狐狸律和第16条异族边区律,并对前言和个别条目作了修订、补充,将一些名词重新作了解释,最后编成《十三法典》。《十三法典》与《十六法典》比较,尽管在内容上大同小异,但在条目的筛选、排列和解释等方面有所不同,这反映了清代藏区统治者对法律条目的具体认识和理解。《十三法典》对每个法律条目的解释更加详实、完备,所依据的资料丰富、可靠。不仅体现了统治阶级法律的观点,而且反映了当时藏族社会的状况、价值观念、人伦关系、生产关系等。[7]
二、藏族成文立法的特点
藏族成文立法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藏族是一个虔诚信仰宗教的民族,神在藏族群众心目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宗教对藏族法制的渗透深广,从原始宗教中衍生出来的神明裁判,宗教禁忌与法律条款的相互交织,这诸多的渗透现象,一直伴随着藏族法律文化的发展而长期存在着。在藏族历史上,藏族曾一度信奉本土宗教苯教。随着佛教传入藏区以后,佛教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使得苯教在与佛教激烈斗争后日渐式微。现在佛教几乎成为藏族全民信仰的宗教。
藏族法律规范将人际关系连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宗教三类关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规范设定中,强调法与世俗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禁忌的结合。吐蕃的《法律二十条》中的“争斗者罚款,杀人者以大小论抵”,“奸通者,断其股体,流放异方”等法律条文,与“要报父母恩,孝敬侍养”,“要尊敬长辈,以德报德”等格言式的道德规范紧密结合在一起。它的执行,不但要靠法律措施,而且要靠舆论力量。在藏区宗教盛行的情况下,大量道德规范也是佛教规范,两者之间相互吸收,融为一体。[8]
自吐蕃王朝兴盛开始,藏族的历史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藏传佛教的创立和广泛传播,佛教的影响更是与藏区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可以说,佛教的影响已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藏区社会制度中重要内容的法律法规,亦受到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不少法律条文还是直接来自佛教教义。
如松赞干布命令大臣吞米桑布札、噶尔东赞域松等大臣制定的《法律二十条》,就是依据佛教“十善”的精神制定的。这20条法律,前4条对于杀、盗、淫、谎的处罚非常严厉,这把佛教最禁戒的有关内容(佛教中对于杀、盗、淫、谎及饮酒特别加以禁止,称为“五戒”)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公布,意在止人为恶,这是宗教教义法律条文化最明显的例证。后16条,也是依据佛教“十善”的精神制定的,作为公众遵守的法规和道德的标准,意在引人向善。由于这20条法律的内容都是从佛教基本思想“十善”的精神中孕育出来的,因此,后世常称该20条法律为“十善法律”。此后,吐蕃王朝的统治者及后世藏区各地政权的执政者在制定法律和确认当地的习惯法时,都将“法不悖教”和遵从佛教教义作为立法的一项首要原则。特别是后世藏传佛教在藏区确立了绝对统治地位,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体制后,佛教教义及其基本思想在藏区法律法规中的影响进一步加大了。[9]
(二)诸法合体
古代世界各国的法律大多是刑民不分、诸法合体的,古代中原王朝的法律是这样,藏族的成文立法也是这样。吐蕃时期的法律规范表现在诸法合体的各种法律中,往往在同一部法律中,既包括民法规范,又包括刑法规范;既包括实体法规范,又包括程序法规范,而未形成一部单一的法典。[10]吐蕃时期的法是一种混合法,公法、私法和教法合一,成文法与不成文法并行不悖,它同习惯、禁忌、道德等相融,在有些方面很难区分。虽然佛家的行为准则已经成为吐蕃君臣老百姓共同遵守的准则,但同时部落习惯法仍起着重要作用。不成文的习惯法与成文法并行不悖,法律中保留了某些原始社会的残余习惯。[11]
例如,《狩猎伤人赔偿律》规定:“……放箭人发誓并非因挟仇有意伤害,可由担保人(即证人)十二人连同本人十三人共同起誓。查明实情,受害人中箭身亡,赔偿命价一百五十两,给受害人和告发人平分。若无告发人,一百五十两全归受害人。受害人中箭未死,赔偿医药、食物费三十两,归受害人和告发人平分。……无论是给死者之命价银还是给伤者医药、食品银,不管是谁,缺一两将处以死刑。……”[12]从这段规定可以看出,其中有诉讼方面的规定:“必须有十二个证人及其本人共十三人,共同起誓作证”等;也有民事损害赔偿的规定:“受害人中箭身亡,赔偿命价一百五十两,给受害人和告发人平分”等;还有刑事方面的规定:“无论是给死者之命价银还是给伤者之医药、食品银,缺一两处以死刑。”《盗窃追赔律》、《纵犬伤人赔偿律》等法律也有相类似的规定。这种法律体例是吐蕃时期法律体系不完善,立法经验尚不成熟的反映。清朝藏区立法也是诸法合体、民刑合璧的。如《番例条款》中,既有处理误杀人、斗殴伤人的规范,又有无力纳罚立誓、搜查贼赃的规范。近代藏族部落法更是如此,各种法律混合在一起,没有明显的分化。[13]
吐蕃王朝当时采取诸法合体的形式,既有刑事方面的规范,又有民事方面的规范;既有实体法的内容,又有程序法的内容;外部结构上虽采取唐朝的律令形式,但内容中很多规范是从部落习惯发展而来,又具有很强的原始习惯法的特征。
(三)惩罚上的等级性
传统藏族法制具有等级性,不同身份、社会地位的人在接受刑事惩罚上有所不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但在古代社会,很多民族和国家的法律明文规定阶级不平等。古印度的法律把人分为四等,不同等级的人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中国古代中原地区也存在身份的划分和等级制度。汉族历史上曾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说法。自《魏律》规定了“八议”制度以后,中原历朝法律都实行此制度。凡属八议特权优待范围以内的贵族、官僚,除犯谋反、谋人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十恶大罪外,流罪以下减等。死罪则根据其身份和犯罪情节,由官吏集议减罪,奏请皇帝裁定。实行“八议”制度,就使得封建贵族、官僚地主更全面地获得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而下层人民的权利毫无保障,只要稍微侵犯封建地主的特权,都会受到严惩。
传统藏族社会,有着森严的社会等级和地位。各等级之间界线分明,不能逾越。这种等级制度,反映在法律方面,就是要承认等级差别,严格区分贵贱,捍卫等级制度。藏区法律和内地法律一样,按等级论罪处罚,不同等级的人在法律上有不同的待遇,犯了罪也有不同的处罚,法律的阶级性非常明显。按照《十六法典》的规定,人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中又分为上、中、下三级。不同等级的人有着不同的命价,法律不仅按等级规定命价,而且按等级来量刑。在杀人赔偿命价的规定中,人有等级之分,因而命价也有多寡之别。凡上等上级的人,如王子、大活佛等,其命价金与尸体等重;下等下级的人如工人、流浪者,其命价如草绳一根。
对于农奴、奴隶和下等人犯上的行为,法律规定严惩,而对于上等人犯下等人的行为,按规定处罚相对较轻,甚至可免除刑事责任。在伤人赔偿的法律中规定,凡仆人反抗主人而使主人受重伤的,应砍掉仆人的手或脚;如主人打伤仆人,仅延医治疗,且不赔偿损失。在偷盗赔偿的法律中规定,凡盗窃活佛的财物,要赔原物的80倍;盗窃官员的财物,要赔原物的5倍;偷窃一般人的财物,要赔原物的4倍;而偷盗穷人的东西,则只赔原物即可。盗窃活佛和部落头目的财物,在赔偿的同时,往往还被判处肉刑,或鞭笞,或断手、割鼻。[14]
清朝藏区的立法也规定按等级论罪、判刑,死刑一般是判处小头目和平民的,若是大头目,即使犯抢劫罪也可以不判死刑。但是,自1733年(雍正十一年)以后,藏区法律虽在身体刑、生命刑方面执行原来的规定,如《番例条款》规定:头目抢劫,罚犏牛了事;平民抢劫,不分首从皆斩。可是在财产刑方面,却作出了相反的规定。该条款规定在犯同一种罪行的情况下,对头目的处罚不但不比平民轻,而且还比平民重;对大头目的处罚不但不比小头目轻,而且还比小头目重。藏区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从清朝统治的实际来考虑的。因为在游牧部落中,土官品级越高,财产越多;平民地位越低,财产越少。如果把平民和土官同等看待,罚以同等数量的牲畜,那判决就会执行困难或根本不能执行,法律就无法维护其严肃性了。[15]
藏族有着独具特色的法律文化传统和上千年成文立法的历史,藏族传统立法一直延续到1959年民主改革时期。今天,虽然形式上的藏族传统法制已经不存在,但传统的法制观念仍然在藏族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力。如藏族古代法典确立的命价制度,在今天的藏区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赔命价现象在藏区重新出现,这种由古代流传下来的以罚代刑观念,常常左右着藏族群众的思想和行为,使本来具有科学性、公正性的国家统一法律难以深入贯彻执行。因此,应加强对藏族传统法制的梳理和研究,对传统藏族法律文化遗产的优秀部分进行批判地继承,使藏区传统法制与国家法制有机对接,从而促进藏区社会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稳定。
[1] 彭宇文.关于藏族古代法律及法律文化的若干思考——借鉴梅因〈古代法〉进行的研究[J] .法学评论,2004,(2).
[2] [7] [10] [13] [15] 徐晓光.藏族法制史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5-16.186.366.367.374-375.
[3] 杨士宏.藏族传统法律文化研究[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83.
[4] 李占荣.历史上藏族社会的经济法律[EB/OL] .http://www.law-lib.com.
[5] [11] 甘措.藏族法律文化研究[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118.67-68.
[6] 转引自黄奋生.藏族史略[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198.
[8] 陈光国,徐晓光.历史上的藏传佛教与藏族法律[J] .攀登,1992,(7).
[9] [14] 洲塔.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M] .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402-404.427.
[12] 吐蕃律例文献[M] .转引自徐晓光.藏族法制史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66-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