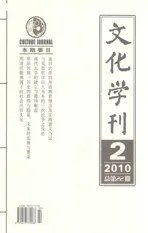文明形式论
2010-03-21吴秋林
吴秋林
(贵州民族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文明是人类的或者说是一个文化体的自然能力和文化能力,以及这两种能力所创造的成果的总的评价和表述。但这里也有一个标志性的表述,即文化力量要在这总的力量中形成一定量的比例后,这样的“能力”才能称为“文明”。一般而言,完全以身体的力量所获得的能力,是生物性的能力,这不是文明,在人类使用某种外在力量方式来延伸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人类的文明就诞生了。比如说使用了工具,进而由于工具的形式不会随物质工具的磨灭而消失,人能够从中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样,人类的文明力量就呈现为几何级数的放大,人类的文明历史开始了。
但是,在人类思考自己的文明的时候,文明也有自己的外在形式,也会在不同的自然能力和文化能力,以及影响这些自然能力和文化能力的多种因素中,形成不同形式的文明。比如说在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两种文明形式——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文明形式会在一定的环境中既定,但形成后的文明形式会成为一种文化的标志,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来影响文化的运行和发展。这很重要,许多文化运行中的令人费解的文化事象,实际就与文明形式直接关联,但我们对于文明的成果往往津津乐道,对于文明形式和独立的文明形式的力量,却知之甚少,这就是我们今天论述文明形式的意义。
一、形式和文明形式
形式最初的呈现是自然法则的力量所致,即每一种可见和不可见的物质存在,自然和宇宙都会给定它一个存在的形式,这个存在只受自然和宇宙力量的限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形式,它是人类所谓文明形式的原始动能。没有这种原始动能的存在,我们的文明形式的发生和存在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于形式的认识,它既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从一般意义上的形式来说,它可以概括所有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凡存在的,都可以说是由形式来标定的。没有形式,我们不可能“看到”内容,没有形式,我们也不能表述内容。我们在“拿起”存在的时候,以为只是“拿起”了内容,得到了内容,但殊不知你也“拿起”了形式。但我们并不知道为何?不知道形式的意义。
形式是随着存在而普遍存在的,它贯穿了我们所有存在的空间和时间,不管是物质的存在还是精神的存在。
形式是重要的,谁最早认识了形式的意义,谁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人类就获得了这个先机。我们今天的人类文明历史有这样的认识,说是人类在工具的制造中“发现”了自己的存在,这种存在就是“自意识”的存在,由于“自意识”的发现,人类才逐步展开了自己的文明历史。这个“自意识”中的发现是什么?就是形式!人类在按照自然法则创造了一件符合于在地球物理环境中使用的工具,延伸了自己的物性能力。在这件工具被自然地使用磨灭以后,人类会自然地寻找同样的物质材料来做一个同样的工具,以延续对这个工具的使用,这样,这个工具的样子(也就是形式)被重复,也就是形式被保留下来了,在当这个工具的创始者自然死亡后,他(她)所创造的工具的样子又被他(她)的后代或者说群体继续延续下来。到这里,这种形式的应用并不重要,而是人们发现,死去的人在他(她)所创造的工具中有一种形式的存在。在这里,人们才意识到,“我”可以在我的工具中存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就是一种形式的存在。
在最初的工具制造中,自然法则的选择是多种多样的,你可以选择这样,他可以选择那样,即最初的人类可以在多种多样的选择中实现自己“自意识”的发现。这样,人类的“自意识”发现就是多点的,即有数个,甚至数百个这样的文化原点出现,它也就预示着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表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是从其文化的原点上开始的。这正好证实了文化发生学派的观点,因为文化的相似性可以来源于自然形式的相似性,来源于“自意识”发现的相似性。
我们在前面说过,谁发现了形式,谁就取得了文明发展的先机。先机是什么?就是唯一的机会,文明的发展中永远只有一个一。这种文化先机是我们人类文明的一种基本属性,在我们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内部,这种表现比比皆是。谁第一个解读了这个世界,谁就取得了这一次的先机。我们今天对此有许多类似的表述,比如说“话语权”就是最接近于此的东西。这样的“根”也就在最初的形式发现。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到,形式在人类文化的发生中的重要性,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说的形式,在“自意识”没有被发现前是自然法则的形式,而在之后,就是人类文化的形式意义了。可以说,我们在发现“自意识”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了形式。
人类的文化就这样在无数的形式的诞生和发现中走过来!人类在文化中也非常重视形式的意义,除了在物质的世界中寻找适合我们人性的物质形式,也在形式中建构一种非物质的事物,并以此来满足我们非物质的一系列需求,最后把它们发展为一种总称为精神的事物,来与物质世界对称。实际上,这种所谓精神的最终极的本质就是形式——一系列的形式!这样,我们的人类文化才可以成为文明,不同形式感的文化,也就称为不同的文明。今天,我们人类在思考这些文明的时候,给予了在历时性中存在的和共时性中存在的文明许多名称。大致地归纳如下:采集文明、狩猎文明(包括渔猎文明分支)、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包括不同自然和水利条件下的农耕形式,以及介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游耕文明”)、工业文明等等。这些文明都有一定的标志性的表述。采集文明是以采集自然中植物生长的可食用植物为主要生存资料,并从而建立起一定的文明形式和能力及文明成果的文明;狩猎文明(包括渔猎文明分支)是一种大量借助工具的力量,从自然中获取以动物的肉、皮为主的生存资料,并从而建立起一定的文明形式和能力及文明成果的文明;游牧文明是在自然环境中放养以羊、牛、马为主的动物,以获取其奶、肉、毛、皮、畜力等为主的生存资料,并从而建立起一定的文明形式和能力及文明成果的文明;农耕文明(包括不同自然和水利条件下的农耕形式,以及介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游耕文明”)是在自然环境中,以土地上种植多种多样的粮食植物为主,辅助性饲养如鸡、猪、牛、羊、马等动物,从而获取生存资料,并建立起一定的文明形式和能力及文明成果的文明;在此,“游耕文明”是农耕文明在中国山区的一种特有表现,即用“刀耕火种”的形式,在山区的一定区域内,三五年一换的游动耕作。既具有游牧文明的移动性,又具有农耕文明的耕作方式和内容。工业文明是以工厂的形式,全面地获取自然中所有物质作为生产资料,全面地生产所有人类所需求的生存资料,并从而建立起一定的文明形式和能力及文明成果的文明。这种文明形式的主要特性有:标准化、商品化、全球化。
每一种文明都有特定的环境对应。采集文明——自然植物生长的环境;狩猎文明(包括渔猎文明分支)——有动物分布的自然环境(有鱼类分布的水环境);游牧文明——有适应大量牲畜生存的草地、草原;农耕文明——有适应于种植的土地;工业文明——有适应于商品生产的市场、交通、信息、人才、科技水平等等。
对于各种文明,可能在我们的文化中会有许多的认知和表述,我们在这里要表述只是它的形式意义,即我们在以上的对应中看到,每一种环境因素,自然造就一种文明形式,但反过来说,每一种文明形式,也会去寻找适合自己文明形式的环境。这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上有许多例子,如属于氐羌族群的彝族人,他们在南下之后,最优先寻找的生存环境是高山草原,因为他们的既定文明形式是游牧文明。在每一种文明中,最外在的是它的形式,并且一旦既定,就会成为一定程度上的永恒。
二、文明形式的力量
在自然法则的力量下得到的形式是自然和宇宙的形式,是形式的基础,但它不是我们所说的文明形式,文明形式一定是人类文化力量体现的过程中形成的形式,它自然要受到自然法则的影响和制约,但它体现的是人的力量和意识,以及意志、精神等等。
在以上的表述中我们知道,有一种文明就有一种文明形式,不管这种文明取得多大的文明成果,或者说没有取得什么有影响力的文明成果,它都有一种形式存在于这种文明中。石器时代有它一定成就标准,陶器时代有它一定的成就标准,……但是,不同的文化体在向这些文明迈进的时候,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完成它,来形成一定的有别于其他文化体的文明形式。
某一个文化共同体一旦在初始的状态中形成一种文明形式,不管是否取得有影响力的文明成就,其形式就会在其文化中起作用,并体现文明形式的力量。我们把这种形式的作用力分为三种:一是与物质生产有关的形式力量;二是与生活方式有关的形式力量;三是与精神观念有关的形式力量。
(一)与物质生产有关的形式力量
一种文明自然就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和工艺技巧,如果这种形式一直在原来产生这种文明形式的原地,我们看不出它的力量,但是,这种形式一旦出现移动,移动到另外一个与之不一样的自然环境中,其形式的力量就显现了。这方面,我们在民族学的田野调查中,看到过无数的例证。
在云南省、四川省、贵州省的彝族人,其文明形式是在其游牧文明中赋予的,在氐羌族群南下到达这三省时,最早的氐羌族群的先民并不以山地农耕文明的形式来选择居住区域,而是以游牧文明的形式来选择居住区域,即他们选择长草的地方来居住,并不是选择长庄稼的地方来居住,但在这三省地域中,长草的地方是好地方吗?虽然经过千年的变迁,大多数彝族人现在已经最终选择了农耕文明的形式,但其中来源于游牧文明的生产方式、工艺技巧方面的形式力量,至今随处可见。
布依族人是百越族群的后裔,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少数民族,他们的建筑文明形式起源于“树居”、或者说“鸟巢居”,即在潮湿的南方山区,居住的房屋一定要支撑离地,在半坡山要伸出吊脚,这种形式的建筑我们称为“干栏式”建筑,也俗称“吊脚楼”。这是自然环境所赋予的形式,但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当这些环境要素消失后,比如在很干燥的地带,布依族人也把其建筑建设成“干栏式”,第一层仍然不住人。吊脚是在山坡上的选择,但他们的建筑到了平地上也要在后屋垒起一个两米多高的土台,把前面脚“吊”起来。
仡佬族人是贵州最早的原住民,其先民是百濮族群的直接后裔。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仡佬族人有篾仡佬、打铁仡佬、花仡佬、红仡佬等称谓,这篾仡佬、打铁仡佬就是关乎某种生产工艺技巧的分属,也就是技巧形式成为这些族群的标志了。奇妙的是,我们今天还能在这些族群中看到这样的物质的形式力量。在这些族群中,几乎人人都是篾工艺形式的技师,人人都是打铁的匠人,今天的社会已经基本不需要这样的生存技能了,但这些物质文明的形式力量仍然在起作用。
在广大的民间,传统工艺中所织的土布,布的功能性差异不大,但不同文明文化来源的织布机却深受其形式力量的左右。在民间,一般使用的是所谓“黄道婆”式样的平机,但我们还可以看到多种多样的来源于不同形式的土织机,其中尤其以彝族人的织机最具有自己的形式感,完全不同于汉族的“黄道婆”式织机。
(二)与生活方式有关的形式力量
任何一种生产都是为了人的生存,生存也有一定形式,比如说各种食物就是生存最初始的事物,但就每一种食物而言,其功能性在科学上都是一致的,但如何“进食”这些食物,就表现了形式的力量。在每一种文明里面,都大致包含了这种形式。
人的生存有几项最为基本的要素,祖先们归纳为“衣、食、住、行”,其实还有性。这几大项,每个文明体中都会有自己的关于这方面的形式因素,其中的成员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文明体中提供的形式来“衣、食、住、行”。在这方面,我们有太多的例子。在中国的苗族中,有几百种不同的“衣的形式”,即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有苗族人穿着几百种不同形式的衣服。我们称这样的“衣的形式”为服饰文化,也有许多人对它进行研究,但至今没有一个人说清楚中国的苗族到底有多少种“衣的形式”,更不要说弄清楚它的文化性质了。有的衣服既不方便劳动,也不方便生活,甚至于与气候变化相矛盾,但人们,尤其是苗族人却一直坚守着自己“衣的形式”。为什么?我们在下文要论述之。在食、住、行方面也有这样的表现,但对于形式的坚守性就大不如“衣”了。
性的功能在文明体中一般只承认其人口生产的一面,不太承认生物性娱悦的一面,并且用“礼仪”的形式来限制其生物性娱悦的一面。在这里,如果这个文明体对生物性娱悦的限制放松一些,那这个文明体中的性关系就自由和开放一些,否则就相反。有时候,人们还会利用节日,或者说其他特定的时间来放松这样的限制,那在这种时间里的性关系也会自由和开放一些。这就是中国西北的“花儿”,中国南方一些民族的“坐坡”、“花房”,西方一些国家的狂欢节等事物出现的根本原因。
我们前面说“与生活方式有关的形式力量主要体现在生产方式的形式力量与精神观念形式力量之间的地方”,是深有所指的,它表明,与生活方式有关的形式力量的运动处在一个文明体中间的状态中,它既与物质性质的事物联系紧密,也能够上升到精神乃至于观念的层面上去,并且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中间状态的形式力量,有时候就是物质形式力量的体现,是主导我们人的物质性的形式力量,但这个中间状态的形式力量还会在其间出现你意想不到的转化。
出现这种转化的原因我以为有二:一是在人的生存述求上,不仅仅是物性的生存,还有精神生存、观念生存的一面,人的文化的肇始就是形式观念的肇始,“自意识”意识到的是什么?就是形式,并从形式走向了精神和观念。也就是说,处于这一状态的人本身就具有二重性。二是人的精神的观念的事物有多种形式和结构,有的精神的观念的分类,其内容上是观念的,形式上也是观念的,比如说哲学的、伦理的,但有的精神观念的分类就一定要有物质的形式来体现它,比如艺术。而这种物质的形式基本上就处于中间的状态中,艺术的精神观念要寻找形式,就必然在这一层面来寻找。
与生活方式有关的形式力量中的物性力量我们不用多说,基本上都好理解,但在这样的形式力量中,一般的物质性形式力量是如何上升到观念和精神层面的?我们试举两例:
第一例为中国苗族的服饰。在功能性上它与其他的服饰是一致的,保暖、体现审美等,这种一般性的服饰中都有的功能性述求它也有,但苗族的服饰中还有一些述求是一般的服饰根本没有的,比如记录文化、作为族群标志、意志体现等等。后者就是从形式力量上走进了观念和精神领域了。作为族群标志的苗族服饰是一个苗族支系外在的标志,看到这样的服饰,就看到了自己的支系族群,看到了同胞,看到亲缘和婚姻集团的成员了。在有外部力量的打击和压迫的时候,这种苗族的服饰还是一种意志的体现,这就完全是一个关于族群的精神和观念的事物了。这样的“衣”已经不是“衣”,而是“旗帜”了。第二个例子是回族人的食物禁忌。这也是与生活方式有关的形式力量上升为精神观念层面的最有力的例证之一。这样的例证中的事物,都不可以用一般意义上的物质功能性意义来解释它们。
(三)与精神观念有关的形式力量
从我们文化的基本性质和根源上讲,我们就是“意识人”,我们不在意识中意识到自己的存在,那我们作为“人”也就不存在。这好像是“意志论”哲学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但我不这样认为,这不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问题。“自意识”的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实,在“意识人”这一点上,没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我们人自身的状态表述。
这样的论述表明,我们人的生存中,除了物质性的生存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存,这就是“意识人”的生存,精神观念的生存,并且我们人一般都把它视为人的终极意义。
今天,人类给予了这样的生存太多的形式,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政治的、主义的……每一个分属中都有大量的划分,每一个划分中又有许多细小的划分,并且这样的划分可以无限,而且每一个划分中都有人坚守。这种坚守有时候是和平,有时候是战争。这里面是一个个的宇宙,但实际上可能什么也没有,只是从某一个文明中的某一点而来的一种精神和观念的形式。但就是这种形式的力量让人一点也不能小视它。我们可能谁也没有能力改变它,但我们可以从与精神观念有关的形式力量中来认知它。
在我们人于“自意识”中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后,我们一面在用工具开拓我们的物质世界,也在用我们的意识建立我们的精神和观念的世界。这种状态是何时出现的我们说不清楚,但在意识中建立精神和观念的世界,我们今天却可以从人类的文明历史中看到它的基本模式。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来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这是《圣经》上的开篇文字,它说明了这个世界的来源,也说明了人的来源。这只是基督教世界的解释,只是一个文明体中的解释。在世界上的其他文明体中,也有大量这样的解释,我们所说的世界和人类的起源神话,就是这样的解释。这几乎是人类的一个普遍性的行为,是人类在所谓的“蒙昧阶段”必须要经历的过程。为什么呢?人类在这个时候要急于建立什么?这就是要急于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化原点,只有构建这两样东西,人类的意识世界才有自己的文化原点。有了文化原点,我们才有可能解释世界的一切。有了这种建构,只是人类意识世界的内容,它还要有一定的形式来确立它,这就是“信仰”的出现。我们在世界上有千奇百怪的世界起源和人类起源的解说,但“信仰”的形式是不变的。这样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唯物主义的,但你不得不承认它是精神和观念的。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一个文明体有了这样的解释,建立了原点之后,其文明体中的文化形式就要受这种解释的根本性影响。
我们在物质的生产方式和有一半是物质性表现的生活方式上,是可以接受其他信仰形式力量的影响,我们可以在这些方面有限度地接受这种改变,但在信仰上,你要保持你的生存基础,其改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你的先民创造了这样一种解释,就为你创造了一种信仰形式,并直接导致你的意识性生存,决定你的生存形式。
还是来源于氐羌族群的中国彝族人,他们的先民给予了他们一种世界的解释,给予了他们一种信仰和信仰形式——祖灵信仰,即用一根竹筒,经过丧祭中的一系列的仪式,把祖先的灵魂象征性地引入竹筒,成为其已经去世的祖先灵魂的居所和象征。这种灵魂形式是典型的“马背民族”的灵魂形式,但彝族人基本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定居并进入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状态后,这种灵魂形式的力量依旧存在,并且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丧葬等一系列文化的形式表现。
我们在前面说过,我们精神和观念的意识生存有许多的形式,大致有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政治的、主义的等等。在这些个大类中,前三种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内容,其最为极致的部分会有一种称为信仰的东西存在,在后两种大类中,也会部分存在这样的东西。宗教中有信仰是不言而喻的,这是它的核心,这个核心主要是形式的,但有时候它会给你一些象征性的实体。艺术中有信仰,它也有在宗教中实现的精神依托的效用,也能在其追寻中实现自己精神的超越。但这里给你的就完全是形式的力量了。追寻这种力量最为极致的就是表现“形式主义”(如康定斯基),就是直接在艺术和哲学上把形式上升到一种精神和意识的表现高度。人们说哲学是一门“世界观的学问”,希望用人的理性认识的方式和能力来替代宗教中对于世界起源和人类起源的神话,这门学问是世界文化的“发动机”,尤其是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动机,但是它仍然绕不开文化原点的问题,这又落到信仰之上了。信仰是一种形式,是人的一种根本意义,没有信仰我们发动这个世界的运转来干什么?而信仰不就是一种形式吗?
而这些基本上都是来自于那个文化原点的事物,都会与人类最初的文化建构有关,而这个原点从来都不是一个“实体”性质的东西,而是一种形式。这就如我们把时间中的某一点称为“纪元”一样,这个纪元在时间的基本性质上只是宇宙的任意一点,对于宇宙一点意义也没有,而对于人类或者说人类的某些个群体,就意义重大,因为这是它的原点,或者说原点之一。
这种对于原点的追根溯源,最终的就是“虚空”,在“微精神分析”学说中,他们说到一个观点,认为心理的最大能量在于一种称为“虚空能动”的力量,这是心理学上的最大的最为原始的力量,比之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的力量更大。他们指的“虚空能动”的力量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原点的力量。
在这个文化原点的认知上,西方的神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很愚蠢的,在全球殖民主义时代,他们曾经寻找过神的全球性证据,特别是寻找过一神的证据,也就是说,文艺复兴时代,他们才开始他们的人文性质的理性认识,而这个过程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老子时代就已经完成了这种人文性质的理性认识。老子时代就坦率地承认,世界的起源是“无中生有”的,早就承认文化在观念和精神中的形式力量。这也许就是我们中国的神话传说不如西方发达的原因,因为我们早就越过了用神来创造天地和人间的时代。
三、中国的文明形式与华夏文化的构合
形式有无所不在的力量,文明的形式力量更是。当我们作为某一种文明形式所“笼罩”下的现代人,更是“躲”不开它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在说到中国的文明形式时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它与所有的文明自信的范式一样,都有国之中心的信念,但有一个事实却不能回避,即华夏文明的演化在历史上就是围绕着这个地理环境的中心和文化发生发展的中心进行的。
中国的华夏文明,其主体是农耕文明,是在理顺了与农耕关系的历法,理顺了水利的前提下,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域内发展起来的文明,它包容了很长的历时性内容和很宽大的共时性内容。在农耕的总的形式下,它又包含了许多区域性的具有独特个性的农耕支系性的形式。比如说北方以黄河流域地区为主的旱地农耕,南方以长江流域为主的水田农耕,其形式就是不一样。在这两大支系性农耕形式中,又有山地农耕与平原农耕的形式区别,也有与游牧文明形式交融的山地“游耕形式”等等。
对于农耕文明,可以说是中国最具有形式感的文明形式。在最初始的时候,人们耕种土地,也许就是散漫无序的,但江河水系、山峰沟壑会给人一种自然的次序,会自然地把人们汇集在一定的区域内,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组合。比如“八百里秦川”、“巴蜀之地”等等……这种自然的次序,慢慢地会生成一种有人文色彩的秩序。方圆九百亩的耕作分布,就是这样的事物,这在中国被称为“井田制”。这种有人文色彩的农耕形式,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这九百亩的四方块,周八块属于8户人家,每户种一百亩,而中心还有一百亩称为“公田”,在每年的春季耕耘中,要求先种公田,而后私田,秋收亦然,这一百亩的“公田”所产属于“公产”。
这种农耕文明的形式存在,使中国古代诞生了一系列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事物:一是信仰;二是政治制度;三是乡村聚落的模式;四是“公”的观念和“集体”的理念。
(一)信仰
我们中国的信仰可能有许许多多的表现,但没有一样如从土地中诞生的信仰更具有本色。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系列的历时性存在中,对土地的信仰在土地的产出对整个文明体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时候,是最大的信仰,我们的古人把它称为“社”。这个“社”的最初就是代表方九百亩的疆域的石头,至今我们在贵州的某些民族的信仰文化中还能看到这样的“社”。这个“社”在春秋时是当时国家、地方、村落都必有的祭祀地方——社庙。这种社庙在春秋的文献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中有一则关于社鼠的故事就是讲社庙里的老鼠的。这种“社”在当时的农业国家中,与谷神一起被称为“社稷”,土地神和谷神是关乎于江山的,故又称为“江山社稷”,即有社稷就有江山,没有社稷就没有江山了。这是国家性质的信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对土地神和谷神的信仰,则是地地道道的农耕文明的本色信仰。
社神信仰在后来家、国一体化的文化演进中,逐渐被祖先信仰慢慢替代,各种级别的宗祠才成为中国农耕文明信仰中的主体,但对于土地的这种信仰,却在中国民间形成了一种“草根信仰”,遍布全国的乡村。这种遍布全国的情形在今天的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慢慢地龟缩到一些特定的区域里,成为村口路边的土地庙了。
在一般意义的信仰中,特别是发展为一种制度化的信仰中,他们在解说了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后,还要给予人们一个“彼岸”的描述。中国人没有这种虚拟的或然的描述,但有类似的这种精神性的事物,而且这个事物也带有浓厚的农耕文明的形式感,即“桃花源”。可见,农耕文明的形式在中国文化信仰上的影响力之大。
(二)政治制度
中国最初的政治制度的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农耕文明的形式,这在中国关于历史和制度的研究中有许多的文献,但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的研究资料却比较少。“井田制”好像是政治制度赋予农耕的一种形式,但是,这种形式一旦诞生,它也就作为农耕文明的基本耕作制度,在形式上影响到国家制度的形式了,即这时候的国家一级一级的制度都是在“井田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实,这种制度还在于它给予了中国人一个政治制度的初始状态,我们后来的国家制度,包括今天的国家制度也离不开这种形式的因素。
(三)乡村聚落的模式
中国是世界上乡村形式最为繁多的国家,关于村寨的名词我们可以数出无数,北方的村落和南方的村落千差万别,层出不穷……但有一点,它的形式的母体一定会在“方九百亩”的基本模式中。不管是聚族而居,还是宗亲血缘为系,或者说以某种编制单位……聚落一定是既定的形式。
(四)“公”的观念和“集体”的理念
在“井田制”的农耕文明形式中,它给予我们的影响在前几项内容中,可能会由于时间和环境的变化,会有很大程度上的变化,但“公”的观念和“集体”的理念,却是我们最难于变化的东西。这不是一种物质形式,或者说半物质形式的影响,而是纯粹形式的影响。这样的东西在我们的文明和精神中,是为历代的中国人和中国的文化基本认同的东西,也在后来的文化中被中国官方和民间使用了多种多样的形式,一遍又一遍地放大,是中国文化中关于“群”的基本形式。这是外国人最不明白中国人的地方,但这是中国人最为迷人的地方,汶川大地震中展示的中国文化中关于“群”的观念和理念就是一例。
这种可以在现代社会中被不断演化发展的文化之根,就存在于中国农耕文明的最初的形式中。在中国的华夏文明中,农耕文明是决定我们今天文化形式最为根本的文明形式。当然,在我们的华夏文明中,还包容了其他许多的文明和文明形式。
从这个角度讲,与中国的农耕文明发生最为密切关系的文明形式就是游牧文明形式。在中国的北方、东北方、西方、西北方、甚至于西南方的一些区域,历史上或者说现今仍然布满了以游牧形式生产和生活的文化群体。虽然在这些区域里,不同的文明形式带来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游牧区域内也已经具有大量的农耕文明形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两种文明形式早就找到了各自的共融点。
但是,这两种文明形式在中国的历史上却演绎了许多文明形式“决战”的故事。这两种文明形式在许多时候,始终处于一种冲突和矛盾之中,对于这样的斗争,我们可以说是草原游牧政治集团和土地农耕政治集团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冲突,这是根本的,但同时也是两种文明形式的冲突。从根本上来讲,土地农耕政治集团在长期发展中,会直接在土地上向游牧土地扩张,这应该是历史上的基本趋势,这样,就会与草原游牧政治集团发生直接的关于生存空间冲突,反之亦然,草原游牧政治集团也会从土地农耕政治集团那里争夺土地。
在中国,华夏文明实际上就是在游牧文明形式和农耕文明形式的不断的冲突中,一步一步地发展过来的。也就是说,虽然说华夏文明是以农耕文明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但它在这种冲突中也包容了游牧文明的诸多因素,中国的游牧文明也在这种冲突中丰富了自己。在中国古代,参与华夏文明构建的还不仅仅是北方的游牧文明,南方型的农耕文明也参与了这样的构建,但这样的构建是同类异形式的冲突,是强势文化针对弱势文化的影响。而与北方的游牧文明的冲突,是异形式文化的冲突。
在中国的华夏文明中,除了游牧文明形式的影响和南方型的农耕文明形式的影响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更为久远的狩猎文化的遗迹。这种遗迹的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在与北方的游牧文明形式的冲突中,受留存于其文明形式中的狩猎文化的影响而来;二是农耕文明形式中自身的狩猎文明遗迹的影响。还有,采集文明的遗迹也在我们的华夏文明中有所呈现,它也是我们的文明形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今,我们仍然在南方的少数民族中看到这样的文化遗迹。
中国的华夏文明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文明体,它以农耕文明为主体,建立了以农耕为基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体系,建立了基本的信仰体系、精神观念体系、哲学体系、艺术文化体系,以及政治制度体系和文化,并且在历史上包容了游牧文明、南方山地农耕文明、狩猎文明等异形式文明和异类型文明,并且在多种文明形式的冲突中,形成了兼收并蓄的文化机制,使我们的华夏文化不但有数千年不间断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在今天仍然具有在新的文明形式中自新的能力。
在经过几个世纪的中国人的努力,在大量吸收了西方现代文明形式力量的基础上,我们国家又完成了由农耕文明为主导形式的华夏文明向以科学文明为主导形式的华夏文明的蜕变。同时,我们的华夏文明中,基本的信仰体系、精神观念体系、哲学体系、艺术文化体系基本未变,但包容了更多的东西,使自己变得更为宏大和丰富;以农耕为基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农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呈现了此方面的文化多样性。在政治制度体系和文化上保持了许多根性文化的东西,也包容了更多属于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