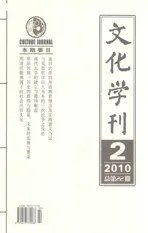吴宓的“一多”思想渊源探析——以《文学与人生》为例
2010-03-21郭英杰赵
郭英杰赵 青
(1.陕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2.西安财经学院公外部,陕西 西安 710061)
一、“一多”问题的提出
吴宓(1894年—1978年)“是我国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诗人、学者、教育家、翻译家和外国文学家,中国比较文学创始人,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1]1947 年 8 月,他在《哲学评论》发表的《一多总表》又奠定了他哲学家的地位。[2《]一多总表》有这样一些经典论述:
宇宙人生,事事物物,皆有两方面:曰一,曰多。
(一)知有一且有多,知一多之关系(是一是二,一分亦合),是曰真知……(二)知一比多更为重要,更有价值,我必当处处为一尽力,重一而轻多,是曰正行……(三)深信宇宙间之精神价值永存长久,不销不减,仅其所表露之形色,所寄托之事物,隐现生灭,变化不息,是为正信。[3]
汤一介认为,吴宓在论述中已明显涉及到中外哲学中一个重要问题——“一多”问题,“《一多总表》不仅从总体上论述了‘一多’关系,而且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文艺学的诸多方面概述了‘一多’问题”。[4]该评述一语中的。众所周知,“一多”是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它指诸多事物的两个方面、两个因素或两种关系,强调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整体与部分、抽象与具体、内在和外化、本体与现象等的对立和统一。世界上纷繁复杂的各种现象,从本质上都可以纳入到对“一”与“多”的考察和研究。吴宓所讲的“宇宙人生,事事物物,皆有两方面:曰一,曰多。”是试图告诉人们,万事万物皆有两面性:有“一”,有“多”。“一”是事物抽象的概括,“多”是事物具体的表现,“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一”、“多”对立,相辅相成。“一”、“多”作为事物的“两面”,互为补充,不可分割。吴宓认为“事事物物”均从“一”、“多”中来,又到“一”、“多”中去。除了知道“一”、“多”关系获得“真知”外,还要“处处为一尽力,重一而轻多”以得“正行”;但是终极目标是“正信”,以使“宇宙间之精神价值永存长久”。从《一多总表》可以看出,吴宓特别强调“一”的价值和作用。他的这种始终如“一”的哲学精神体现在他做人、做事、做学问等各个方面。[5]
二、“一多”与《文学与人生》
吴宓的“一多”思想与《文学与人生》息息相关。《文学与人生》是吴宓系统阐述哲学理念的重要著作,是他思想和智慧的结晶。吴宓本人也把该书列为“哲学类”书籍。[6]虽然目前我们所见的版本只是一个讲义和提纲,但是细细品读,其宏伟博大的理论体系让人感叹折服,尤其是“一多”思想集中反映了“他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7]
《文学与人生》体现的不仅是吴宓对“文学与人生”现象学层面的探讨,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多”思想映射了他的文学观、道德观、史学观,体现了他对文学欣赏与艺术创作的真知灼见。然而,寻根问底,吴宓“一多”思想的渊源如何?
首先是儒家学说:吴宓家族有宣扬儒家思想的传统,因此他自幼受“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训诫,接受正统的儒学教育。吴宓曾撰文《我之人生观》论及此经历:“自吾有生有知以来,长读儒家之书,行事待人,亦常以儒家之规训自按。”[8]吴宓特别尊崇孔子,称孔子是“中国道德理想之所寓,人格标准之所托”。这在《孔子之价值及孔教之精义》一文中有精辟论述:“(孔子)常为吾国人之仪型师表,尊若神明。自天子以至庶人,立言行事,悉以遵依孔子,模仿孔子为职志。”[9]在阐释他的“一多”思想时,吴宓自觉把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纳入到自己的哲学体系,如“天下同归而殊途”、“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等等。在吴宓看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国粹精华为“一”;言传身教,现身说法为“多”。因此,在清华国学院教授《文学与人生》课程期间,他积极倡导学生诵读四书五经,学习中国传统哲学。
其次是希腊哲学:希腊哲学尤其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哲学对吴宓影响也很深远。吴宓曾说:“世之誉宓毁宓者,恒指宓为儒教孔子之徒……不知吴宓所资感发及奋斗之力量,实来自西方……宓看明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为西洋文化之二大源泉……宓曾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而吸收其中心精神。”[10]基于此,吴宓广泛涉猎希腊哲学,接受柏拉图“一”与“多”(the One and the Many)的哲学观念。但是,吴宓在吸收希腊哲学精华的同时,“择其善者而从之”,是有所保留的——“若论精神理想一方,吾自笃信天人定论、学道一贯之义,而后兼蓄并收,旁征博览,执中权衡,合覆分核……(然后)得其真理,撷其菁华,而为致用。”[11]所以,在《文学与人生》一书中,吴宓精辟地以“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与《政治学》”为专题探讨人的道德与德行、意志、情感、智慧之间的关系。[12]至于“哲学之进步与方向”,吴宓说,需本着“一多兼具”的思想“由情入道”才能“执两用中”,不是“多中之一”,也不是“多中之另一”。[13]
再次是基督教义:基督教和《圣经》的基本精神几百年来渗透在西方社会的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等各个方面;作为学习西方文化和哲学思想的东方人,吴宓对此深有体会和洞察。在吴宓看来,东方的中国孔子和西方的基督有共同的思想核心,那就是它们都是“主仁”的;宏观上讲,“耶稣基督”是支撑起世界文明大厦的四根文化砥柱之一,是构建人格大厦的精神支柱之一。[14]而且,《圣经》往往给人以哲学的启示——《圣经》“除了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还在行为方式方面引导人们真诚、笃信。[15]这对吴宓的“一多”思想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吴宓来说,西方基督教的精神是“一”,其影响是“多”;领会其基本精神实质是“一”,途径和方法是“多”。所以,在教授《文学与人生》课程时,吴宓要求学生研读Holy Bible;A.E.Zucker著之 Western Literature-Vol以及 Bible&Middle Ages、Paul E.More 著之 Christ of the New Testament等,这也符合吴宓所提倡的宜博采东西,并览古今,然后折中而归一的主张。[16]
第四是佛教经典:佛教对吴宓的影响由来已久。吴宓出生于陕西泾阳,唐宋年间即兴盛佛教,所以他自幼耳濡目染。在美国哈佛学习比较文学期间,吴宓与汤用彤、陈寅恪等学人朝夕相处,而汤、陈等人当时在梵文印度哲学及佛学系,师从哈佛著名教授Lanman,吴宓受他们的影响开始研读佛学。[17]吴宓常与陈寅恪谈佛学,认为“中国之佛,即西国之耶教,特浸渍普通,司空见惯,而人在其中者,乃不自觉尔”。[18]与俞大维“谈宗教之流派,及其精义”,认为“当复兴佛教,昌明佛学”以实行民族自救。[19]当“俞君讲授哲学史略毕后,即由锡予每晚为宓讲授印度哲学及佛教”。[20]……总之,佛学对吴宓“一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不容忽视的作用和影响,这与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不无关系。[21]所以,当吴宓推理论证“一多”思想时,会经常运用佛学知识。这在《文学与人生》的“人与宇宙之关系图”、“天人物三界”、“万物品级图”等章节均有反映。基于此,吴宓要求清华学生研读黎锦熙编之《佛教十宗概要》、《频迦精舍校刊大藏经》昃十卷等。
第五是新人文主义:吴宓认为人文主义不是宗教或自然主义,而是个人之修养与完善。这是吴宓师从白璧德(1865年—1933年)和穆尔(1864年—1938年),学习他们的新人文主义后的感悟和体会。吴宓深受这两位大学者的熏陶,曾有感触地说:“吾年来受学于巴师(白璧德教授),读西国名贤之书……方知中西古今,皆可一贯。”[22]“之(穆尔)‘Platonism’一书”,述人文主义之学说,“(使宓)获益至深”。[23]吴宓接受白氏提出的反对物对人的役使,追求健康和美好的精神理想的主张,回国后把《学衡》作为宣传和介绍新人文主义的后方阵地,把《大公报·文学副刊》作为实践人文主义学说的重型武器。[24]据后人研究,《学衡》杂志以及“学衡派”的背后都有白璧德的“影子”;以及此后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都与白璧德的思想有着极深的渊源。[25]吴宓“新人文主义学说”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多”的湍流中不能踌躇,“一”才是谋求真理的根本。这在《文学与人生》“公民教育与文学”中有具体阐述,吴宓以人文主义的本质为“一”,以文学的功用及表现为“多”,认为“和谐、均衡”的“一”与“文学之要理”的“多”并不矛盾。这于当今我国的公民教育和文学国民性教育无疑有借鉴意义。
第六是“原欲”说:“原欲”(Libido)最早是弗洛伊德(1856年—1939年)精神分析学的一个术语。弗氏认为人的“原欲”乃是一个本源,“这种本源是人体内的一种紧张状态,而它的目的便是消除这种紧张。在从本源到实现它的目的的过程中,本能在心理上变成能动的力量。因此,我们把它说成是一种向一定方向冲出的一定数量的力”。[26]关于原欲概念在《文学与人生》中的使用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一章,吴宓用来描述中世纪基督教的“三欲”(Three Lusts)。在吴宓看来,基督教里的感官欲是“肉”,对应弗洛伊德的“本我”;知识欲是“智力”,相当于“自我”;而权力欲是一种意志力,相当于超我,是一种“支配或统治的”欲望。吴宓对此的理解是,“三欲”是人的本能的滥用或过度放纵。吴宓发挥对“原欲”的认识,基于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的人格结构的分析,对Three Lusts有恰如其分的阐释。他以“原欲”为“一”,“原欲”的表现形式(本我、自我、超我)为“多”;并认为基督教中的“三欲”相当于浪漫主义的三种类型,也可参比孟子论人一生之“三戒”,即“色、斗、得”。[27]
第七是道教、伊斯兰教等:吴宓曾与陈寅恪、汤用彤谈论过道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现状和发展,认为“回、蒙、藏诸教”与“儒、道教”并行,呈“大度宽容……不事排挤”之势。[28]在救国与礼俗文化方面,吴宓认为道教、回教同其他宗教一样,乃“立国之精神”,不可小视。吴宓认识到道教与伊斯兰教的本质区别以及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认为它们在世界文明史上,“大有可研究者”。这与吴宓在《文学与人生》中所探讨的“统一与和谐”关系的论述不无关系,即“本体世界”(“一”)与“价值观念”(“多”)是对立而统一的。[29]吴宓在“论宗教”中提到,“一切人一切事皆可云具有宗教性”,具体表现为“内质”(“一”)和“外形”(“多”)两个方面。道教、伊斯兰教作为宗教的“外形”有其现实因素和道德因素,符合“从信仰到理解”、“从理解到信仰”的“信”、“知”转化。[30]
第八,其他:德国的康德哲学和法国的启蒙思想在《文学与人生》中也有涉及。在“自由意志与命运”的论述中,吴宓除了参阅苏格拉底的《恶魔》或《内在抑止》,还引用了康德的“应该”或“绝对必要”的理念;同时还借用法国哲学家贝立登关于驴的一个著名假设对此进行论证和说明。[31]此外,在叙述“文学与人生之关系”时,吴宓对卢梭的启蒙思想,尤其是对《忏悔录》的阐述和引证也符合“仁智合一”的“一多”思想,认为“文学≠历史”,“文学≠直接与真实的经验”。[32]
三、结论
“一多”思想是吴宓哲学观的重要内容;《文学与人生》是吴宓“一多”思想的集中体现。吴宓主张“仁智合一,情理兼到”,[33]这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阐述中有充分论证。吴宓将诗歌、哲学与小说视为三途一体,但是特别肯定“哲学主理”,这又是“一多”思想的直接体现。吴宓的“一多”思想是深邃的。纵观吴宓一生,正是“一多”思想影响其文学、人生及艺术创作;影响其做人、做事、做学问。
[1] 郭英杰.律人律己,心怀天下——吴宓诞辰110周年再读先生日记有感[A] .王文,蔡恒等.第四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C]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215-218.
[2] [4] 汤一介.读吴宓先生的《一多总表》[A] .王文,蔡恒等.第四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C]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117-122.
[3] 吴宓.一多总表[J] .哲学评论,1947,(10):6.
[5] 蔡恒.学习吴宓真诚精神,做人做事做学问[A] .王文,蔡恒等.第四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C]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
[6] [7] 吴学昭.〈文学与人生〉后记[A] .吴宓.文学与人生[M] .王岷源,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253-254.
[8] 吴宓.我之人生观[J] .学衡,1923,(4):16.
[9] 吴宓.孔子之价值及孔教之精义[N] .大公报,1927-09-22.
[10] [11] [15] [17] [18] [19] [20] [22] [23] [28] 吴宓.吴宓日记(1917-1924)[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8.
[12] [13] [18] [27] [29] [30] [31] [32] [33] 吴宓.文学与人生[M] .王岷源,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14] [16] 王泉根.孤独人文精神的智者——论吴宓与20世纪中国文化[A] .刘家全,蔡恒,石宪.第三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C]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6-29.
[21] [25] 徐葆耕.吴宓:会通派与解释学[A] .王文,蔡恒等.第四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C]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31-52.
[24] 刘淑玲.吴宓与〈大公报·文学副刊〉[A] .王文,蔡恒等.第四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C]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70-71.
[26]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M] .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2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