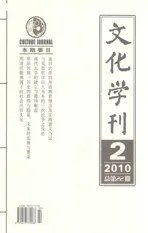现代大学的建立与德国崛起
2010-03-21朱崇开
朱崇开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010)
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德国与它现在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恰恰相反的。作为一个拥有360多个邦国、公爵、主教、侯爵、自治城市以及其他主权形式的集合体,德国境内关卡林立,赋税苛刻繁多,各大邦国相互攻伐,严重的内耗令它始终不能摆脱“贫穷、疲惫、四分五裂”[1]的状态。中世纪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虽拥有令人生畏的头衔,但它始终游离在主流国家的边缘,更多时候扮演的是欧洲中心事务的配角。
1806年,拿破仑军队的强势入侵对德国来说是一个代价沉重的历史转折点。一方面,德国军民伤亡惨重,并且要承担巨额赔款;另一方面,德国人不得不进行救亡图存式的改革。在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中,唯教育事业改革得到了社会各阶层最广泛的支持。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III.,1770年 -1840年)声称:“国家在物质方面的损失要用精神的力量去补偿。”[2]他在内阁的一次讨论中说:“正是由于贫穷,所以要办教育,我还从未听说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办穷了,办亡国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穷的最好手段。”国防大臣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Scharnhorst,1755 年—1813 年)将军说:“普鲁士要想在世界上取得军事和政治的领先地位,就必须首先在教育和科学上有世界领先的地位。”[3]
一、柏林大学成立
时任普鲁士内政部教育司司长的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 年—1835 年)对德国教育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因此被称为“德国教育之父”。在威廉·洪堡看来,办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只有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以及全世界的尊敬,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威廉·洪堡和普鲁士的一些有识之士一起,于1809年至1810年的短短15个月中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座现代化大学——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Friedrich Wilhelm Universitat zu Berlin)。
威廉·洪堡对德国大学进行了从形式到内涵的彻底改造。他反对国家干预教学和研究,认为“自由”是教育的“第一个和不可缺少的条件”。他说:“总的来说,国家决不应企望大学同政府眼前的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但应该相信,大学如果能够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够服务于政府眼前的任务,还将不断地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也会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础,并且也将更大地发挥人力和物力的作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前部署所能意料的。”[4]威廉·洪堡明确了科学的本质属性,强调在科学中永无权威可言。科学在当时的欧洲其他国家还处于卑微的地位,而在德国大学中却受到普遍的重视。威廉·洪堡认为大学是“知识传播之地与知识产生之地”,教学必须与研究相结合。科学研究职能成为洪堡式大学的最显著特征。威廉·洪堡的现代教育理论或许比其建立柏林大学的影响更加广泛、更加深远。
柏林大学作为研究型大学的翘楚从最初就把科学研究作为其主要目标,将授课效能作为次要的问题来考虑。按照著名数学家外尔(Hermann Weyl,1885年—1955年)的说法,德国大学做了4件紧密联系的事情:它提供了普适的科学教育,以最慎重、最庄严的形式将文化与智力遗产传给年轻一代;它为牧师、法官和律师、医生、中学教师和行政机构中较高级别的部门提供专业训练;它指导研究工作;它培养能够从事独立研究的人。后两项功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德国大学的教授首先把自己看成是一名科学研究者。[5]
德国现代大学颠覆了人们对传统大学作为知识储备与传播机构的印象,开启了大学作为社会中心研究机构的时代。这也是德国现代大学与英国、法国大学的重要区别之一。在英国和法国,大学基本上不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科学研究工作由大学以外的科学研究机构承担,即法国的皇家科学院和英国的皇家科学院。而在德国,科学研究的最高机构是大学,德国的大学是科研与学术水平的真正代表。在英国和法国,那些一流的头脑在大学之外,在德国则是在大学之内。因此,在德国,大学对国家生活施加了更为广泛和更加重要的影响。到19世纪中期,实际上所有德国科学家不是大学教师就是大学里的研究学者。[6]
柏林大学先是为普鲁士的大学,而后为几乎德国所有大学树立了榜样,德国大学逐渐在欧洲确立领先地位,并成为全世界公认的“学术机构的楷模”和科学研究中心。世界各国的学生要想真正了解一门学科,必须阅读德文教科书;科研人员要想了解科研的发展趋势,就必须阅读德文杂志。1820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改革家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1800年—1891年)在给哈佛大学校长柯克兰(John Thornton Kirkland,1770年—1840年)的信中写道:“没有任何政府能像普鲁士那样清楚如何创办大学和中学。”[7]当时美国的大学均以德国的大学为发展模式——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就是以柏林大学为蓝本建立起来的。
二、研讨班与实验室研究
为了引导学生从事科学研究,柏林大学在草创之初便大胆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研讨班(Seminar)。所谓研讨班,是围绕特定课题和研究方向在大学的院系里设立的研究组织。研讨班拥有独立的工作场所,图书馆或者实验室,并且能够获得相应的经费支持。研讨班由一个教授和至少一个编外教授领导,进行特定方向的研究。研讨班的存在具有双重意义:首先,通过参与研究活动,学生能够学习研究方法,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让不同年级和专业的学生参与进来,教师能够得到多方面的帮助。[8]威廉·洪堡将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思想渗透到研讨班之中,使研讨班具备了民主性、研究性和学术性的独特品质。在研讨班中,老师们基于最新的资料,在较高层次上教会学生研究所需要的技能。研究不再只是私人的事情,而成为老师与学生所组成的共同体的事情。老师指导学生的工作,以一种对他们无论今后从事研究还是从事实际工作都有益的方式组织起来,为学生的未来做好准备。研究活动越来越接近职业训练,而非通识教育。因此,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传统慢慢形成了,而这一传统正是德国现代研究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有学者认为,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模式是促使德国这个后进国家迅速走上先进的重要原因之一。
德国现代大学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将实验室与教学、科研相结合。现在成为大学里不可或缺的实验室研究,在19世纪20年代之前还处于一种卑下的地位。它被认为是专门为药剂师今后的职业培训所设计的,并不适合在大学里讲授。当时教师们进行实验室研究都是不公开的。1826年,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1803年—1873年)在吉森大学建立了德国首个现代化实验室,他一改先前只讲授教材的做法,而是在一个专门的教学实验室里,让所有的学生都亲自参加实验。这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大大激发了青年学生的科研热情,他们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过的空前规模和热情,夜以继日地进行实验研究。吉森化学实验室一跃成为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一流实验室。李比希让学生在实验室中从系统训练逐步转入独立研究的教学体制,这为后来的一系列实验教学做出了榜样。一些新兴学科,如生理学、实验生理学能在德国兴起,与此有极大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化学实验室与工业需求联系起来。李比希把科学原理应用到生产活动中,促使有机化学向全新的农业化学和药物化学的迅猛发展。
当时,德意志各邦的教育部长为了提高自己邦的学术声誉,总是愿意出巨资聘请著名的科学家来任教。这些科学家也就趁机提出必须在大学建实验室,开展自然科学研究的要求。大学实验室教学研究很快就在德国得到推广。结果,大约从19世纪中期开始,某些德国大学的实验室变成了研究中心,有时实际上是国际科学共同体的各个领域的活动中心。正如英国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SirWilliam Cecil Dampier,1867 年 -1952 年)所说,从1826年吉森实验室的建立到1914年,学术研究的有组织工作在德国异常发达,远非他国所及。[9]实验室与教学及科研的结合为科学活动的体制化、科学家的职业化创造了必要条件,从而为科学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三、德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及德国崛起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将现代化教育体制尤其是现代大学的建立看成德国现代化的开端。德国教育史专家埃尔温认为,19世纪普鲁士的教育制度,已成为现代化的决定因素,是这个世纪下半期跳跃式的德意志工业化发展重要的,也是后来经常被人模仿的前提。而德意志的大学表达了这种教育体制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为教育思想提供了一个跨世纪的开端,它用“科学”这个思想模式造就了它自己,并形成了它自己的基准点。[10]
日本学者汤浅光朝统计显示,从柏林大学的创立(1809年)到德国失去科学中心地位(1920年)期间,德国拥有200名科学家,279项科技成果。同期英国的科学家人数为122人,科技成果为174项,法国为88人和107项,德国几乎为英法之和。[11]由此可见现代大学对德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决定性意义。
整个19世纪,德国的教育体制在欧洲都是一流的。直到“一战”前,英国的教育体制与德国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英国诗人及文化批评家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年-1888年)对德国大学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法国大学缺乏自由,英国大学缺乏科学,德国大学则两者兼而有之。[12]
德国现代大学卓越的教育与研究能力为德国进行工业革命及后发式超越提供了可能。1870年,德国再战法国,实力不可同日而语的德意志民族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法兰西人,并在凡尔赛宫宣告德意志帝国诞生。从1806年到1870年,短短的半个多世纪内,德国为什么会发生堪称19世纪最具戏剧性的变化呢?也许法国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学家勒南(Ernest Renan,1823年-1892年)的回答最接近真相,“赢得战争的是德国大学。”[13]
在19世纪最后25年中,欧洲的技术创新中心转移到德国,英国的技术落后于德国,特别是在电子工程、有机化学、光学以及汽车工业等新兴工业领域。德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主要依赖科学技术。1850年至1913年,德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2.6%,其中“技术进步”作出的贡献占42%。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作用,则德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1.5%。[14]
从19世纪6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人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和发现中几乎处于独领风骚的地位。人们广泛相信经验的或实证的科学,确信人类可以理解自然并且控制其力量。细胞病理学的创始人微耳和(Rudolf Virchow,1821年-1902年)在1865年召开的德国自然科学和医生协会(Gesellschaft Deutscher Naturforscher undÄrzte)第40次大会上宣称,对我们而言,科学已经成为一种宗教。著名生理学家杜波伊斯-雷蒙(Emil Du Bois-Reymond,1818年 -1896年)把自然科学看做是“我们时代的世界征服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都是在科学界和工业界占主导地位的看法。1911年1月,著名化学家赫尔曼·菲舍尔 (Hermann EmilFischer,1852年-1919年)在德国威廉皇帝学会成立大会上宣称,未来并不依赖于对殖民地帝国的征服,而在于“化学及其应用,或者更广义地说,今后自然科学才是我们未来的无限机遇所在。”在公开场合,许多科学家都宣称他们对科学进步以及科学潜力有信心。[15]
德国的人口从1890年的4900万猛增到1919年的6600万,成为仅次于俄国的欧洲第二人口大国。它的煤产量从1890年的8900万吨上升到1914年的2.77亿吨,只落后于英国的2.92亿吨,但远远领先于奥匈帝国的4700万吨、法国的4000万吨和俄国的3600万吨。钢的产量甚至更加惊人,1914年,德国1760万吨的产量高于英、法、俄三国的产量总和。更引人注目的是德国在电力、光学和化学等新兴工业中所取得的进展。像西门子和通用这样的电气公司雇佣着14.2万名工人,它们控制着欧洲的电力工业。以巴斯夫和拜耳为首的化学公司生产了世界工业染料的90%。德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14.8%)高于英国(13.6%),是法国的1.5倍(6.1%)。从1890年到1913年,德国出口总额增加了两倍,已接近世界头号出口大国——英国。[16]长期以来,英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对英国贸易中商品结构的改变可以清晰地说明德国工业能力的提升。1870年,德国输往英国的产品中仅39.7%为工业品,原料和食品类却分别达到34.7%和25.6%。到1913年,德国出口英国的产品中工业品已占70.8%,而原料和食品类分别下降到20.4%和8.8%。[17]“一战”前的德国已成为欧洲经济的动力源泉。
四、对我国的启示
回顾历史上德国崛起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教育、科学、技术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德国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并且迅速跻身世界科技大国和经济强国之列,主要得益于其创立的现代化高等教育及科技创新体系。当今全球正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即以高技术为支柱产业,以智力资源为依托,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模式。因此,如何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如何培养和吸引高技术人才,如何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如何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是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德国在发展教育、重视科技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第一,要充分认识并重视教育对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
从德国崛起的经验中可看到,发展科学技术是手段,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是基础,教育优先对于发展经济来说是不二法门。只有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人才,才能保证科技和教育协调发展,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主要体现在教育经费投入上。在现阶段我国财政经费相对充裕的情况下,必须保证教育经费逐年有较大幅度地增长;另一方面也可采取德国科研资助模式,发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等多渠道筹措资金,为教育及科技的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保障。
第二,坚持高校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德国高校自威廉·洪堡改革以后,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促进了学术水平和人才培养水平的提高,并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科技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因而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典范
我国的高等学校自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初步形成了教学、科研两个路径,今后要进一步促进教学、科研的结合,在科研成果转化、科研与经济界紧密结合,更大程度发挥高校科研的作用,提高高校科研效益方面进一步探索。
第三,教育要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
人才的培养,目的是为了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服务。德国的教育是紧跟科技发展的步伐,满足其不断变化的需求,从而达到了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我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要更好地认清科技发展的新趋势,根据国家科技发展的总体规划,主动适应新科技发展的形势,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从而不仅在新的时期取得自身的新发展,而且最大程度地实现科技、教育的协调发展。
[1]Golo Mann.“Deutsche Geschichte”,aus Dieter Raff.Deutsche Geschichte.Bonn[J].Inter Nationes,1985,S.101.
[2]“Fragen an die deutsche Geschichte”a,Historische Ausstellung im Reichstagsgebaude in Berlin [J].Katalog,4.ErweiterteAuflag,1981.S.64.
[3]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一卷[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51.
[4]弗·鲍尔生.德国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25.
[5][7]赫尔曼·外尔.德国的大学与科学[J].科学文化评论,2004,1,(2):89,94.
[6]约瑟夫·本·戴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211.
[8]Lode Vereeck.2001.Das deutsche Wissenschaftswunder:Eine ǒkonomische Analyse des Systems Althoff(1882-1907) [M].Berlin:Duncker&Humboldt.
[9]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77.
[10]Thomas Ellwein.Die deutsche Universität[J].vom Mittelalter bis zur Gegenwart,Königstein1985,S.115.
[11]汤浅光朝.科学文化史年表[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96.
[12]Matthew Arnold.Higher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in German[M].London:Macmillan and Co.,1892.152.
[13]Willis Rudy.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M].1100-1914.Cranbury: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1984.127.
[14]小威廉·贝拉尼克、古斯塔夫·拉尼斯.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几国的历史与比较研究[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114.
[15]弗里茨·斯特恩.爱因斯坦恩怨史——德国科学的兴衰 [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5-6.
[16]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204-205.
[17]Paul M.Kennedy.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M].1860-1914.London:Allen&Unwin.1980.46,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