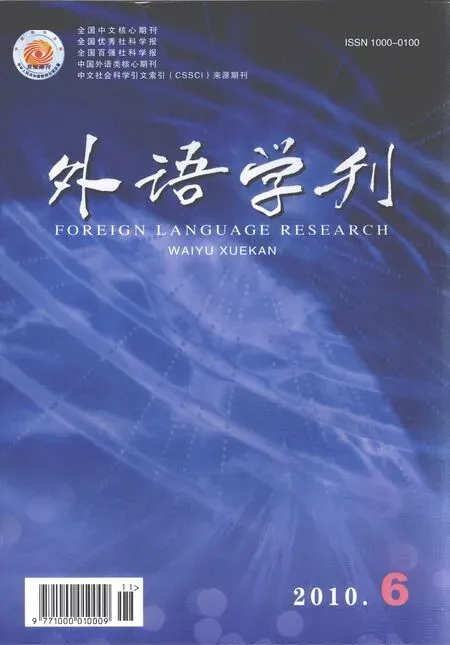乔纳森·卡勒文学语言符号论研究*
2010-03-21刘莹
刘 莹
(哈尔滨师范大学,哈尔滨150080)
文学语言符号问题一直是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诗学研究的起点与基点。尽管其学术志趣和成就更多体现在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方面,但卡勒在自己的研究中一贯重视作为文学媒介的语言问题,对符号学有着精深的研究,他早年还曾在英国获得现代语言学的博士学位。他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乔姆斯基语言学观点中找到了诗学创新的有效资源。卡勒从语言学视角出发,借助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和范式,探索文学研究的模式与方法,加深了对文学现象及理论的认识,推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从卡勒的学术实践看,他的文学符号研究在促进美国文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成就卓越。
1 文学符号的自指性与传统程式
卡勒明确指出文学语言具有某种特性,即文学符号的自指性(self-reflexity)。自指性是文学符号最突出的特点。文学语言的诗性本质就表现在它的符号指向自身,而不指向别的外物。“文学就是由于符号的自指性而使能指优势加强到一定程度的文本。文学性,就是由于符号自指性而获得的能指优势。”(赵毅衡1990:108)认识到文学符号的自指性特征,从语言的维度来把握文学的特质是文学研究的关键,是文学性在语言形式上的基本特征。
诗歌等文学语言被俄国形式主义者和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以“突显性”来界定,即通过语言的变异处置和反常化让其突兀地显现在读者的面前,以达到强化读者感知性的目的。“通过形象语言和高雅语言的运用,让读者付出更多的感知努力,得到更多的新鲜感,最终使读者在接受文本时,不把文本当作传递信息的简单而明了的工具,而是深深地介入语音和其他语言结构形态的物质性之中。”(王敬民2008:45)事实上,文学语言符号表达手段的突显,对人们惯用的语言符号范式来说无疑是一种反叛,从而使文学具备了批判的功能。但并非具备强烈的、可感知性的语言结构的文本都是文学作品,比如某些新颖、别致而充满创意的广告,到目前为止还不能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雅各布森提出了从语言的维度来辨析文学性和文学的特质。他把人类语言的交际归结为6种基本功能,在这样一个参照体系中,“通过对人类语言活动方式的全面考察与分析,论证了雅各布森对语言艺术本质的看法,即语言艺术的审美性质是一种功能性的性质。诗功能不是把人引向外在现实,而是一种自我表现、自我宣扬。它使语词以其声音、节奏、格律、句法等形式结构引人注目,加剧了符号与对象间的对立,破坏了能指与所指、符号与对象间的任何自然联系,极大地增强了符号的可感性,从而与其他功能鲜明地区别开来”(方珊1994:118)。也就是说,文学作品里面的语言结构没有一个它将通达的具体目标,而是以其手段作为参照。正如卡勒本人所言,“在一部文学文本中,语言的突现方式等于把它从其他背景(陈述文学生产的时间及现实环境)中分离出来,把文本语言试图完成的行为(如邀请友人)变成一种文学手法,并把它置于一系列文本与文学的背景之中。任何关于文学性的讨论,都不会把文学手法视为表达信息的手段,而看做文学言语的主人公和主题”(Jonathan Culler 2000:35)。
卡勒试图从文本的结构出发来界定文学文本的特性,探讨文本的“文学性”。在卡勒的时代,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再到结构主义和解构思潮,对文本语言结构的关注成为文论思潮的一条稳中有变的主线。但卡勒对制约文学文本解读的习惯和条件进行考察,又将文学性的界定置于文本形式主义的研究范式和传统文学研究范式之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界定文学性的艰难。通过文学性的研究来确立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这种研究方法行不通。但“如果研究的目的在于鉴别什么是文学最重要的成分,关于文学性的研究则展示出文学对于澄清其他文化现象并揭示基本的符号机制的极端重要性”(陈红 王敬民2007:5)。卡勒指出文学作品本质上是一种语义事件,绝非是对非虚构性语言行为的虚构性模仿,而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行为,与非文学语言行为的叙述模式有着明显的差异。在文学性的语义事件中,不仅叙述者的情感和理想世界得以呈现,而且还召唤着读者的强烈共鸣。
尽管卡勒没有解决“什么是文学性的本质”这一问题,但卡勒认为不同的研究视角都可成为文学研究的有效途径,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认识和解读文学。从语言符号的维度看,“许多复杂的符号系统是建立在其他符号系统,特别是语言系统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称之为‘二级系统’。文学就是一例。语言是文学的基础,语言的特殊用法又形成了文学的辅助系统。隐喻、换喻、夸张、提喻等修辞格都可以看做二级文学代码。显然,在文学领域中,为了解读文学作品所必须掌握的知识既超乎语言之外,又贯乎语言之中”(Jonathan Culler 1999:96)。卡勒在此论述的其实是文学符号的自指性特征,也就是通过修辞和陌生化等手段,使语言指向其自身的音韵、语词和句法等诸多形式要素。文学符号的这种自指性,奠定了语言形式结构的重要性,使文学研究关注于文学语言结构的审美功能,这有助于确立文学研究的独立地位和科学品格。
而另一方面,“文学与传统程式和习俗又密切相联。文学作品存在的形式往往受制于传统的文学形式。按照传统和文学背景的规范建立起统一的功能性相互依存关系,似乎更应该成为文学特征的标志”(王敬民 2008:57)。这就要求文学作品把原本没有功能作用的结构或关系加以融合,通过形式结构的组合,在语义和题材方面产生文学效果。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文学作品对其统一性的诉求导致了不同语言结构和层次之间出现种种矛盾和不和谐,而这恰恰构成文学表达的效果。在受制于文学传统和惯例的同时,文学文本也在文学背景、文学手法、读者的阐释规则等方面表现出自己的新见,甚至质疑。因此,文学在依赖传统、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对传统观念加以批判,从而具备自反性的特征。在文学传统和惯例的制约中,文学性得以体现;同时,文学文本对既定范式的反叛,也使得文本的文学性得以凸显。
如上所述,卡勒在大力强调文学符号自指性的同时,又指出文学传统和惯例的重要性。在他的《索绪尔》一书中,他指出:“索绪尔一语中的,指出了文学中存在的一个重要的惯例系统,即人物的塑造受制于一系列的文化模式,阅读中正是这些模式使得读者可以从行为判断动机,从外表推知品性”(Jonathan Culler 1999:98)。这里表明了卡勒诗学建构的显著特点。他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入手,从文学语言符号的自指性出发,深入研究了文学之为文学的内在特质,但同时,他又极为重视文化模式中文学传统和惯例对文学研究的强大影响,也把读者的接受过程和阅读的建设性作用纳入考察的视野。这种几近中庸的特色,在卡勒进行结构主义诗学建构时有所反映,也同样体现于他在解构视野中所进行的诗学探索。
2 文学符号学的悖谬性
基于对文学语言符号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探究文学符号的意义生成,而且也为我们研究诸多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参照系统。但问题却远非如此简单,因为符号学本身存在着某种悖谬性。卡勒曾就此指出,“通过对符号及其意义指称进行严密的考察,符号学形成了一门学科,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这门学科最终揭示了意义指称过程的最基本的矛盾。符号学必然走向对其自身的批评,走向一个显示其自身谬误的前景”(Jonathan Culler 1981:37)。符号学虽然为我们研究一系列文化现象提供了理论视角,但符号学的追寻也使我们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意识到我们不可能用某一种连贯的综合性的理论来掌握意义指称问题,这就是事实。
看来,文学符号学研究本身带有自指性的过程,而且是一个不断指向自身的复杂过程,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言:符号若非作为对自身的批评就不能得以发展。在其发展历程中的每一时刻,符号学必须将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加以理论化,从而使符号学自身更具理论性,成为其自身科学实践的理论。它是向研究永远敞开的一个方向、不断反观自身的一个理论流派、一种永久的自我批评”(Julia Kristeva 1969:30)。文学符号意指过程的复杂性,使其明显有别于语言符号的实用功能,意义未定点和空白处让文学意义的阐释有了广阔的空间,而其自身的意指模式又可以不断地重加审视。这一切使得文学符号成为符号学研究中一个最为复杂也最为有趣的实例。“符号学家试图揭示出使文学交流成为可能的编码的本质。”(Flowler 1975:37)文学符号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追寻文学符号的意义,要确定使文学意义得以确立的程式系统。与具体文学文本的阐释不同,文学符号学研究的最终旨归是要建立一种诗学,这种诗学与文学的关系,就像语言学与语言的关系一样。
符号学研究是为了求得符号的意义,它必须揭示特定文化中使意义得以成立的规则和程式。这些规则和程式,说到底,是一套深深扎根于特定社会语境的文化准则,对其社会成员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某一特定文化的成员,不管愿意承认与否,他的观念和逻辑思维无不受制于其文化规则的制约。这样,如果说符号学最终要揭示出特定文化的规则和标准,那么它就具有文化祛魅的功能,这也是符号学研究的动力所在。但是这种结构主义式的符号学研究,在文化祛魅之中究竟让人们获得了更大的自由,抑或相反,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毕竟结构主义及其符号学常常被冠以恶名,被贴上反人本主义的标签。其实人们在揭示文化内在规则时获得了相对的自由和愉悦,但人本身却永远不能成为意义之源,成为意义之源的只能是制约符号对立项之间关系的文化规则和程式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主体地位被剥夺和消解了。
3 符号学批评方法
符号学给文学理论家提供了完整而富有分析力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实用性比费莱等文学批评论家所提供的更为强大。然而,语言模式的权威性来自它科学性的结构及其理解语言现象取得引人注目的进展的基础,同时还因为语言学讨论的是语言——文学的媒介。因此,语言学的发展,开辟了运用语言学进行文学研究的某种前景。它的实施就是索绪尔预见到的:语言学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更大的领域——符号学(符号的总学科)内的一个分支。但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是符号学总体系内的一个子系统,或一种特别的实例。系统研究符号学热潮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结构主义”运动,尤其是结构语言学。结构主义关注的是:决定产生意思的基本单位及其关系是个别的现象或行为表示的意思所依据的成套法则和程度的系统性功能。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勾勒出一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要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就必须探讨文学作品的表意过程,并描写使我们得以理解作品的常规、代码和表意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不可分。但从根本上说,对符号学的形成起最关键作用的是现代语言学。索绪尔不把语言视为“实体”,而将它看成“形式”(一系列系统的关联)。这里重要的不是本体,而是它们之间的区别。语言的不同点体系,在各个层次起作用,从音素和词素的基本区别到语义和词义的差别,区别总是构成可表示意思范围的方式。另外,“相同的运行和分析法则,也见于言语的各个层次,在每个层次人们都看到语言单位之间起到联合的关系和结合而成的关系,也就是现代语言学家所说的横组合关系确定的均等成分”(刘润清2002:45)。从这个系列挑选出来的成分结合在一起,在纵聚合的轴心上形成一个新的整体。这个新的整体由更基本层次向最复杂的层次变化,反之亦然。
在索绪尔看来,符号学的眼光是研究语言的主要眼光。那么,既然人的行为和作品是有含义的,既然它起着符号的功用,那么肯定潜存一个使意义得以表达的常规和差别的体系。因此文学符号学的任务,就是发掘潜存于文本中的这种体系。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曾在《结构热力学》中说,为了分析有意义的现象,为了探讨有含义的行为或对象,我们应当假定潜存一个关系的体系,并试图发现个别成分或对象相比的结果,但一种文化对于这种体系并无自觉意识。描写这样的体系近似语言学研究。人类学家认同语言学家,都试图阐明使一个具体社会中的人得以交往和理解彼此行为的内在知识。既然在一种文化内每个有意义的事物都是一个符号,是符号学探讨的一个对象,那么符号自然包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因此它能表明文学语言如何与别的语言代码相连。符号学将结构主义思想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关注的是符号的含义和意思的产生。然而,建立有效的文学符号学必须有令人信服的分类法。卡勒在《索绪尔》一书中,将符号分为三大类:“像、标记和严格意义的符号”,并且认为这样能使严格意义的符号成为符号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在《追逐符号——符号学、文学、解构主义》中,卡勒指出,“思考在研究最复杂的符号体系——‘文学’方面的符号学已经做了什么和可能做什么”,是看待符号学研究方案最好的方法。索绪尔早就对文学符号表示出兴趣,而且意识到它的某些问题。他曾在未发表的研究日尔曼传说的笔记中写道:“(一个传说)是由一系列符号组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还有待于进一步解释”(Jonathan Culler 1983:53)。尽管这种符号更难以解释,但支配它们的原理,无疑跟支配某些其他符号的一样,都是符号学的一个部分。文学的符号跟语言的符号一样,基本问题是识别本体的问题。文学里的符号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永远以一种意思系统的一定形式出现。文学总是利用先存的符号,兼并它们并不断从它们身上吸取新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读者所面临的是一个完整系统的成分(专有名称、特征、与其他任务的关系和情节),所谓的任务其实是读者的创造,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综合所有不同成分的结果。
卡勒在论述符号学的前景时,指出这门学科为我们研究一系列文化现象提供了有益的方法和理论探索,“文学符号学的追寻使我们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意识到我们不可能用某一种连贯的综合性的理论来掌握意义指称问题,这是事实”(Jonathan Culler 1981:65)。但这种事实不应该成为我们拒绝符号学分析模式的理由。其次,符号学形成了一种解释活动,一种德里达的“双重科学”,一种解构式的阅读模式。它既在符号学的框架之内起作用,又对符号学加以反抗。两者既相对抗,又难以割舍,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文学研究的动力之源。
4 结束语
目前的文学符号学还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它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要价值不言而喻: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在认识论的层面,它都为我们洞察文学语言符号的本质特征,掌握文学符号的意义指称规律,全面认识文学语言符号系统的逻辑规则提供了有益的参照模式。有学者指出,“将文学与符号学联系起来,不但是合适的,而且是有效的,因为语言是人类最成熟、最丰富,且结构性、系统性最强的符号体系,而文学的媒介恰恰就是语言。因此,从符号学的角度研究文学表层话语链的意义生成是结构主义批评的重要维度”(李广仓2006:240)。诚然,在结构主义者看来,符号学可以用来观照文本表层话语的意义链,其实符号学之于文学批评的作用并非局限于此。它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手段,使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科学主义的品质,这有利于文学研究的长远发展。当然,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语言的艰涩,这也要求我们更为敏锐地分析文学的语言要素,而符号学在这方面为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源。无论是走进文学文本,还是置身社会文化语境,符号学分析作为研究方法,其优势一定会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
陈 红.乔纳森·卡勒文学符号观发微[J].外语教学,2007(5).
方 珊.形式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
李广仓.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杜,2006.
李幼蒸.结构与意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乔纳森·卡勒.索绪尔[M].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
孙丽秀李 增.克里斯蒂娃符号学思想探源——克里斯蒂娃研究之二[J].外语学刊,2008(1).
王敬民.乔纳森·卡勒诗学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
赵毅衡.文学符号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
Culler,J.Literary Theory[M].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Culler,J.The Pursuit of Signs[M].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2.
Culler,J.Structuralist Peotics:Structuralism,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M].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2.
Divis,R.& Ronald,S.Com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M].New York & London:Longman Publishing Group,1994.
Eagleton,T.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M].London:Blackwell Publishers Inc.,1996.
Flowler,R.Style and Structure in Literature[M].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5.
Hartman,Geoffrey H.Beyond Formalism:Literary Essay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