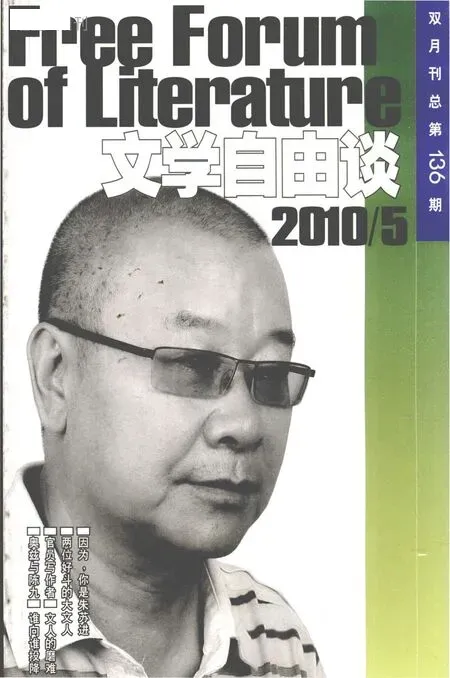谁在为谁唱盛唱衰?
2010-03-21严英秀
●文 严英秀
这个时候才来谈论这个话题,实非聪明之举。关于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关于如何高度如何低谷,如何黄金如何垃圾,如何中国立场如何世界眼光,从去年底开始,关于这一切的争论可谓达到了中国文坛近年来又一个“前所未有”的聚焦状态,至今方兴未艾,人声鼎沸。而戏已过半我才踉跄冲进来的加入,充其量只能算个掺乎,任你有多大的嗓门,多猛的姿势,多雷人的言辞,终究不过是拾人牙慧,唱口水歌而已,混夹在人堆里看似帮人打架、劝架,实则自娱自乐而已。
所以,选择在黄花菜早已凉透了的当儿愚蠢地加入这个话题,并非因为我突然生出了自己也必得掺乎一下的使命感,必得上一下场的言说欲,而是基于我旁观大半年来的一些沉重的思虑。大半年过去了,事情还在进行时态中,还未到尘埃落定的总结时候,但它从一开始就潜伏着的问题的另一面,在我看来现在已是非常鲜明地呈现在众人面前了,那就是:当代文学是盛是衰似乎并不重要,唱盛唱衰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在唱盛,谁在唱衰,唱盛唱衰在进行着怎样的较量,最后谁胜谁输,如何了结。
也许,这就是文学在媒体时代的不堪遭遇,一切严肃的声音都被娱乐化,一切有益的探讨争鸣都被煽风点火成这派和那派的擂台战,赚人眼球的永远是各路骂派的队伍阵容,出手的章法技术,而真正的主角——文学却被蒙尘,被冷落,被遗忘,到了最后,骂的双方和看骂听骂的众人都想不起为何要骂为何在骂,我骂故我在,反正只要骂着就行。就是这样,媒体真是个怪东西,被它的聚光灯一照,许多人便情不自禁地理直气壮地纷纷登台演将起来,扛着神圣的旗帜映红自己的脸,用凛言厉语诽词谤句染白别人的脸。殊不知,在台下看热闹的人眼里,戏之所以好看,是因为那台上的铿锵唱将们鼻子上都抹着一抹白灰。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都是媒体惹的祸”,你之所以“被媒体”,是因为你自身刚好具备了吻合了“被媒体”的要素。回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这个话题上来,从一开始,如果唱盛唱衰派都不是那么各执一词真理在握的架势,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水火不容,不是不仅要驳倒对方的“盛”“衰”观点,而且要把对方连人也一并打翻在地的骁勇姿态,那么媒体的苍蝇会无故来叮一颗圆润正常、自在运动的蛋吗?且不说学术商榷的正常形态云云,哪怕稍稍多一点态度的平和、宽容、理解,多一点对对方学识人品的应有尊重,多一点对常识人情的尊重,事情其实原本都可以离文学近一点,离媒体远一点。而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大家都知道关于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学界著名人士们还正在吵着一场著名的架,但他们的唱盛唱衰到底对大多数人正确认识当下文学起了怎样的引领作用,有什么启迪意义?经过他们的吵,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是否有了豁然开朗的认识?中国当代文学,到底是好,是坏?说好说坏唱盛唱衰对它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在这样的唱盛唱衰中,关于文学又有什么新的学术生长?
我很难过地看到,答案是否定的。这场著名的争鸣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毫不客气地说几无建设性可言。本来驳杂难言的中国当代文学经过这场唱盛唱衰,更加地面容模糊,本来并不清澈的一潭水,现在被搅得更混了。为什么在一些人看来是前所未有的高度,偏偏在另一些人眼里就成了无法饶恕的低谷?为什么一样东西,可以被人既看成是黄金又能看成垃圾?为什么你说的污秽下流之作到他的口里却硬是成了标志着“高度”水平的“穿透之作”?在这样两极分化的观点面前,读者该听谁的,如何做出自己的判断,从而最大程度地接近本来的真相?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一千个评论家,或该有一千种中国当代文学(可惜的是,现在没有一千种,只有两种,即黄金的中国当代文学和垃圾的中国当代文学)。这第一句话是从一张非凡的嘴说出又被无数张嘴重复过的真理,这第二句话是从第一句话衍生出来的,它自然也不会错哪儿去,但比这话更对的是关于人和事的一些常识,一些可以靠人的肉眼就能看出的真相,一些通常的普适的标准。虽然横看成岭侧成峰,虽然黄金有时候会掉落到垃圾里,但一般情况下在正常人眼里,高度和低谷,黄金和垃圾,它们之间的区分度还是明显的,被混淆的概率约等于零。那么,为什么,一般人可以凭借常识做出的判断,在著名学者们那里,却会变得如此地“高难度”起来?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没停息过,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对它表示失望。目下的文学,无论是在整个新文学史框架中,还是就建国60年而言,都不可能如唱盛一派所说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样的褒扬之语,若不是出自无知(又怎么可能是无知),就肯定是昧心的谄媚。然而,不是前所未有的高,就是万劫不复的低吗?不是黄金就肯定是烂苹果吗?我是旗帜鲜明地反对顾彬的垃圾论的,无论他是多么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无论他出于对中国文学何等的热爱和责任感,他的垃圾论在我的评价里从一开始就是站不住脚的,我自信这不是因为我潜意识里有什么“义和团”情结,而是出自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贯认识和基本判断。
就是这样,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说出来似乎显得极其多余,因为它看上去多么中庸、调和,是最没有学术含量的无观点派,也是最容易被人诟病的“骑墙派”,中间派。但我不能为了把自己装扮成有思想的“疑似学者”,就背叛自己的眼睛,漠视内心的声音。从文学青年到文学中年,从一个当年自觉选修有关现当代文学的所有课程的学生到今天以专门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为饭碗的教师,时光荏苒,见识也略长一二,但有一种认识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和任何时代的文学一样,有好有坏,也许太多外部内部的环境导致它坏多一点,好少一点,但它绝不是垃圾,它从来就没有断绝出现过启迪人心温暖人性的好作品,没有断绝出现过直面现实拷问灵魂的好作品,没有断绝出现过让人对世界同时也对文学充满信心的好作品。它早已走过了青春花季,但还正在艰难地生长着,它离甘甜如饴的境界还差得太远,它可能是酸酸甜甜的李子,但不会是烂苹果。只要有一些善良、光明、有良知、有尊严的作家还在认真地写着,中国当代文学就不是也不会是倒人胃口的烂苹果,让人掩鼻而过的垃圾。但与此同时,我也不认为它在这几十年里走到了什么高度,它充其量就是一座高高低低逶迤交错的丘陵。
前几日,电影《唐山大地震》公映。随即就有人高喊,此片是大师级的史诗性的作品。对此,冯小刚回答说,我不是大师。他还更进一步地指出,谁也别装大师,因为这不是一个出大师的时代。这话本是一句很平常的老实话,但在时下的环境里,从一个一向以逗乐国人为己任的贺岁片电影导演口里说出,就显得弥足珍贵。多么奇怪啊,这不是一个出大师的时代,却是一个忙着封大师的时代,动辄“被大师”的时代。正如某作家自言一不小心就会写出一部《红楼梦》一样,现在是某几位(或某一类)作家但凡写出作品,小心不小心都会被提前送进文学史,封为“大师”、“经典”。
所以,我认为这“最好的时候”出现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在创作当代文学的人身上,这些作家们其实和任何时候的作家们在本质上并无二致,有崇高的,也有卑琐的,有清洁的,也有龌龊的,有以笔为旗坚守理想和精神的,也有卖稿子数钱写文章求荣的。这难道不是历来有之的景观?“痛心疾首”派一直以来很有市场的一个说法是90年代以来的商品消费社会导致了文学的种种堕落沉沦现象,但我觉得这种观点其实是极没有历史眼光的偏执和褊狭。几千年来血雨腥风的历史,多少的探照灯都无法照亮的幽暗的过往,偏就作家诗人们个个干净挺拔得像松竹梅兰了?我们在今天尊崇古代敬仰传统,那只是因为历史已经给了我们最后的答案,我们看到的是在时间这个惟一的标准下以文学永恒的光芒照亮了后世的真正的经典。所以,现在也一个道理,虽然现在的毛病更多一点,但有什么好着急的,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大浪淘沙,该流芳百世的自会流芳百世,该遗臭万年的活该遗臭万年,该自生自灭的就让它再苟延残喘几日得了。一个时代的进步、繁荣和成熟,最大标志该是文化文学的多元并存,这也是常识。过多地指责作家缺乏这个丧失了那个,指导他们要这样不要那样,等等诸如此类,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无效劳动。难道作家们自己就不想一步站到“高度”上去,不想收获一个“前所未有”?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这么说,当然不是抹煞文学批评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文学批评是重要的,而且在一个充满病症的文学时代,文学批评更是应该“前所未有”地重要。但并不是所有的文学批评都是重要的,因为文学需要的永远只是好的文学批评。这一点毋庸置疑。之所以重复这太过老生常谈的观点,是我认为在今天,比作家们的创作更严重地表现了这个时代文学的症候的恰恰是文学批评,这个领域其实比作家群体更集中地暴露了“中国当代文坛之怪现状”,要说有病,批评要比创作病得更重。我不能说这样的想法是我的原创,因为近年来,对文学批评的批评其实是很热门的话题,可谓骂声四起,几乎被人断定为“走向死地的文学批评”。但骂与被骂者,永远都是一个锅里搅粥吃的人,他们的声音虽很嘹亮但却内虚,扩散不到圈子外的写作者和阅读者那里。批评界的自娱自乐,窝里斗,这种狗咬狗两嘴毛的事早已不是一天两天了。并且,骂过,斗过,咬过,反思过之后,他们的行径并无大的改变,永远都是“病并快乐着”的满足样。
文学批评最初的出发点和最后的落脚点都应该是文学,文学批评家应该对文学负责,对作家对读者负责,这是责任也是义务,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基。然而,放眼看看,细致认真褒贬有据的作品论越来越少,切中要害全面客观的作家论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是凌空虚蹈、浮躁媚俗、无的放矢,越来越多的是故作尖锐故作宽容故作宏观故作崇高,越来越多的是这一群把一小撮作家作品捧上天,奉若神明,另一群立马把他们踩到脚下,弃若敝履。在这样的文学批评中,文学不再是最高宗旨,不再是所有的惟一的原因和结果,而成了背景音乐,成了文学批评家们的帮派之争、圈子之争、意气之争的工具,成了供他们争夺山头和话语权而尽情表演的舞台和场子。远的不说,就回到今天的话题,唱盛唱衰大半年了,有目共睹,现在“唱”已升级成破口大骂了,此起彼伏,一片叫嚣,但街市依旧太平,文学永远流驶。你说当代文学是高度是黄金,“十七年”是永不过时的经典,这一点都无法说服我使我认为当代文学确实已高到我们须仰视才见,无法掩盖我在阅读讲授“十七年”文学时所感到的那种无以复加的倦怠感,也无法消除我对那些“高度”之作的极其不信任;但他说当代文学是低谷是垃圾,“十七年”也好新时期也罢都是什么都不是的不堪回首的过往,我也只能置之一笑,我知道所有的文学都是整整一个时代精神历程的记录,是承载了它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和梦想的,今天的我只能细读手中的书,也不忘回望那些时代,才能窥见局部的真相,见好说好,见坏说坏。缘于此,在我的理解里,文学批评最原色的特质就是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一定要勇于批判它的无价值,但同时也绝不吝于发现它的价值。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任何一种非好即坏的思维,任何一种一刀切的判定都是草率的,也是最终站不住脚的。
所以,那些把粗糙平庸低俗之作奉为“高度”“经典”的表扬家们,那些一听当代文学就好像有八辈子仇恨的“憎恨学派”们,他们并不是真的在为文学操什么心,要不他们怎么会像赌气较劲的顽童,你说高度我就偏说低谷,你说黄金我就偏说垃圾,你说最好我就说最烂?他们争的无非就是自己在这一亩三分地里的话语权、命名权、编选权、评奖权罢了。其实唱将们也心知肚明,本来就没有打算要唱出什么结果来,本来要紧的就不是为何唱盛唱衰,而是谁在唱盛,谁在唱衰。所以我们也不要期待会唱出什么结果来,更不必操心唱盛唱衰何时休,让他们继续唱下去吧,因为无关文学,文学该衰照衰,该盛还盛。
所以,我写此小文,决无对唱盛唱衰派做个判决各打五十板子的意思,我虽无知,但也不至于到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境地。我和唱盛唱衰派那些学者大家们之间的距离,要比那些写出了“高度之作”的著名作家们和斯德哥尔摩之间的距离还要远,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我不过是想说,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且让他们唱去,我们该读的读,该讲的讲,该编的编,该写的还低着头写去,该干嘛干嘛,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