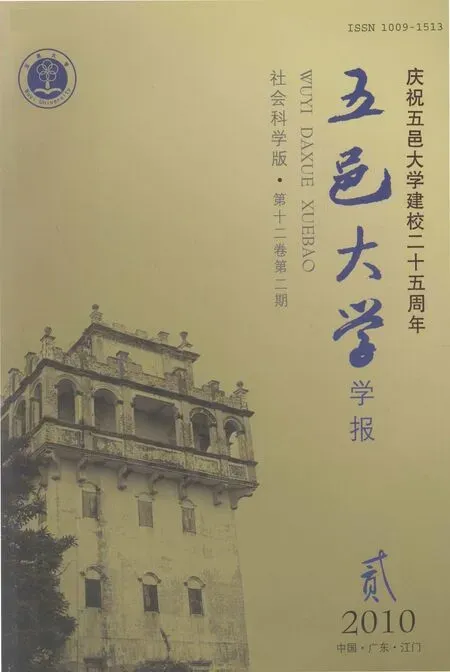中国“放生”习俗渊源简论
2010-03-21冯军
冯 军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中国“放生”习俗渊源简论
冯 军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放生”作为一种民俗事象,与人类历史共时,各个时代文化背景、人类认识观念的差异令放生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内涵特征与审美趋向。放生在其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放生思想、放生题材类型、放生作品的艺术表达方式,放生表达既是一种宗教关怀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延绵不息的精神财富。
放生;历史;内涵
古人最重视生,《周易·系辞》下云:“天地之大德曰生。”[1]《左传》中也说“生好物也”[2],“万物之生意最可观”[3]。正是由于万物之生,世界多姿亦多彩。而重视生、尊重生的前提则必须是好生、放生。好生与放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广义的放生是放纵所有生命,包括无生命的植物,有生命的动物以及人类。放生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民俗活动,与人类历史共时,但因各个时代文化背景、人类认识观念的差异,使放生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内涵特征与审美趋向。
远古社会人类对自然认识极其有限,在他们看来,世间万物,无论动物、植物、无生物都有灵魂,这就是著名的万物有灵论。“万物有灵是在人的灵魂信仰基础上产生的,是对人灵魂的仿制和设想,是把自然进行人格化。”[4]把自然人格化的同时即是“以天道类比人世,以人世把握天道”[5]102,是“人把对自身的认识所形成的认知模式投射到宇宙万物并赋予其人的情感、生命、价值和意义,然后再从自然万物的变化中体认人道的酸甜苦辣,那么天道人道之间的关系就只是印证、比拟的关系,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是对应性的感性关系”[5]104。在彼此的类比对照中关注万物的生命价值与生存意义,爱生重生放生自然成了不容逃避不可忽视的问题。《群书治要》、《六韬·虎韬篇》引神农之禁指出对“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6]。《逸周书·大聚解》提到“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7]《礼记》中的《曲礼》、《檀弓》、《王制》、《月令》、《玉藻》等篇也有类似的记载和论述。
迨及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战乱频仍,人及万物面对天灾人祸的冲击,生命受到严重威胁。面对惨重的人生灾难,有识之士奔走呼吁生的尊贵与重要,积极寻求生存的意义与价值,放生也被提到日程上来。孔子主张“钓而不网,弋而不射宿”[8]346,孟子声称“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9],他们都呼吁给万物以生长发展的机会,进行适时性放生。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奴隶制逐渐瓦解、封建制逐渐形成的社会政治文化转型时期,诸子百家在重重危机中纷纷确立理想的人生与政治理念。庄子在“以道观之,物无贵贱”[10]239、“万物与我同一”思想观念的指导下齐万物等生死,主张“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10]96,万物之生得到足够尊重,同时肯定生死的辨证因循规律。吕不韦等人在“人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11]85的前提与基础上,强调贵生、全生,认为“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11]74。列子则讲述了简子“正旦放生,示有恩”[12]99事,并说明“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12]99的道理。孔子本着儒家“恻隐之心”与“仁者,浑然与物同体”[13]的思想,确立放生与仁政的关系。他说:“舜之为君也,其政好生而恶杀,其任授贤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静虚,化若四时而变物,是以四海承风,畅于异类:凤翔麟至,鸟兽驯德,无他也,好生故也。”[14]孔子这种好生的仁治观念确立了仁者爱民爱物的放生核心基调,成为儒家“仁政”的立论基础,成为几千年来中国理想的传统政治统治模式以及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修养的道德标准之一。
万物之生是人类社会构成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是人逍遥自为、物我合一、天人相契的根本基础,是政治是否清平、国家治乱与否最重要的标志,人与万物和谐同一的思维在放生中得到充分体现。诸子百家的放生思想更多的是从社会纷乱的现实处境出发,是对客观真实存在提出的一种积极应对方案,是借对万物之生的思考来反思现实社会人生,高扬个人的人生理想与政治主张,因而这一时期的放生主张实际上是一种借题发挥式的智慧与理性思维的结果。
佛教从汉代时传入我国,在与本土宗教的冲突、融合中站稳了脚跟,到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得以迅猛发展。对佛教来说,“世间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惨者杀伤”[15],不杀被列为佛教诸戒之首,放生被视为众善之先。“《梵网经》云:‘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16],“上及人伦,下沾蝼蚁,但能救死,无不放生”[17]。放生戒杀被作为佛教教义要求严格遵守。
佛教放生作为一种民间宗教形式,本着大慈大悲众生平等之心,上可以广施博爱,对“含灵蠢物”进行终极关怀,下可以借助放生果报关注个体的利益与生命的归宿。正是由于它可面上可朝下的灵活教旨,令其在当时受到人们的热情追捧与尊崇。晋人董勋《问礼俗》曰:“五月俗称恶月,俗多六斋放生。”[18]梁武帝奉佛戒杀,梁元帝荆州有放生亭碑,唐肃宗“下旨在各大寺庙内建造鱼池,要各家各户把金鱼放生”[19]。唐乾元中,命天下置放生池八十一所。作为现实生活反映的文学创作尤其是魏晋六朝志怪小说与唐小说“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宗教色彩异常浓厚,“搜奇记异”的放生事项数不胜数。《幽明录》中毛宝、《会稽先贤传》中孔愉、《梦隽》中桓邈、《续异记》中刘沼、《独异志》中严泰、《儆戒录》中陈弘泰等都是因救助他物得到或财富或职位的善报。而《搜神记》中海盐士人陈甲、《纪闻》中当涂有业人子、《幽冥录》中曲阿民谢盛、《宣室志》中汾州道士王洞微、《稽神录》中朱氏子等则因杀生而遭受报应,善恶故事皆由放生融入佛教因果报应的内容。
大唐经济的繁荣、政治的开明开启了唐代作家“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的创作理路,在小说意识的觉醒与自觉影响下,宗教果报风气之外仍有不俗之作。譬如《广异记》。“华州进士王勋尝与其徒赵望舒等入华岳庙,入第三女座,悦其倩巧而蛊之,即时便死。望舒惶惧,呼神巫,持酒馔,于神前鼓舞。久之放生,怒望舒曰:‘我自在彼无苦,何令神巫弹琶琶呼我为?’众人笑而问之,云:‘女初藏己于车中,适缱绻,被望舒弹琶琶告王,令一黄门搜诸婢车中,次诸女,既不得已,被推落地,因尔遂活矣。’”[20]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放生的对象是人,而以往放生对象多以物为主,这在放生史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其二,人神相恋的情节生动感人,乐死而不愿生的人物形象鲜活饱满,这与后世的人与异类相恋或人与异类殊途而彼此放生有诸多相似之处。这完全剔除了宗教轮回报应观念,更多地体现了小说虚构与浪漫的特质,对后世同类文学作品影响深远。
在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因思想观念的不同,长期进行着不断的冲突与斗争,但在宋元时期它们彼此逐渐相互吸收、融和而形成新儒学。新儒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经世致用思想,这种思想意识也明显而深刻地表现在放生事项上,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对“仁者爱物”体验深刻,他们发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8]728的精神,设身处地,推己及物,关注万物的生命存在,饱蘸悲悯之情抒写放生的必要性,如陆游“血肉淋漓味足珍,一般痛苦怨难伸!设身处地扪心想,谁肯将刀割自身”,苏轼“记取金笼放雪衣”,他们都强烈呼吁拯物放生并付诸于行动。王安石“喜放生,每日就市买活鱼,纵之江中”[21],苏轼曾买西湖为放生池,“出御赐金钱筑堤障水”[22],欧阳修的话更具有典型性与概括性,他说:“王者仁泽及于草木昆虫,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为私惠也。惟天地生万物,所以资于人,然代天而治物者当为之节,使其足用而取之不过,万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23]儒家“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24]、“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25]的“生生之德”,在这一时期得到最确实最透彻最诚挚的阐述与积极发扬,这也是几千年来一直延续不衰的儒家知识分子的生命关怀精神血脉。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社会矛盾尖锐,变革要求强烈,各种思潮此起彼伏、风起云涌,在这多变的时代氛围中放生现象也呈现出多元倾向。既有传统儒释放生,如莲池大师《戒杀放生文集》、屠隆《戒杀放生文》、李之藻《广放生说》、钱牧斋《放生说》、施闰章《逸园放生歌》等;也有因思想观念的开放与更新给放生活动带来的新的理论支撑,如在“物物皆宗,人人本圣”心学通谈与狂禅思想影响下陶望龄的《放生辩惑》、《放生诗十首》[26],深受晚明个性解放自由思潮影响的张岱的《西湖梦寻·放生池》“但恨鱼牢幽闭,……孰若纵壑开樊,听其游泳,则物性自遂”[27],则从自身人生观、价值观角度来解读放生。在这充满变动也善于总结的时期,人们对放生事项已有了全面而较为深刻的认识,放生现象蔚为大观。
放生作为一种民俗事项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传统、广泛的理论基础与群众基础。它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历代相传的社会习俗、时尚,是被大众被社会所普遍认同的信仰活动。放生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始终,自古以来与放生相关的名目种类繁多,如放生日、放生节、放生会、放生乡、放生社、放生庵、放生池、放生桥、放生碑、放生矶、放生阁、放生潭、放生台、放生券、放生诗、放生剧目、放生小说等等。放生事项在其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放生思想、放生题材类型、放生作品的艺术表达方式,更表达了深沉而强烈的宗教与人文关怀。放生事项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直充实着人们的生活空间,滋养着人们的心灵。
[1]周易[M].韩康伯注本.上海:上海书店,1997:48.
[2]杜预.左传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1517.
[3]冯友兰选集[C].涂有光选编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243.
[4]宋兆麟.巫与巫术[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8:98.
[5]季广茂.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6]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
[7]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释[M].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6:191.
[8]南怀瑾.论语别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9]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4.
[10]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1]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 1984.
[12]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龙门联合书局, 1958.
[13]程颢,程颐.二程遗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66.
[14]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M].上海:上海书店, 1987:61.
[15]曹越.明清四大高僧文集·竹窗随笔[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209.
[16]莲池功德会.放生问答[M].台南:和裕出版社, 1988:4.
[17]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八十[C].北京:中华书局,1994:110.
[18]徐坚.初学记[C].北京:中华书局,1962:74.
[19]蒋楚麟,赵得见.生活常识一[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54.
[20]戴孚.广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2:151-152.
[21]郭本超.四库全书精华本[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2342-2343.
[22]王士祯.池北偶谈[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62.
[23]欧阳修全集[C].李逸安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 2001:2232.
[24]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钟哲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2:251.
[25]戴震.孟子字义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61: 48.
[26]易闻晓.公安派的文化阐释[M].济南:齐鲁书社, 2003:333.
[27]张岱.西湖梦寻[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98.
[责任编辑朱 涛]
G112
A
1009-1513(2010)02-0061-03
2009-12-04
冯军(1976—),女,辽宁营口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与古代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