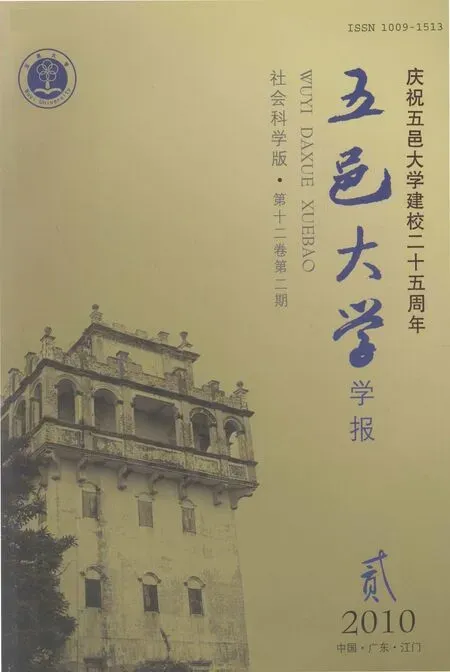义利合一: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与实践
2010-03-21赵建国
赵建国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义利合一: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与实践
赵建国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百年商务以扶助教育、沟通中西为宗旨,编辑教科书与工具书,整理古籍,介绍西学,发展文化,同时在商言商,坚持营业主义。这种文化与商业并重的经营模式,不仅兼顾社会效益,而且追求经济利润,实现义利合一,值得特别关注。
商务印书馆;义利合一;出版理念;经营实践
作为一家百年老店,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早已引起学界与业界的热情关注。不过,既往研究集中于馆史、张元济与王云五两个核心人物,以及文化传播的实际行为,商务的出版理念却未曾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已有研究成果大多关注商务的社会效益,对其商业利益往往略而不谈。其实,编教科书—编工具书—介绍西学—整理古籍,是商务振兴中华、服务社会的主要路数,但这四位一体是离不开商业利润的,其间蕴藏的出版理念和时代精神,显然值得后人仔细思量和体会。
一、扶助教育
张元济在加盟商务之时,即与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1]近百年后,陈原回忆道:“张元济办出版社,确实不是单纯为了出书,他是在办一个旨在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大学校’。”[2]张氏与商务其他灵魂人物所持的“教育救国”观念,对商务的影响极为深远。
编印教科书可视为商务“扶助教育”的典型行为,同时,它也是靠编印、发行教科书起家的。[3]陈叔通对此深有感触:“商务发财主要是靠教科书。”[4]据时人记忆,商务的各种教科书风行海内外。1905年,《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出版后,销数达10多万册。《共和国教科书》自1912年推出到1929年为止,先后出版了2 654版,重印300余次,销了7 000余万册。中华书局估计,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的教科书占有当时六成的市场。[5]
一些同时代人回述少年就学,从侧面印证了商务教科书的影响力。冰心说:“我和商务印书馆,有一段很长的学习和文字的因缘。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我在学认‘天地日月,山水土木’这几个伟大而笔划简单的字的同时,还认得了‘商务印书馆’这五个很重要的字。我从《国文教科书》的第一册,一直读了下去,每一册每一课,都有中外历史人物故事,还有与国事、家事、天下事有关的课文,我觉得每天读着,都在增长着学问与知识。”[6]可以这样讲,商务教科书伴随学生一起成长,从小学到中学,塑造出“终身的读者群”。[7]
工具书的编辑出版,也体现了商务对教育的重视。在张元济亲自策划下,1915年,我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问世,接着商务又出版了《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地名大辞典》和各色各样的中外工具书。1931年商务再出版《辞源》续编,1939年出版《辞源》合订本。[8]胡焕庸说:“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看到报人登载《辞源》出版了,什么需要知道的东西,在《辞源》里都会找到,因此我立刻买了一本,作为我的良师益友,到现在我还珍藏着这部书。”[9]
扶助教育的同时,商务更强调教育的普及,以文教服务社会。“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尤要。”[10]围绕出版,商务还尽可能致力于社会公益,开办艺徒学校、商业补习学校、工人夜校、同人俱乐部,设立扶助同人子女教育基金和上海国语师范学校,兴办图书馆讲习所,制造各种仪器、文具、玩具,拍摄电影。就这样,商务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继而向综合性、文化性出版机构转变,最终成长为一家集出版、印刷、发行于一身的大规模出版集团。所以,陈云在商务创建85周年之际为其题词:“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这是对商务极确当的评价。[11]444陈原也认为:“(张元济)从事出版,创办学校,拍摄电影,几乎可以说,为了实现‘开发民智,振兴中华’,他将当时能用上的传播手段都用上了。这种‘文化教育集团’的架势,就在今天来看也是超前的。”[12]
二、沟通中西
商务人一致认为编译书报“为开发中国急务”,是“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的重要途径。[13]因此,引进西方知识,传播新文化,并竭力保存传统文化,“谋沟通中西以促进整个中国文化之光大”[14],成为商务义不容辞的责任和重要的出版理念,这在其系列化的出版实践中得以证明。
商务一贯重视汉译科技和社会科学名著,在翻译外国作品方面不遗余力。如严(严复——笔者注)译名著,商务自1903年起,先后出版或重印《群己权界论》、《订正群学肄言》、《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原富》、《天演论》等8种,给予我国思想界极大的影响。叶圣陶就说过:“我幼年初学英语,读的是商务的《华英初阶》,后来开始接触外国文学,读的是商务的《说部丛书》
……至于接触逻辑、进化论和西方的民主思想,也由于读了商务出版的严复的各种译本……我的情况决非个别的,本世纪初的青年学生大抵如此。”[15]与严译社会科学名著齐名的,当推林纾翻译的欧美小说。1903年,商务首次出版林氏的译作《伊索寓言》。自此,林译小说收入“说部丛书”陆续出版,并又有选择地收入商务的《万有文库》、《新中学文库》、《新学制中学国语科补充读物》,后以《林译小说》为书名重新结集整套发行。[16]109
商务的译作,很多开风气之先,对近代文化和社会影响极大。钱钟书认为:“林纾的翻译所起到‘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公认的事实。他对若干读者,也一定有过歌德所说的‘媒’的影响,引导他们去跟原作者发生直接关系。我自己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17]
出版杂志是传播新文化的另一重要表现。张元济就任商务编译所所长的第二年,国内最有影响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创刊。从1909年起,商务又先后创办了《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少年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儿童画报》、《自然界》、《学艺杂志》、《社会月刊》等月刊9种,《英语周刊》、《儿童世界》等周刊2种;《国学论丛》、《哲学评论》、《经济学季刊》、《农业杂志》、《乐艺》等季刊5种;此外还办有半年刊《小学教育》、年刊《社会学界》。连《东方杂志》在内,共计出版杂志19种。这些杂志有商务自己编辑的,有由其他学术团体编辑而由商务出版的。在“一·二八”事变前这些杂志都按期出版,有的一直办到解放前才停刊。[8]商务的出版物着眼于全国,种类繁多,以致不管哪行哪业,都可以从商务找到自己需要、喜爱的书刊,其文化影响也遍及全国,几乎所有的著名作家都在商务出版的著作或杂志上发表过作品。
在引进新知识启蒙民众的同时,商务还着手较系统地出版善本古籍。这在商务历史上算是一个显著变化。商务出版过的大型古籍丛书包括:《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道藏》、《续道藏》、《道藏举要》、《学津讨原》、《选景宛委别藏》、《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景印元明善本丛书》等。[18]此外,商务还整理出版了多种单行本,例如《通俗编》、《恒言录》、《恒言广证》、《迩言》、《容斋随笔五集》、《困学纪闻》、《十驾斋养新录》、《陔余丛考》、《蛾术编》、《存稿》、《札朴》、《越缦堂读书记》;重印了《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二十二史考异》、《畴人传》、《畴人传四编》、《天工开物》等。商务的古籍整理工作,正像张元济所说的那样有三个目的:一为抢救文化遗产,使其免于沦亡;二为解决学者求书的困难,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三为汇集善本,弥补清代朴学家所未能做到的缺陷。[19]
三、营业主义
商务人时常自誉:“百年来,我馆虽有‘商务’之名,却从未唯利是图。”[20]此言诚然不虚。商务的创始人与继承者,都极看重出版业推动社会的作用,强调社会效益。但是,另一个重要事实也不能被忽略:商务历任主持者都严格遵循营业主义,“从来不出亏本书”。毫无疑问,以商业方式努力于文化教育事业,才是他们的旨趣所在。因为“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21]4,商务人不是圣人,不可能免俗。
在创办之初,商务以编印中小学教科书为最主要的业务。这是因为教科书销路广,最能赚钱,是当时一切出版社不能不努力开展的业务。[22]教科书之外,商务大量印行古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此类图书不必付稿费,编辑亦简单,而且又有相当不错的销路,正是获取利润的终南捷径,仅《四部丛刊》一种收入即达百万余元。[23]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商务扶助教育、传递新知,起源于经济上的考虑。
而且,商务一贯坚持“在商言商”的原则,力图避免与政治抵触。后期负责人之一李宣龚1950年在向股东会报告时谈到:“此前业务,向来避免和政治接触”,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损害自己的营业,也就是“采取有利于自己的出版方针”。[24]作为一家民间出版企业,一旦因出版为当局所不能容忍的出版物遭或罚款或查封,必招致巨大损失。袁世凯复辟帝制前后的教科书出版一事,可视为商务“趋时”的显例。1915年夏秋之际,“洪宪帝制”已经是呼之欲出,当时,商务印书馆刚发完秋季课本,正筹划次年的春季课本。张元济为此大费周章:一旦帝制成功,小学课本名为《共和国教科书》,便与国体、政体不符,就得报废;如果继续观望,春销时无书供应,就会失去商机。几经权衡,张元济决定停印《共和国教科书》,删去“平等”、“自由”等与帝制明显冲突的字眼,将课本更名为《普通教科书》,并呈报教育部,请求批准。此外,张还特意委托傅增湘代为活动。帝制宣告破产后,张元济则立即通告各地分馆,“将普通速即销去,勿退回”。5月22日,又命陈叔通起草上教育部呈文,声明复用共和民国书事,并向军务院递禀,请求推行共和教科书。[16]75-76如此反复无常,甚至出尔反尔,实际上只是着眼商机,与政治立场毫无关联。
秉承“在商言商”原则,对身份敏感者的著作,商务一律不出版、不代销。康有为,陈独秀,孙中山等显赫一时之人都曾有过被商务拒绝的经历。1941年9月30日,日伪印发《上海租界内中国出版界的实况(二)》,对商务、中华、世界三大出版社在抗战爆发前的表现作了较客观的陈述:“保持着与国民党的联系,又采取有利于自己的出版方针,出版了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古典书籍之类的东西,它大体上维护着政治统治,又不出版富于激进的带有煽动性的书籍。”[16]78
营业主义必然导致商务“有所不为”,局限性自不待言,蔡元培就有异议:“商务之纯粹营业主义,不肯稍提赢余以应用于开辟风气,且为数年以后之销路计,亦可谓短视矣。”[25]但回归具体的历史场景,可以发现,商务之所以坚守营业主义,实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舒新城在谈到中华书局的出版方针时说:“中华书局在形式上与性质上,虽然是一个私人企业机关,但对国家的教育和文化同时也想顾到。因为要谋公司的生存,不能不注意营业;同时觉着过于亏本的东西,又非营业所宜。在这‘左右为难’的境况中,我们只好两面都‘打折扣’。这就是说,凡属于营业有重大利益,而与教育或文化有妨碍者,我们弃而不作;反之,某事与教育或文化有重大关系,而公司要受较大损失者,也只得弃之。换句话说,只求于营业之中发展教育及文化,于发展教育文化之中维持营业。因此,我们在营业上无惊人之成绩,在教育与文化上也无特殊的贡献,而成为所谓中庸之道的‘中’字了。”[26]形式与性质都大体相当的商务,也只能左右逢源,无法例外行事。
不过,坚持营业主义却为商务生存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减少政府、政治的注意和干涉,为形成其相对独特的出版风格提供了可能。商务人曾自称,商务只出版好书,没有出版过一本不象样的坏书。[27]如果这是说1949年后的情况,那需另当别论;如果这是说1949以前的情况,则是抬高了商务这样一家私营出版社。实事求是地说,商务在1897年到1949年间出了不少好书,也出了不少平庸的书,但没有出很坏的书。在旧中国出版格调普遍低下的情况下,商务的品格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这是不争的事实。[16]83-84它以正当的出版经营方式为读者服务,为民族积累和保存了很大一笔文化财富,“虽然不是最前进,但还不是很落后”[11]445。
虽说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要的价值追求。[21]商务在追求经济利润的过程中,始终兼顾社会效益,强调义利合一,“于营业之中发展教育及文化,于发展教育文化之中维持营业”[26]。王建辉曾以“文化的商务”为题,来说明商务的两面性:“文化的商务的含义既是指商务进行的出版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事业,同时也是说把文化作为一种商务来动作。它是作为产业出现的近现代出版业在形成过程中的文化经营和商业动作的结合。这种结合是文化走向现代必不可少的。经营企业而注重文化性,经营文化而注重商业性,是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发展理念。”[28]此可谓一语中的。
[1]张元济.东方图书馆概况·缘起[G]//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1.
[2]陈原.陈原书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45.
[3]谢振声.郑贞文先生与商务印书馆[G]//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89.
[4]陈叔通.回忆商务印书馆[G]//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35.
[5]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16-217.
[6]冰心.我和商务印书馆[G]//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12.
[7]于卓.我和商务印书馆[G]//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447.
[8]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M].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5.
[9]胡焕庸.我和商务印书馆[G]//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07.
[10]周其厚.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2007:13.
[11]王天一.我和商务印书馆[G]//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444.
[12]侯样祥.商务百年访陈原[G]//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93.
[13]杜亚泉.记鲍咸昌先生[G]//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9.
[14]何炳松.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G]//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37.
[15]叶圣陶.我和商务印书馆[G]//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02.
[16]张学继.出版巨擘:张元济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109.
[17]钱钟书.林纾的翻译[M]//钱钟书集·七缀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92.
[18]王绍曾.记张元济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办的几件事[G]//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31.
[19]许振生.商务印书馆与古籍整理[G]//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568-572.
[20]商务印书馆一百年[G].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68.
[21]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张静庐自传[M].上海:上海书店,1984:04.
[22]陈岱孙.我与商务印书馆[G]//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417.
[23]吴方.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173.
[24]王建辉.出版与近代文明[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260.
[25]高平叔,王世儒.蔡元培书信集[G].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208.
[26]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M].北京:中华书局,2002:112.
[27]杨宪益.只出好书的商务印书馆[G]//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93.
[28]王建辉.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03.
[责任编辑朱 涛]
C93-03
A
1009-1513(2010)02-0057-04
2010-02-27
赵建国(1972—),男,湖北当阳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