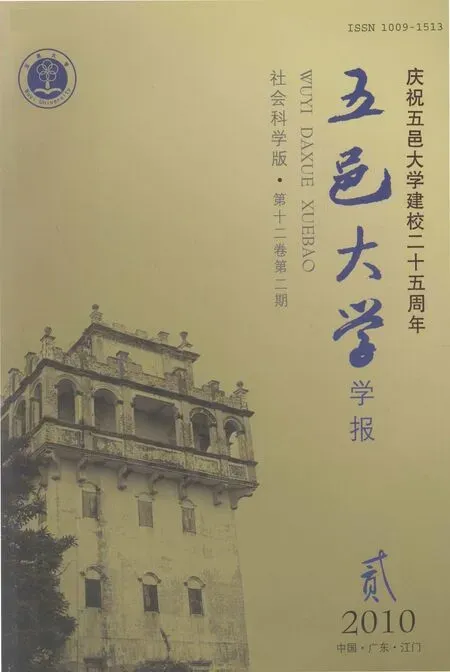许之衡词学活动考论
2010-03-21谢永芳
谢永芳
(黄冈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许之衡词学活动考论
谢永芳
(黄冈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许之衡是近世广东中后期词坛上的名家,其词学活动主要包括创作《守白词》、与当世词坛名家的词学交游以及编著词学启蒙专书《词选及作法》。考察许之衡的词学活动,可从侧面体认近世中后期广东词坛的去边缘化进程。
许之衡;守白词;词选及作法;近世广东词坛
许之衡(1877—1935),字守白,号饮流斋主人、曲隐道人,室名饮流斋。本籍浙江仁和(今属杭州),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康有为入室弟子。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副贡。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曾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教授。著有《守白词》、《中国音乐小史》、《词选及作法》、《曲律易知》、《声律学讲义》、《曲史讲义》、《中国戏曲研究讲义》、《饮流斋说瓷》以及《玉虎坠》、《锦瑟记》、《霓裳艳》等传奇。
许之衡以曲学鸣世。1917年,吴梅应聘为北大教授,许之衡得与吴氏及李释勘、刘凤叔订交,共同研讨曲律。1922年,吴梅南归,向校方荐许氏以自代。次年,许之衡担任北大国文系曲学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许氏精心抄录或改订明清传奇名著如《金丸记》、《五福记》、《潜龙佩》等34种,向为治曲者所重。许之衡又精通词学,是近世广东中后期词坛(1840—1948)①名家,然词名为曲学之名所掩。兹勾稽史料,从创作、交游、研究等方面对其词学活动予以考论。
一、声誉甚隆的《守白词》
许之衡所著《守白词》有两稿,甲稿一卷印于1929年。该稿行世之先,即已颇得词坛耆宿如朱祖谋等人好评:“丽以则”;“把臂汴京,其次者亦不堕金源以下”;“不难独树一帜”;“以两宋为融合,以清真为归宿”。[1]同年,许之衡自序《守白词》乙稿一卷,并于次年付印,凡64阕。此稿专收和周邦彦词作,故一名《步周词》。朱祖谋等亦深为推许:“深得清真法乳”;“守律至严”;“意深而能透,辞碎而能整”;“能从最细处入,从最大处出”;“学清真得其沈著”。[2]
两稿中名作有为叶恭绰《广箧中词》卷三所录入者,如《摸鱼儿·见三海捕鱼有感》:
是何年、龙宫纵壑,潜鳞翔溢如许。鲛丝织就千重网,好趁月明抛取。闻客语。道劫火昆明,尚有临渊处。遥望玉宇。见碧海铺银,鸣榔喧笑,乐意到渔父。苍纹额,指点金牌非误。旧时銮液曾贮。探珠岂藉垂纶手,满载合装柔橹。愁月去。便捉得锦鲸,难觅神仙府。鱼龙漫舞。君不见繁华,御园平乐,阅代也尘土。[3]
全阕以小见大,由此及彼,感慨遥深,适如叶恭绰所评:“可入《词林纪事》。”叶氏并非轻易以此评语许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春,广东词家桂文耀闻知虎门败讯,心情抑郁而作《扬州慢》(末丽鬟风),对故乡遭受战火蹂躏的痛苦叹息溢于言表。叶恭绰于同书卷一中品曰:“哀时感事,悲愤弥襟,与下一首(《满江红·悼荔》)可同入《词林纪事》。”由此处用语,可以判定上引许之衡词也是“哀时感事”的,而实际上,其内蕴的感情烈度较之桂氏词有过之而无不及。又如《八声甘州·团城古松和次公》、《一萼红·三海启禁,偕文叔同游》,两阕均幽愤盈襟,借物事而遣怀,词法谨严,的确深得宋人风调尤其是清真词神髓。
许之衡是近世中期广东文坛名宿许其光之孙,学有所自,深造有得,其所以能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相当成就,决非偶然。据《番禺县续志》卷二十记载,许其光遇事敢言,接物谦退,又曾与本土名士谭莹、沈世良、金锡龄等共结山堂吟社,唱酬繁密。[4]当然,对于许之衡的《守白词》乙稿,已故著名词学家吴世昌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吴先生在未完稿《清人词目录》中说:“此集虽亦和周,但不如方、杨、陈三家之悉依周集词调次序,其排列殊为杂乱,小令全不和,慢词亦不全。”[5]所言也是客观事实,而非吹毛求疵。吴氏又有言:“眉端批语多谀词滥套,了无新意。”[5]此“批语”可能是当时或后来读到此集者(类似于评点是编的长洲药庵居士)所加,纯乎一家之见,兼以囿于一时风尚,甚或乃随意应酬之语,褒扬无度,滥调重弹,本无足多怪。凡此,谅不至大损于许之衡《守白词》在彼时彼地日渐昌隆的声誉。
二、与当世名家的词学交游
经过查检多种总集、别集、选本、方志、日记、书函等文献资料,可以考得许之衡的词学交游对象至少有19人,其中粤籍词人6位,外籍词人13位。兹将其生平、交往简况考列如下:
其一,粤籍交游对象。
邓万岁(1883—1954),原名溥,字季雨,号尔雅,东莞人。有词见林葆恒《词综补遗》卷九十二。
张锡麟(?—1931后),字务洪,别号虫天生、贲南拙夫,番禺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拔贡生。有《榘园词钞》一卷。
曾习经(1867—1926),字刚甫,号蛰庵,揭阳人。梁鼎芬弟子。有《蛰庵词》一卷。
陈洵(1870—1942),字述叔,号海绡,新会人。有《海绡词》、《海绡说词》。
徐礼辅(生卒年不详),字儁村,香山人。有《渌水余音》一卷。
文叔(生卒年不详),或为伍文叔。伍氏与谭颐年、戴翰风等为陈洵在广东本地的词友。
许之衡有《高阳台·唁邓尔雅悼亡》、《丁香结·某君与某郎红毹合歌,张榘园有词赋赠,约同作,步片玉韵》、《多丽·和榘园听歌有赠》、《百字令·寿曾刚甫六十》、《绮寮怨·闻陈述叔北来成咏》、《一萼红·三海启禁,偕文叔同游》。许之衡序《渌水余音》有云:“(徐礼辅)复得吾友邵次公词宿与之切磋。”[6]
其二,外籍交游对象。江苏如皋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瓯隐,亦号疚斋),江阴夏孙桐(1857—1942,字闰枝,与朱祖谋为儿女姻亲),苏州王季烈(1873—1952,字君九,别号螾庐,光绪甲辰(1904)进士),浙江归安朱祖谋(1857—1931),淳安邵瑞彭(1888—1938,字次公),永嘉夏承焘(1900—1986,字癯禅),江西新建夏敬观(1875—1953,字剑丞,号吷庵),宜黄黄福颐(?—1933后,有《词庵词》四卷),广西临桂况周颐(1859—1926),湖北蕲水陈曾寿(1878—1949,字仁先,别号苍虬,曾任广东道监察御使),湖南宁乡陈家庆(1904—1970,号碧湘,徐英(澄宇)室,吴梅弟子),张芋庵(不详),贵州息烽姚华(1876—1930,字崇光,号茫父)。
冒广生评《守白词》甲稿:“大集诸词能通消息之微,此昔人所谓丽以则者”,许之衡有《蕙兰芳引·和冒鹤亭丈沪上赠琬华(梅兰芳)作》。朱祖谋评《守白词》甲稿:“托旨深故无浮藻,选言洁故无滞音,高朗之致,把臂汴京,其次者亦不堕金源以下。把卷三复,唯有低首”;评《守白词》乙稿:“思窈而沈,笔重而健,是深得清真法乳者”。夏孙桐评《守白词》乙稿:“守律至严,字字熨贴,会心处独有千古”,许之衡有《兰陵王·和夏闰枝丈咏柳》。夏敬观评《守白词》乙稿:“意深而能透,辞碎而能整”。许之衡有《浣溪沙·和况夔翁听歌词》。邵瑞彭有《渡江云·上巳之会,守白得“当”字倚此调,予拟作》,又评《守白词》乙稿:“守白能从最细处入,从最大处出”,许之衡有《八声甘州·团城古松和次公》。陈曾寿评《守白词》乙稿:“绵密之中时饶远韵,学清真得其沈著,无一字落近世町畦”,许之衡有《征招·题陈家庆女士〈碧湘词稿〉并赠别》。王季烈评《守白词》甲稿:“小令间有一二语直摩南唐宋初之垒,长调则多变徵之声。规模特立,由此锲而不舍,不难独树一帜矣。”黄福颐评《守白词》甲稿:“守白论作词之法,云以大、重为主脑,以两宋为融合,以清真为归宿。今观所作,殆骎骎骎乎能副所言矣。”许之衡有《丹凤吟·和芋庵白门感春》、《扫花游·同张芋庵游万生园》。姚华有致李释戡书札一纸,函中所谓“前和守白词”,当指姚氏所和许之衡词,或姚氏所和者乃李释戡和许氏词作。
许之衡在近世中后期广东词坛词学交游不是最为活跃,不过,由于其处在词体创作最为成熟之际,又长期生活在当时国内词学中心之一的北京城内,所以他得以与其时叱咤词坛的风云人物甚而一代词宗朱祖谋等时相过从,这成为许之衡词学交游的重要特点。近世中期广东词坛建立在以血缘、里籍和师友关系基础上骤然频密的词学交游活动,使本土词人拓宽了眼界,不同程度地意识到走出粤东、主动加强与主流词坛联络、沟通的重要性。[7]许之衡便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员。
在本土之外广阔的词学舞台上,近世广东词人通过与外籍词人盛况空前的词学交流,对广东近世词坛的去边缘化进程创造了重要的外部条件,产生了直接而显著的推动作用。正是得力于广东词坛与当时词学中心的紧密联系,广东词人在近世中后期愈来愈受到关注和重视,岭南词风愈来愈被理解、接受和认同,广东词坛的地位渐渐有了实质性的提高,对近现代词学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如果从这种视角观察,即把个体零散、片面的词学交游活动置于宏观、统一的整体中去对待和把握,那么,许之衡词学交游的价值会得到更为准确、充分的评估。
三、《词选及作法》的特定价值
1929年,许之衡接替已故词学家刘毓盘,讲授“词选及作词法”课程,《词选及作法》当在课程讲义的基础上编成。其著述缘起、目的等如许氏在《绪论》中所言:“论作词之书向无专著,仅散见于词话、笔记中。近日始有专论词学书籍,然便于研究者尚无善本,如《填词百法》等书,虽然供参考,但徒占篇幅、未道着实际之病不能免。故将此等书全部读毕,未必即能作词也。愚著此篇,拟力矫此弊,于古人作词之方法,昔人所未言或言而未尽者,一一以最新科学之方式解明之,使吾国此种文学完全露出真相。而学者将此编阅毕,再专研古词,聪俊者多则一月,少则十余日,必然执笔作词,斐然成章。此则愚对于斯学之贡献。此种目的必能达到,似非夸言也。”[8]
该书对关乎词体创作和词学研究的诸多方面均有程度不同的涉及,可以看作前述词学交游活动深入浅出式的产物,与民国期间同时或先后出现的若干部词学著作相比,尚有一定特色。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尽管在现在看来,很多已经变成了词学常识,但在当时的特定时期,考虑到其所针对的是一群特定的讲授、阅读对象,这些观点确实具有相当的价值,并且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譬如许之衡在“绪论”中认为,应“将中调并于小令”。这与梁启勋在《词学》一书中表露出的观点相同。[9]这种提法是对明人所创以字数多寡为准三分词调为小令、中调、长调的反动,尽管不能算彻底,但仍然在当时得到了一些人的响应,甚至在20世纪中后期这种观点仍有一定的市场,如村上哲见在《唐五代北宋词研究》②、黄文吉在《北宋十大词家研究》③中都持此种观点。
又如,在“四声之区别”一章中,许之衡以导师般的口吻说:“惟有取字练习,练习稍多则自然了然”;“初作时,亦不必尽泥”。许之衡是有这个资格的,参考前述黄福颐评其《守白词》甲稿所云,洵非虚誉。又如,在“词谱检用法”一章中,许之衡分别指出了几种常见词谱的缺憾:“《钦定词谱》颇不易购”;“《天籁轩词谱》即《词律》之缩影,颇便检查,但无注明可平可仄”;“《填词图谱》误者太多”;“白香词谱旁注平仄,亦不尽可靠”;认为“究以《词律》为比较妥善也”。在“词韵检用法”一章中,他首先断言“坊间所见《词林要韵》题为菉斐轩刊本者,系后人伪托”,接下来指出“《词林正韵》分部过多,亦有繁琐之病”,并提出最好用《天籁轩词韵》。大抵都是来自自己的直接阅读与创作体验,可谓有得之言。
又如,在“论研究捷法宜先分类”一章中,许氏认为,分类的好处在于:“一则划分小令与长调,由少字句渐进于多字句,以便学者研究也”;“一则分门别类,各派兼收,毫无偏见,任学者各就所好而研究之也。”又说:“以人分者,多重于客观方面,亦有因人存词之弊;以类分者,则重于主观方面,全为学者之获益起见。”并认为,在具体研读过程中,要先读选本,再读专集;在选本中,《花间集》、《花庵词选》、《绝妙好词》、戈载《宋七家词选》、《宋词三百首》五种本子要先阅读。这与陈廷焯“先多读唐宋之词,以植其基”[10]的思路是完全吻合的。分类,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本来是普遍适用的,许之衡在这里单独拈出来,进行介绍和分析,与梁启勋《词学》一书也相类似,应该是当时词学研究中普遍注重词学研究方法论的一种自然的表现。
又如,在“长调总论”一章中,许之衡承继周济重新强调了宋词研究中的一个经典命题:“南宋有门径,有门径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径,无门径故似易而实难。”另外,他还说“研究词学,宜先破除推崇一家之见”,这也被证明是一条不刊之论。在“论标准”一章中,许之衡认为要“以雅正为归”④,并且认识到“厉(鹗)、项(鸿祚)其实非纯浙派”,而郭(麐)则“专提倡浮滑一路”。在“论四要”一章中,许之衡提出的“大、重、新、雅”,事实上是本于王鹏运、况周颐而稍事修正的结果。他同时论到,常州词派“论则高、大”,而创作成绩却赶不上浙派,因为他们不知道“北宋者多用实字领起,多用厚重之字”,“所知者,不用词眼、数句接连而下”而已。对于清代词人及词派的认识均不为无见。
又如,在“历代词家略论”一章中,作者主要是从创作的层面来谈的,这一点也与梁启勋基本相同,说明当时的词学家在重视词学研究的同时,对词的创作实践指导也是高度重视的。只不过,这些见解是感性、直接、具体的,并未上升到理性的自觉总结词体创作理论的抽象思维阶段。此前,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便拈出“词境”、“词心”两个核心范畴深刻阐释了词体创作理论的相关问题。[11]许之衡则单就创作长调而言,提出了应该经常阅读、浏览和不宜入手的词家名单。其中特别指出刘克庄“驰骋太过,多类于清人词,为入手最忌者也”。同时,他也谈到了清代词学,认为清人词话值得认可的只有谭献的和况周颐的,“周济尊辛抑姜,殊未允”,等等。评骘用语虽不免锋利,却也不失为度人金针之言。
许之衡在《词选及作法》一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选录词作,论说与赏析并重,一以教示作词之法为旨归。其选录词作的做法,跟梁启勋的《词学》十分接近。许之衡的词学研究文字还有1930年发表于《北大学生》第1卷第5、6期上的《研究宋词的我见》、《唐宋乐曲内容考略》两文,以及刊载于1934年《词学季刊》第2卷第1号上的《与夏瞿禅论白石词谱》等。
注释:
①参见拙文《粤东词史论纲》,载于《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②参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村上哲见所著《唐五代北宋词研究》。
③参见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黄文吉所著《北宋十大词家研究》。
④此点,许之衡序徐礼辅《渌水余音》亦可参:“吾粤夐隔中原,僻处南峤,声名文物,未能与大江南北相颉颃。而倚声一道,作者尤尠。赵宋一代,惟南海刘随如名动海宇,今百咏一编虽已散佚,幸《中兴以来绝妙词选》采辑尚多,足资讽咏。此外,若李文溪词搜于汲古阁,赵玉渊词刊于四印斋,皆足以骖之靳,余则罕闻矣。有清以来,斯学几绝。迨至同、光后,始稍稍复振,其间揖让风骚、驰骋坛壝者间有人,然求如刘随如词之冲雅,殆犹未易觏也。”
[1]许之衡.守白词:甲稿[M].民国十八年北平石印饮流斋丛书本.
[2]许之衡.守白词:乙稿[M].民国十九年北平石印饮流斋丛书本.
[4]叶恭绰.广箧中词[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691-692.
[4]梁鼎芬,等.番禺县续志[G].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68.
[5]吴世昌.清人词目录[G].稿本.
[6]徐礼辅.渌水余音[M].民国十九年香山徐氏刻小红雨楼丛刊本.
[7]谢永芳.近代风云与岭南词学[C]//古典文献研究:第九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8]许之衡.词选及作法[M].民国北京大学出版社铅印本.
[9]梁启勋.词学[M].民国二十一年北平京城印书局铅印本.
[10]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词话丛编: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3936.
[11]况周颐.蕙风词话[M].//词话丛编: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4407.
[责任编辑文 俊]
I206.5
A
1009-1513(2010)02-0009-04
2010-01-06
谢永芳(1969—),男,湖北天门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词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