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已踏遍,翰墨有余香——怀念民族学家李绍明
2010-03-02伍婷婷
○伍婷婷
2009年8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我正在昆明家中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启程回京,突然接到四川大学石硕教授托人打来的电话,称李绍明先生病危,希望见我一面。我顿时愕然,转而哀伤阵阵袭来。
然而次日昆明赴成都的机票已经售罄,我和在北京的丈夫简单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按原计划先回北京,当日再一起飞赴成都。当我辗转赶到华西医院李先生的病房时,已是深夜两点,先生已经睡着了。守候在病房外的每个人都面色凝重,不过对我的到来,大家又显露出了一丝欣慰。这个时候,李先生的心愿显然就是每个人共同的心愿,他提出要见的人,大家都努力去张罗联系。第一天和第二天,我守在医院的过道里,只要先生一醒来,大家就会很默契地在第一时间通知我,希望我俩能够说上话。可惜这时我们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随意地聊天了。由于表达困难,李先生留给我的最后几句话,大都含糊不清,倒是专门照顾他的医院护工刘师傅,后来向我转达了他的嘱托。第三天,也就是8月20日清晨,噩耗传来,先生驾鹤西归,享年76岁。
我实在无法原谅自己的疏忽大意,导致了和李先生的诀别是如此仓促。李先生近两个月来的身体状况,我是大致了解的。5月下旬我去成都开会,见他气宇间满是疲惫,当时并没有太在意,只当是舟车劳顿所致。因为他刚从南方丝绸之路考察回来,期间甚至在印度的阿萨姆邦一带逗留了十多天,当时正值印度酷暑难耐之际;一回来又马不停蹄地去参加各种会议和答辩。我婉言劝他不可过分劳累,纵是老骥伏枥,也不必过于奋蹄。我们相约7月底到昆明再见,届时第16届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将在那里举行。这个会我听他叨念过多次:“我是一定要去的。”孰知到了6月下旬,就听说他身体不适住院了,昆明之行也在反反复复之后最终取消。电话里先生甚是遗憾,不过照旧一副乐天派的样子:“胆囊炎,不用担心,再做一次手术就好了。”我依旧劝慰他安心养病,说一有机会就去成都探望他,并把我的博士论文带来,请他当面批评。谁料先生其实是肝癌晚期。我现在无法确知他自己当时是否已经了然于胸,按说至少应当是有所察觉的,可他电话里言词之泰然达观,让我未起丝毫疑心。电话联系之后约一个月,等我匆匆入蜀的时候,竟是最后一别。
当我和丈夫郑少雄在李先生的灵堂前鞠躬时,都禁不住涕下沾襟。看着悬在正中央的遗像,几年来我们和李先生交往的种种细节因由都浮上心头,历历可见。郑少雄因为博士论文研究四川康区的关系,曾屡屡到李先生府上请益,得到了先生的悉心指点。每次谈完话,先生和师母必定留饭,或者在家吃,或者三人慢悠悠地上街。先生和师母把臂同行,郑少雄则紧随其侧,文殊坊周围的大街小巷,算来已经走了好些遍。每思及此,又欲潸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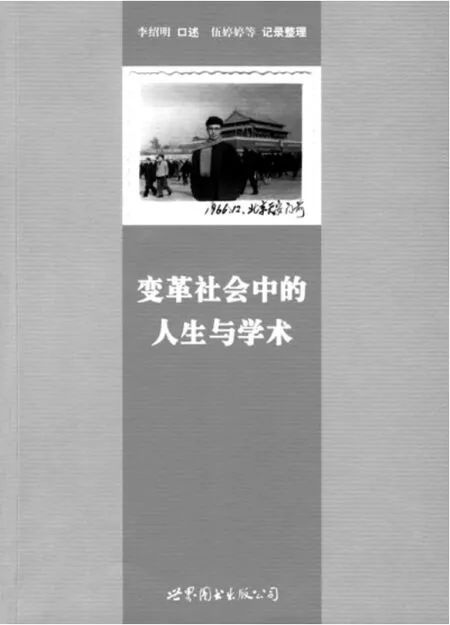
《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李绍明口述,伍婷婷等记录整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6月版,29.80元。
而先生于我,除了传道、解惑之外,更欣然应允我将他本人作为对象去研究。博士论文大概是一种“不近人情”的学术研究工作,无疑我需要抛开个人好恶,把李先生置于国际和国内人类学史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和分析。我写作论文的主旨,固然不是为李先生作传,不是对李先生功过得失的评价,而是试图通过对他的人生经历进行个案研究,揭示西来的人类学、民族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内地的特殊面貌和观念转型,但尽管如此,同行、尤其是师辈们仍然颇有些担心:人都还好端端地活着,怎么研究?言下之意就是,不管你如何极力回避,间接的、隐晦的褒贬总是难免的。老行尊还在,看你小毛头怎么“信口雌黄”?
起初我也有些惴惴不安,庆幸的是我的导师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鞭策,尤其难得的是,李先生主动找到我宽慰道:“你放心写,我不看的。”后来,李先生除了应我的请求,陆续寄来几本书以外,果然绝口不问我论文的进度,更不要说要求阅读之类的了。老一辈学者的风度,由此可见一斑。论文答辩之后,一切已经尘埃落定,自觉这个研究不很成功,和师长们的期许相距甚远,但其实我还是很想请李先生批评的。只可惜自己生性散漫,屡屡动起寄出的念头,又想着有机会面呈,这样犹犹豫豫,竟拖了下去。李先生一副笑眯眯的好老头模样,总是说“:不急不急,你再沉淀沉淀。”一念之差,遂成永痛,到李先生故去,要送给李先生的这一本论文,仍然搁在我的书架上,渐渐蒙上了薄薄的一层灰尘。
拂去浮尘,留给我的,是对先生无尽的追思。
1950年先生进入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民族学专业,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异于今人的是,由于院系调整,以及新时期民族工作的迫切需要,李先生四年之间竟然辗转三所高校,后两者是四川大学历史系及西南民族学院民族问题研究班。这个经历使得他的知识体系杂糅了诸家之长,学科领域也从民族学跨越到了民族史学、民族政治学。大学毕业后的10年,是李先生人生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他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足迹遍及川滇黔三省,并参与《彝族简史》、《羌族简史》的编写工作。正是这个难得的人生机遇,奠定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总体认识,形成了对该地区少数民族研究的通盘考虑。历经“文革”时期的困顿之后,70年代末开始,先生迎来了学术生涯的又一春。他极力推动“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创立,把西南八省的学者紧密团结起来,尤为重要的是,由他和童恩正领导、始于1982年的“六江流域民族科学考察”,是新时期起步最早、规模最大、成果最丰的田野考察活动之一。这一活动得到了费孝通等前辈的大力支持,并且直接呼应了费老晚年对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研究“分族写志”思路的反思。李先生力倡“大西南”的研究理念,主张将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迁徙、社会交往、文化变迁置于区域历史地理空间内进行考察。其深意在于,学者不应孤立地研究某一少数民族,而必须首先理解各民族互相型塑的过程与结果。李先生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是,七八十年代之交,组织编写《凉山奴隶社会》一书,重新深入讨论了凉山社会性质的判定问题。除此之外,在李先生等人的呼吁下,藏学、壮学、彝学、傣学等学科今天都已蔚为壮观。
民族学原是西洋的学问,探究海外异族的社会、文化之种种,晚清民国之际传入中国,最初的研究者多为来华的传教士、探险家或职业学者,其研究范围涉及中国境内各族。中国的民族学家如果从吴文藻、潘光旦等前辈算起,中间经费孝通、林耀华这一代,李先生可算是这个学科的第三代人。由于所处时代的因素,李先生所学的,应当有苏维埃学派的特色。他擅长依据摩尔根诸人的社会形态进化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框架去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与文化;同时,出于那一代学者共有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他们进行民族研究的初衷和手段大都自觉服务于民族-国家建构的需要,而非仅出于对“他者”的兴趣和对社会、文化理论本身的探讨。但是,拥有教会背景的华西大学的教育也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注重边疆民族的实地研究,并且继承了民国以来本土民族学家对历史因素高度关注的学术特征。当然,民国时期民族学家对历史材料的解读,也许比李先生一代更具有文化相对主义的特征。今天,尽管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各种潮流看似争妍竞艳,但李先生他们继承和发展出来的这种史志结合的研究风格,越来越受到年轻学者们的重视和借鉴。这是我博士论文研究试图阐释的道理之一,但不知在天国的李先生是否会以晚辈为然?

李绍明先生在四川羌区调查
李先生并非纯粹的书斋式学者。一方面,他毕生奉行田野调查,也即“踏遍青山”;另一方面,他著述甚勤,泽被后学,堪称“翰墨留香”。尤其难得的是,李先生为人谦和宽厚,处世通达历练,因此颇能得人服众。曾与他共事多年的学界前辈马曜先生曾经说:“绍明治学严谨朴实,一如其为人,尝默察其于出处去就之际,约己让人,故能得众多助。(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成立十余年来,内部始终保持团结一致,堪称‘人和’。这是同绍明折中协调分不开的。”李先生毕生以研究为主,教学为辅,因此真正受业的及门弟子寥寥无几。但是,李先生生命中的最后几天,每天默守在病房外的人,常以数十计,其中多人,实际上早已经各自气象俨然,但仍然对李先生执弟子之礼,恭敬有加。他们每日朝至夕去,为的是陪伴先生最后一程。此情殷殷,动人肝肠。
先生尝说:“历史的发展必然把一个人推到某个风头浪尖。在这个浪头上要做什么事情,有时候你可以选择,有时候个人是不能选择的。但既然已经把你推上去了,你就去做好这些事情。”李先生做到了,因此他逝后哀荣备至。
先生唯一的孙女,2009年秋季刚升入大学,选择了社会学专业。她说,她们学校所有的专业里,这个学科是和民族学最接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