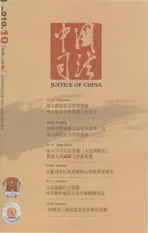《律师法》的迷途及其证据法进路*
2010-02-15王进喜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法学博士北京100088
王进喜(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法学博士 北京 100088)■文
《律师法》的迷途及其证据法进路*
The L aby rin th of the'L aw yers'L aw'and theW ay-ou t th rough the Evidence L aw
王进喜(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法学博士 北京 100088)■文
2007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律师法》进行了修改。在诉讼权利方面,修改后的《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相比,其修改主要表现在赋予或者更充分地赋予了律师四方面的权利:(1)会见权。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2)调查取证权。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3)阅卷权。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4)法庭上言论豁免权。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
《律师法》的上述修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律师法》的修改对于解决"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有利于完善律师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促进民主法制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依法治国;其次,这一修改将促进现行侦查模式的改变,进一步增强了侦查活动的公开性、诉讼化,促进侦查模式的转变。然而,由于这些修改缺乏相应的机制建设,因而缺乏操作性,在笔者看来,其宣示意义大于实践意义。今年6月1日起新《律师法》实施后广大律师在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等方面面临的窘困局面,对此作出了直接印证①例如,可参见陈虹伟等:"新律师法实施一周年:不能在拒绝贯彻中去等待完善",《法制日报》,2009年6月4日;尹恒:"律师维权,任重道远---写在《律师法》实施一周年之际",http://www.acla.org.cn/pages/2009-5-22/s52024。htm l,2009年7月1日访问。。《律师法》甚至被称为一部遭到"打折"的法律,甚至有学者哀叹《律师法》已经"夭折"②参见汪海燕:"一部被'折扣'的法律",《政法论坛》2009年底2期。。由是观之,新《律师法》实施前对这些修改的相应赞誉,大都害了严重的幼稚病。实务部门的部分观点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刑事诉讼法》的位阶高于《律师法》的位阶,《律师法》不能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尽管2008年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政协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1524号(政治法律类137号)提案的答复"中说:"依照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在不与其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修改和补充。新修订的《律师法》,总结实践经验,对《刑事诉讼法》有关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权利的有些具体问题作了补充完善,实际上是以新的法律规定修改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此应按修订后的《律师法》的规定执行",这一答复对此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然而,从问题的根源看,根本不是《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效力高低问题③关于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效力高低之争的讨论,可参见樊崇义、冯举:"新《律师法》的实施及其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中国司法》,2008年第5期;田文昌:"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互动与衔接",《法学》,2008年第7期;万毅:"直面新《律师法》的缺陷与不足",《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一方面,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对《律师法》在维护公民基本权利方面的作用认识不足,因而执行新《律师法》的自觉性不足④例如,有观点认为,"《刑事诉讼法》被称为'小宪法'、'宪法的施行法',所规定的皆是公民的基本人权,而《律师法》仅是一部行业法、组织法,所规定的仅是作为一个社会职业的律师的执业权利等,两者在效力位阶上明显存在着高下之分,我们怎么能够仅仅因为《立法法》对此未作明确区分便否认两者在效力位阶上的差异呢?"万毅:"直面新《律师法》的缺陷与不足",《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然而,《律师法》中关于律师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主要是为了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而非为律师本人。从这个意义上将,《律师法》同样具有宪法维度,同样是宪法的施行法。当然,从《律师法》的体例来看,确实包括了律师管理体制的内容,但是仅仅据此就将《律师法》视为不过是一部行业法、组织法,则未免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另一方面,新《律师法》关于律师权利的规定缺乏救济机制,可操作性不强。换言之,即使在今后的《刑事诉讼法》中把新《律师法》的内容一字不差照搬过去,律师的"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问题也不会有根本性的改观。未来如何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行补牢之举,强化律师会见权、调查取证权和阅卷权应当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持续关注的问题。
本文将围绕律师权利的操作性展开论述。本文认为,解决律师执业活动中的上述"三难"问题,关键在于以证据法原理为指导,完善律师权利的操作环节,构建上述权利的救济机制。
一、调查取证权的救济
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指律师在办理法律事务过程中依法向有关单位或个人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其后制定的1996年《律师法》第31条则相应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许多问题。许多观点认为,辩护律师收集证据必须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显然增加了律师取证的难度;其次,这造成了控辩审三方极不平等的诉讼地位⑤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5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而辩护律师收集证据受到限制,相比之下极不相称。;再者,有关被害人提供的证人的证言收集,需要经过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才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这三重限制严重至极,几乎无法操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唤起了许多学者和律师对于五届人大常委会1980年通过的《律师暂行条例》中相关规定的回望和误读。《律师暂行条例》第7条规定:"律师参加诉讼活动,有权依照有关规定,查阅本案材料,向有关单位、个人调查。""律师进行前款所列活动,有关单位、个人有责任给予支持。"1981年4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具体规定的联合通知》规定:"律师参加诉讼(包括参加调解和仲裁活动),可以持法律顾问处介绍信向有关单位、个人进行访问,调查本案案情,有关单位、个人应当给予支持。"有观点因此认为,《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的出发点,显然是站在限制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立场,而不是强调被调查人应当予以协助的角度。因此,"将现在的《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与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相比,在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的规定上,显然是一个退步。⑥青锋:《中国律师法律制度论纲》,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7月北京第1版,第354页。"
如何认识"有关单位、个人应当给予支持"或者"有责任给予支持"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认识到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律师的一项重要权利,不具有"天然的"强制性。上述立法中的"应当"、"责任"实际上徒具虚名而已,不具有义务性。律师在调查取证遇到障碍之时,并不能采取强制性手段⑦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司法部在《关于律师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请示的批复》([56]司公字第2042号)中就曾指出:"关于律师能否进行调查问题,我们认为在目前侦察技术水平还不高、法院案卷材料往往不完整的情况下,为了使律师出庭辩护或代理诉讼,能够根据充分的事实,提出辩护或诉讼理由,应该规定律师在开庭前可以单独对案情进行访问,包括到现场以及向有关证人、鉴定人或机关单位进行访问了解等等。但由于律师和司法、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不同,故不仅访问应采取请教的方式,而且还应区别证人的具体情况,避免直接访问与对方当事人有共同利害关系的证人,以免引起争执。此外,律师在访问案情时,应当严格防止以自己的见解影响任何有关的证人。"。从这个意义上看,《律师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与1996年《律师法》的规定在运行机制上并无本质差别,只是措辞上的分贝略有高低。二者共同的问题都是在律师调查取证权运行遇到障碍时,缺乏有效的救济措施。
新《律师法》第35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这一规定从机制上看,与《刑事诉讼法》第37条的规定相比并无实质创新⑧有观点认为,"把律师申请调查取证排在自行调查取证之前,其立法意图是提示律师优先考虑申请检察机关或法院调查取证",参见余为青:"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比较法考察",《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3期。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应当指出的是,新《律师法》第35条的这两条规定在逻辑顺序上颠倒了。从资源配置角度讲,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首先应当自行调查。在自行调查不能的情况下,才得申请有关机关帮助调查取证。。而《刑事诉讼法》第37条存在的两个重要问题,也一并遗传给了新《律师法》。
《刑事诉讼法》第37条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证人作证是不是一种义务,其义务对象是谁?我国关于证人作证行为的性质在立法上应当是很明确的。《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从实践的执行情况来看,对这一性质的理解还存在很多含混的地方。这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向证人调查取证必须经证人同意,辩护律师如果要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提供的证人调查取证,则不仅要征得证人同意,还要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的许可,据此可以认为刑事诉讼法赋予证人有拒绝向辩护律师提供证据的权利;第二,《刑事诉讼法》第157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应当当庭宣读。这一规定又似乎表明证人履行作证义务的方式具有可选择性:既可以到庭口头作证,也可以不到庭而以书面方式作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民法院《解释》)第58条也规定:"对于出庭作证的证人,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等双方询问、质证,其证言经过审查确实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该解释第141条还规定了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四种情形。这些规定使得证人在是否必须出庭问题上具有很大的选择性⑨参见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64~65页。。
因此,如何认识证人作证的义务性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肯认证人作证的义务性。这种义务性的对象首先是法院。这具体表现为法院是对拒绝作证行为进行处罚的机关。此外,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检控方对证人也有进行强制性调查取证权利。英美法系国家从当事人主义出发,侦查和起诉机关没有对证人进行强制性调查的权力。就我国的立法而言,我国对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证人所承担的义务都进行了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这一规定一方面规定了公检法机关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另一方面也规定了有关单位和个人如实提供证据的义务。这一规定将证人作证义务的相对方确定为公检法机关,从实践情况来看本身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它使得侦查机关和起诉机关的活动缺乏司法控制,这也是实践中经常发生侦查或者起诉机关侵犯证人人身权利事件的根本原因。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借鉴日本《刑事诉讼法》的做法,规定检控方不具有向证人强制收集、调取证据的权力,他们对证人的强制行为必须通过人民法院的干预来进行。同样辩护律师本身也没有对证人进行调查取证的强制性权力,他们的调查取证权只能是没有国家强制力的权利。因此,辩护律师对证人的调查从实际的运行效果来看,肯定是在证人同意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可以说证人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是否同意接受调查确实是他的权利。如果辩护律师要进行强制性的调查,也必须取得司法权的支持。例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被告人、被疑人或者辩护人,在不预先保全证据将会使该证据的使用发生困难时,以在第一次公审期日前为限,可以请求法官作出扣押、搜查、勘验、询问证人或者鉴定的处分。"我国人民法院《解释》第44条也规定,辩护律师向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因证人、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同意,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的,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同意。第45条规定,辩护律师直接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人民法院认为律师不宜或者不能向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并有必要的,应当同意。这一规定本身说明我国现行的做法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了司法权对于控辩双方庭前调查取证活动的调控问题。从司法实践情况来看,一方面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当前对于辩护律师援请司法权来调取证据的渠道还存在很多问题,导致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活动难以顺利进行。而检控机关则因拥有强制性的调查权力而在证据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导致事实上的控辩不平衡。这就是实践当中律师界强烈主张律师拥有对证人的强制性调查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人民法院来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进行救济,符合证据法的原理。证人翻证是令司法实务部门颇感头痛的问题。审判人员在出现庭前陈述和庭上证言不一致的情况时,与检察、辩护人员之间往往产生意见分歧,感到难以决定证据的取舍。于是,干脆不传唤证人出庭以求方便。这直接导致了证人出庭率低、证人证言无法质证的痼疾。而人民法院庭前取得的证人陈述,因法院的中立性具有作证的可靠情况保证,因而具有可采性。因此在发生证人翻证的情况下,可以采纳为实质证据。相反,人民检察院作为检控机关,不具有中立性,因此,一般而言,人民检察院取得的证人庭前陈述不具有可采性。因此,在律师调查取证遇到障碍的情况下,只能由人民法院提供救济⑩1995年10月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草案)》第31条曾规定:"律师承办业务,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情况,收集证据,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予以协助。""律师在诉讼案件中,对不予协助调查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其到庭作证。"。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法院的中立性具有亲为性,不能为委托调查令等文书所取代。有的观点认为:"律师在调查取证时,根据实际需要有权要求人民法院授权调查,法院接到律师的请求后,经审查认为律师所调查的事实,直接影响到案情的认定的,应当立即发出授权调查书或委托调查令,保证调查取证的顺利进行。⑪陶髦等著:《律师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79页。"此外还有论者甚至设计了相应的程序⑫例如有论者认为,可以由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制定一个刑事辩护活动中律师的调查取证规则,明确建立起我国的"调查令"制度。律师在诉讼过程中一旦发现对于某个方面的证据必须进行庭前调查,而这种调查又可能得不到被调查人的积极配合,他可以向案件的主审法官提出申请,请求签发"调查令"。"调查令"一经签署,即赋予律师实质意义上的执法者身份。由于律师所持的"调查令"已经具有了国家司法权的性质,被调查人如果不配合调查或拒绝提供证据,将承受直至受到刑事处罚的不利法律后果。考虑到我国基层人民法院的法官业务水平,应赋予律师一次复议的机会。即律师如果对法官不予签发"调查令"的决定不服,可以向该法官所在法院的审判委员会申请复议。复议决定为是否签发"调查令"的最终决定。参见杨亮庆:《律师需要"调查令"》,《中国青年报》,2001年4月30日。。然而,律师并不能因为手持调查令而取得人民法院的中立性,因此其所调查取得的结果并不因此而具有可采性。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指出:"对于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调查取证的,应当由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不应当向律师签发准许调查决定书,让律师收集、调取证据。"这项规定的精神是正确的,符合证据法的基本原理,应当继续坚持。
《刑事诉讼法》第37条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没有对律师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救济的条件加以明确规定。这导致在实践中,一方面人民法院人力、财力的限制,律师的要求往往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民法院对律师的请求以种种借口加以搪塞,使得律师的调查取证工作难以进行。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对证人的强制性权力应当运用在两个层次中。首先,在庭审时,经人民法院依法传唤,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因此,在律师庭前调查遇到障碍的情况下,原则上应当通过申请人民法院传唤出庭作证的方式来取得证人证言。其次,在庭前,律师申请人民法院进行调查不能毫无限制,否则一方面会使得人民法院负重不堪,另一方面会严重冲击证人出庭作证的原则。只有在证人证言可能灭失、串证、证人逃匿等情况下,才能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人民法院进行调查,具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弥补律师调查权的不足,为其提供经济途径;二是人民法院进行的调查活动,具有证据保全的重要作用。
二、律师会见权的"阿喀琉斯之踵"
新《律师法》第3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从该规定的执行情况来看,存在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律师的会见权仍然得不到有效落实;二是实务部门对"不被监听"的理解有悖证据法原理。
就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权而言,我们所要考问的是,侦查机关为什么会设置各种障碍?障碍的作用无非是拖延律师的会见,使得侦查机关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秘密讯问。而在现行诉讼制度下,这种秘密讯问时间的长短对于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效力没有任何影响⑬人民法院《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因此,从现行的规定来看,律师帮助权受到阻碍以及长期羁押并不能成为排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理由。。拖延的时间越长,侦查机关就越能够从容地获得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这是侦查机关拖延、阻滞律师会见的重要动机。而会见手续繁简之论不过是隔靴搔痒,未能触及问题的实质。因此,制裁机制之缺乏,成了关于律师会见权的规定的"阿喀琉斯之踵"。要从根本上解决律师的会见难问题,就必须建立否定侦查机关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效力的机制。
这种否定证据效力机制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成熟做法。例如在美国,如果被告人要求会见律师,警察必须立即停止讯问。在律师到场之前,警察绝对不得为任何的询问,否则所取得的自白不得作为证据⑭参见王兆鹏:《美国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9条规定:"处于强制、拷问或者胁迫的自白,在经过不适当的长期扣留或者拘禁后的自白,以及其他可以怀疑为并非出于自由以及的自白,都不得作为证据"。判例认为,在限制被告人人身的过程中,以侵害被告人的辩护权的手段获得的自白,也应予以排除⑮参见彭勃:《日本刑事诉讼法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页。。借鉴这些做法,《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应当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要求会见律师的,未经律师会见,侦查机关所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不具有证据上的可采性。会见的不合理延迟应当被视为破坏犯罪嫌疑人供述任意性的因素之一。唯此,侦查阶段抗辩模式的建设才会有根本性的突破。在缺乏制裁机制的情况下,新《律师法》的规定不过是"新形式的旧错误"而已。当然,立法应当设定若干例外,在涉及公共安全、人身安全等明示的紧急情况下,可以不经律师会见而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紧急讯问。
对于律师会见"不被监听"的理解,凸显了部门的利益。侦查部门的声音是,"监听"仅仅指利用监控设备对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谈话进行监督⑯一些地方成立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机构,专门办理农民工、未成年人、妇女等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案件,促进法律援助服务专业化发展。。换言之,《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应当继续执行⑰《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的,应经侦查机关批准。"。然而,会见犯罪嫌疑人并了解有关情况,是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发挥其辩护职能的前提条件。会见只有在保密的条件下进行,才能促进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坦率交流而具有实质的意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都规定了律师---委托人特免权来保护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交流。而这种特免权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这种交流是秘密进行的⑱例如在美国,关于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规定是多种多样的,一般认为证据法专家威格莫尔关于该特免权的概括具有经典性意义。威格莫尔认为,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包括以下几个因素:(1)某人(委托人)寻求法律服务和帮助;(2)该服务或帮助由为委托人提供代理服务的律师提供;(3)该不作证的特免权可以在不确定的时间内,并且是为了委托人的利益援用;(4)该特免权涉及到委托人与律师交流的内容;(5)该交流是由委托人或其代理人进行的;(6)该交流是秘密进行的;(7)该交流是同律师或律师的亲信代理人进行的;(8)除非委托人明示或暗示放弃该特免权。在这样的限定之下,如果律师与委托人的交流是委托人不注意或有意在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则视为放弃其保密特免权。。联合国大会批准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在"保证律师履行职责的措施"一节中规定:"各国政府应确认和尊重律师及其委托人之间在其专业关系内所有联络和磋商均属保密性的。⑲《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2条。"在"刑事司法事件中的特别保障"一节中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不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的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⑳《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从这个角度看,"不被监听"应当理解为不受任何形式的监听,而不仅仅是通过仪器设备进行的监听。
新《律师法》尽管扩大了律师保密的范围㉑新《律师法》第38条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但是,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第二款为新增加的内容。,但是同原《律师法》一样,并没有关于律师职业特免权的规定。因此,我国在相关问题上的做法,同国际通行做法是存在较大差距的。这种做法如不改变,律师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秘密交流就难以实现,律师和犯罪嫌疑人的会见就会被架空。
三、律师阅卷权与证据完整性、律师---检察官的工作成果豁免
新《律师法》第34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就律师的阅卷权而言,这次《律师法》的修改有了重大突破,即建立了两个阶段的阅卷权。但是立法对"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却未作明确界定,不仅在实践中未循此进行操作,在理论上也引起了诸多争论。例如,有观点认为,"案件在移送审查起诉时的书面材料和法院受理之后的书面材料其实质内容是相同的,即这两个阶段律师能看到的书面材料在内涵和外延上是重合的,也就是说新《律师法》虽然对两个阶段的阅卷范围作了不同的规定,但是在实践当中它们的范围其实也是重合的"㉒万毅:"直面新《律师法》的缺陷与不足",《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如何循诉讼机理而进行操作,直接关系到律师的阅卷权能否得到落实。在律师阅卷权问题上,《刑事诉讼法》如何对应《律师法》进行修改,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技术节点。
新《律师法》的规定涉及一个重要的证据法原则,即证据完整性原则。证据的完整性可以从三种意义上展开:第一是证据形式上的完整性,第二是证据含义的完整性,第三是整个案卷的完整性。因此,证据的完整性原则有不同的层次含义。最微观的层次,应当是每种证据形式的完整性;最宏观的层次,应当是整个案卷的完整性。此外,证据完整性在不同诉讼阶段也有着不同的含义。在侦查阶段,证据完整性原则要求侦查机关要尽可能地全面收集证据;而在审查起诉阶段,则意味着控辩双方要尽可能地交换证据;在审判阶段,则意味着要完整地呈现整个案情。完整性原则与排除性规则不同的是,它是包容性的,而不是排除性的。排除性规则应当是完整性原则的例外。在证据的完整性问题上,存在完整性与当事人的惰性的矛盾,共时性与历时性之间的矛盾,国家权力与当事人权利之间的矛盾;涉及完整性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之间的关系、完整性与诉讼效率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笔者将另文赘述。在此仅就律师阅卷权所涉及的证据完整性原则的片段进行论述。
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上述审查起诉阶段对律师阅卷权的限制,做法本身就破坏了整个案卷的完整性。1997年《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在律师阅卷问题上,实践中一些操作人员甚至将一份完整证据切割,将部分内容允许律师查阅的做法,更是违反了证据完整性原则。
然而,从诉讼机制的角度看,对审查起诉阶段的律师阅卷范围进行限制又有必要。例如,从对抗制出发,美国在诉讼中,考虑证据的可再得性、庭审的司法民主宣示、证人保护等因素,对于各自收集的证人证言等证据(普通工作成果)以及公诉意见书、辩护词(意见工作成果)一般性地免予证据开示,以保持诉讼活动必要的对抗性、公诉人员和辩护律师诉讼准备工作的隐秘性和削减其诉讼准备工作的惰性。这就是所谓律师工作成果原则豁免原则的主要内容㉓关于美国律师工作成果豁免的基本理论,可参见美国法律协会(Am erican Law Institute):《律师法重述》(Restatem entof the Law Governing Lawyers)第87-90条之规定及其释义。。
因此,笔者认为,新《律师法》的上述规定,实际上建立了两个阶段的证据开示制度。在具体操作中,应当贯彻证据完整性原则和律师---检察官工作成果豁免原则。公诉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当进行第一次证据开示,开示的内容原则上不应当包括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普通工作成果、公诉意见书等意见工作成果。在公诉机关进行第一次证据开示后,辩护律师也应当履行开示义务,并以此启动公诉机关在第二个阶段即审判阶段的证据开示义务。此阶段的关键之处是,对于证人证言笔录、被害人陈述笔录,双方均不进行披露,而是在相互提供证人、被害人姓名、住址等基本信息后,双方各自进行调查,以便多增加一重发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瑕疵的机会。对于不一致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则在审判阶段进行第二次证据开示即全部材料的开示时予以发现。"案卷材料"与"全部材料"的最重要区别,就是案卷材料一般情况下,不包括庭前所取得的证人证言笔录。此外,证据完整性原则要求"全部材料"应当包括在侦查程序启动后形成的、未纳入"案卷材料"的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但检察委员会讨论记录、涉及国家秘密的材料等敏感性材料除外。
为了落实这样的证据开示制度,必须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侦查、公诉机关保留所有与案件有关的材料的义务以及毁损、隐匿这些材料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此外,必须对现行的案卷制作技术进行相应改革。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审查起诉阶段的案卷材料包括侦查案卷、检察内卷和公诉卷宗。其中检察内卷包括阅卷报告、审理报告、会见犯罪嫌疑人笔录、起诉书草稿;公诉卷宗包括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和照片。在新《律师法》的框架下,应当将侦查案卷和检察案卷分别区分为四个部分,即(1)不含证人证言笔录、被害人陈述笔录的证据卷;(2)普通工作成果卷(证人证言笔录、被害人陈述笔录);(3)密卷(含意见工作成果、检察委员会讨论记录、涉及国家秘密的材料等敏感性材料);(4)其他材料(在侦查、起诉过程中形成的未纳入前三种卷宗的所有的材料)。对于公诉机关而言,在审查起诉阶段需要向律师开示或者说律师有权查阅的案卷,应当是指(1),在审判阶段需要向律师开示或者说律师有权查阅的案卷,则应当是(1)、(2)和(4)。
四、结论
新《律师法》关于律师调查取证权、阅卷权、会见权等的规定之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得到落实,关键在于未遵循证据法原理进行制度设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当从证据保全、不一致证言的采纳、非法证据的排除、证据完整性、律师---检察官工作成果豁免等证据法原理出发,设计律师权利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重复错误。从根本上看,目前律师面临的执业难题,并不是新《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法律效力高低的问题,而是这些规定缺乏相应的机制建设,以及公安司法机关对于律师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方面的作用的认识仍然严重不足。加强证据法原理指导下的机制建设正是下一步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 张文静)
book=45,ebook=450
*本文是2008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