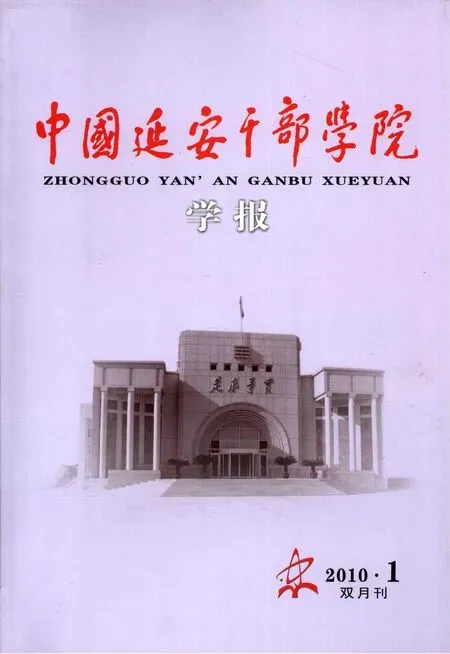百年来中国的三次伟大革命与三次民族觉醒
2010-02-15齐卫平
齐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学系,上海闵行 200241)
百年来中国的三次伟大革命与三次民族觉醒
齐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学系,上海闵行 200241)
20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三次历史性巨变的伟大革命,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第一次革命以意识觉醒为特征,唤起了中华民族近代思想的醒悟。第二次革命以方向觉醒为特征,标志着中国人民政治道路的抉择。第三次革命以模式觉醒为特征,显示现代化建设模式的创新。中华民族通过三次革命,实现了意识觉醒、方向觉醒和模式觉醒,这就为创造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现代化的世界先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次革命;意识觉醒;方向觉醒;模式觉醒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用“三次伟大革命”的概括,揭示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历程,显示了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道路上艰辛探索和不懈奋斗的历史心路。本文拟从革命效能的视角,分别用意识觉醒、方向觉醒和模式觉醒来认识这三次伟大革命,以期深化对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这个论断的认识。
一、意识觉醒:第一次革命唤起中华民族近代思想的醒悟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第一次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1]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是进入 20世纪后发生的一场扭转中国历史的深刻革命,它以制度变革的方式颠覆了几千年的传统统治方式,推动了国家形态向近代社会的转变。尽管辛亥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并未真正实现社会转型,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没有根除,但这场革命所产生的社会效能仍然是显著的。
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始终有高度的评价。1922年党的文件中就指出,辛亥革命“推倒了几千年因袭的帝政”,“在中国政治史上算是开了一个新纪元”,[2](P33—34)并将自己领导的革命看做“继续或完成辛亥革命”,[2](P337)表示要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完成辛亥革命未了的事业。毛泽东指出:中国只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3](P564)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孙中山领导的。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4](P2—3)胡锦涛总书记用“第一次革命”的明确概括,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在中华民族为实现伟大复兴奋斗历程上的地位。
从新陈代谢的社会变迁视角审视,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影响最明显的当然首先是国家制度的变化。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封闭中国的“帝国壁垒”,随着西方近代文明的涌入,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民族的落伍,一些爱国之士试图向西方寻找真理,救国救民。从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形成“中体西用”实践,求强自富的路径选择首先是瞄准“船坚炮利”的器物技艺层面。可是,西方物质形态的仿效成效甚微,“船坚炮利”并不能保证中国不受耻辱,更难以将中国纳入近代世界的轨道。19世纪末掀起的戊戌变法开始将视线转向制度变革,这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虽然没有真正触及封建制度的根基,但它对君主专制发起的挑战则是向近代国家制度形态转型的肇始。辛亥革命是改良运动的历史顺延,它坚决主张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在制度变革上比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走得更远,其历史价值也在近代国家制度形态的转型上得到了证明。民主共和制度的国家形态取代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形态,使中华民族迈出了与世界近代潮流相融合的步伐。
革命的社会效能必定表现在制度变革的调整上。然而,当我们审视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时,除了肯定其终结封建专制制度的伟大功绩之外,还应当看到蕴含在这场制度变革背后更为深刻的东西。笔者以为,辛亥革命所产生的近代民族意识觉醒远比制度变革的意义重要得多。辛亥革命前的 70年,中国虽然在西方炮舰的淫威下进入近代社会,但近代民族意识还处于懵懂状态,丧权失地的耻辱虽然时时激发亡国危机的忧患,但传统的缠绕还在潜意识上支配着中国社会。直至 19世纪末,许多中国人虽然因本国衰败的客观现实而不得不承认中国的落后,但国家制度和伦理文化“优越感”依然是一条难以逾越的底线,以致不仅统治阶级抱持“琴弦之更”的顽固立场,即使那批改革态度鲜明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也舍不得丢掉已经失范的传统,硬是要走一条“托古改制”的变革之路。这是整个民族意识尚未真正摆脱“帝国情结”的表现。
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以空前的震撼强烈刺激了中华民族,前人曾反复提到。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5](P113)“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6](P71)吴玉章回忆道:“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7](P955)陈独秀 1916年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说:“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富强之策,虽圣人所不废”。[8](P106)这些论述符合历史事实。然而,甲午战争失败所促使的民族觉醒,还只是停留在国人对亡国灭种的切肤之痛上,很难说是近代意义上民族意识的觉醒。
对于中国来说,真正的民族觉醒必须表现为思想上告别传统,制度上接轨世界,行为上合乎现代。这样的觉醒在辛亥革命显示了端倪,并在此后的历史实践中反映出来。伴随 20世纪初席卷中国的欧风美雨,培育近代民族意识的土壤开始生成,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人格独立、民主自由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妇女解放等等思想得到宣扬。尽管这些思想宣传的深度和广度十分有限,普及程度很低,但它为中华民族近代意识做出的思想铺垫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辛亥革命唤起的民族觉醒在随后几年的实践中很快得到证明。比如,虽然中华民国依然保留着专制统治的痕迹,但谁再搞帝制复辟之类的把戏则必然遭遇“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失败命运。这正是近代民族意识觉醒使然。又如,虽然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不免思想激进得偏颇,但在东西方文明论战中则表现出颠覆历史传统、领受近代文明、开启思想启蒙的自觉倾向。这背后体现的又是近代民族意识的作用。再如,虽然 1919年的五四运动延续着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传统,但它已经有别于以往纯粹应对外国侵略的抗争行动,表现出民族尊严、国家威权和主权意识的觉醒。人们深刻地觉悟到:“惟中国人之视国家也,与社稷齐观;斯其释爱国也,与忠君同义。盖以此国家,此社稷,乃吾若祖若宗艰难缔造之大业,传之子孙,所谓得天下是也。若夫人民,惟为缔造者供其牺牲,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焉”。[8](P67)这一国家认识中体现的近代意识觉醒表明:“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3](P559)如果说,不彻底的辛亥革命没有把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交给中国的话,那么,促进民族意识的觉醒则是它留给中国的一笔历史遗产。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二、方向觉醒:第二次革命标志中国人民政治道路的抉择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第二次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合并起来称之为“第二次革命”,是一个新的概括,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看,这个概括涵义十分深刻。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曾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三次历史性的巨变指“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革开放”。[4](P2—3)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三次伟大革命的论断与江泽民关于三次历史性巨变的论断基本是一致的,但有两个明显的不同。一是采用“革命”的概括替代“巨变”,使提法更加明确,它不是从社会影响的层面而是从历史进程的层面去把握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动,脉络更为清晰。二是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连在一起,使第二次革命包含的范围更加准确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它不是从时段的层面而是从使命的层面去概括党领导的革命,使涵义更加完整。
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同一次革命来概括,有其理论根据。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这两种革命关系的认识就长期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党的历史上,“两步走”革命战略涉及的就是两种革命关系的问题。在实践中,党内围绕这个问题的认识曾经出现过分歧。有的将这两种革命相混淆相等同,有的将这两种革命机械地分离对立起来。是毛泽东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20世纪 30年代末毛泽东以精湛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构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的基本认知。毛泽东首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相区分,提出了“新旧两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论断。然后从党的革命使命详细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肩上承担着中国革命的双重任务,“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3](P651)毛泽东还将这两种革命形象地比喻为同一篇大文章的上篇和下篇,认为只有做完了上篇才能做下篇。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顺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了自己革命的使命。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阐述,与胡锦涛总书记概括“第二次革命”是相吻合的。
第二次革命解决了什么问题?解决了政治道路的抉择,这是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方向性的觉醒。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在封闭的状态下陷于一种内循环的发展轨迹,王朝盛衰兴亡的规律周而复始地不断重演着单向度的社会变迁,但却从来不存在方向选择的问题。鸦片战争中断了中国社会的内循环发展轨迹,何去何从问题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变得严峻起来。辛亥革命凸现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次方向性选择:“以英美为师”。这个方向选择具有历史合理性,也是当时看似唯一具有先进性的选择。西方近代革命所创造的民主主义方向,成为社会进步的楷模,舍此别无他道。但是中国人沿着这个方向走却陷入了死胡同,中华民国“共和其名,专制其实”的糟糕实践,破灭了人们对这个方向的期待。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向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选择,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方向。李大钊曾经用“新纪元”的说法来表达对人类社会出现社会主义新方向的欣喜,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9](P246)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0](P1471)“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10](P1470)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沿着十月革命提供的新方向,开辟出一条崭新的政治道路。“走俄国人的路”取代“以英美为师”,成为中国历史发展新的方向选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始了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道路。
革命实践的过程就是向社会展示其价值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新的方向选择需要通过革命来实现广大人民的政治认同。这样的政治认同在第二次革命中是通过两个步骤来达到的。第一个步骤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非法”状态下,马克思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社会主义方向陷于被“妖魔化”的境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将方向选择鲜明地展示在中国人民面前:第一种方向选择是继续保留国民党政权的一党专制,继续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第二种方向选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联合各种民主力量,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并逐步转向社会主义;第三种方向是继续仿效英美式的道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三种方向选择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种政党和政治组织激烈较量的焦点,最后的结果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历史抉择。第一种方向选择陷中国于衰败耻辱而不拔,为中国人民所唾弃,第三种方向选择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下陷于不可能实现的空想,被历史所抛弃,只有第二种方向选择才展现出光明前途的征兆,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民选择了第二种方向。第二次革命的第二个步骤以中国共产党执政为前提,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衔接,通过制度构建完成社会主义方向的选择。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 (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3](P559)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步骤,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胜利地以“和平赎买”的方式,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是一次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联系的一次革命。用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革命的观点来说,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一次完整革命任务的完成,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方向选择至此得到真正的实现。
三、模式觉醒:第三次革命显示现代化建设模式的创新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第三次革命是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1]改革开放是一场全新的革命,它不仅史无前例,而且独具特色,它所引起的民族觉醒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20世纪后期的中国,经历了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尤其是“十年文革”的劫难,“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1](P808)党和国家在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又一次选择了革命,即改革。关于第三次革命的说法,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1984年 10月 6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讲道:“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12](P78)同年 10月 10日他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又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12](P82)1985年 3月 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来宾时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2](P113)最初的社会反应表明,中国在接受改革开放决策上并非一致,或者可以说分歧远远超过共识。这既有受长期“左”倾思想束缚和传统思维定势惯性作用的因素,又有接受新事物的认识障碍因素。进入 80年代,围绕改革开放决策的认知面临着“姓社姓资”的拷问,80年代中期和末期国内发生的学潮和政治风波,将这样的拷问推上风口浪尖。邓小平以深邃的思考作出了回应,他不仅反复表明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而且将改革与革命相提并论。当时邓小平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概括上作出两次革命的概括的,因此,将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与胡锦涛总书记概括的三次革命论断没有矛盾。
邓小平关于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论断,根据他的论述,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从社会功能上看,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举措,与革命具有同样的意义。1992年邓小平在巡视南方的谈话中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2](P370)其次,从历史过程上看,改革是承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后继任务,巩固革命的成效。“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那个革命搞了三十几年。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12](P134)“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12](P135)邓小平就是从这两个角度赋予改革以革命的涵义。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1]如何认识第三次革命促成的“伟大觉醒”?本文认为最为深刻的是模式觉醒。与前两次革命相比较,第三次革命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革命范式的转变。从范式看,前两次革命属于制度颠覆型的革命,结果都表现为以一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制度替代既有的制度,而第三次革命则是制度调适型的革命,结果是在坚持既有制度基础上的改进和完善。二是革命对象的转变。第一次革命是“革清朝的命”,对象是封建统治阶级。第二次革命先是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命,后是革资产阶级的命,而第三次革命则是革体制弊端的命。三是革命手段的转变。第一次革命采取的手段是以武装斗争开路,以“南北和谈”收尾。第二次革命采取的手段先是暴力革命,后是“和平赎买”。而第三次革命则剔除了任何疾风骤雨式的色彩,采取体制创新的手段稳步推进社会变革。
第三次革命的范式、对象和手段决定了其标志性的内涵:制度调适、机制完善、稳定有序、解放思想、和谐发展,它的功能就是寻找一条符合时代要求和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第二次革命遗留下的问题。毛泽东在领导人民完成第二次革命的任务之后,思想上意识到这个问题。1956年他清醒地认识到要“以苏为鉴”,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但实践上却没有找到中国自己的路。在改革开放之前的 20多年里,照搬苏联模式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充分发挥出制度优势。总结起来说,党执政实践中的“左”倾错误的发生尽管原因很多,但革命时期仿效俄国革命中形成的传统思维,以及建设时期照搬苏联模式中形成的手脚束缚,导致社会主义建设长期脱离中国实际,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接连不断的曲折使社会主义事业陷入极大的困境。邓小平指出:“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12](P237)“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12](P261)围绕着模式问题,邓小平阐述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他强调,世界上没有统一的建设模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搬别国的模式只能失败。改革开放首先就是从改变建设模式开始的,邓小平提出要走中国自己的路,就是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第三次革命最有实质性的贡献,就是建设模式的转变。2007年 10月,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对改革开放 30年伟大实践的深刻提炼,也是对中国模式定型的明确概括。
第三次革命显示模式觉醒的意义已经体现出来,并将在中国未来的进步发展中进一步显示它的价值。必须承认一个现实:迄今为止,世界上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模式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从早期率先进入现代化行列的欧洲国家,到 20世纪以“四小龙”著称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跟进,积累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丰富经验,我国现代化建设应当认真汲取这些经验。但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实现现代化的模式决不可能锁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上,社会主义制度同样可以实现现代化。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实现现代化就成为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百年夙愿,实现现代化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通过三次革命,实现了意识觉醒、方向觉醒和模式觉醒,这就为创造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现代化的先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模式完全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世界先例。
[1]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8-12-19(1).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3]毛泽东选集: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江泽民文选: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梁启超.戊戌政变记[C]//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
[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
[7]吴玉章文集:下[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8]陈独秀文章选编: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9]李大钊文集: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毛泽东选集:第 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2]邓小平文选: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China’s Three Great Revolutions and National Awaken ing since Nearly One Century
QIW ei-ping
(PoliticsDepart ment,East China Normal Un iversity,Shangha i200241)
China haswitnessed three great revolutionswith historical vicissitude since 20th century,giving especially profound effects in the processof developmentof Chinese nation.The first revolution,characteristic of consciousness awakening,aroused the modern thoughts of Chinese nation.The second revolution,characteristic of direction awakening,symbolized Chinese choos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The third revolution,characteristic of pattern consciousness,manifested the innovation ofmodernization pattern.Through above three revolutions,China has fulfilled awakening of consciousness,direction and pattern,which provides fine base for creating the world precedent of socialis m modernization.
three revolution;consciousness awakening;direction awakening;pattern consciousness
D61
A
1674—0351(2010)01—0047—06
2009-10-10
齐卫平(1953— ),男,浙江慈溪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研究。
[责任编辑郭彦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