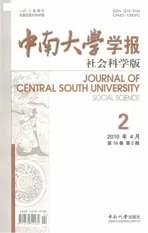论“文学自觉”始于春秋——兼与赵敏俐先生《“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商榷
2010-02-09李永祥
李永祥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一、对《“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的反思
众所周知,关于中国文学自觉,目前主要有“魏晋文学自觉说”和“汉代文学自觉说”两种观点。关于“魏晋文学自觉说”及“汉代文学自觉说”的提出背景及论证过程,赵敏俐先生在《“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一文中有详备的描述[1](155−158)。 赵敏俐先生也赞成“汉代文学自觉说”,并补充论证:第一,汉代的文学已经“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汉人不仅“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汉人已经“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为了巩固“汉代文学自觉说”,赵敏俐先生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对曹丕的《典论·论文》作了重新理解和评价;二是讨论了“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的关系。
赵敏俐先生不太赞成用“文学自觉”这一词语来概括汉魏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变化,因为“文学自觉”这个论断的内涵有限,歧义性太大,并提出几个与学界同仁讨论的问题:其一,在中国古代,本没有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完全相对应的概念,只有明晰的文体观,却没有明晰的文学观。其二,鲁迅所特别强调的曹丕的时代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不存在的。其三,如果说魏晋是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就意味着汉代以前的文学都是“不自觉”的,这不仅不能很好地解释魏晋以后的“文以载道”的问题,也不能很好地解释先秦两汉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美问题[1](160)。
赵敏俐先生的论述确实为“汉代文学自觉说”补充了一些坚实的证据,尤其对曹丕《典论·论文》的精到阐释使他的“汉代文学自觉说”迅速地确立起来。然而我们再“反思”一下,赵先生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现条述如下,以与赵先生商榷。
其一,赵先生说,汉代的文学已经“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文学”“文章”,虽然二者只是一字之差,却有着重大区别,“文章”的范围远比“文学”要广。这一说法不符合汉代史实。实际上,汉人所谓的文学是包括经学、儒术、历史、掌故在内的一切学术,并没有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
《史记·孝武本纪》:“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又“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儒林列传》:“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这里的文学是指经学儒术。
《晁错传》:“晁错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儒林列传》:“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又“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仪为官”。这里的文学指历史掌故。
《儒林列传》:“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 ……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这里的文学指礼乐。
《太史公自序》:“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这里的文学指的是律令、军法、章程及礼仪等。
至于不指学术而带有词章的意义者,则称为“文章”或“文辞”。如《史记·三王世家》:“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再以《汉书》为例。《汉书·公孙弘传赞》:“文章则司马相如。”又说:“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可见,汉时对辞赋、史传文或奏议文,都称之为“文章”。
由此可知,汉代有文学、文章之称,文学包括文章和学术,而文章或文辞则偏重于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
(1)高校应当从管理制度出发,结合自身实际,多措并举,制定科学合理的激励政策,使实验技术人员的待遇和工作条件得到真正改善,激励其发挥更大的工作热情[1]。(2)用精细型管理模式取代粗放型管理模式,制定明确的管理条例或者给已有条例确立执行标准,促使实验技术人员科学化、规范化、条理化开展工作,改变其散漫的工作态度。
在汉代还有以文章之义称“文”,以博学之义称“学”的语辞现象。如《汉书·贾生传》:“以能诵诗书属文闻于郡中。”《终军传》:“以博辨能属文闻于郡中。”这是称文章为“文”的证据。《汉书·韦贤传赞》云:“汉承亡秦绝学之后,祖宗之制因时制宜,自元、成后,学者蕃滋。”《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云:“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这又是称文学为“学”的证据。
郭绍虞先生也强调文学包含文章和博学,他说:“我们假使知道汉时有‘文学’‘文章’之分,‘学’与‘文’之分,那就可以知道六朝所谓‘文’‘笔’之分,就是从汉时‘文’或‘文章’一词再加区分罢了。如果不经这个阶段,断不会从包含文章博学二义的‘文学’一词,分别出‘文’‘笔’来。”[2](29)
因此,在汉人的语境中,“文学”和“文章”起初是对等的概念,不存在包容关系;到了东汉后期,汉人的文学观念在演进,文学之“文”指“文章”,文学之“学”指“博学”,“文学”与“文章”衍生了包容关系,文学概念的外延在扩大,文章概念的外延在相对缩小,文学包括文章,而非赵敏俐先生所谓“‘文章’范围远比‘文学’要广”。这种广义的文学观虽经魏晋南北朝文论家的纷争,仍然是悬搁未定的文学观。
南朝宋颜延之有言、笔、文之区分。他所说的言,指直言不加文饰,如经典;笔,指书檄一类文字;文,指诗而言[3](376)。刘勰针对颜延之的文笔说进行批判。《文心雕龙·总术篇》云: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请夺彼矛,还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果言文,不得谓经典非笔矣。将以立论,未见其论立也。予以为发口为言,属翰曰笔,常道曰经,述经曰传。经传之体,出言入笔。笔为言使,可强可弱。六经以典奥为不刊,非以言笔为优劣也。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故知九变之贯匪穷,知言之选难备矣。[4](469)
刘勰反对颜延之的主张,认为“文以足言,理兼诗书”,“言”中有文饰,而“诗书”中也有义理,一切语言文字形式均“出言入笔”,将“文”与“笔”“别目为名”是自相矛盾的。刘勰的文学观是不分文笔的广义文学观。这种传统的文学观在他的《原道篇》里就标宗立义了。刘勰又反对陆机的文学观,认为陆机的《文赋》“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意即《文赋》太琐碎,太片面,不足以代表变动的含义丰富的文学的全貌。
萧统选文的原则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5](1)固然将诗赋选入,然而,论、赞、碑、铭、诔、吊、哀、祭等也在入选之列,这看似驳杂的选文方式,正反映了萧统的广义文学观,他没有将文学进行狭隘的区分。
由以上对中国古代、近代论者文学观的简单梳理可知,中国人一直主张的是传统的广义文学观,而不是外国学者如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代表人物雅各布森和法国非功利性文论的代表人物罗·埃斯卡皮等所主张的纯文学观。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应以中国传统文学观为准的,不能以今人甚或外国人的文学观来羁勒中国古代文学。赵先生的“文章的范围远比文学要广”的说法与汉代实情接榫不上,故其说不甚牢固。
其二,赵先生认为,汉人不仅“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以班固《汉书·艺文志》把诗赋单列一类、刘向编辑楚辞时所收作品只限于屈原及汉人摹仿《离骚》《九章》之作、扬雄的理论、张衡的作品、《后汉书·文苑列传》及蔡邕的《独断》作为证据,证明汉人已经把诗赋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开,说明当时人对文体的区分已经非常细致,从而证明汉人的文体区分是汉代文学自觉的标志。然而赵先生在后文却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学审美观是在六经建立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体系的”,“先秦经书的分类,也正是最初的文体区分”,“在经学的发展和经学的研究中,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显示了自觉的文学理论意识”。本意是在论证“汉代文学自觉”,却为“先秦文学自觉”提供了切实的证据,这给人一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感觉。
之所以“顾左右而言他”,是因为赵先生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赵先生有深厚的经学功底,在经学研究中,赵先生敏锐地觉察到了先秦时期文学已经自觉了,因为在六经建立的过程中,文学审美观逐渐成为体系,六经文体的区分也趋于精细,自觉的文学理论意识业已形成。但是,由于拘于前人的“汉代文学自觉说”,赵先生没有再向前迈进一步。然而,赵先生心底里分明感觉到“汉代文学自觉说”的偏颇之处,所以,他委婉地提出:“‘文学自觉’这个论断的内涵有限,歧义性太大而主观色彩过浓,因此不适合用这样一个简单的主观判断来代替对一个时代丰富多彩的文学发展过程进行客观的描述。”
二、“文学自觉”应始于春秋
由以上论述可知,不是“文学自觉”“内涵有限”,而是“汉代文学自觉说”内涵有限,它排斥了丰富多彩的先秦文学。其实,“文学自觉”歧义性并不大。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应该袭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德国浪漫主义宗教哲学大师施莱尔马赫在阐述“解释学”时认为,由于时间距离和历史环境造成的词义变化及对作者个性心理的不了解而形成的隔膜,使解释必然产生误解,因此,研究者必须通过批判的解释来恢复文本产生的历史环境和揭示原作者的心理体验,从而达到对文本的真正理解[7](169−170)。解释学之父威廉·狄尔泰也认为,解释学的任务在于从作为历史内容的文献、作品文本出发,通过“体验”和“理解”,复原它们所表现的原初体验和所象征的原初的生活世界,使解释者像理解自己一样去理解他人[7](172)。“文学”语词在春秋时期就产生了。孔子曰:“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又曰:“君子博学于文。”(《雍也》)《述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公冶长》云:“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雍也篇》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由此可知,春秋时期文学概念是广义的,可以指学术、道德修养,也可以指有文采的文章、经润饰的言语,凡是经过有意识文饰的口语、书面语、甚或性情上的东西均可谓之文学。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始终未作大的变动。所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应该“根据文本作者及当时公众所处的语言情势来加以确定”,“复原它们所表现的原初体验和原初的生活世界”,不应该用今人的纯文学观念来羁勒古人的文学观念。这样做之后,“文学自觉”的歧义性就不大了。
有了文学观念的产生,就有了文学的自觉。世间一切有灵性的东西均须经历萌生、自觉、发展、成熟、衰亡等阶段,文学也不例外。文学自觉应该从远源探讨起。犹如一颗大树,由种子萌生树苗,由树苗长成树干,由树干分蘖出枝条,再由枝条分蘖出新的枝条。春秋文学自觉是树干,汉代文学自觉是枝条,魏晋文学自觉是再次分蘖的枝条,唐宋词、宋元曲又是再次分蘖的枝条,由此,中国古代文学大树才青葱勃郁,荫蔽无边。这也符合黑格尔所谓的“再醒觉”发展说。如果以汉代为“文学自觉”的起点时间,就意味着汉代以前的文学都是“不自觉”的,这就否定了丰富多彩的先秦文学,不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表征及发展规律。所以,春秋时期文学的自觉,既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又可以为弘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添加一个佐证。那么,“春秋文学自觉说”的证据何在?下面胪列证据加以论证。
首先,借用赵敏俐先生证明“汉代文学自觉说”的证据来证明“春秋文学自觉说”。中国人对“文的形式技巧和审美方面的主动追求在六经中表现得已很明显”。《周易·系辞下》曰:“夫易,……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礼记·少仪》曰:“言语之美,穆穆皇皇。”《左传·成公十四年》:“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由此可见,早在“六经”的写作中,就已经有了审美意识的追求,这其中尤以《诗经》的写作最为明显。我们看《诗经》大小雅的创作,整齐的四言句式,严格的押韵规则,词语的雕琢绘饰,章法的细密安排,风格的典雅庄重,已经达到了那样的艺术高度,如果说“这些诗在写作的过程中没有自觉的艺术美的追求,没有精心的艺术锤炼,是可能的吗?”[1](160)
在赵先生的论据基础上,还可补充一些春秋时期重文的例子。
春秋时期,诸侯大夫在朝聘、会盟、宴享场合,往往赋诗言志,既增加了语言的文采、显示自己的文学修养,又曲畅情志,营造了一种彬彬尔雅的文学氛围。如《左传·文公十三年》:“郑伯与公晏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8](599)一次关系着郑国存亡的外交活动就这样通过赋诗来完成了,春秋人欣羡文雅的风气于此可见一斑。《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重耳流亡到秦国,秦穆公宴请他,重耳想让子犯跟随,子犯推辞说:“吾不如衰之文也。”而推荐谈吐博雅的赵衰跟从。
郑国大政治家子产最重视文雅,他的外交辞令渊深美秀。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子产献捷于晋,戎服将事”。这篇外交辞令既显示了子产知识的渊懿,又展示了子产的机锋敏对,且多用“我”字,情感溢于字里行间,与吕相绝秦书有异曲同工之妙。应对机敏之中深藏博雅,不像魏晋士人那样故弄巧慧。所以,孔子感叹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
子产言辞的文雅不仅是其天质外现,还是他善学他人文辞的结晶。他曾与子大叔等人揣摩外交辞令的修饰技巧,并重用子大叔等人。《襄公三十一年》:“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吿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可见,重视文饰是子产政治上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左传》本身就是春秋时期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是不争的事实,其作者左丘明的文学意识在春秋时期早已觉醒了。上述所论之春秋士大夫的言论和外交辞令的深美特质与左氏有意润饰之功密不可分,这只要与《国语》中士大夫辞令一比较,便知左氏是在有意为文学了。
唐刘知几早喜《左传》的文学性。他在《史通·自叙篇》中说:“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如此,吾不复殆矣。’先君奇其志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9](85)他在《叙事篇》中说:“观丘明之记事也,当桓、文作霸,晋、楚更盟,则能饰彼词句,成其文雅。”[9](50)《杂说上》对《左传》叙事的精彩推崇备至,因人熟知而常引用,不再赘引。《申左篇》云:“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措思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9](121)
章学诚《文史通义》提出“六经皆史”,有文即有史,史皆文饰之,文史通义,今古之例也,进而认为六经皆重文之作。《辨似篇》云:“《传》曰:‘辞达而已矣。’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经传圣贤之言,未尝不以文为贵也。”[10](68−69)《黠陋篇》云:“取蒲于董泽,何谓也? 言文章者,宗《左》、《史》。《左》、《史》之于文,犹六经之删述也。……斯亦陶铸同于造化矣。”[10](81)《与汪龙庄书》云:“左丘明,古文之祖也。”[10](272)。由此可知,博雅敏达的章氏早已指出了六经及《左传》文的觉醒。
《左传》的文学性在《左绣》一书中得到高度张扬。朱轼为《左绣》作序云:“《左氏》,文章也,非经传也。……近《庄》《列》诡谲之风,启战国纵横之习。大率定、哀以后,有绝世雄才,不逞所志,借题抒写,以发其轮囷离奇之概云耳。”[14](1−3)简直把《左传》的文学地位等同于《庄子》、《列子》和屈原的《楚辞》了。张德纯为《左绣》作序亦云:“自有书契,六经炳垂。是时,元气混沦,菁华未洩。于是乎有闢生人灵慧之府,轩鼚极致,以章天地之大文者,丘明氏实为之创,而庄周、屈原乃继之。”[11](12−13)冯李骅在《读左卮言》里论《左传》笔法,有连山复岭法,有层波叠浪法,有提应法,有偶对法,有正叙、原叙、顺叙、倒叙法,有宾主互换法,有埋伏法,有褒贬法,有牵上搭下法,有中间贯两头法,且赞扬左氏极工于叙战、左氏好奇、左氏长于诗、左氏善于辞令、左氏有绝大线索。《左传》之文学性几被冯李骅道尽。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里说:“(襄公二十一年)州绰曰:‘然二子者,譬如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按此为初见,语详意豁。二十八年,卢蒲嫳曰:‘譬之如禽兽,吾寝处之矣。’再见语遂较简而意不醒。昭公三年,子雅曰:‘其或寝处我矣。”三见文愈省,若读者心中无初见云云,将索解不得。一语数见,循纪载先后之序,由详而约,谓非有意为文,得乎?”[12](216)学贯中西的钱先生早就看到了《左传》在“有意为文”,看到了《左传》的文学自觉。
由此可见,一部《左传》足以证明春秋时期文的觉醒,更遑论《周易》《诗经》《礼记》等其他六经了。至于赵敏俐先生说,先秦的经书分类,也就是最初的文体区分;在经学的发展和经学的研究中,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显示了自觉的文学理论意识。这也恰好可以证明春秋时期文的觉醒。因为文体区分、文学理论的形成正是文学自觉之后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学自觉是本,文体的区分、文学理论的形成是末,没有文的自觉,便无所谓文体区分、文学理论的形成。探讨中国古代文学自觉,应该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从本源开始探讨。春秋时期文的自觉是本源,有春秋时期人性觉醒和艺术觉醒作为滋养的土壤和源泉,有春秋时期的文献及后世有识之士的评论作为佐证。春秋时期文的自觉,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先锋,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意义重大。龚克昌等先生提出“汉代文学自觉说”,为弘扬民族文化迈出了可贵的一步。在这可贵的一步的启发之下,我们提出春秋文学自觉说,以期学界同仁拿出更确切有力的证据来呼应声援,也希望睿智大方之家来批评指正。
[1]赵敏俐.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 2005, (2):155−158.
[2]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3]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4]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5]萧统.文选序[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6]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7]王岳川.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M].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9]刘知几.史通[M].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10]章学诚.文史通义[M].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11]冯李骅, 陆浩.左绣[M].台北: 文海出版社印行.
[12]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 中华书局,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