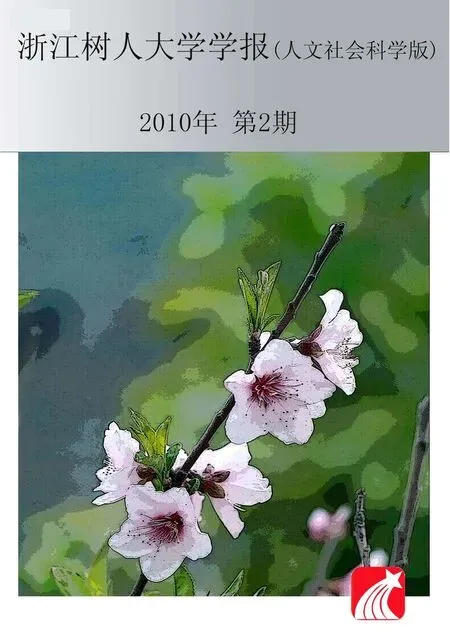俄罗斯转型期非国立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分析
2010-02-09顾鸿飞
顾鸿飞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俄罗斯转型期非国立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分析
顾鸿飞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在俄罗斯非国立高等教育近20年的发展中,其赖以生存的教育政策环境数次发生变迁,政府对非国立高等教育的态度由昔日的鼓励、扶植逐步走到后来的规范、管理,期间各种变迁都是政府利益诉求的结果。分析其原因,主要是政策决策者结构单一、对新型的非国立高等教育缺乏理论思考、政府短期行为所至以及历史的惯性选择等四个要素。
非国立高等教育;民办高等教育;教育政策;俄罗斯
一、俄罗斯非国立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
学术界对“教育政策”的界定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出于本文的写作目的,笔者将“教育政策”定义为:“国家在一定时期为实现教育目标、完成教育任务所规定的各种政策、法规的总和”。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议会民主、多党政治和思想多元化开始主宰俄罗斯的政治生活,在经济上打破了国家垄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了私有化。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中断了半个多世纪的俄罗斯非国立高等教育复苏了。
迄今为止,非国立高等教育走过了近20年的历程,虽然这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但对俄罗斯而言,却有着深远的意义。如今,它已经发展成为俄罗斯高等教育系统的组成部分,成为与国立高等教育必择其一的教育形式。然而,它却是在不断变迁的教育政策环境下发展到今天的,且每一次的变迁都影响着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
“俄罗斯联邦不是缺少教育政策的国家。”[1]从苏联解体到1999年底仅联邦级的教育法律法规就达462个之多,[2]但没有专门的非国立教育(高等)法。在这些教育法律法规中,对非国立高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有:(1)俄罗斯联邦《教育法》;(2)俄罗斯联邦《宪法》;(3)俄罗斯联邦《大学及大学后职业教育法》;(4)其它“行业”联邦法,指与《教育法》和《大学及大学后职业教育法》一起发生法律效力的教育法律文件,比如《俄罗斯联邦教育发展纲要》《俄罗斯联邦教育民族学说》等;(5)其它“非行业”联邦法,指非教育部门制定的政策,其中的部分条款涉及到了非国立高等教育,比如俄罗斯联邦《公民法典》、联邦《税收法典》等。
纵观转型期俄罗斯非国立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笔者认为,它的政策价值取向发生了三次变迁。
1.非国立高等教育的萌芽(1985年初至1991年底苏联解体)。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影响下,1988年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允许国内实行私有制的决议,已经遍布全国各地的专营“影子经济”的非国家所有制的培训机构借机公开活动,并且活动空间越来越大,从高考补习班扩大到针对高考落榜生、社会人员的营利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助学机构等,成为后来的非国立高等学校的雏形。
1990年12月25日,叶利钦签署了《企业和企业家活动法》(№445-1),其中的第34条规定:为满足社会需要和为国民提供服务,允许各种法律组织形式的企业在其所在地的地方级人民代表委员会注册合营公司、股份公司、私营企业,允许它们开办学校。该法打破了一切资源由国家统一配置的局面,允许包括私人所有制在内的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为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复苏发出了许可信号。
1991年7月11日联邦1号总统令《发展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的首要措施》颁布。它首次直接提出了创建非国立学校的问题,并要求“支持非国立教育机构”;建立教育发展基金会,为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组织、机构投资教育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总统令是非国立教育在苏联中断了半个多世纪之后,政府首次在国家层面上公开鼓励、支持非国立教育,为非国立教育的复苏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教育政策点燃了一些善于经营、又渴望从事教育活动的私人企业和组织等创办各种类型非国立教育机构的激情,首批以私人企业、有限公司、股份公司等法律组织形式出现的、具有大学意义的非国立高等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仅在1991年初,待注册的非国立高等学校就已经达到45所,到1992年初,全国拥有非国立高等学校92所。③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出现打破了国立高等教育长时期一统天下的局面,为高等教育系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非国立高等教育是应时而生的产物,是自下而上的自发行为,是个人或者集体渴望从事教育活动的自由选择。学校的举办者、办学者都是逐利的商业人士,办学活动完全背离教育规律,用经营企业的方式管理学校,结果导致学校秩序混乱,倒闭现象屡见不鲜。
2.非国立高等教育的法制化、制度化(1992年初至1999年底)。1992年6月,在叶利钦的领导下,俄罗斯私有化进程全面启动,在经济上选择了“休克疗法”的改革模式,妄图快速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休克疗法”从根本上瓦解了生存了70余年的国家垄断的计划经济,催生了私人资本,客观上为非国立高等学校的大量出现奠定了经济基础。
1992年7月31日联邦《教育法》(№ 172)诞生,标志着非国立高等教育法制化、制度化建设的开始。
联邦《教育法》是新政府根据新的需求,从新的意识形态出发制定和通过的第一部联邦级教育法。它首次使用并确定了“非国立教育”这一概念,规定了非国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创办者(11.1.)①、机构的性质地位(12.3.)、管理(3.36.)、学校财务(4.39.)、受教育者的权利和社会保障(5.50.)以及国立学校和非国立学校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原则。联邦《教育法》是俄罗斯转型期第一部允许非国立教育合法化、保障非国立学校创办及运作的联邦级法律文件,是非国立学校得以恢复与创立的法律基础,成为俄罗斯教育非国家化进程中的里程碑。
联邦《教育法》表明了政府对非国立高等教育持积极扶植的态度,不仅让它获得了与国立高等教育一起生存的权利,而且对它的发展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通过对条款的分析发现,联邦《教育法》是政府急功近利的“作品”,带有极强的乌托邦痕迹,国家承担了过分大的义务(40.2.),很多条款不切实际,无法落到实处,这也是后来《教育法》被数次修改的原因之一。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宪法》通过,它与前苏联《宪法》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允许企业私有化,“私人、国家、市政以及其它形式的所有制在俄罗斯联邦可以得到同样的承认和保护”(8.2.)等规定是非国立教育合法生存最充分的法律依据。“从事私人活动不受任何限制”(34.1.)、“俄罗斯联邦制定国家教育标准,支持不同的教育和自我教育形式(43.5.)”等国家意志进一步肯定了政府允许多样化教育形式的存在,允许俄罗斯公民接受各种不同形式的教育,保障实现自己的教育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联邦《宪法》暴露出政府对非国立教育的矛盾心理,对“究竟允许非国立教育发展到何种程度”没有清楚的认识,这体现在它始终没有正面提及“非国立教育(机构)”,对所支持的“不同形式的教育”含糊其词,允许它存在的最现实的目的就是希望它帮助政府缓解高等教育问题。
此后,非国立高等教育开始了规模大扩张,迎来了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发展走的不是工业私有化的道路,它没有将国立大学私有化,而是建立一种全新的所有制形式的学校,成为国立高等教育的有益补充。
非国立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不可避免地抢夺了国立的教育资源,引起了“国立派”的不满,他们打着“加强教育主管部门参与、管理非国立高等学校的办学过程,强化教育主管部门的权威地位”的旗号,强烈建议政府修改联邦《教育法》。“国立派”认为,联邦《教育法》为非国立高等学校制定的政策框架太宽泛,条款太优惠,给予的保护性措施和“独立权”过于强大,他们担心这可能会导致国家失去对其教育过程的影响和管理。此外,他们还认为,非国立高等学校办学经费不足,缺乏对消费者的社会保障,教师队伍流动大,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低。在他们的游说下以及教育主管部门出于战略考虑,从1994年中期起,俄罗斯政府相关部门开始了修改《教育法》的工作,在1996年1月13日新版联邦《教育法》(№ 12-ФЗ)颁布。
新版联邦《教育法》在“非国立教育机构”(11.1.)下增设了若干规定,强调非国立教育机构独立的法人地位,规定它具有组织统一和财产独立的特点,独立地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此外,还修改了某些条款,比如:将1992年版第41条“国立和市立高校按照与自然人以及非国有企业、机关、组织签订的合同,有偿培养法律、经济、管理等方面的人才时,招生人数不得超过该专业招生总数的50%”改为“招生人数不得超过该专业招生总数的25%”。第41条从表面上看是在保护非国立高等教育,实际上则是政府希望保留这些专业免费学额的数量以控制国立大学的商业化进程,但在保护国立高等教育利益的同时,却促使了追求短期利益的非国立高等学校的蜂拥而至。在物质短缺、没有足够教师和教学场地保障的情况下,非国立高等教育质量低下的问题暴露了出来。
1996年8月7日联邦《高等及大学后职业教育法》(№ 125-ФЗ)颁布,它是联邦《教育法》的细化和补充,“鼓励非国立高等学校创办和运营”(3.6.),将非国立高等教育纳入了国家高等教育系统。
联邦《高等及大学后职业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非国立高等学校的权限划分完毕,非国立高等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大,1999/2000学年非国立高等学校毕业生比1993/1994学年增加了282%,学校数量也增加了4倍多,一些在1992年之后创建的学校开始申请国家鉴定,非国立高等教育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高峰期,成为俄罗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
通过对联邦《高等及大学后职业教育法》具体条款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的非国立高等教育政策的两面性暴露无疑。一方面非国立高等教育减轻了政府的负担,政府不可能轻易放弃它,便将通过国家鉴定的非国立高等学校和国立大学置在同一层面,用统一的国家教育标准要求它们,但实际上两者并不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国立高等教育始终被视为国家的主体教育形式,因为“苏联时期形成的国立高等教育在世界上具有很高的声望,我们有义务、也必须将它保持住,并努力发展起来”[3]。
3.国家宏观调控非国立高等教育(2000年初至今)。非国立高等教育规模的无序扩张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教育质量低下,教学基本设施不足,教师管理效率低,成为“兜售教育文凭”的基地,似乎在给“学术上失败的人开展另一级别的教育”。[4]这些不仅损害了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声誉,而且污浊了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俄罗斯政府开始重新依赖国家职能整顿非国立高等教育系统的混乱状况,利用国家机器加强对其的控制。
1999年12月30日普京在《独立报》上发表了纲领性的文件——《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主要教训之一是“俄罗斯一直在摸索着、盲目地前进,对全国性的目标和发展水平、如何使俄罗斯成为世界上一个发达、繁荣和伟大的国家,缺少一个明确的概念……缺少一个为期15—20年或者更长年限的远景发展战略”。俄罗斯不仅过去、现在,而且将来仍然是一个大国,因此必须尽快并且快速地发展,因为俄罗斯需要多年的努力才能够达到世界上较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为此,“国家需要制定一项长期的全国性的发展战略”[5]。
“任何一国教育政策的制定都不是一个自然、自动的过程,而是一个人为的、有选择性的过程。”[6]在这样的背景下,2000年1月14日~15日,全俄罗斯教育工作者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通过了《联邦教育发展纲要》《俄罗斯联邦教育民族学说》与《到2010年俄罗斯教育现代化构想》等联邦级教育发展的战略性文件。这些教育文件集中体现了国家“强国、强权”的意志,将高等教育问题提升到国家层面,标志着俄罗斯高等教育回归国家,结束了非国立高等教育放任自流、自由发展的状态,非国立高等教育进入了规范管理阶段,形成了与国立高等教育并存,两者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
2004版联邦《教育法》将支持非国立高等教育的经济优惠政策取消殆尽,比如:取消了1996版“允许国立大学若干专业招收有偿教育生人数不得超过该专业招生总数的25%”的规定,不再规定招生比例和限制专业;将第11-1“非国立教育机构”改成“国立和非国立教育机构”,说明决策者已经不再将非国立高等教育视为一个特殊的领域,给以特殊的扶持政策,而是让两者展开竞争,这种“适者生存”的政策价值取向严重地阻碍了非国立高等教育的继续发展,因为“发展中的非国立高等学校还需要国家的特别支持和保护,俄罗斯立法删除了能够使非国立学校站稳脚跟的条款,极大地恶化了非国立学校的生存与发展环境”[7]。
今天,就整体实力和所发挥的功能而言,“国立教育是整个教育系统强大、坚实的核心,包在它外围的那层薄薄的、且不断变厚的表皮就是非国立教育”[8],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任重而道远。
二、非国立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分析
一项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如果说非国立高等教育复苏的主要原因是政府退出部分教育空间、自由市场介入的结果,那么日后十几年的发展历程却十分清晰地显示出,这是政府、市场与学校之间在利益驱动下的力量博弈,在博弈过程中,政府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引导教育政策向政府利益诉求的方向发展,市场和学校则发挥着从属性的作用。
1.政策决策者结构单一的结果。教育政策的决策过程是“各种具体利益的代表之间的力量相互博弈并取得自身最大权力的过程”[9]。因为参与的每一方主体都是该利益团体的代言人,在决策过程中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追求各自的需要,谁的意志对政策的决策过程施加的影响力最大,教育政策所体现的价值就倾向谁。
非国立高等教育政策的决策过程没有允许学校和市场参与进来,政府是唯一的决策者,行使着非国立高等教育生死攸关问题的决定权,教育政策价值取向自然是完全随着政府的利益需求而变化的。尽管高等教育职业同盟会和非国立大学同盟会也参与了决策过程,“其实也只是一种装饰而已,他们并没有真正地行使自己的参与权和表决权”[10],所拥有的关于非国立高等教育的丰富信息并没有弥补政府信息的不足。可以说,非国立高等教育政策是缺乏民主的,单一的、纯粹的中央集权主义的“一家之言”,是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
2.对新型的非国立高等教育缺乏理论思考的结果。从政策学的角度看,政策的制定需要对所要制定政策的领域进行必要及全面的分析,找出它的规律和特点,并以此确立政策目标和实施方案。俄罗斯教育政策的决策者自觉或不自觉地用管理国立大学的办法去约束非国立高等学校,并没有注意到后者之所以被称为“非国立”是因为学校的创办者和所有制形式完全不同于前者,有着由自身属性所决定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可以说,前文所有的教育政策在制定时前期准备都不是很充分,对“非国立高等教育究竟是什么”并没有认真地思考,非“度体量衣”的政策带有很强的“国立”味道,最终导致教育政策既没有满足非国立高等教育的需要,又致使国立和非国立之间在相互关系上始终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和谐因素,使得政府、社会各界对非国立高等教育始终有一种不认同的感觉。
3.政府短期行为所至。法要统一,这样不会因人而异;法要固定,这样不会朝令夕改。由于俄政府对非国立高等教育缺乏系统的认识,在制定教育政策时,缺乏全盘考虑,只追求短期利益,因而教育政策带有鲜明的临时性特点。比如联邦《教育法》在1992年至2008年底大大小小共经历了43次修改,联邦《高等及大学后职业教育法》从2000年至2008年也被修改了30次,其中也涉及到了非国立高等教育。②当问题出现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因不能根本性地解决问题致使教育政策不断被修改,政策环境频繁变迁。而教育政策环境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学校办学的稳定,让学校疲于应对。
4.历史的惯性选择。俄罗斯的国家发展史自古以来就是集权的中央制,无论从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还是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前苏联,都是高度的中央集权,这也是历史上非国立高等教育时“兴”时“衰”、断断续续发展的原因。从历史上看,自由主义在俄罗斯并没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即使是20世纪90年代起的社会主义制度被自由资本主义取代,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资本主义。在非国立高等教育经历了十几年的缺少国家监控、无序的发展之后,最终又返回国家控制的轨道,这既与当今俄罗斯国家民族主义相吻合,也是俄罗斯传统惯性的选择。
三、结 语
俄罗斯非国立高等教育是客观现实的产物,自复苏之日起就肩负着扩大教育机会、提供多样化教育形式、促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使命。它使得俄罗斯结构单一的高等教育系统成为历史,为国立高等教育提供了借鉴,增添了办学活力。
今天,非国立高等教育还未发育成熟,更需要国家的呵护,“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政策只能说是政府营造了一个竞争性的教育环境,向国立高等教育倾斜的教育政策并没有以公平竞争为原则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政策环境已经威胁到了非国立高等教育的生存。更为严峻的现实是俄罗斯已经陷入了巨大的人口危机,2009年秋享受国家财政预算的高校学额已经超过了中学毕业生的数量,意味着国立与非国立大学对教育资源的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如果国家教育政策环境不做倾向于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变迁,后者将很快失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但同时,创建市民社会、营造一个民主政治生长的多元化社会是俄罗斯长期的战略目标,这又为非国立高等教育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俄罗斯高等教育的历史经验都表明,教育机构形式多样化是推动国家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进步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所以俄罗斯非国立高等教育有继续发展下去的社会基础。“任何单一力量对大学的极端控制都是危险的。”[11]“谁是政策的决策者”、“政策的决策过程如何进行”决定着一个非国立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政府、市场与高校三者民主协商、取得平衡是未来非国立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理想基础。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以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内在属性为根本出发点,从其法律地位去理解所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依据三个原则有意识地打造一个适宜于非国立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环境:(1)国立和非国立高等教育统一原则,拒绝它们相互排斥,而是让其相互补充;(2)权利和义务统一原则,即赋予其多少权利,使其担负多少义务;(3)不允许颁布与联邦《宪法》相悖的教育政策。
注释:
① 括号里面的数字11.1.指第11条第1款,文中其他类似处不再特殊注明。
② 数据是对Сектор Закона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网站上的资料整理而成。
③ http://stat.edu.ru./stat/vis.shtml(俄罗斯教育统计网站)。
[1] И.Л.Ручинская. Антикризис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и высше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России[J]. Полемика,2007(3):38.
[2] Ж.Адриан, Э.Бентабет, А.Винокур, Т.Линей. Белая книг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Ч.1[M].Москва: Изда-во МЭСИ,2000:66.
[3] А.В.Сиволапов.К новой модели обучения-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й подход[J].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1994(3):46.
[4] Dan E. Inbar, Wadi D. Haddad, Terri Demsky, André Magnen, John P. Keeves.教育政策基础[M].史明洁,许竞,尚超,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143.
[5] В.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N].газет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1999-12-30.
[6] 肖刚,黄巧荣.影响教育政策制定的因素分析[M]//袁振国.中国教育政策评论.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81.
[7] Светлана Чичкина.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ектор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принес на рынок конкуренцию[J].Обучение & карьера,2006(4):27.
[8] И.М.Ильинский.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вузы России:опыт само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M].M.: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универститета,2004:104.
[9] 陈正华.我国教育决策民主化的本质、问题及其对策研究[M]//袁振国.中国教育政策评论.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81.
[10] И. М.Ильинский. У нас амбициозная задача: стать лучшими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вузы россии намерены быть такими же престижными, как кембридж и принстон. : интервью президента Нац. союза негос. вузов И. М. Ильинского о перспективах негос.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N].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2004-02-23.
[11] 张德祥.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市场、大学”新型关系的研究总报告(二)[J].辽宁教育研究,2004(10):18.
On the Policy of the Non-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Transitional Russia
GU Hongfei
(Xiamen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5,China)
During the past 20 years of development of Russia’s non-national high education, its educational policy environment, which he relied on, undergo several outbreaks of change. Government’s attitude towards non-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changed from encourage, support to regulate, manage gradually. All these changes are due to the result of Government’s interest. The main reasons include single structure of policy decision makers, lack of new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 of non-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short-term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inertia historical elements.
non-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non-governmental higher education; education policy; Russia
2009-12-02
教育部2007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转型期俄罗斯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研究”(07JA880019)的研究成果之一
顾鸿飞(1969- ),女,吉林吉林人,副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G512.72;G648.7
A
1671-2714(2010)02-0013-06
(责任编辑毛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