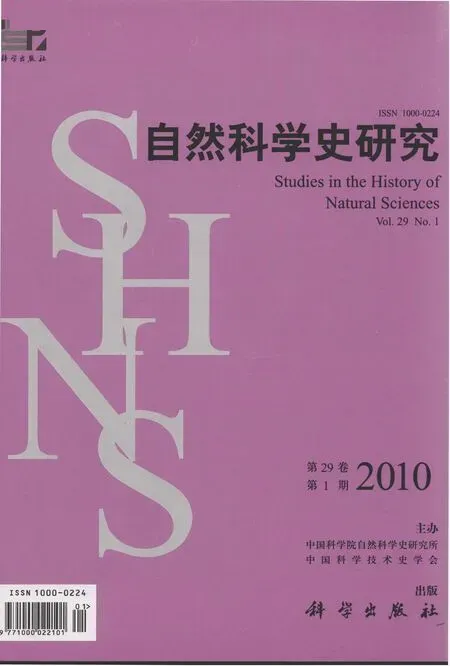元明中国伊斯兰天文机构研究二题
2010-01-25陈占山
陈占山
(汕头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有目共睹,近数十年来学术界对于元明时期有关伊斯兰天文学的研究已有很多进展,取得不少成绩,但由于这一领域所牵涉的问题实际上颇为广泛、复杂,加之学者们的学术兴趣和关注点有所不同,由此应该看到迄今为止仍有不少问题尚没有被明确提出并加以研究;一些问题虽在以往的成果中已有一定的涉及,但尚存在着一些不妥当的甚至错误的说法而没能在全面梳理现有资料的基础上予以明确的论述和纠正。笔者认为,本文选取、讨论的两个论题就属于或存在上述问题。而对这些问题进行专门、认真的研究,其学术意义显而易见:探讨元明政府设置伊斯兰天文机构的动机,有助于深切了解伊斯兰天文学在中国官方被接受及在华流播演变的政治生态、文化背景,而考察这种机构受命举行星宿祭祀(即所谓的“禜星”),则不仅有益于全面展示和认识伊斯兰天文家在华工作的多样性,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拓展本领域的学术研究空间。
1 元明政府设置伊斯兰天文机构的主要动机
元明政府在中国传统天文机构之外,另设伊斯兰天文机构,其动机究竟是什么?有关文献没有明确记载。或正是出于这种情况,可能还由于一些先入之见,使得学术界曾经存在过一种说法,即认为这种机构设置的动机或说主要职责是元明政府为满足国内伊斯兰教徒宗教生活的需要,为其编订回回历书①如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说“我国少数民族中有不少信奉伊斯兰教。元政府为了满足这些教徒的需要,设立了回回司天台,每年颁行回回历书”,“(明朝)也仿照元代的办法,设立回回司天监,后来把它改为回回科并入钦天监,它的职责就是每年编造回回历书”(《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 238—239页)。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也说:“为了适应国内各伊斯兰民族的宗教和生活习惯,朱元璋是仿照元朝的办法,设立回回司天监,后来又把它并入钦天监,成为回回科。它们的职责主要是编制每年的回回历书”(《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 39页)。。不过,随着有关研究工作的广泛开展和深入,目前上述说法已很少再见被研究者沿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根据有关文献记载解释上述机构的职责时,已有颇为精当和全面的说法,如陈美东先生说“回回司天监‘掌观象、衍历’,观测、推算与占卜天象,以及依万年历编算历日,是其职责。”[1]但由于所讨论问题的中心和关注点不同,应该看到有关元明政府设置伊斯兰天文机构的动机 (或说目的),至今尚没有被明确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当然也就谈不上做专门、系统的讨论。笔者认为元明政府设置这种机构的动机,或说主要动机,主要是要利用伊斯兰天算家的星占术。关于这一点,可通过以下两方面的考察得到切实的说明。
首先,伊斯兰天文机构的始设者既然是蒙元统治者、是忽必烈,那就有必要看看他们在与此有关的事务上的一贯作风,看看其需要究竟是什么。文献记载表明,忽必烈之前蒙古统治者有热衷求卜的传统。成吉思汗就十分迷信占卜:“帝每征讨,必命 (耶律)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胛以相符应[2]。”窝阔台亦乃父风格,凡事必决于一卜。太宗四年 (1232年)三月,木华黎之孙塔思向其请求:“愿分攻汴城一隅,以报陛下”。帝壮其言,命卜之,不利,乃止[3]。定宗贵由执政时间很短,笔者经眼文献似未留下这方面的记载,而其妻斡兀立海迷失摄政时期“嗜巫术,终日与珊蛮共处”([4],263页)。至宪宗蒙哥“酷信巫觋卜筮之术,凡事必谨叩之,殆无虚日,终不自厌也”[5]。亲眼目睹过此状的欧洲人鲁不鲁乞写道:“正如蒙哥汗所承认的,他们的占卜者是他们的教士,占卜者命令做的任何事情,统统立即执行,毫不迟延。……占卜者们宣布有利于或不利于进行各种事情的日子。因此,除非他们同意,蒙古人从来不进行军事演习或出发作战。”[6]鲁不鲁乞的记载具有代表性,可以真实地反映蒙哥之前蒙古统治者的一贯作风。一般说来,蒙哥之前采用的卜术十分原始。赵珙《蒙鞑备录·祭祀》载:“凡占卜吉凶、进退杀伐,每用羊骨,扇以铁椎火,椎之看其兆坼,以决大事。类龟卜也。”[7]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也云:“其占筮,则灼羊之杴子骨,验其文理之逆顺,而辨其吉凶。天弃天予,一决于此,信之甚笃,谓之烧琵琶。事无纤粟不占,占必再四不已。”②据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鲁不鲁乞的记载可印证上述说法,见《出使蒙古记》[6]第 182—183页。
文献记载同样表明,在听命于卜者这一点上,忽必烈完全继承了他前任的作风,所谓“帝笃信星术”:“汗八里城诸基督教徒、回教徒及契丹人中,有星者、巫师约五千人,大汗亦赐全年衣食。……其人惟在城中执术,不为他业。”[8]只是必须指出,在对卜者的利用上,忽必烈即位后有一个明显的转折:由此前主要听命于萨满或自灼动物的骨头预卜,到此后转变为主要求教于星占家。据拉施特《史集》,在中国为伊斯兰天文家设置天文台的想法始于宪宗蒙哥,但由于某些条件不具备,才使这一愿望暂告搁置[9]。而忽必烈即位前就“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札马鲁丁等以其艺进”[10]。他们必然要以蒙哥时期未实现之愿望,复请于忽必烈,遂有置西域星历司、建回回司天台事。而也正是自忽必烈统治开始,大力起用拥有不同传统的中国天文家和阿拉伯天文家,遂使其择吉推卜的方式为之一变。那么,蒙哥是如何看待建天文台这件事的?忽必烈又是抱着什么目的最终将其付诸实施了呢?对此,汉文献不见相关记载,而多桑笔下伊儿汗国马拉加天文台建立之缘起极富启发性:
天文学家纳速剌丁求择地建一天文台,旭烈兀许之。纳速剌丁曾建言曰:“欲卜事变吉凶,必须编定良善天文表,按日指示日月五星之方位。”([4],93—94页)可是,当纳速剌丁将建台的经费单呈批时,“旭烈兀嫌其费巨”:
乃询天文台有何功用,而所费如此之多。纳速剌丁请其命人持一铜盘击之山上,士卒闻声皆仓卒出帐观之。旭烈兀与纳速剌丁知此声之所自来,则不为动。纳速剌丁曰:“星宿运行认识之功用在此。盖其预其事变,知之者可能预防,不知者则惊愕也。”旭烈兀许以巨款建天文台。([4],93—94页)
这两段文字最引人注意的是,作为中世纪伊斯兰天文学界巨星、旭烈兀的亲信大臣、同时也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的纳速剌丁竟然对天文台的功用作了这样的解释,特别是只字未提编订教历之类的事情。显而易见,无论是与忽必烈,还是与后来续设伊斯兰天文机构的明太祖朱元璋、清世祖福临统治下的中国相比,在伊斯兰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伊儿汗国才是穆斯林的海洋。难道旭烈兀没有觉察出伊斯兰教徒的这一需要,纳速剌丁也没有想到吗?其实,纳速剌丁的解释没有问题,与中世纪的其他天文学分支及其相关机构的主要使命一样,伊斯兰天文学的主要任务确实就如纳速剌丁所说“编定良善天文表,按日指示日月五星之方位”,目的即在于“(预)卜事变吉凶”。鉴于处于同样的历史时代,且有着大体相同的文化背景,似可以认定蒙哥、忽必烈同意为伊斯兰天算家建立天文台以及忽必烈进一步为之设立配套机构回回司天监,应与旭烈兀的着眼点完全一致:他们看重的是天文台测定星宿、预卜吉凶的功能,目的是要利用伊斯兰天算家的星占术。
至于伊斯兰天文机构在明朝的复置,的确有萧规曹随、因循前朝旧例的因素。如朱元璋自己就说:“朕仰观天象,敬授民时,乃循近制,仍设其职。”[11]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实际上仍然是为利用伊斯兰的星占术,如他曾明确表白:
天文之学,其出于西域者约而能精,虽其术不与中国古法同,然以其多验,故近世多用之,别设官署,以掌其职,盖慎之也。[11]我们认为这段表白足以说明朱元璋之本心。
其次,中国本来就具有自己的星占术,何以要从国外引进另外一套?要而言之,那主要是由于伊斯兰星占术拥有中国传统的一套所不具备的某些优长。那么,与中国传统的一套比较起来,伊斯兰星占学究竟有何优长?由于探讨的是元明政府的“接受史”,所以在这里笔者无需作其他援引,只要有效展示这一时期或稍后对此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中国人士的看法就可以了。笔者以为可以举耶律楚材、朱元璋、徐光启和梅文鼎四人的有关言论来说明这一问题。耶律氏是随成吉思汗西征、并最早对伊斯兰天文、历法之学有深度了解的学者,他“尝言西域历五星密于中国”[12]。“五星”就是五大行星,“五星密于中国”,也就是说伊斯兰天算家对五大行星位置的观测和推算比中国传统的一套要来得精密。至于朱元璋,他在洪武十五、十六年曾为受命主持翻译回回天算书籍的汉、回官员说过:“迩来西域阴阳家,推测天象至为精密有验,其纬度之法又中国之书所未备。” 的确,若是朱元璋自己,他的发言权可能不够;可是他有“九五至尊”的身份,他的说法一定是来自其身边的某些于此领域最有发言权的学者。其看法主要指出伊斯兰星占学推测天象的“至为精密有验”,还特别指出前者体系中的“纬度之法”是中国传统体系中所没有的。徐光启是晚明杰出的天文历法大家,兼通中西,他说:
五星一节,比于日月倍为繁曲。汉以后治历者七十余家,而今所传《通轨》等书,其五星法不过一卷。以之推步,多有乖失。所以然者,日月有交食可证作者尽心焉,五星无有。故自古及今,此理未晰也。回回历则有纬度,有凌犯,稍为详密。[14]
而清初同样贯通中西的天文、数学大家梅文鼎也表示过与徐光启类似的看法:
五星之迟、疾、逆、流,汉以前无言之者,汉以后语焉不详。虽《授时历》号为精密,而于此未有精测,至西历乃能言之。[15]
这里,梅文鼎所说的“西历”是包括回历的,只要去翻翻他的《历算全书》即可证实这一点。综上所引,各家看法是伊斯兰星占学对五大行星的观测和推算技术要比中国传统的一套先进、完备,其中的一些还是中国传统的一套所缺少的。而种种迹象表明,伊斯兰星占学所具备的这些优长的知识和技能,对于满足中国传统星占术中“月、五星凌犯”天象精确预报的要求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得到中国当政者的特别重视。
现在,可以为本节讨论的问题作个小结:无论是从回回天文机构的始设者蒙元统治者的一贯作风看,还是就这种机构续设者朱元璋的有关言论观之,他们的动机都很明确,就是要利用其人的星占术。而伊斯兰星占术的价值就在于其“不与中国古法同”,而“推测天象至为精密有验”,由此独具一格,拥有了可与中国星占术相辅而行的参考价值。
2 禜星与元代伊斯兰天文机构的“职事”
据《元史·祭祀一》称:“日星始祭于司天台,而回回司天台遂以禜星为职事。”这样就把回回天文机构的职责与“禜星”联系起来了。可是,究竟什么是 “禜星”?它怎么会成为回回天文机构的“职事”的?与此有关的问题目前尚未见笔者之外的学者注意过。既然,文献明确记载此事与伊斯兰天文机构有关,那就有必要纳入到我们的研究中来。
首先,什么是 “禜星”?对之,明初修《元史》者已称 “未详”[16],这就为后人的考察留下很大的困难。考虑到《元史》汉语语境的关系,我们还是先从汉文典籍中追寻它的源头。从种种迹象看,禜 (yǒng,音永)星本是一种相当古老的祭祀。据《周礼·春官》记载,其为大祝所掌六祈之一。六祈者,“一曰类、二曰造,三曰襘,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说”。又,何谓 “祈”?郑氏注云:“祈,嘄也。谓为有灾变,号呼告于神以求福。天神人鬼地祈不和,则六疠作见,故以祈礼同之。”对于 “禜”,郑玄注曰:“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左传·昭公元年》曰:“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由上引述,已足以说明禜星在古代中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活动了。
不过,由于被规定为伊斯兰天文机构的“职事”,那么,它是否有来自阿拉伯的可能?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一方面伊斯兰教唯崇奉真主安拉,反对任何偶像崇拜,因而不可能祀星;另一方面,伊斯兰在华传承的唯一汉译星占文献《明译天文书》中也无任何这类活动的痕迹。
那么,元代统治者举行“禜星”活动,其直接的文化传承究竟来自于哪里呢?鉴于蒙古统治者兴起于大漠,元朝文化是吸收、融合包括汉族在内的周边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由此笔者以为这种活动的直解来源有下述三种可能:一是从中原的传统文化中来。的确,秦汉以后至宋代之前,以 “禜星”为名目的星宿祭祀活动再未见载于有关文献,可是名异实同的相关星辰 (星神)的祭祀活动却从未停止,如历代正史中的《礼仪志》(或《礼乐志》、《祭祀志》)就有程度不同的反映。二是藏传佛教。元朝统治者与喇嘛教高僧的亲密关系是众所周知的,而喇嘛教来自于佛教密宗,密宗经典中就有许多有关星占和以七曜或九曜为对象的禳灾祭祀活动①在汉文《大藏经》中,这类文献较集中的地收在密教部。如《大正新修大藏经》 (台北:大藏经刊行会,1983年)第 21册所载 1299—1312号共 14种均为这类典籍。。三是来自于西夏。12世纪,西夏王朝通过翻译藏、汉佛教,接触并接受了密教中的星辰崇拜,使得这种活动在西夏地区颇为兴盛②对此种事实的描述和研究,可参考以下两文:(苏联)H·A·聂历山著,崔红芬、文志勇译,《12世纪西夏国的星曜崇拜》,载《固原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 2期; (俄)萨莫秀克著,谢继胜译,《西夏王国的星宿崇拜——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黑水城藏品分析》,载《敦煌研究》2004年第 4期。。笔者认为上述三条线索都有可能是元朝统治者禜星活动的直接来源。
至于这种活动何以被规定为伊斯兰天文机构的职事,那首先应是由于禜星的对象与七曜或九曜有关,也就是说与“天文”有关。而之所以会与伊斯兰天算家联系起来,一方面伊斯兰天算家要想在元朝官方天文机构立足就不能不接受最高当局要求做的任何事情;另一方面,有记载表明,此事伊斯兰天文机构远未得专,并行汉人天文机构禜星的次数实倍于前者。下据《元史》所载,将有元一代禜 (祭)星活动资料搜罗,制成表1,以资考证。

表1 《元史 》1)载元代禜(祭)星活动

续表1
需要说明的是,还有三次禜 (祭)星未被列入:至元三十一年 (1294年)五月壬子祭紫微星于云仙台;至治二年(1322年)五月庚寅禜星于五台山。这两次禜、祭星活动均不在天文机构进行,亦不详由何派天文家 (或系别的官员)主事。又,至顺元年 (1330年)七月壬子,“命西僧禜星”。“西僧”通常即指藏传佛教僧人,这次也未说明禜星地点。
从上所具可见,上述祭祀星宿的活动,实际上主要是元朝汉、回两套天文机构的共同职事。故可综合,放在一起讨论。据表1,我们以为至少有下述三个观察点值得注意:
(1)禜星的种类。绝大多数情况都不详确指,估计当时举行仪式时就不曾分别,属泛禜情形;有少部分具体指出了所禜之星,计有太阳和火、水、木、金、土五颗行星。而火星(即荧惑)似被特别强调。伊斯兰天文机构总共 9次禜祭中,唯一有确指的 1次即以荧惑为对象。汉人天文机构 3次有明确目标的禜祭中 2次都有它。火星在伊斯兰和中国传统星占学中,均属灾星。如《明译天文书》载:“土星、火星、凶。土星性极寒,火星性极燥热。因极寒、极燥热,故凶。”(第一类第三门)“若火、土二星相冲,或二弦照,则有灾祸征战之事。”(第二类第三门)[17]而《汉书·天文志》说:“荧惑为乱,为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所居之宿国受殃。”由此,元朝伊斯兰、汉人天文机构把火星等作为祭、禜的重点,是深合禜星消灾弭变之本意的。
(2)禜星的时间及重要性。若以“年”为单位,即可发现两套机构禜星之具体月份除十月为空白外,在其他的十一个月中均有举行,殊无规律。据《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五年十二月戊寅:“敕二分二至及圣诞节日,祭星于司天台。”但这五个时日一般应分别在二月 (春分)、八月 (秋分)、十一月 (冬至)、五月 (夏至)和八月 (中国传统阴阳合历比现行公历迟一月;圣诞指忽必烈生日,其生于八月),似也多不合。另,政府一般向两套机构下达的禜星时间不同,但也有例外,如天历二年 (1329年)八月举行的一次即在同一个时辰;禜星所费时间大部分不具,但就有记载的两次看,英宗执政初在回回司天监举行的一次长达40昼夜,延祐五年五月在司天台进行的一次是 3昼夜,可说都费时不短。若再把元政府先后派遣过集贤院使阿里浑萨理、太常卿丑闾、昭文馆大学士靳德进及平章政事王毅等主持、参加汉人天文机构禜星等因素考虑在内,可知蒙古统治者对这种活动非常重视。又,有元一代 11任皇帝执政,禜星次数最多者为泰定帝也孙铁木耳。其执政不到五年 (1323年 9月至 1328年 7月)却禜星 9次,约占元朝天文机构总共禜星 30次之三分之一。从《元史》等有关文献看,泰定一朝,灾变连年,国家、民众处于危难之中。外籍文献也载:“也孙铁木儿即位之初年,地大震,月全蚀、大雨淹没田亩,复有旱蝗等灾,尤以彗星见一事,为中国人及蒙古人所警惕,盖其视为天怒之征”([4],363页)。可见,如此频繁的禜星活动,必然与当时灾变的频生有紧密的联系。
(3)禜星与星占的关系。从现传世中国传统星占学著作来看,其星占预报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是“凶多吉少”,所以预报的目的之一就是图谋“先期救护”,消灾弭变。而禜星为救护措施的一种,所以它与星占密切相关。
明王朝建立后,最初也从元朝继承了禜星的活动,但洪武二十一年却最终为这一活动画上了句号: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增修南郊坛壝于大祀殿丹墀内,迭石为台四,东西相向以为日月星辰四坛,从祀其朝日夕月,禜星之祭悉罢之。[18]
综上所述,禜星是一种古老的以星辰为对象的禳灾活动。元朝统治者将其作为包括伊斯兰在内的两套天文机构的共同职事,从远源上讲可以追溯到先秦,从近缘上看很可能接受的是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星辰 (星神)祭祀或藏传佛教密宗经典中的星曜禳灾仪式和西夏王朝星辰崇拜等文化传承。这方面的探讨可以说刚刚开始,还有较大的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1 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523.
2 (明)宋濂,等.元史·耶律楚材传 [M].卷 146.北京:中华书局,1976.
3 (明)宋濂,等.元史·木华梨传附 [M].卷 119.北京:中华书局,1976.
4 (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M].冯承钧译.上册,商务印书馆,1936.263.
5 (明)宋濂,等.元史·宪宗纪 [M].卷 3.北京:中华书局,1976.
6 (英)道森.出使蒙古记[M].吕浦译.周良宵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216—217.
7 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M].北京:文殿阁书庄,1936.
8 马可波罗行记[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54.103.
9 (波斯)拉施特.史集 [M].卷 3,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3—74.
10 (明)宋濂,等.元史·百官六 [M].卷 90.北京:中华书局,1976.
11 (明)王祎.王忠文集·温都尔除回回司天少监诰[A].卷 1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Z].第 122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2 (元)宋子贞.国朝文类·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A].卷 57.四部丛刊初编[Z].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13 (明)吴伯宗.明译天文书序[A].明译天文书[M].涵芬楼秘笈本,1927.
14 (明)徐光启.新法算术·缘起[A].卷 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Z].第 78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5 (清)梅文鼎.历学疑问·答沧州刘介锡茂才[A].卷 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Z].第 79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6 (明)宋濂,等.元史·祭祀一 [M].卷 72.北京:中华书局,1976.
17 明译天文书[M].涵芬楼秘笈本,1927.
18 (清)秦蕙田.五礼通考[M].卷 3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Z].第 13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