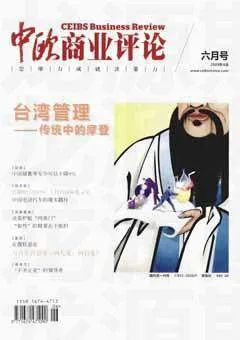黄少卿:中国储蓄率至少可以下降4%
2009-12-29黄少卿
中欧商业评论 2009年6期
如果将生产要素价格提高到合理水平,并且强化国有企业分红,那么,中国的家庭在2007年可以多收入1.455万亿元,这将使中国减少大约1万亿元的储蓄。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扬教授5月15日撰文阐述当前中国保持高投资的重要性,其基本逻辑是,在中国高储蓄不能有效下降的前提下,唯有通过高投资和高出口来“吸收”掉这些储蓄,否则有可能陷入通货紧缩。因此,扩大投资是当前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逻辑的前提——中国高储蓄是否真的有那么坚实?真的不能有效地降下来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了解中国的高储蓄是怎么来的。李扬教授认为,中国的人口参与率还在提高,人口红利依然为正,加上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改革,因此短期内看不到储蓄率下降的迹象。这一分析如果仅仅用于讨论家庭储蓄,基本上是正确的。的确,中国家庭储蓄占GDP的比重最近几年都保持在16%的水平,和中国情况类似的印度是22%,随着收入的提高,家庭部门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到印度的水平都是可能的。
可是,中国的情况是,家庭储蓄并不占整个经济中总储蓄的绝大部分,甚至不是最大的部分。根据统计数据,2004年以来,企业部门储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总储蓄的最大来源,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20%,再加上政府部门储蓄占GDP比重接近10%,因此,中国的总储蓄率近年来保持在50%左右的水平。
相比于本世纪初,2005年中国的总储蓄率提高了大约10个百分点,这10个百分点中,有6个百分点是由企业部门储蓄增加所贡献的,有2个百分点是政府部门贡献的,由家庭部门贡献的只有2个百分点。考虑到中国政府的收入与企业的经营状况有更大的关系,因此,近年来总储蓄水平不断升高是企业利润大幅增加的表现。
如果中国国民收入在家庭、企业和政府之间的这一分配格局不能发生变化。那么,李扬教授的观点便不会发生动摇。但是,这样的分配格局是否合理?能否改变?如何改变?
中国企业从2000年以来利润迅速增加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根据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郑玉歆等人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分析,“十五”期间,中国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13%。显然,效率的提高是企业效益不断改善的重要基础。然而,也有不少人指出,中国企业的效益是建立在对生产要素和重要资源产品价格低估的基础之上的。
分配格局如何改变
中国的新增非农部门就业劳动力中超过一半(每年大约700万人)是农民工,这些劳动力由于享受不到正常的社会保障,实际上企业支付的劳动力成本是不足的。此外,根据北京大学卢锋等人的计算,从2000年以来,中国的1年期实际贷款利率从大约12%下降到不到1%,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高增长速度的国家而言,这一实际利率显然远远低于均衡意义上的利率水平(自然利率)。还有土地价格的低估问题,据估计,我国长期的工业用地批租价格相比于“招、拍、挂”方式的市场价格要低40%以上。此外,还有能源、电力、水和环境等重要资源的价格也是被低估乃至根本付诸阙如。
生产要素的价格被低估,意味着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要素的所有者——家庭的收入被人为压低了。大致估算,2007年,企业部门给2亿左右的农民工少支付了占他们工资总额20%左右的社会保障金,约合4 000亿元;如果把中国的短期均衡利率估计为4%,则企业部门大约少支付了3个百分点的贷款利率,约合7850亿元。仅这两项相加,就意味着家庭部门少收入了近1.2万亿元,也意味着2007年企业部门由于劳动力和资金两大要素价格的低估导致的虚增利润占其实际利润的43.6%。
如果在初次分配之外,再由政府部门对国有企业的利润进行二次分配,则家庭收入的水平还可以更高。国资委从2007年开始要求部分国有企业按照税后利润的10%或5%分红,假设分红的比例提高到50%(根据世界银行专家的估算,这大体是美国工业企业的分红水平),并且进一步假定中央政府按照相同数量减征个人所得税(或者以其他形式转化为居民收入,如为个人缴纳社会保障金),那么,刨掉成本低估虚增的利润(姑且也按照43.6%的比例计算),2007年,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大约2 550亿元。
由此可以算出,如果将生产要素价格提高到合理水平,并且强化国有企业分红,那么,中国的家庭在2007年可以多收入1.455万亿元。这部分收入如果留在企业部门,则100%成为国民经济的储蓄,而如果转移到家庭部门,按照当前中国居民的边际储蓄倾向0.3计算,则这一收入结构的调整将使中国减少大约1万亿元的储蓄,从而使整个经济的储蓄率下降足足4个百分点。
也许有人认为,对于中国接近50%的总储蓄率而言,区区4个百分点并不足以使消费一储蓄结构发生根本变化。但是,笔者认为,如果再考虑企业应该更多地为环境保护支付成本(可以显著减少居民的医疗支出。由此减少预防性储蓄)、要素价格比例关系理顺后资源配置的优化可以增加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及政府可以通过减税来抑制近年来财政收入的大幅增加,那么,居民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还能够进一步提高。而且,如果利率和汇率调整到合理水平,还将有助于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房价的下降也将带动中国居民储蓄率的下降(根据莫迪利安尼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房价泡沫起来后,日本的国民储蓄率提高了)。
笔者推测,经过一系列结构改革,中国经济的总储蓄水平应可以降到40%以下,与日本和韩国工业化后期的水平相当。
总之,中国当前首要的问题不是要去保持多高的GDP增长率,而是要进行结构改革,形成合理的生产要素价格体系,优化资源配置,增加居民在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从而形成经济的良性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