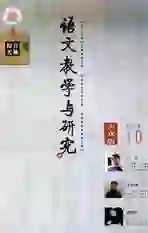韩愈《师说》的四个字
2009-11-28张文颖
张文颖
作为一篇传统教材,《师说》的教学已有不少人作过成功的探索。我教《师说》,只抓了四个字,即“师”、“愚”、“圣”、“学”。这篇文章的题旨是反对轻视师道,提倡尊师重道。故此四个字中,“师”是最主要的,是“主帅”。“愚”、“圣”、“学”三字则是其“兵卫”。
《师说》全篇由“师”字统领:轻“师”必“愚”,重“师”则“圣”,兴“师”在“学”。
第一段的立论是阐释从师道理,尤须紧扣“师”字进行教学。这段文字解决两个问题:人为何要从师?以什么人为师作者的观点很清楚:其一,学必从师;其二,唯道是师。理解第一个问题是重点,作者从三个角度来阐发:首先从古代传统看,学者有师;其次从为师职能看,道要人传,业要人授,惑要人解;再次从认知实际看,人非天才。人皆有惑;这三点足以证明人必从师。三层意思的阐发是紧密勾连的,一、二层以一“师”字勾连,二、三层以一“惑”字勾连。文章为何从“古”字发笔?因为观今宜鉴古,从“古”说起说服力强;韩愈尚“复古”,从“古”说起势在必然。关于师之职能,论者多谓“传道”、“授业”更重要,这诚然是不错的,但高远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最基本的教学实践——“解惑”,“惑”之不解,遑论其“业”?“惑”终不解,遑论其“道”?“道”得以“传”,“业”得以“授”,必自“解惑”始。因而下文很自然地谈到人皆有惑,惑须从师的问题。这就说明,作者所谈论的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与人生密切相关的问题,也就是说,从“师”不仅仅是童子的事情,为“师”者也不限学塾课徒者流。既然人皆有惑,惑须从师,那么谁可为师?作者指出“闻遭先”者足可为师,师者,有“道”而不论贵贱,“先”“闻”而无关少长。择师、从师的原则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一段围绕一个“师”字做足文章,为下文发论叙事埋下伏笔。
第二段“嗟乎”一转,反承上文以抨击轻师世风,从反面证实“人必从师”。文章结构这样安排,既是作者“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使然,也是论说文“有的放矢”的文体特点使然。分析这段反面论证,须抓住一个“愚”字。开头一个因果性论断就暗古了“愚”之一字:“师道不传”的直接后果就是“无惑也难”,亦即积惑难解,而积惑难解就是“愚”。上面从事理上总说,下面通过对比分说。“古”与“今”、“大”与“小”、“下”与“上”诸多对比,着眼点、侧重点在于今之众人、今之家长、士大夫之族。所有的对比,最后都归结到一个“愚”字,说尽今人何以“愚”。今之众人耻从师,今之家长不善师,上流社会嘲相师,致使全社会是处皆愚,愚不自知,愚不可及。以上三层“愚”之论是逐层深入的:耻从师害己——使己愚;不善师害子——己与子俱愚;嘲相师害人——己与人俱愚。“愚”的范围愈来愈大,“愚”的程度愈来愈深,“愚”的社会层次愈来愈高。同样是轻视师道,而士大夫之流轻视师道的危害性最大,他们影响整个社会!就是在他们的恶劣影响下,今人或耻从师,或不善师,或不敢师,也正因为如此,“师道”久被封杀不传!换言之,师道不传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士大夫之流嘲相师。
第三段引经据典,遥呼文首以树立从师典范,从正面证实“唯道是师”,与第二段构成鲜明对比,因此教学时应扣住与“愚”相对立的“圣”字,让学生思考:圣人何以为圣?圣人何以无常师?第一个问题是不难于理解的,圣人之所以为圣,肯定与上述三种态度和做法不同,圣人不耻从师,善于择师,学无常师,一句话,转益多师才能成为圣人(有孔子之行为证)。第二个问题文章从两方面阐述:其一,是处皆有师(有孔子之言为证);其二,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是明摆着的实情)。是处皆有师,是说人人身上都有值得“师”的地方,隐含要善于发现别人长处的观点。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是说能者为师,即后“闻”者必以先“闻”者为“师”,未“专”者必以“专”攻者为师,隐含不拘一格、不耻下问(“师”问“生”,“长”问“少”,“贵”问“贱”)的意思。圣人深刻认识到是处皆有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所以能虚怀若谷,不耻下问——“无常师”,也正因为如此,“圣人”最终达到“益圣”的境界。这一殷处处关锁前文,“圣人无常师”既照应篇首发句,又与“三人行”句照应“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问道有先后”上呼首段“传道”、“其闻道也”;“术业有专攻”上呼首段“授业”。就是一段之内也是内义脉注:孔子以郯子之徒为师(事实)——“师不必贤于弟子”(结论)——“问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原因),由事实得出结论,由结论追溯原因,有论有据,无懈可击。
中间两段均是论证,最后一段则为结论,总收正反论证,寄望从师后学。这一段交代写作缘起的文字,历来很步人着意挖掘,其实与上文逻辑联系非常紧密,这不仅在于“不拘于时”反呼了第二段的反面论证,“能行古道”顺乎了第三段的正面论证,而且在于它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复兴师道?这一段实质上就是这篇文章的指归。讲清这个问题要抓住一个“学”字,“好古文”,是说李蟠学习目标对头,正与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相吻合;“通习之”,是说李蟠学习方法正确,前述童子们“习其句读”与之不可同日而语;“学于余”,是说李蟠老师选得恰当,找到了真正能“传其道、解其惑”的人。这样“学”,人方可远“愚”;这样“学”,人可望近“圣”:这样“学”的人多了,“师道”方可复兴流传。
综上所述,《师说》一文以“师”字立骨,说“愚”“证“师道”不可废弃,说“圣”以显“师道”意义深远,说“学”以明“师道”复兴途径,“愚”、“圣”、“学”如辐之凑毂,与“师”结为严密而完美的整体。窃以为,若抓此四字讲授,可望事半而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