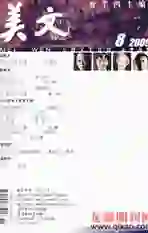释“普慧”
2009-10-24普慧
普 慧

普慧本名张弘,1959年生于陕北。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副院长兼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这个题目如果不是给“普慧”二字加引号的话,读者一定会以为这是一篇写和尚的文章。不错,以“释”为佛教出家者的姓,由来已久。早在东晋十六国时的前秦国国都长安,有一位著名的大和尚叫道安,河北冀州扶柳人,住在长安城郊的五重寺,是长安佛教界的领袖人物。从佛教传入中土始,佛教僧人的姓一般都是跟着师父的国土来姓的。譬如,师父是从天竺(古代印度)来的,弟子的姓就是“竺”;师父是月支(ròu zhī,氏)国(今阿富汗、巴基斯坦交界一带)过来的,弟子则姓“支”;师父是从安息国(古代伊朗)来的,弟子则姓“安”;师父从康居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来,弟子则姓“康”;师父从于阗国(今新疆和田)来,弟子则姓“于”。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东晋中后期。道安和尚认为佛教出家人都尊师佛祖释迦牟尼,应以“释”为姓。在道安大师的倡导下,佛教僧人逐渐放弃原来的以师为姓的做法,统一到“释”姓上来了。后来,一部名叫《增一阿含经》的佛经翻译成汉文,里面果然讲到各种姓的人,祇要皈依佛门,都称“释种”,为“释子”。从此,中国汉地的佛教出家人,全姓“释”。“普慧”,从字面上看,也是佛教出家人的名字。近代有一位山西的和尚就叫“普慧”,很有些名气。近代还编纂了一部大藏经,也用“普慧”冠名,叫《普慧大藏经》。这些说明“释”与“普慧”都是佛教用语。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以“普慧”命名,那么他一定与佛教有关。
然而,题目上的“释”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是解释的意思。“普慧”,则是我给自己起的笔名,就是说,我要在这篇文章里解释我的笔名的来源。“普慧”由我的家乡两个县里的著名泉水的名字和合而成,与佛教尚无关系。我出生在陕北黄河边上的一个小县吴堡,县城叫宋家川。两岁时,随父母亲到了榆林。榆林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白翟(dí)地,“翟”通“狄”,是说这一带为北方狄人所辖。战国时,魏国文侯(445~396B.C.)率先占领榆林,置上郡。秦昭王三年(304B.C.),秦国军队北上击败了魏国驻守上郡的魏军,重置上郡。从此,上郡便成了秦、两汉中原帝国与北方匈奴长期争夺地盘的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不过,那时上郡的治所在肤施县。而肤施县的治所不在现今的榆林,而是在今榆阳区所辖的鱼河堡。今天的榆林城是在两汉以后所建的榆林寨基础上扩建的,明清时期是长城沿在线的重要卫府。据《明史》卷42记载,榆林城于明英宗(朱祁镇)正统二年(1437)所扩建。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六年(1470)三月以榆林城设卫,屯驻军队,主要防御蒙古铁骑。清雍正八年(1730)改置榆林府,重视与蒙古民族的贸易。北京、天津、苏州、无锡、杭州的皮货商,云集榆林。有些皮货商不习惯西北塞上的饮食,便经常要带着厨师来。于是,在榆林的饮食谱系中,夹杂了京味和淮阳菜的味道。陜北各县的口味一般都偏咸、酸、辣,只有榆林城的饮食中有诸多的甜食。譬如,有一道名小吃“炸豆奶”,据说就有江南的口味。还有榆林城里的人喜欢喝汤,有的一桌婚宴就要上好几道汤,什么鱿鱼蛋片汤、粉条肚丝汤、口蘑豆腐汤、苹果醪糟汤、金针海带汤、砂锅什锦汤、橘子银耳汤等等,好象也是受了江南饮食习惯的影响。清代榆林府的知府大都是北京和江浙一带考中进士的人来做。如,撰写《唐两京城坊考》、《西域水道记》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徐松,就是北京人,在嘉庆年间做过榆林知府。这些外地来的知府,喜好修建楼阁,榆林城的一条街上,就建有星明楼、钟楼、古楼、万佛楼、凯歌楼、牌楼、文昌阁等楼阁。遗憾的是,这些楼阁的多数在文革期间被拆毁。我于八七年离开榆林时,仅有星明楼、钟楼和万佛楼尚在,然而已是破败不堪。据说,这几年榆阳区政府又将原来的楼阁一一复建,眞可谓是件大好事。榆林的风俗文化在整个陕北地区是独特的,更是翘楚的。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最让榆林城里人受惠的,不是那些外在的景观和好吃的东西,而是那眼汩汩不息的“普惠泉”水。“普惠泉”在榆林城的东北角的榆林农业学校的校园里,泉的上边建了一座梅花楼,保护泉水免受污染。那时,榆林城外的东西两面都是丘峦起伏的沙漠,普惠泉水就是从沙漠深处的地下水经沙漠过滤后流出来的。泉水甘醇甜饴,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水质极佳。水的比重很大,接一盆水,把五分的硬币平平地置于水面上,它会漂浮于水上而不会下沉。榆林人骄傲地称之为“桃花水”。意思是说,吃了这眼泉水的人,面如桃花,皮肤洁白。所以,榆林城里的姑娘,尽管年年都要经过塞外寒冬凛冽刺骨的西北风吹刮和春季弥漫的沙尘暴袭击,但因常年饮用“普惠泉”水,一个个皮肤白皙如润玉,细腻如凝脂,人长得就像江南秀女一样,绰约似蓝蕙,落落若大方。“普惠泉”的水量颇大,供应了当时全城4、5万人的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记得我刚上小学的时候,还和同学一起到榆林农校看过“普惠泉”。与我印象中电影里看到的山涧泉水不同的是,“普惠泉”不是由自然石块形成的,而是一个用水泥砌起来的大水池子,让人感到很失望。但看着那清澈见底的泉水,饮几口,甘爽沁脾,又让人对桃花水有了一种浓浓的深情。我小的时候在榆林城内住了12个年轮,“普惠泉”水滋养了我的身体,也沐浴了我的心灵,更让我对榆林有了一份童年和少年的乡愁。当我二次重返榆林学习、工作时,人们已经很难吃到“普惠泉”的水了。据说,70年代以后,榆林的城市规模逐渐扩大,人口也增加了许多,原来“普惠泉”的水量远远满足不了人们的用水需要。市政当局便从城南的五雷沟引了一条水,供应钟楼以南的居民。这条水比起“普惠泉”来,水质自然是差了很多。所以,一些权贵单位及其家属院,仍然将上水管道接通“普惠泉”水,继续享受着“桃花水”的滋润。于是,吃“普惠泉”水便成了一种身份和权力的象征。我住在西沙的学校里,父母住在城里的曹辣肉巷,家里吃的自来水是五雷沟水系的,沉淀比较多,烧一壶开水,水底就会沉积水锈。每当我回家探看父母,我都尽可能地提溜着大茶壶跑到行署家属院打“普惠泉”水,专供饮用。
我上初一快结束的时候,父亲又被调往神木县工作。神木,古称麟州,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十二年(724)设置,治所在今神木县北十里。北宋太祖(赵匡胤)干德五年(967)移治今神木县西北三十里的杨家城。杨家城,就是以抗击契丹名将杨业家寨为基础扩建的城池,坐落于草垛山上,易守难攻。因城内有神松三株,枝柯相连,故又曰:“神木”。北宋著名抗击西夏的名臣范仲淹在麟州治所的杨家城住了四年,写下了著名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榆林府志·艺文志》题为“麟州秋词”。金熙宗(完颜亶)黄统八年(1148)被西夏占领,遂废。今天的神木县城则是明正统八年(1443)建造的。民国十七年(1928)神木作为一个县,曾直属陕西省所辖。神木县城坐落于神木川,东、西两面为高山,东边的是东山,山上有蘑菇峰,甚为奇特。神木城西是陕北地区第二大河流窟野河。河西是悬崖峭壁、驼峰高耸的西山,因山上建有二郎庙宇群,又称为二郎山,属于道教系统。神木城外的这两座山,东山佛教香火旺盛,西山道教青烟缭绕,彷佛佛、道二教各显神通,守护着神木城似的。神木人处在佛、道二教的氛围中,不自觉地深受其影响。尤其是佛教文化在神木人的语言和文化中保留了许多印迹。神木人时常以和尚自称或他称,譬如,我要给别人介绍我的父亲和哥几个,常会这样说:“我们家老和尚,大和尚、二和尚、三和尚怎么样怎么样……”,或对他人说:“你们家老和尚、大和尚、二和尚、三和尚怎么样怎么样……”,别人会感到很亲切。婆姨们也时常把自己或亲戚的女儿称为“姑子”(尼姑的意思),也表示十分亲切。神木人特别好客,待人诚恳,颇有些蒙古民族的习风。
我在榆林的时候,虽然住在军分区的大院里,在当地同学看来是很羡慕的,但伴随着六五年全面社教,我的父母亲也开始遭到批判和排斥。母亲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被单位辞退,美其名曰“精简”。我们姐弟便成了大院里被孤立、排挤、欺负的对象。一个诺大的院落群,有三四百号孩子,尽然没有一个敢与我们为友的。从那时起,我的心里便多了许多一般孩子所无的忍辱负重和不屈不挠。从榆林到神木,虽说由地区所在地到了小县城,生活条件艰苦了,但我和我的姐姐、哥哥一下子快活了许多。因为在这里,再没有人把我们当成黑五类了。人格上的独立,精神上的愉悦,让我们把过去的那些积郁全部抛在了脑后。特别是我们姐弟三人优异的学习成绩,赢得了神木中学师生的共同称赞。我们似乎从过去压抑的精神炼狱中获得了新生。
我从小喜欢体育运动,小学三年级时进了榆林体育学校,练习乒乓球。到了神木以后,由于有过乒乓球训练的体育基本素质,对于其它体育项目也学得比别人快,滑冰、足球、篮球、手球、径赛等,在中学生里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地区祇要举办体育运动会,县里在中学生中选拔队员,一定会有我。尤其是乒乓球、篮球、手球等项目,我一直是县里的绝对主力。我从初二到高中毕业,祇干过两种事:一是体育训练,参加各个项目的比赛,有县里的、地区的、省上的;二是到农村辅导政治夜校,宣讲党的新政策:什么“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反击“右倾教育翻案风”、批判“三株大毒草”等等,整天不是批判这个就是打击那个。我对后者实在是没有兴趣,整天就想着出去参加体育比赛。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要先跑个三千米,然后再爬东山。东山半山腰上有一石窟,窟中有一眼泉水,名叫“慧泉”。此泉大小差不多一米见方,水量很足,但奇怪的是绝不会溢出泉池。我每次爬山经过“慧泉”窟时,已是嗓子冒烟,干渴如枯了。“慧泉”水便成了我的水分补给源。咕嘟,咕嘟,痛痛快快地大口喝着“慧泉”水,眞是透凉心底,爽快提神。然后就是津气充裕,爬山如猱。每当我登到山巅,俯瞰神木川时,都会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成功之感。我时常想,要不是半山上有“慧泉”水的补充,前面大运动量消耗后的我,是很难再攀登上去了。所以,“慧泉”水不仅给了我力量,也给了我走向成功的信心。高中毕业后,我插队到陜蒙交界处的一个小山村,那里距神木县城七十多里地。我回县城的机会少了,爬东山的机会就更少了。到考上大学后,我就再也没有爬过东山了,更不用说喝那甘醇的“慧泉”水了。
我在榆林和神木两个县生活了24年。1987年我前往省城攻读硕士学位,算是离开了养育我的黄土地。这一走,真是彻底地告别了我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压抑、屈辱、奋斗、崛起。随后,便是漫漫长长、遥遥无期的求学之路。我从硕士读到了博士,从博士到了博士后,博士后一站完了又进了第二站;求学之地也遍布东西南北,算一算,前后在近10所大学求过学。说实在的,我当年拚命奋斗爬滚出那黄土沟壑,就是讨厌那里的贫穷、落后、愚昧、儿气。我庆幸自己考出了榆林,我彷佛是一个法国外省来的青年,揣着自己的满腹才华,向往着大都市的文明生活。然而,当真正走入大都市的时候,我却有了一种莫名的惆怅,而且这种惆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加的浓重,以至于剪不断、理还乱。在一次写好文章拟投稿的时候,不经意间却联想起了榆林的“普惠泉”和神木的“慧泉”,于是,便未加深思地将两泉之名的第一字组合起来,署名于文章上。这就是“普慧”。值得庆幸的是,在那个年代发表论文极为困难的情形下,那篇文章投出去以后不久便被一份学界颇有影响的刊物登载出来,而且很快又被人大复印数据转载。这真让我喜出望外。从此,“普慧”这一名字便成了我发表文字的专用名。它既蕴涵了我对故乡的一种暗念,又体现了我对研究对象一种独钟。
当然,因为我用了“普慧”这个名字发表著述,而且我所研究的内容又多与佛教有关,学界和社会上的诸多朋友便望文生义了,以为我出了家,或皈依了佛门,成了在家居士。其实,尽管我对佛教文化格外钟情,但也仅仅是学术研究而已,根本谈不上信仰。记得上小学前,父亲陪上级领导视察榆林的防务,要到榆林城北的红石峡看石窟,我也嚷嚷着要去,大人们没有嫌弃我,把我拉上了吉普车。到了红石峡的石窟,那一个个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佛教造像紧紧吸引了我的目光,不管是慈眉善目、雍容肃颜的佛陀,还是金刚怒目、叱喝世间的天王,都让我感到说不出的稀奇。我爬到一个高台上,抱着一个穿着铠甲的天王,对父亲说:“这个叔叔的腿可粗了。”惹得几位大人哈哈大笑,那位大官还说我很懂礼貌。从那时起,我就对佛教有一种说不出的好感觉。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佛教作为封建主义的残余和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遭到了惨重的打击,尤其是佛教石窟、寺塔、造像等,遭到了灭顶的毁坏。我们的思想,经过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洗礼;我们的灵魂,经过了共产主义的熔铸,已形成了稳定的世界观,对宗教神学自然有了一种客观上的抵触。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对宗教神学形成的偏见得到了改观,但对宗教信仰的冷静和思考,早已成了我的思维惯性。尽管我研习佛教文化近30年,读了大量的佛教三藏,发表了60多篇研究佛教文化的论文,但都是站在学术立场上看待的。对此,台湾一学者还颇感诧异。他在我的书扉页上写道:不信佛教而叫“普慧”,甚感异之。为了消除诸友的迷惑和不解,有必要撰写这篇文章,解释一下我的笔名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