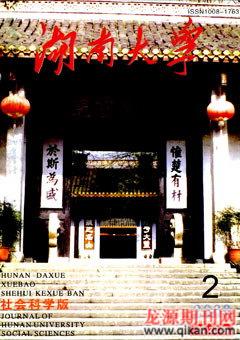走下祭坛的母亲
2009-09-29焦敏
焦 敏
[摘要]从女性主义关于母女关系的视角出发,分析了《灶王之妻》中一个美国华裔家庭的母女关系如何从疏离走向亲密,指出主流的“为母之道”话语对华裔母亲的母性体验的边缘化及病态化,从而切断了母女之间亲密联系的纽带,而母女纽带的重建有赖于互相的倾听与诉说。在倾听中了解母亲的历史就是一段重新发现母亲的自主性及主体性的旅程,也是女儿找回其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自我意识的旅程。
[关键词]谭恩美;灶王之妻;母女关系
[中图分类号]1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2-0087-04
《灶王之妻》是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Amy Tan)的第二部作品。尽管未能重复她的第一部作品《喜福会)的辉煌,却进一步确立了作者在文艺界的地位。小说的热销及评论家对小说的热衷也进一步打破了通俗文学与经典文学的樊篱。谭恩美的成功,带来了美国华裔文学的进一步繁荣,也使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更为关注第一代与第二代华裔移民的种族与身份问题。
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美国华裔家庭本应亲密的母女关系却因为母亲与女儿成长的文化背景的差异而日渐疏离。随着母女之间有效交流的实现,母亲温妮与女儿珍珠逐渐互相理解,母女关系趋于和谐。使母女俩生疏的两种文化反而成为联系母亲与女儿之间的纽带,消融了俩人心中的坚冰。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和解有赖于双方有效的沟通。通过有效的沟通,女儿意识到母亲的现实处境,即母亲是由她们过去的经历与斗争所塑造而成的,因而母亲们也有自己的恐惧与需要,从而使女儿们不再加入到主流文化对母亲的谴责中,而是意识到对自己母亲的谴责不过是父权体制及种族歧视对母亲们的压迫;通过沟通,母亲与女儿能够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不是互相斗争,而是联合起来与主流的种族歧视文化抗争;通过沟通,母亲能够重新获得她们独特的为母体验,而女儿也能对自己的身份——在两种或多种文化与传统纠缠下的身份有更清晰的认识;通过有效的沟通,母亲与女儿对各自的性别身份与种族身份也将有更清晰的认识与更深的相互理解。
一理想化的母亲形象及少数族裔母亲的边缘化
小说的开头展现的是母亲与女儿之间交流的障碍。在从母亲家回来后,珍珠思考着她与母亲温妮之间的关系:“回家的路一里接一里,每一里都那么熟悉,分开我们的却还不是这个距离。”“她和我现在都这样,总是彬彬有礼、小心翼翼的。像陌生人一样小心翼翼地避免冲突。”福斯特指出,母女之间的生疏是多元文化碰撞带来的问题之一。《灶王之妻》小说中的这对母女也不例外——一个生长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母亲与一个美国长大的女儿在美国这一文化大熔炉背景下,矛盾与冲突不可避免。其中既有性别身份认识的冲突,更有种族身份认识的冲突。
首先,母女之间的疏离源于主流话语倾向于理想化母亲。南希,乔多罗与苏珊,康乔多撰文《完美母亲的幻像》指出近年来女性主义学者对母亲行为研究的相关误区,其中之一就是对母亲行为完美化,认为母亲们是万能的及完美的,通过母亲们完美的母亲行为才有了世界的完美。而一旦母亲们不能符合这一完美幻像,则母亲行为成为了毁灭世界的源泉而倍受谴责。理想化的‘为母之道是孤立母亲的一种方式,它将母亲物化。
社会构建的为母之道作为一种理想化的传统,是孤立主体的一种形式,主体成为他者的欲望的目标,社会化的对象。其作为主体的存在被抹杀,由于其主体的地位不被认可,这一主体迟早也会变得畸形。
因此,视母亲为有自己需要、感情及兴趣爱好的主体在与贬低女性的力量的斗争中尤为关键。对有色人种的母亲而言。她们不仅被主流话语理想化的母亲标准所孤立,同时更被从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母亲体验出发的“为母之道”边缘化甚至于病态化。
主流的母亲体验及为母之道被种族化,即他们代表的仅是一种母亲体验,仅是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母亲体验,并将该体验作为最真实、最自然、及普遍的母亲体验。因而对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族裔母亲而言,挑战是双重的,她们成为主流社会中的他者的他者。而她们的女儿们,也陷入了民族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这表现在一方面他们趋同于西方文化主流;另一方面,这种文化认同又与她们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民族文化记忆相冲突。而在母女关系上,由于成长的背景原因,女儿们一直在努力接受与融入主流文化,不知不觉中按主流社会的标准构建了一个理想化的母亲形象,与此同时边缘化甚至于病态化自己的母亲。因此,少数族裔母亲的女儿生活在一个责备母亲的意识形态中,源于她认为自己的母亲不符合美国主流话语定义的理想化母亲形象:
“她只知道她的母亲是温妮,路易,她的美国名,她友好但却令人费解;由于母亲,她不得不有时被一些无聊的传统束缚,而其他美国人却根本不在乎那些传统。”
在女儿珍珠的眼里,温妮除了被一些无聊的传统束缚外,还是一个迷信的女人,相信命,只会被动地接受命运,而不相信自己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生活在对过去的懊悔中,而不是积极向前看。“应该意味着她应该可以改变命运的轨迹却没有,她应该可以让灾难远离却没做到。对我而言,应该意味着母亲过着懊悔的生活,而且她的懊悔从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此外,珍珠将母亲温妮与逻辑对立起来,在她看来,逻辑思维才是最正确的思维方式:
直到今天,听她各种各样的假设,听她将宗教、药方还有迷信与自己的信仰混在一起,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抓狂。她从不信任其他人的逻辑推理。逻辑推理于她而言,只是悲剧还有错误,还有事故的拙劣借口。于母亲而言,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的。她就像中国版的弗洛依德,甚至更甚。
鲁枢元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中比较了中西方对“精神”一词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思维方式。中国古代哲人视“精神”为宇宙间一种形而上的真实存在,一种流动着、绵延着、富有活力的生命基质,是人性中至尊至贵的沟成因素。中华文明对于“精神涵义”的界定、对“精神价值”的偏爱使中华文明一直远离“机械”与“机事”以维护心灵的清洁、精神的平衡及信仰的纯真。而在西方文明中,“精神”更倾向于被看作是一种纯粹的“观念”、“理念”,精神是相对于现象世界的本质、规律、秩序、逻辑。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看来,精神是纯粹理性的、思辩的、形式化的,因而也是抽象的。而此后的唯物主义者以及唯心主义者,包括笛卡尔、斯宾诺莎、爱尔维修和康德,都一无例外把精神等同于理性,把精神等同于思维和以思维为内核的人的意识,等同于人的认识事物本质规律的能力。而只有在20世纪初当西方社会的工业文明渐渐暴露弊端时,才出现了以“生命哲学”为代表的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反思。只有在此时,非理性的东西才逐渐开始纳入到精神的研究视野中。而在心理学界就得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呼应。在女儿珍珠看来,母亲就是非理性的代表,将宗教、信仰、药方与迷信混
在一起,唯独不相信逻辑。这也正是西方世界中定义的他者的形象。正如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所述,东方主义是一套关于理性与感性的话语。西方自由与进步的精神根源是理性主义,东方专制与停滞的原因是感性主义或感官纵欲主义。在近现代史阶段,由于西方相对于东方的优势,以理性与思辩著称的西方思维方式也凌驾于传统的东方思维方式即感性思维。女儿珍珠将母亲的思维方式与‘正确的逻辑思维对立起来,说明她已经认同西方价值观将母亲视为了‘他者,这一经常强加于不按主流价值行事的外来的移民的术语。以母亲为代表的他者面临的是人为构建的分界线,她们被归为另类,且由于不同而带来问题。
珍珠与她母亲之间的疏离在珍珠的丈夫——菲尔,一个病理学家的推波助澜下变得更为严重。菲尔对华人持有的是殖民者的态度,华人被当作‘他者。他责备温妮操纵她的女儿,使她女儿相信她别无选择,同时又试图将这一思维运用于他的身上,反过来操纵他。母亲所代表的文化被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边缘化甚至于病态化——母亲过于情感化而不是理智;被动接受而不相信自己能够改变命运;因为不相信命运能够被改变而心甘情愿被操纵同时也在想方设法操纵着女儿;没有逻辑地将人生交给命运,而将命运又交给迷信而不是自己以及科学性的逻辑思维。因此,菲尔使珍珠相信只要她不剥离她‘祖传的中国性,她就是在暴露一个低等文化不理智、过于情感化的弱点。菲尔使珍珠对表现她与母亲中国式方式的认知之间的联系感到羞耻,使她对任何要将这一认知模式传承下去的努力感到羞耻。
二倾听与诉说:走下祭坛的母亲
一方面,母女之间的疏离源于两种文化的碰撞。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碰撞带来的沟通不畅更加剧了这种疏离。《灶王之妻》小说的开头展现的就是母女之间沟通方式的匮乏:“不管什么时候妈妈和我说话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谈话才开始,就仿似我们已经处于争论的中间了。”缺乏有效的沟通象征着母亲和女儿都失去了各自的声音。然而,到小说结尾,当女儿最终能坐下来倾听母亲倾诉她隐藏多年的秘密时,横亘于两人之间的冰融化了,而女儿也开始向母亲倾诉自己的秘密。这些秘密的交换,母女之间的交流带来的是互相理解,不仅给母女关系带来希望,也给母亲与女儿带来了希望。“她将我的保护层剥去,我的愤怒,我内心深处深深的恐惧,我的绝望也被她带走。她将所有的这些都带到她的心深处,留给我的最后就是希望。”
通过沟通与交流,母亲与女儿都获得她们的声音,因而也获得了各自的自主性与主体性。更重要的是,讲述与倾听使双方对对方的情感投入更为深入,而这也是母亲与女儿获得各自的自主性与主体性的关键。
情感的投入,这一动态的认知——情感表达过程将对方的主观体验与自身联系起来并使自己能够理解对方的主观体验,是这一关系的中心。在真正的情感投入中,每一方既是主体又是对象,双方都共同投入到情感表达中,同时也成为情感表达的对象,既理解了对方也被对方理解。在一个共通的情感投入中,每个个体允许对方,帮助对方更完整、更清晰地了解现实与双方的联系,每个个体都在塑造着对方。”
通过交流,女儿了解到母亲是江伟力,一个成长在旧中国、经历了日寇的侵略与占领、经历了一场灾难性婚姻的女人,一个不能按自己的选择而生活的女人。当母亲温妮将自己的过去告诉珍珠,女儿珍珠才意识到母亲怎样承受着她过去的丈夫文福令人发指的虐待,而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不仅没有干预他的虐待,反而成为共谋。女儿这才理解母亲为什么不相信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因此,珍珠逐渐理解为什么母亲对好命与坏命是那么的在意——在父权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她的母亲,很明显,不能像女儿及其他美国人现在一样,总是有个人自由的选择。母亲是被命运所掌控,被她自己无能为力改变的命运所掌控。她的命运是被更大的一些因素所决定,如国家的命运。此外,她的命运也是与其他同时代女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同时,珍珠也发现她其实是母亲灾难性婚姻的产物——她的父亲文福,就是那个折磨母亲、让母亲不顾一切要逃避的男人。珍珠这才意识到母亲的生存现实,同时也理解了母亲的恐惧——恐惧珍珠会从她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他的劣性,害怕她不爱她的继父——是她的继父英雄般地救了她们母女。
“这么多年来,我总以为他会从柜子里飞出来,或者从我的床底下跳出来。……我绝不会让那个男人称你是他的女儿。他永远都不可能从我这里得到你。”她的嘴紧闭着,坚决无比地说。
为了不让女儿认为自己是个软弱的人,同时也因为害怕珍珠从生父那继承哪怕一点点的劣性,温妮对女儿格外地紧张。然而在珍珠看来,母亲对她充满了控制欲,几近苛求。正如萨摩拉多所述:
温妮的直觉让她将珍珠尽量拉到她的身边,尽量克隆她自己。温妮想要通过展示外在的力量保护她的孩子,而尽量避免表现出自己懦弱的一面。然而,令人伤心的真实却是:女儿将母亲展示出来的外在力量解读成了操控。
海伦是文福同事的妻子,两人虽心有芥蒂,命运却将她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海伦一直见证了温妮与文福的斗争,且帮助温妮逃到了美国,尔后自己又在温妮的帮助下以温妮大嫂的名义来到了美国。她是这样对温妮说的:“我知道你尽了多大努力想让珍珠成为你的,而不是她父亲的。”作为一名见证人,海伦理解温妮是有着自己过去的女人,而不仅仅是一名母亲,因此,也理解她与众不同的母亲行为。通过有效的沟通,这两位一直以来的合作伙伴对她们之间的友谊有了更新的理解。温妮意识到了这么多年来,海伦,尽管表面上是与文福站在一起,实际上是在发挥她作为女人的从属策略,在温妮的危难时刻更好地帮助她。有效的沟通不仅带来了互相的和解,更帮助两个女性获得了声音与自主性。
倾听母亲的故事,也使女儿开始反思主流意识将注重感性思维及偶然性的中国文化传统等同于劣势文化是否有其公正性。在小说的结尾,珍珠不再抗拒中药,也逐渐看到中国文化中富有浓浓亲情的谎言的力量:
“我在笑,面对层层叠叠的谎言有点不知所措。也许那些不是谎言只是他们互相之间表达忠实与关心的一种形式,这种忠实与关心远非我所能理解的语言能够表达。”
理性思维中,谎言就意味着背叛,中药相对于西医就是巫术。然而女儿对中药的重新认识,对独具中国人情味的谎言所蕴含的力量的发现,无不解构了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的病态化的认识——是否相信偶然性就是非科学性、非理性的;是否理性思维就可以凌驾于感性思维;是否谎言就意味着背叛。(对感性思维与偶然性相对于理性思维与必然性的重新认识,林泰胜在《东方合理主义的‘新理性》中就提出了对西方理性的扬弃及对东方艺术精神的重新发现,并以古典性——被现代理性压抑的感性与偶然性的复苏作为研究结论。女儿珍珠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重新审视就是对母亲的重新认识的过程,也是逐渐去除母亲‘他者,身份、还
原母亲的主体性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对于女儿而言,对母亲的理解标志着她学会了在多元文化背景的环境下,表达自己的声音,重新获得自我及身份。
她表现的是不理解母亲的‘重要性,因而也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重要性的女儿们;大多数的女儿们似乎从未被告知母亲的经历,或者甚至根本不愿意倾听母亲的经历与过去。直到他们意识到母亲的重要性,她们才能获得自己的声音。她们被同化,她们嫁给美国人,假装成美国脸。她们适应着的同时,她们的母亲们就像灶王爷的妻子“无忧女”一样坐在她的祭坛上,等着女儿们倾听她们的声音。女儿获得声音的旅途只有在她们来到母亲的祭坛倾听时才算完成。
虽然我同意福斯特所述,倾听才能意识到母亲的自主性与主体性,即认识到母亲作为一名女性,有着自己的过去,自己的需求以及自身的局限性。意识到母亲的主体性,对女儿定义自身的自主性与身份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认识到母亲作为独立个体的重要性,女儿才可能意识到自身的重要性。然而我不认为做女儿的应该是来到母亲的祭坛,对母亲像神一样顶礼膜拜,反而是认识到母亲的主体性,承认母亲首先是一名女性,女儿才能学会表达她自己的声音。理想化母亲或崇高化母亲只能让母亲失去作为女性的主体性与自主性。而只有在女儿对母亲的处境与身份有最真实的了解后,母亲与女儿才都有可能实现各自作为主体的存在。
对母亲过去的逐渐发掘,对母亲所经历的历史的了解就是一段重新发现母亲的自主性及主体性的旅程,就像小孩的自我意识总是与他们的表达能力及被母亲倾听的能力联系在一起,母亲的个体自主性也是与她表达自己及被她的小孩倾听、理解的能力联系在一起。“尽管主流体制将少数族裔母亲放置于子女关系中稍为弱势的位置,但是母亲与子女通过理解对方所处的位置,通过依赖互相的力量而变得更为强势。”
对关于母亲角色的主流话语的批评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大多数关于母亲角色的主流话语都是从某个特别的与阶级或种族的角度定义的。对里奇而言,有色人种妇女作为母亲的主观体验是不可避免要与相关种族的社会文化相联系的。通常而言,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的母亲体验被构建为正常及自然而然的母亲体验。柯林斯也指出,忽略养育子女的母亲们所处的种族及阶级背景将会削弱女性主义理论。移民母亲们由于有着各自不同的过去,因而产生了不同的母亲经历及对子女不同的期望,而社会却不顾移民母亲们的背景,将移民母亲的体验病态化为匮乏的母亲甚至是非法的母亲,而中产阶级白人的母性体验则被典型化,自然化。从这点看来,切断母亲与子女之间的联系不单单是父权体制的作用,也是种族歧视的结果——通过将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母亲经历正常化与自然化而生生切断了有色人种母亲与子女之间亲密的纽带。《灶王之妻》中母亲与女儿的和解,并不象征着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同化——这是我们所不愿见到的,而是从某种程度上解构了主流的西方文化价值,尤其是解构了被当作是“普世的”及“自然的”理想化的母亲的形象,以及内化于理想化的母亲形象中的种族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