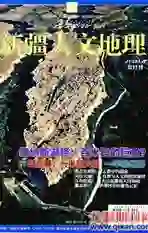歌者的岁月
2009-09-24刘湘晨
刘湘晨
这片遥远的风景,对许多人来说都不能不是一段距离,一段地理和心理的双重距离。每年的五月草青,六月第一枝野罂粟怒放,八月草黄,九月白桦叶变红,属于这片风景的花季很短。更多的时候,岁月似乎都在刻意强调它的苛刻、严酷,这里只有风,严寒和冰雪,而环围这片风景的四周则是更大范围的荒漠。
没有对岁月更迭的足够认识和对荒漠切身的感悟,你恐怕很难理解这极致的花季。如同酒是五谷的精纯,玉是石的华晶一样,这如画的风景则是岁月荒凉到极致和荒漠荒凉到极致的双重塑造。
有朋自远方来,你是谁?你从哪里来?都不重要。只要走近这片风景,就会有一扇门豁然洞开,而这“门”里的内容,一丝鲜蛮的空气就足以让你跌过去。会有一种沉着却十分有力的震撼向你袭来,这完全是劫掠式地对你的剥夺,让你为往昔所有与她的隔膜和对她的知之甚少汗颜,然后换一种眼界,让你重新认识一些最简单的东西。
生活在这片风景中的牧人们完全属于这片风景本身,他们最大的幸福就在于可以毫不顾忌这片风景的意义而活得自由自在,如梦如痴,踏过去的每一行步履间都充满浓浓的汗腥气。与这片风景突然遭遇,你会意识到你正在走近你血脉印记中那片遥远的故土,从中嗅到生命久远的气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会在一刻间成为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在这片每一波草浪都会无限延亘下去的风景中,牧人戴的表,特别是那些姑娘们戴的表,完全没有指时的功能而仅有装饰作用,他们永恒的时间参照是太阳的升落、草色的枯荣和每一只土拨鼠用爪子扒开洞口的时候。一棵树可能是一位仙女,一块石头是一个咒语,一条河则是一段叙述不尽的梦境,一个嗜酒的汉子醉倒在任何一个角落里都会坦然地如同睡在自己的家里,一个孩子去一架陌生的毡房里吃睡绝不会有谁感到不安……
对这里的一个牧人而言,所有的信仰都不及他们对一次日出、一场落雪和一只小羊羔降生的认识敏感而深刻。从一碗奶茶,到整幢的一座华丽毡房,从生到死,大自然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所必需的一切,这种必须和每天都在无数次重复的琐碎细节都在强调大自然对于人们生存的意义,对这种意义的理解则成了一代一代牧人们最天然的本能:出生时他第一眼看到的东西,也将是离去时他最后一眼恋惜无比的东西。
大自然是人们心灵的唯一对应,她的风花雪月,她的沧桑苍凉,无不在勾划每个人的人生,这是这个世界唯有可能的整体形象的塑造,从心理、个性到他的人生见解和嗜好,大自然是每一个牧人的生父、生母。唯其如此,在这里没有读一天书并不觉得是太大的遗憾,满腹经纶也不会觉得特别富有,人的喜怒哀乐唯有一碗酒、一把琴和一声长歌便足矣。
当一个牧人想唱歌的时候,那一定是他最动情、最有话想说的时候。可能有词儿,也可能什么都不确定,仅是用了唱这种形式,心底的所思、所欲吟为一首长歌,人生的所有体验便蕴在其中了,情浓于声,血浓于情……
这是一个诗人还不曾以其诗作成为诗人,而哲学家还不曾以其著书立说来阐释思想的年代。唯有歌声蕴有最丰富的寓意,唯有歌声才是最好的传说方式。儿女情,英雄气,伴一匹骏马游走四季,这终将是一个让人缅怀不尽的年代。
这片遥远的风景如今不再遥远,因为许多牧地已变成旅游景区。唯有这片风景中的牧人,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传统,用歌声,用一生来保护生存的环境。他们永远是让人尊敬的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