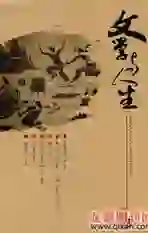危险的夏天
2009-09-19朱小勉
黄昏像个迟暮的老人蹒跚而来,它美丽羞涩的乳晕使我沉醉、着迷,也会使我坠入无穷无尽的恐惧之中。黑夜裹挟着它巨大的能量向我奔涌而来,包裹并压迫着我脆弱的身体和神经,如同死亡就要来临,令我窒息。这时候,我总想奔跑到旷野上呼喊,我的呼喊声想让一些事情停止下来,可是它们却像河水一样跳跃闪烁着,无情地从我的眼前流走。
这种恐惧一直持续了好多年。多年以后,当我端坐下来,带着愤怒和无助的情绪用文字来记录这些如烟的往事时,我焦灼的内心已经燃烧起来,以此来毁灭我的整个身体和麻木的神经。经过多年的思考和积淀,今天我来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书写冲动。我认为这种书写本质的冲动是人们与生俱来的。
我们的故事总是在冬夏之间穿梭徘徊,无关春秋。在我的印象中,这两个极端的季节贯穿着我童年的全部记忆,而且删减着、雕琢着,使它成为一个简单的课本,我的故事在课本里已经泛黄,像冬日里一片枯死的腐朽的树叶,仅剩下清晰的脉络。有时候记忆又像锯齿一样使我脑海深处的某些神经轻轻地抽搐,这种抽搐的疼痛让我明白它们曾经孤独地、懵懵懂懂地存在过。
哥哥,我的哥哥一直存在于我支离破碎的记忆中,像一个简单的标点符号,或者像一串被打散拆开后的字母。当他以一种秩序排列组合起来的时候,总是那么的富有激情并具有特殊意义,他编织着、分割着,使我看见层次分明的故事。
那个夏天,我和哥哥像往常一样去学校的时候,午后的阳光像泛滥的洪水一样汹涌地倾泻下来,天空中好像呈现出远古时代的十个太阳。路上,我们看着那些穿着短裙的女孩们时,觉得她们的身体都很轻盈、很有质感,像高温下的石蜡一样。她们裸露着的腿就像一截截藕,她们微微凸起来的胸,还有圆滚滚的屁股,朴素的连衣裙将我期待的部分恰如其分地遮挡起来。我站在学校旁的池塘边看得目瞪口呆。
这时,坐在池塘边的哥哥站了起来,他的屁股一颠,书包就被赶到了背后,他先是朝刚走过的女孩子喊叫着,停下来,停下来哟,等着我们呀!他的脸上挂满了既老成又幼稚的笑容。女孩转过头来,白了他一眼说,流氓!然后响亮地“呸”了一声就准备走开。哥哥问那个女孩,你说谁是流氓,你爸爸才是流氓呢。我看着那个女孩在阳光下的身影,她身体在午后的太阳底下像一朵刚刚绽放的花,我忽然感觉身体内的某些神经为之颤动,我慌乱地瞟了哥哥一眼,他正得意洋洋地盯着朝我们走过的另外几个女孩看。待她们走过去后,哥哥轻蔑地对我说,这几个小骚货一点都不好玩,她们都觉得自己长得漂亮,其实她们是自作多情,他最瞧不起她们几个。他还说其中那个比较漂亮的叫何亚丽的女孩,她妈妈在县城的车站当售票员,被一个浑身上下都油腻腻的司机拐跑了。
我问哥哥,拐跑了干什么?
哥哥瞧不起我似的说,还能干什么啊,当然拐去睡觉了。
我困惑地听着哥哥的话,想着为什么一个女人会喜欢自己身边睡着个跟油箱差不多的男人呢?
我们站在树荫下,密集交错的树叶像一个孔眼均匀的筛子,筛着阳光,地面被斑驳成一张静悄悄移动着的豹皮地毯。
那一刻,我的心中开始灼热,像一团火猛烈地燃烧着,仿佛我单薄的身体在片刻之间就要化为乌有,脑海里也是一片空白茫然。哥哥对我说,走,咱们到那边玩,那边好玩的多着呢。他一只手拉着我,另一只手指着不远处的房屋。我看见他脸上有细密的汗珠,似乎他还很激动。光线像天空倒下的豆子一样带着微妙的呼呼啦啦的响声撒在我们身上。不知不觉,我们走到了白老师家的门口。哥哥说“这家伙”教他语文课,课讲得挺好,不过喜欢教训男同学,经常揍他们,他的耳朵曾差一点被“这家伙”拽了下来。阳光聚集在他家的院落里,我看见院子里的铁丝上挂着几个颜色沉闷的深蓝色裤头,被太阳暴晒得像一排站得整齐的老头,只不过都奄奄一息的,风吹过来,它们无精打采地挪动一下,再挪动一下,然后继续低垂着,并没有表现出它们该有的生机勃勃。哥哥看到这些时,显然比我更为激动:“我们用根竹竿将它们挑下来扔到学校的厕所里。”
我吃惊地看了哥哥一眼,他脸上写满了严肃谨慎,还掺杂着一种莫名的冲动。
“这家伙并不是个什么好东西,”他悄悄地对我说,“我从不尿他这种人。尿他他又能怎么样。”
在刺眼的光线下,我看见哥哥机械地挪动他轻盈的身体,像一只野兔机警地潜伏到那棵老槐树下,顺手抄起一根竹竿,朝铁丝下跑去。炎热也许使我产生了幻觉,我看见哥哥的身体像一只小鸟那样飞了过去,没有声响地落在地上;光线又将他的身体分割成无数个部分,最后每部分小得都看不清楚了。我想可能是蒸发掉了。我不断地流淌着汗水,它们顺着额头往下流又钻进我的眼睛里——很酸也很疼。但是,他并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开始去挑它们,而是迟疑了起来,表情僵硬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好像被什么东西惊呆了。我惊讶地望过去,远处的光线像风中的火苗一样激烈地跳跃着,舞蹈着,穿透哥哥的身体,哥哥的身体被火光弄得伸缩着,变了形状。
这时候,他匆忙地朝我挥了挥手,示意我也过去,我看见他的表情一直凝固着,好像什么事情使他疑惑了。阳光稍微再炎热点儿,光线再毒一点儿,我害怕哥哥的身体会融化。
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忐忑不安,惊讶于哥哥为什么会这样做。那个曾快要拽掉他耳朵的家伙这时候出来会是怎么样的一副情景呢?我想他肯定会发疯似的把我们绑起来,就绑在那棵老槐树上,让太阳把我们晒成跟风干的死鱼一样的东西。想到这些,我恐惧地望着哥哥,拿不定主意,正犹豫不定时,我看到哥哥紧张而迫不及待的样子,与此同时,那个沉闷的颜色摇晃着像在向我发出富有激情的召唤。
太阳的光线像一把巨伞。
等我蹑手蹑脚地跑过去,他才反应过来,做出一个不要我出声的手势。我怎么敢轻易出声啊,我觉得自己早已经从这个院落里消失了。我屏着呼吸,除了自己心跳的声音外,就是天空中撒下豆子的声音,光线带着那种美妙的旋律包围着我们。慢慢地周围的一片死寂被打破了,我听到了其他的声音,心底猛然荡起一个巨大的波涛,升腾起来撞击着我的大脑,顿时我觉得浑身上下都麻木了瘫痪了,这个从内心深处激荡起的颤抖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它就像一个噩梦一样纠缠着我,使我后来的生活一直处在恐惧中。我沉浸在那种欢快的吱嘎声中——茫然、恍惚,手足失措。我看见哥哥脸色凝重仔细地侧着耳倾听,好像他还没听出那个声音的来源,他求助似的看了看我,紧接着便开始窃笑——嘴角便出现一个复杂的弯曲。他诡异的笑容让我捉摸不透。
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像一条在水中的鱼一样游荡到白老师家的窗台下,认真地听着,然后捂着嘴笑了,笑得比阳光更加灿烂。因为他的手紧紧地捂住嘴巴,所以没有声音。渐渐地,我听到那种声音越来越强烈,像奋力挣扎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的一艘船。声音按照某种鲜明的节奏激情澎湃地响着,猛烈地撞击着我那不堪一击又稚嫩的身体,贫瘠单纯的身体的每个角落都被声音灌满了,显得异常迟钝和笨拙。
接着,我还听到那种接连不断的呼吸声,忽高忽低,十分急促,好像马上就要断气了一样。我想那家伙一定很难受。这个时候,哥哥的身体像沉入水中后的木头一样又慢慢地飘浮起来,他用手小心翼翼在密不透风的窗户角上撕开一个洞,然后满脸渴望地往里边瞧究竟。隔着纷纷跳跃的光线,我清晰地看见他脸上浮现出惊愕的表情,十分痴迷。那种痴迷的表情这么多年来一直出现在我的眼前,作为一个纯粹的符号和方式来表达它真正的意义。
当我凑到窗户前的时候,哥哥赶紧把我拽下去,他并没有说话,而是继续把一只眼睛贴在那个新鲜的洞口上。那个黑糊糊的洞口好像吸走了哥哥所有的精力和能量,他如饥似渴地占据着那个属于他的洞口,完全把我忘在一边了。我焦急地等待着,希望他早些看完后走开,让我也看看,那儿究竟有什么东西使哥哥如此痴迷。我烦躁地蹲在哥哥旁边,身上的汗水一个劲地流淌着,滴在哥哥的脊背上,但是他置之不理,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似的。这时,那个声音更加清晰了,以某种节奏感冲击着我的耳膜,放浪之势几乎要粉碎我的身体。我的手心已经全是汗水,下面那个奇怪的玩意儿也开始不由自主地膨胀起来,好像被燃烧了一般,灼热,滚烫,全身的神经都被它的冲动而搞得紧绷绷的。那一刻,我的脑海中一片空白。
过了一会儿,哥哥才想起我,他有点不情愿地挪开他那颗坚硬的头颅让出那个属于他的洞口,并挤眉弄眼地示意我也去看看里边的动静。他盯着我,坏笑着。于是,我拨开他的身体从那个洞口望进去,屋内的光线并不暗淡,那个白老师正像波浪一样起伏着,他精光着身子,身上挂着的汗珠使他的身体闪闪发亮;白老师的身体下边,是一个被遮掩着的身体,我想那肯定是他妻子。白老师一直不厌其烦地起伏着,并发出野兽怒吼一样的声音。我的身体像充满了气体一样又急剧膨胀起来,使我几乎无法呼吸。
我和哥哥一起跑到操场上的时候,哥哥激动地问我刚才看到了什么,他的表情里隐藏着一股尚未消失的兴奋。我面红耳赤地看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太阳像发疯似的要烧坏我们的身体,而我的身体正在燃烧。
哥哥说,刚才那阵儿他的那个玩意儿很硬,硬起来的时候他觉得世界都小了许多,只剩下我们两个和白老师夫妻俩。他又问我,我的硬了没有,他这样问的时候我的脸更加红了,我想我的脸红得肯定像一块猪血。我鼓足劲对他说,没有!说完,我的全身像泄了气一样开始瘪下去。
自从我和哥哥窥视白老师床上的那一幕后,很多时候,我连和女孩子们对视的勇气都没有了,我觉得她们的目光里藏着许多秘密,令我无法破解。那段时间一直持续到夏天真正来临。
正值那个夏天最炎热的时候,我和邻居家的女孩在镇子上转了整整一圈,当然是她邀请我的。我们路过镇子旁缓缓流动的河流,又从散发着恶臭的冷库边的庄稼地里穿过,最后跑到学校后边的假山上看繁茂的树林和远处的天空。她对我说了很多话,她的声音很甜美,嘴巴肉嘟嘟的,很好看。我假装和她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一边偷眼去看她那匀称的身体,然后我下面的那玩意儿就开始膨胀,简直就是一匹脱了缰的小烈马。不知道我那副猥琐的样子被她看到了没有,反正当我心惊肉跳地望着她绯红的脸颊时,感觉心脏上像爬满了蚂蚁。
她烦躁地对我说:“烦死了,烦死了。你知道吗?我们班上的那几个男生想追我,我不知道咋办才好。他们几个小流氓,呸!我妈知道肯定会骂死我,你也知道她对我那么严厉,我该怎么办呀!”说完,她低下头,慌张地用一只脚尖狠狠地蹂躏着那片土。我倒显得冷静许多,只是听着她接连不断地唠叨。
她又说:“其实我根本不喜欢那几个臭男生,我对他们说,想交朋友回去找他们姐姐交去。可是,他们死皮赖脸地厚着脸皮纠缠我,他妈的。”她的脸上带着愠怒的表情,光线柔柔地笼罩在她的身上,十分饱满,这使我胡思乱想,想起那个烦躁的夏日午后。
我看着她今非昔比的身体,眼前的身体和我们小时候一起玩游戏的身体完全扯不到一块,现在她的每个部位有如雨后的庄稼,枝叶繁茂,并且恰如其分地搭配着,散发出成熟的气息。我不知道说啥才好。事实上,我早已魂飞魄散,身体的某个部位早已恣肆地放纵了。——她的身体就像田野上的庄稼一样,令我充满无限美妙的想象。
我觉得我比哥哥肮脏许多,只是没有人发现罢了。
假如她邀请的是哥哥,我敢肯定,哥哥一定不会像我这样猥琐的,尽管大多时候他喜欢向女孩们说些荤话,但说荤话并不能证明一个人有多肮脏。
而事实并不像我所料想的这样,因为后来的这件事情又印证了我的看法,这也多少改变了我的一些看法,甚至使我对身边的这个世界开始产生深深的怀疑。
那天,我在池塘边看见那个新近娶了寡妇的中年男子躺在躺椅上午休。他只穿着一条裤头,身体的其他部位全部裸露着。我看见他浓密得如丰盛的水草一样的体毛,特别是长在胸口上的那丛黑色杂草。风从池塘上吹过来,粼粼的水波反射着赤日炎炎的光线,湿润的空气轻轻地拂着中年男子强健的身体。我看见他那被裤头勒紧鼓起的玩意儿,吓得赶快跑开。我失魂落魄地跑到学校,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脑海里被一些乌七八糟的颜料涂抹着,根本没有心思听老师讲课。
放学后,我把这事告诉了哥哥。哥哥正捧着一本书津津有味地翻看,并没有在意我所说的事情。当我说到最激情的地方,他忽然合上书,不屑一顾地说:“我还以为是啥新鲜的呢,还没这里边的好看。”他将书递给我,说,“你看看这儿,日他娘的,这家伙真没人性,连条狗都不如,”他停顿了一下,又说,“这个主人公是个女的,一点儿人性都没有。”他补充道。我透着他手指的缝隙看到书的封面上是一个近似妖精的女人,身上敏感部位被她用手以及摆出的姿势掩盖着,封面的右上角赫然写着“意乱情迷”四个字。
顿时,我打了一个寒战,驱赶掉周围的炎热,思维上留下一条条像蚯蚓爬过去的痕迹,错综复杂地交叉着。
哥哥说:“我日!这比你看到的那些要刺激一百倍吧。”
过了几天,哥哥学着他手头上那本书中描写的语气在中年男子家的墙壁上写了一段话,当然,他依据我的叙述,再经过他的加工,一段有滋有味的故事便呈现在那儿。我看后,深深地佩服哥哥捕捉细节的能力。他勾勒出来的形象至今都使我无法忘怀。
起初的几天,我和哥哥藏在隐秘的角落里看着学生们站在那儿看,他们小心地念着,生怕漏掉一个字似的,念完后便大笑起来。
又过了两天,在一个放学的下午,我们看到那些字被白石灰刷掉了,墙上一片苍白。当我和哥哥正发愣时,一双大手忽然从我们身后伸了出来,像把大钳子钳住了哥哥的胳膊,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只听见一个粗壮的且带着喘息的声音恶狠狠说道:
“我日他个姐,今天终于抓住你了!”接着一张长满了横肉的脸悬挂在我们面前。
正是那中年男子怒气冲冲的黑面孔。
我害怕极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他说完便开始教训起哥哥来,只见他一个拳头挥过去,哥哥便打了一个趔趄,差一点摔倒在地上。他追上去,一只手死死钳着哥哥的胳膊,另一只手朝哥哥的脸上左右扇去,一边扇,一边说:“我的事关你个小崽子啥事,你说你是不是皮发痒!”他的声音并没有透露出他的气愤,倒显得有点儿沉着冷静,“妈的,日寡妇怎么了,关球你什么事。你这个贱骨头就是他妈的一个小流氓,小流氓——你就是流氓的种。”
听他这么一说,我无比羞愧,因为按照逻辑来推,我毫无疑问也是流氓的种。
中年男子并没有松开手的意思,他好像非要向周围的人证明哥哥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才肯罢手。他用手紧紧地箍着哥哥的脖子,哥哥的脸涨得通红,甚至发紫,但他并没有挣扎、反抗,而是任眼前那个身体魁梧得像一匹公马的男人“驾驭”他。傍晚的太阳睡在夕阳里,毛茸茸的,我们沉浸在这样的光线里,慢慢地我看见哥哥的鼻子冒出两股殷红的血,血迹有如两根红漆筷子插在鼻孔里,随后他的身体开始模糊,像融化了一般,消融在金光灿灿的夕阳里。
“我日个寡妇也要被你看笑话,也要被你写出来让我丢人现眼,你说说我的这张脸还怎么拿出去见人呢……”他的声音像苍蝇的嗡嗡声一样回荡在我的耳边。他的手掌在哥哥脸上扇来扇去,直到寡妇站在池塘边尖细地喊叫他的名字,他才松开手,说,“今天先到这儿,老子绝对不会轻易地饶了你的。”说完,便扬长而去。
这时我看见哥哥的眼里慢慢盈出一汪泪来,他的脸上指印鲜红,鼻孔下是蚯蚓般爬动的血迹。
那次,哥哥并没有抱怨我,可是我认为我亏欠哥哥太多,毕竟那件事并不是哥哥独自寻乐而写出来的,多半他也是为了满足我的某种欲望吧。可是事情的结果令我们都始料未及,哥哥不仅遭受了一顿毒打,而且还使他的生命画上了休止的符号。
哥哥被打的消息像瘟疫一样传遍了我的村里,人们都认为哥哥简直就是个流氓,将来肯定会坐牢。
这事令我极度惶惑与悲伤,我始终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认为哥哥简直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混蛋,想来这是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对于人们这种莫名其妙的判断能力我一直深深地怀疑着,不可否认他们荒谬的判断如同一把锋利的刀伤害着我的故乡和那些人。
当我想起遍体鳞伤的故乡、人和那些事情时,它们好似淹没在傍晚的炊烟中,缥缈,虚无,最终飘至我大雨过后一样泥泞的记忆最深处。
自从哥哥被打后,一连好多天我们都躲避着中年男子,而中年男子却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每天下午依旧像以前那样裸露着身体睡在池塘边的宽躺椅上。我觉得他就是一只蜷伏在椅子上的野兽,熟睡时在养精蓄锐,待势以发,醒来后会像颗冰冷的炸弹爆发出巨大的威力。
我和哥哥每天都要等他睡熟后才提心吊胆地从他的身边经过,我们的脚步声很轻也很小,生怕弄醒了他,因为我和哥哥都在为那天他临走时留下的那句话而耿耿于怀,于是十分地谨慎起来。
七月初的一个午后,挂在天空中的太阳与往常一样大,烈日炎炎,池塘的水波被微风推得起了一层层皱纹,我和哥哥走在滚烫的马路上,这时中年男子冷不防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如同一堵墙壁阻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他狰狞地笑着说:
“往哪儿逃?”他脸上的横肉在太阳下闪着黝黑的亮光。
我们赶紧收住了脚步,惊恐地望着他。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容中分明带着危险、凶恶和残忍。那一刻,我多么地希望他闪开肥厚的身体让我们过去,或者我和哥哥有穿墙而过的本领,从他的身体里安然无恙地穿过去。光线十分强烈,我眼冒金星,却看见那群上学的姑娘们高兴地蹦跳着朝学校走去,她们的身体依旧那样轻盈,但更加成熟丰满。
中年男子慢慢地朝我们逼近。他笑着走上来,笑容十分复杂,而我和哥哥呆若木鸡地站在那儿。他像上次那样先是用一只手卡着哥哥的脖子,哥哥的身体就不由自主地朝后退,一直退到他家的墙壁上,退到那片房屋遮盖的阴影下。哥哥的整个身体都紧紧地贴在墙壁上,仿佛他是一副挂在墙上的画。中年男子狞笑着,又开始狠扇哥哥的脸庞,他的动作娴熟、自如、轻快,好像没用多大的力气,但几巴掌下去,哥哥的嘴角便挂着血滴。过了一会儿,哥哥挣扎起来,他的两条腿开始朝空中乱踢,可他只能够踢到空气。不知道是不是在阴影中的原因,我看见哥哥的脸开始变成紫色,两只眼睛像是怒视,又像是在乞求,眼珠子都快撑破了眼眶,他试图晃动身体来摆脱中年男子那只巨大的手,但他像被死死地钉在了上面一样,他的挣扎显得那么徒劳。最后,哥哥艰难地把目光朝我转了过来,似乎在求救,但他的嘴巴不能发出任何声音。我非常绝望——我多么地希望寡妇此时出现,像上次一样喊走中年男子,这样他就会松开哥哥,可是她一直没有出现。我已经彻底绝望!夏日纷乱的光线在我的眼前跳跃着,我的目光逐渐模糊了,隔着跳跃的光线,我看见哥哥的眼睛里开始冒出血丝来,慢慢地好像哥哥的身体也随之跳跃不定,像风中的火焰。最后,在中年男子松开手的一刹那,他像一条有气无力的绳子一样顺着墙壁缓缓地滑了下来,再也没有站起来。村里人都说哥哥这是报应,死了就不用去坐牢了,他这么个坏孩子死了就等于为人们除掉了一个祸害。
在一个漆黑的闷热的夏夜,我惊恐地从梦中醒来,当我的一只手力不从心地朝裤裆摸索过去,顿时感觉双腿间有黏稠黏稠的感觉。我有点儿惊恐,同时也感到有点儿不可言说的美妙。我很想把这种感觉告诉我的哥哥,可是他永远地消失了,我知道永远不会有人和我分享这件美妙的事情了。
朱小勉:男,1983年11月出生,河南省邓州人。曾获得第六、八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作品发表于《长城》、《黄河文学》、《草地》、《东京文学》、《都市》、《湘湖》等文学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