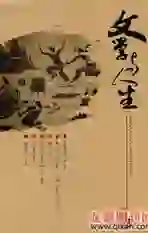在冬天的峡谷里打盹
2009-09-19茅店月
小屋
房子后面的池水已经结冰了,残断的芦苇三三两两弯腰挤在一起,像一只只久病的水鸟,羽毛黯淡无光,沉重的眼皮一翻,伸出尖尖的嘴,在冰块的缝隙中呷水。一个中午,都没有人经过这里,细微的风从南面的坡地上滑下来,掠过池塘,干枯的荷叶和芦苇发出飒飒的声音,如同秋天深处虫子的鸣叫。我吃过了饭,坐在红柳下面的竹椅上晒太阳。冬天的阳光如此吝啬,淡白色一层,在我的皮肤上轻轻弹奏,一如低柔的轻音乐。此刻的池边,风在薄薄的冰层上漫步,流水安静地偎着黑黝黝的淤泥,一点点,打着旋涡向东流去。
时光在这个午后变得慵懒无比,光影轻轻转换,从坡地的顶端开始,慢慢变暗,灰白的颜色像一件破烂的披风,铺展到峡谷深处。没有人注意这里的生活,泥土和植物在冬天如此萧条,寒冷冰封住了橡皮虫尖尖的嘴巴,它们拖家带口躲进黑暗的泥土深处,于是,这里充满了神秘的寂静。我的房子就坐落在槐树林里,它瘦小而孤单,像一粒被风吹落的草籽。好长时间了,我没有回来过,房子一直空落着,灰尘和杂草在庭院里四处安家。这个冬天,我从遥远的海滨小城跑了回来,看上去很困倦,眼睛红红的,头发枯草般蜷曲着生长。回到乡下时我就想到了这间小屋,它依旧安静地躺着,在坡地的一个小平台上晒太阳,麻雀站在屋顶叫唤,干燥的声音像擦着的火柴,在昏暗的空气里飘荡。每天早上,我亲自生火做饭,煮玉米珍子和红薯,用很多年前母亲买的瓷碗盛着,坐在弓背椅子里慢慢吃。阳光透过木格子的小窗洒进来,寒冷的空气带着干爽的枯草味,乳白色,贴着地面流淌。天真的很冷,我戴着棉帽子不停搓手,把门紧紧关起来,到火炉边取暖。天气好些的中午,我会走到院子里看那些高大的椿树,有时,会端着椅子走到屋子外面,沿着曲折的小路前行,在池塘边阳光丰茂的地方坐下。就像今天,整个中午,我眯着眼坐在荒草地上,同虚弱的阳光一起沉静地呼吸着,怀想那些烛焰般摇曳的陈年往事。
这是一个寂静的世界,被人们遗忘。我似乎也忘记了它,开始打盹,或许,真的太累了。我的身后,大堆藤本植物扭曲着粗糙的身子,在槐树林里缠绕着,暗绿色的斑斑草蜷缩在岸边的大堆树叶里,干灰的梧桐叶子已变得残缺不全,一层,铺展在潮湿的泥土上。几只麻雀蹦跳着,踮着细瘦的腿,从坡地上的槐树林里飞下来,在岸边湿地上找草籽吃。没有人打搅它们,我坐在远处看着它们飞起,又落下,自由自在得像一阵风。
晚餐开始了
姑利山在冬天显得萧瑟无比,栗子树赤脚站在河边,瑟瑟发抖,灰黄色的身子像一根根虚弱的蜡烛,插在老旧的木制橱窗后面摇摇晃晃。阴沉而寒冷的风,缓慢地挪动步子,蜷缩着,从灰皮鼠躲藏的树洞口经过,往霉暗的干槐树那里走去。树叶发出了诡秘的声音,它们被气流搅动,或者,在黄昏开始苏醒,重复一些经年累月的故事,遥远得,如同张口哈出的一团热气,漂浮在没有人迹的峡谷里。
灯已经亮起来了。在木房里,我喝过了两壶茶水,杯子正躺在一旁的杨木茶几上打盹,浑身冒着热乎乎的气息。炉火发出愉快的光芒,跳跃着,柔软的肢爪在炉塘内轻快腾挪,我听到了熟悉的嗞嗞声,温暖而光滑,可我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围坐在这里,伸出手烤火,翻几页书,然后找两块新买的酥饼充饥,权当晚餐之用。我站了起来,把书搁在夹板上,一个人,披着黑色的大衣悄悄走出屋子,来到外面这块平坦的湿地上。就这样,我看到了冬天的姑利山,看到了光秃秃的枝丫,暮色下的村舍隐藏在远处的荒林里,没有人出来走动,也没有奔跑的长耳朵兔子、松鼠、嘎嘎叫唤的野雉,这一切是如此寂静。一路上,我安静地走着,衣领竖了起来,试图挡住峡谷里游走的冷风,我的脚下,冰碴泛出沉静的幽暗之光,它们被皮鞋踩碎的嚓嚓声,轻微地回响着,一如遥远的童年清晨的冰凌,挂在低矮的瓦房檐下熠熠生辉。
许多年来,在暗灰色的冬天,我坐在不同的阳台上晒太阳,闭着眼,就记起一间温暖的房子。它妥贴地扣在公路旁边的石台上,如一枚斑斑草,在枯萎的画卷里坚强生长。一个黄昏,还有其后的许多个黄昏,房子里充满了氤氲的热气,母亲刚从镇子里做木匠的舅舅家回来,她两只手提满了各种颜色的袋子,里面装着熏肉和腌菜,还有一些放在小盒子里的奶油蛋糕。天还没有黑下来,空气里已经飘着蜡烛燃烧过后的味道,油腻得有点刺鼻。母亲示意我们继续呆在房子里看书,她把炉火拨弄得愈加旺盛,自己则系上蓝灰色围裙走进厨房。我和姗姗靠着炉子烤火,她坐在我的对面,脖子上紧紧缠着一条肥厚的橘黄色围巾,我讨厌这种颜色,这使她看起来相当肥胖,如一只蠢笨的粗脖子芦花鸡。于是,我离开了炉子前往厨房,那里总是充满了令人幻想的东西。母亲站在案台前忙碌着,铝壶里的开水咕咚咕咚冒着泡,她看到我就轻声喊着,你把水壶拿下来。我做了自己能做的事情,为此感到很开心,在瓷砖贴成的灶台边,我趴着,看到了上面丰盛的晚餐,黄焖肉、藕片,还有粉丝汤,盛在盘子里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另一边,松针和刨花在火塘里燃烧着,发出毕剥的声响,淡蓝色的烟气,一缕儿,向屋顶缓慢飘散。这时,我们听到了父亲推开铁门的声音,他唱着愉快的祝福之歌,手里提着几只摇晃的兔子,细腰子的猎犬卡儿跟在他身后,摇头摆尾地踱进院子里。我跑了出去,来到父亲跟前,用手摸着兔子绵茸茸的皮毛,卡儿适时用它温热的舌头谄媚似的舔了下我的脸蛋。父亲哈哈地笑着,开始整理自己的猎物,我又听到了母亲的呼喊,谁把桌子搬一下!
接着,我们就要开饭了,吃一顿丰盛的晚餐。
茅店月:本名高锋科,先后在《芳草》、《辽河》、《散文诗》、《读者》等发表文章1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