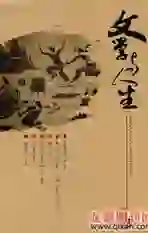散文的“陌生化”
2009-09-19沈荣均
沈荣均
需要承认,汉语散文写作在经历“新散文”大规模拒绝体制写作的努力后,大量“美化乡村”、“美化庸常”的“伪抒情”和“泛文化泡沫”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现在仍然没有步出“公共写作时代”。乡村正在向自认为正确的方向前进。城市化正在制造无差别世界。这很可怕。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需要为此保留一份清醒。“文学的作用不是为了消除差异,而是为了突出差异”,这便是拒绝“公共写作”,洁身自好的“杨永康式”气质——陌生化、差异性、我行我素甚至为所欲为。“新散文”之后,一些作家妥协了(“被主流招安”),一些作家被拒绝(“向民间转移”)。杨永康属于被拒绝的那一部分——自觉与“公共写作”划清界限。对于这样的作家,我表示景仰。对于这样的散文,我保持期待。
读杨永康的散文,我是以后退的思维进行的,从《信仰史》(《再往前走》代后记)开始。在这篇可看作杨永康散文信仰自我清算的文章里,始终流淌着一股孤独悲壮的血液——散文的血液——拒绝“公共写作”的决绝姿态以及对散文前景的担忧。杨永康显然是个散文的冒险主义者。因为冒险,制造“陌生”;因为“陌生”,付出代价。于是,有评论家一面对他的冒险气质大加褒扬,一面又对其冒着牺牲换来的“陌生”不以为然。对于散文,评论家免不了易犯一厢情愿的错误,希望对象能按照自己的经验出现。这会不会导致某种误导——从一种体制进入另一种体制?作家的想法往往不是这样。谢有顺认为,散文应“写给身边熟悉的人”;杨永康则认为,“作家写作的终极努力和原初动力来自作家本身”,甚至干脆发出了“公共写作时代”的散文“完全依赖于个人的觉醒和发现”的感慨。
应该说,《再往前走》在给评论家制造麻烦的同时,也给散文制造了麻烦。克罗奇说,“文学本身是个错误”。面对现代化的无序、不可预见和无所适从,杨永康保持了警惕,“我们无法接受这种乱,却无法阻挡这种乱”。这与我的理解是一致的。现代化制造了诸多困惑,比如“误会”,比如“偶然”,比如“错位”……于此背景下的散文,不得不放弃原来诸多崇高、宏大、美好的“想法”,低下目光来关照矮小、细部,以及坚硬、后退、背离和驳杂等。这本是世界的秩序常态,作家要做的不是整理、规劝、修正和提纯,而是让它呈现出曾被大多数忽视的本来“陌生”。
——“误会”与“偶然”。现实之所以陌生,是因为世界变化太快,而时间以及紧随其后的我们“慢了”。好不容易跟上来,忽然发现,等在我们前面的是更多的误会和偶然,无半点嗔怪,还温情脉脉——熟悉的渐渐远去,陌生的愈加澄明。《找不见的人》中,罗圈腿的黄书郎演洪常青是个误会,黄书郎的枪走火伤人是个误会,最后“找不见的人”葛老十自己开枪了结这场误会是更大的误会!误会的意义在于,它以幽默的力量,成功抵御了冷漠和麻木,放大了潜在于心灵深处某种温暖的东西,以此赋予我们重拾未来的信心。“外面的世界是太吵,外面的世界是太闹。我还是希望它们的生活中能出现一些美好的晕眩与一些美好的意外。”(《世界上最小的口袋》)当小偷把手伸过去的时候,一声清脆的咳嗽,小偷只好把手缩回;当“我”胡乱猜测的时候,又发出一声同样的咳嗽;当“我”不由自主地把手伸进口袋,“我”意外地摸到了一朵玫瑰……“我真想告诉杰西:走着走着花就开了。四月的花。我们在花下等啊等,一会儿就是一大群。”(《走着走着花就开了》)许多的意外,都是小人物的意外,虽然仅是“过渡、短暂和偶然”,但它却通过放大“小”的“误会”与“偶然”,谋划了某种“大”的“本质”——极度彰显小人物的生命体验。韩国的金圣坤认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到头来还是相信恢复总体性——把秩序与和谐赋予片断性——和顿悟的一瞬”,而“后现代派,以对矛盾、不连贯、无所作为和偶然性的欣赏来代替对总体的追求,以赞美过去的滑稽模仿的形态。”照此观点,对比杨永康笔下的“误会”与“偶然”,我们似乎已察觉到杨永康散文的某种追求。
——“错位”与“间离”。《再往前走》、《阴影里舞蹈轻》、《生命中的细节和秘密》、《天国里的杂质和暧昧》、《爱整个世界及你的左肩》……还有很多。这是一组洋溢着浓郁的“杨永康式”气质的散文。很“陌生”,很难读,就像阅读那些大师一样难读。要“深入”大师,仅仅靠阅读难以实现。杨永康的高明在于,他不负责消除读者和大师之间的阅读障碍,但他可以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提供另一种理解,甚至不惜“把两个互不相干的截然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乍一看,好像有些突兀甚至不可理喻,但你不得不承认这样设置带来的意外力量——“有冲突就有震撼”——“错位”与“间离”最后制造了“陌生化”。“即便是聪明的驴子,也无法让这个可疑的季节、细碎的季节‘站住。即便比我聪明的母猪和葡萄,也无法让这个可疑的季节、细碎的季节‘站住。但我们可以短暂地回到海鸥相馆和童年。”(《可疑的细碎的》)如果事物不能随着我们的愿望而改变,那么我们能做到的也只是换个角度去看了。换个角度的效果是,“我”和对象彼此成为对面的“另一个”,虽感“陌生”,但互为风景。
——“镜像”与“符号”。如果说“镜像”还保留现实仅存的模糊和混沌状,“零零碎碎,未作出总体归纳之倾向”(麦克黑尔),那么“符号”,最终完成了杨永康散文的“陌生化”——在虚实相间与真伪并行中,文本与世界、艺术与生活以极端的“短路”方式实现对接。对此,杨永康颇为得意,“我惯用的伎俩是,用一个真实的东西(现实物景)证实另一个并不真实的东西(非现实物景或者梦),这样做的好处是,你根本没法分清哪个是真实的东西,哪个是不真实的东西,结果都成了真实。”我的理解,这样做的本质是一次充满冒险的“证伪”过程(制造识别的混乱)。还好,文学不是逻辑,散文的“证伪”同样具有“陌生化”的力量。“现代主义的必然趋势是象征性,一方面涉及某一具体的情形,另一方面又通过象征来反映更广泛的意义。”(杰姆逊)在杨永康看来,这种象征性似乎就是“作家与事物之间肯定存在一个秘密通道”——从“镜像”到“符号”(从捕捉现实困惑到把问题抽象)。“镜像”(画面感、流动性、记忆片段、毫无拘泥的梦境、时空转换,以及那种陌生的、奇特的甚至是想象力也难以触及的世界等等)在时间上,是不完整的片段,保存了作家的记忆。文学不解决问题,但揭示问题;散文不解决问题,但预示生活。而生活尤为欠缺“形式”。这个形式就是隐藏在日常生活经验当中的某种秘而不宣的符号,只不过我们没有“看见”罢了,散文的目的就是把它揭示出来。《睡吧,床》、《露在外面,许多年》、《千万别碰上伊万》中,大师眼里的床、露在外面的屁股、二丫碰上的那个伊万,这些“镜像”并不“清晰”,但通过作家的抽象,人与床的问题、屁股问题、伊万问题,等等,俨然成为某种“符号”(正是生活所欠缺的“形式”)。现实的“形式”不是单数,世界的“形式”也不是单数。在杨永康的作品里,我们时常看到界线隐退、空间消失,问题和冲突交叠,秘而不宣,却分明昭然若揭。如果说,散文一定有“意义”,这就是杨永康散文的“意义”所在。
因为自身身份、经历、处境、生活方式、趣味、个人经验、价值判断等因素,杨永康的散文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显著的“杨永康式”烙印,这既是杨永康散文需要警惕的问题,也是杨永康保持叙述定力的优势。当代汉语散文作家要走得更远,恐怕需要在每次提笔的时候,像杨永康一样自觉地去思考身边那些“陌生的熟悉”(在别人看来,接近于孩子天真无邪的“撒谎”),而不是抱以漠视,或者对日常的经验盲目乐观。生活中,我们往往毫无成功、喜悦、幸福可言。那些津津乐道于各种感悟、经验的,与散文无关。散文本质是“小”的——通过叙述小个体形形色色的遭遇,揭示我们共同的命运。从这一点讲,我有信心对杨永康的散文前途一如既往保持阅读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