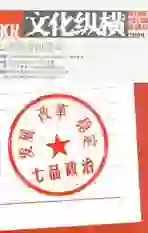民族国家的观念与中国实践
2009-08-27吴飞
吴 飞


一、从世俗国家到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一般被认为是现代世界基本的国家形态。有人指出,我们经由日文把nation-state翻译成“民族国家”是一个错误,因为这个概念所指的并不只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而是“世俗国家”。确实,nation-state的含义并不只是单一民族建立的国家,而且是摆脱了神权枷锁的主权国家。不过,对这个概念的误解,并不是从它的日文翻译或中文翻译开始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民族觉醒的浪潮中建立的很多国家,就已经把nation-state理解成了“单一民族的国家”。日文和中文的理解,只是当时世界范围内对这个概念的普遍理解的一个延续,而不是因为日本人和中国人特别地误解了它。
在欧洲早期现代,随着世俗王权的强大和宗教改革的推进,nation-state也逐渐形成了。当时民族国家的主体,确实不是20世纪意义上的族群概念。不过,由于世俗方言的兴起,以及新教各教派的形成,也就形成了单一语言、单一教派、世俗王权至上,这样三位一体的nation-state,来对抗罗马教廷拉丁语的神权统治。这些国家的公民,也就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民族,而这样的“世俗国家”,也就慢慢可以被理解为“民族国家”了。
这一点尤其可以在19世纪末德国完成统一的过程中看到。随着拿破仑的战争以及普鲁士帝国的逐渐强大,以前极为分散的德意志各邦的民族意识日渐兴起。但把这100多个小邦国统一成一个国家不仅在政治上不是易事,在理论上要说服每个邦国的公民也需要大量的工作。因此,当时德意志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所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研究看上去非常不同的各个小邦国人民之间的共同性,然后把他们塑造成统一的德意志民族,从而成为国家统一的基础。虽然这些学者的工作在大多数邦国是成功的,但在奥地利这个与德意志民族有明显亲缘关系的人群中,却始终未能建立起民族认同。德意志的统一,既是德意志强大的现代世俗国家的建构,也是德意志民族的形塑过程。
所以,虽然nation-state指的不只是民族国家,但这种世俗国家确实是经常建立在单一民族基础上的民族国家。这个并不是绝对的误解。因此,现代中国人在接受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还是准确把握了20世纪初西方世界对它的基本理解,其所缺的部分只是未能了解这个概念形成的复杂历史过程,无法洞彻从世俗国家到民族国家这一历史过程的思想史意义。但这一点,是现代中国在接受很多西方观念时所犯的通病,比如无法理解自由民主背后的思想内涵,无法看到现代科学背后的人文意义,等等,这都是要假以时日,慢慢探索和澄清的。
二、民族国家与多民族的现代国家
既然nation-state并不内在地意味着单一民族的国家,那么,在现代西方,就完全可能形成非常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事实正是如此。即使在西方,单一民族国家也并不是唯一的现代国家形态。
我们姑且不说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基本上不存在,很多国家的现代性建构过程也并不符合在单一民族的基础上建立世俗国家这一路向。比如率先崛起的英国,可以说是现代世俗国家的典范。虽然我们一般也把它当作以英格兰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但且不说它早就吞并了威尔士和爱尔兰这样的异民族,而且在它走向现代国家的关键时刻,英格兰与苏格兰形成了联合王国,这一多民族的特性甚至体现在了它的国旗上:两个十字架的交叉代表了两个基督教国家的联合。更不必说拥有众多殖民地的大英帝国,当然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以欧洲移民为国民主体的美国更不是单一民族的世俗国家。美国建政之初,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之间的那场争论,多少就和这个问题相关。究竟是建立小型的道德共同体,还是建立容纳多民族、多宗教,甚至多语言的众多群体,建立一个庞大的现代帝国,正是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争论的焦点之一。要打破启蒙思想家所谓民主制不可能在大国实现的断言,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国家形态,就必然包容不同的信仰、文化和民族背景。美国的成功为现代国家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模式,与在单一民族的基础上建立自由民主的世俗国家的传统已经非常不同。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美国这个多民族、多文化混杂的大帝国,反而逐渐变成了西方自由民主的代言人。难怪托克维尔要特意远渡重洋,去研究民主在美国安家后究竟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
超越民族国家的模式,其实并不只是英美政治思想的发明,而且代表了现代西方政治理想的一个更高境界。这种超越多少类似于当年罗马帝国对城邦制度的超越。在希腊罗马的古典城邦,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也和启蒙思想家一样,认为大国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希腊人普遍认为,文明人的生活只有在狭小的城邦中才有可能,像波斯和埃及那样的大国,只能是野蛮人。但是,随着亚历山大对城邦模式的打破,以及后来庞大的罗马帝国的崛起,城邦制不仅无法维持它的政治安全,而且根本就无法存在了。基督教的兴起和传播,也打破了民族宗教的形式,为跨民族的大帝国提供了意识形态。
到新教改革的时候,庞大的天主教会重新分裂为各自为政的新教派别,并与世俗政治体结合,于是有了建立世俗的民族国家的要求。像英国的亨利八世成立圣公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过,从天主教会分裂为新教教派,这并不是回到基督教之前的民族宗教。每个新教教派都有普世的宗教要求,只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力量而不得不把自己限制在狭小的民族国家之内。因此,圣公会的英国仍然愿意与天主教的苏格兰联合。
正是因为基督教文明的这种普世要求,哪怕是到了今天,欧洲人不仅不满足于民族国家的模式,而且试图统一欧洲,恢复罗马帝国的光荣。美国人之所以从一开始就不满足于民族国家的模式,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建立现代新罗马的迷梦。美国之后,加拿大、前苏联等国家采取的都是这一模式。
三、从“五族共和”到五十六个民族
中国建立现代世俗国家的任务,恰恰与革命党人的排满思想同步发生,于是就很容易接受民族国家的概念中的民族主义成分。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排满的热潮渐渐消退了,“驱除鞑虏”的口号也逐渐被更理性的“五族共和”思想取代,但民族国家的理念依然延续了下来。民国时期的民族学受德国影响不小,其基本倾向就是,从中国传统的宗法思想出发,试图将汉、满、蒙、回、藏五族比附为同一宗族的不同分支。于是,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说:
“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诗经》上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诗经》上又说:‘岂伊异人,昆弟甥舅,就是说各宗族之间,血统相维之外,还有婚姻的系属。古代中国的民族就是这样构成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全体的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崇高的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决不是徒托空言的。”
陈伯达在批判此书时指出:“民族血统论,本来是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糟粕,德、意、日法西斯就是拿这类怪论去作为进行侵略全世界的工具的。不料蒋先生也以血统立论,实属怪事。”这一批评虽有其政治上的目的,但他指出国民党的民族政策与德、意、日的民族国家路向更加接近,却是实情。
共和国建立之后,则采取了另外一条路线,就是学习苏联的经验,通过细致的民族识别,把本来差别也许很细微的族群区分成不同的民族,最后确立了五十六个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这种通过苏联学来的模式,就是多民族并存的现代国家模式,是与单一民族国家不同的一种现代国家模式。虽然这一模式不无它的问题,但总体而言,苏联后来的诸多民族问题,在中国并没有出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所学习的并不只是欧洲的多民族国家模式,而且中国文明继承了几千年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模式,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多元一体格局”。
应该说,无论国民党的“五族共和”,还是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都既从现代社会的国家建构中寻找支持,也从中国历史上寻找资源。凡是异族入主中原,官修史书总要把该族的祖先说成是黄帝的某个子孙,因故窜于夷狄,所以这个民族只不过是华夏民族的一个分支;这就是国民党宗族论的古代资源。但“民族区域自治”的背后,却是“夷夏之辨”的更深层含义。
四、夷夏之辨与多元一体格局
古代圣人向来重视夷夏之辨,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非常不同。很多时候,“夷夏之辨”被理解成了族群之间的问题,好像这就是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斗争,如吕留良所谓“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此乃域中第一义”;但若从历史的角度看,则夷夏之辨重视的是礼乐文明,而非血统或族群。孔子作《春秋》所推崇的尊王攘夷,乃是“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唐代的程晏更明确指出:“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历史上各民族的融合并不是以一个主流族群吞并各少数民族,而是以礼乐文明统合各个民族。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汉族”,并不是因为血统的同源,而是由于文化的融合。所以当年进入中原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等民族,就慢慢融合成了统一的民族。
我们也不能把儒家礼乐文明理解为汉族的民族宗教或民族文化。它是中华民族的一套文明框架,在它之下可以容纳各种文化形态和宗教形态。佛教在中原地区兴盛起来,也并没有使佛教徒不再是汉族;今天的很多汉族人成为基督徒,也不妨碍他们仍然是汉族。甚至,在儒学传播的其他地区,像日本、朝鲜,也自称为“中华”、“华夏”。把汉族当成一个与其他民族并列的族群,只是在有了现代民族观念之后的一种强行划分。
今天的中国,当然已经不再只是古代儒家文明的承载者,而是在中华文明的框架之下,吸收了大量的现代文明建立起来的一个现代世俗国家。它并不是以“汉族”这个族群为国民主体的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可以容纳多元民族、多元宗教的一个文明和政治实体。在这个政治实体之下的各个民族,都可以享受和进一步创造共同的礼乐文明,也可以维护和发展各自独特的民族文明;但在政治层面上,各民族都只有一个忠诚的对象,那就是中国。
中华文明向来有普世性的天下诉求,这与基督教文明的普世精神有相似之处,但也有重大区别。西方现代文明在建立诸多民族国家的同时,仍然要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等办法重温罗马帝国的普世旧梦。但中华文明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完全陷入民族国家的狭小局面;其普世理想更不是通过征服与兼并完成的。而今,中华文明在进入现代世界之后,通过西方现代国家的政治模式,艰难但基本上成功地继承了“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普世理想。虽然现代中国还有很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没有解决,现代中国的文明框架也并未完全安顿下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样一个现代大国,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使自己或其中任何一个族群缩回民族国家的模式。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