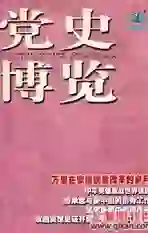张学良眼中的周恩来
2009-08-18窦应泰
窦应泰
1991年张学良恢复自由后,先后对旅美学者唐德刚、日本NHK(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美国之音广播电台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作过多次历史口述,同时也对媒体发表过有关西安事变历史真相的谈话。在这些公开或不公开的历史回顾中,张学良多次谈到了周恩来。他明确表示:“中国现代政治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
肤施初会之前,业已久仰周恩来大名
1989年,尚未完全恢复自由的张学良,在台北凯悦酒店首次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公开谈到了他对周恩来最初的印象。他说:“我在南开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应为‘他在南开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之误,张学良从未在南开大学就读。当年周恩来分别在辽宁铁岭银冈书院和天津南开学校就读,与张学良属于同年同期的学生——引者注),就已经知道了周恩来的名字。不过不是作为政治家,而是因为他的京剧演得特别好,是作为一个具有演剧才能的学生知道他的。他最拿手的是演坤角,演得确实好。但当时我们没有什么交往,因此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后来会成为那么有名的一位政治家。”
当日本NHK电视台记者向张学良进一步询问他对周恩来的印象时,张学良这样爽快地作答:“怎么说呢?他肯定是个相当高明的人物,反应快,对事情的理解很深,对谈话的反应极其敏锐。他话不多,但常常一语中的,见识非常广。因此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很对脾气,像老朋友一样彼此敞开了胸怀。……同周恩来会谈之后,我甚感得意,觉得今后国内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矣。”
张学良不仅对日本记者这样评价周恩来,从稍早在台北寓所对秘密采访自己的旅美学者唐德刚的谈话中,也可觅到他对周恩来不容置疑的好感。张学良说:“这个事情(指唐德刚询问他对周恩来的印象),我现在直截了当地说了,我是跟周恩来见了面。我跟你说,中国现代政治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这个人,我俩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刺透了。他也是相当佩服我。你看到周恩来说的话了吗?可以说,我俩一见面,就成为知己了。”
张学良对唐德刚的谈话比对日本NHK电视台记者的表白更进了一步。他对周恩来的评价,并不是没有原则的一味吹捧或简单的点评,而是有理有据,生动具体。张学良对周恩来的评价,只有经历过患难与共的考验才可以说得出来。张学良说:“当时,我答应了周恩来。周恩来说,‘如果你能做到这点,我们共产党可以放弃那些事情。我说,我去试一试。我当时太自傲了……”
张学良以上这些谈话,都是他在获取一定程度的自由之后的坦荡表白。他在被幽禁期间亲笔撰写的《杂忆随想漫录》中,也对周恩来大加褒扬。张学良这篇于1954年在台湾幽禁期间写的《杂忆随想漫录》,实则是遵从蒋介石之命,写给蒋亲阅的历史回忆录。在这篇专供蒋氏父子亲阅和国民党中常委们传阅的回忆录中,张学良也为当年在肤施大教堂里与他彻夜交谈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大大地记写一笔。他说:“我遂飞往肤施,在天主堂寓所和周恩来会见。周恩来为人捷给,伶俐机敏。我二人谈至深夜……”
恢复自由后,公开肯定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历史地位
张学良和周恩来两人结为至友的另一媒介,则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
张学良在对唐德刚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周恩来见面后对我说,我和你初次见面,就感到张将军是一个痛快人,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因为我当年也在东北读过书。我就说他,你是南方人,怎么会到东北读书?周恩来告诉我说:‘其实我是在东北长大的,是我的家叔把我从江苏淮安带到铁岭读书的。当时我读书的地方是银冈书院,你知道吗?我少年时在东北曾经做过张大帅的三年臣民。我对东北人的性格是熟悉的,我也喜欢东北人的这种性格。当时我听了,就随口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周恩来就问我,张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师?你也到天津读过书吗?我就对他说,我没有去天津读过书,不过张伯苓到过我们东北,那时我在基督教青年会多次听张伯苓讲课,所以他就是我的老师。后来,我抽大烟,打吗啡,其中也是听了张伯苓的规劝,下决心完全戒掉了。”
张伯苓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的校长,也是张学良在东北时期最为崇敬的长者。因为有张伯苓这位教育家作为两人的媒介,所以自然拉近了周恩来和张学良之间的感情距离。也就是在这次历史性的接触之后,张学良向周恩来表达了他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要求表示支持和理解,但由于当时共产国际对张学良持有极其强烈的偏见,张学良的入党要求最终没有实现。
从近年解密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的采访资料中可以见到,张学良对周恩来和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作为有较为详细的谈话。采访者向张学良求证处理事变善后过程中他和中共人士尤其是周恩来的接触情况。采访者问:“共产党那边也有许多派,有主战派还有缓和派,就是周恩来、叶剑英吗?你和他们接触最多的是周恩来还是叶剑英?”张学良答:“叶剑英是激烈派,他主张把蒋介石消灭了。”采访者问:“毛泽东是希望把他(蒋介石)公审。毛泽东本来的意思是要把蒋先生提出公审。”张学良答:“毛泽东没有提出这个办法。那时候在我那里的就是叶剑英跟周恩来。周恩来是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采访者问:“那时候你跟他(周恩来)谈得来?”张学良答:“那是‘三位一体嘛。周恩来这人好厉害。他们都控制住了,连我的部下,杨虎城的人都听他的。他说出来的话很有理。这个人好厉害,不但会讲,也能处置事情,是我佩服的一个人。”
张学良还说:“西安事变过了两三天,周恩来和其他两个人一起到西安来了,一位是博古,一位是叶剑英。从那时起,周恩来似乎成了西安的首领。周恩来一到西安就对我说:‘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时,我们吃了一惊。他接着还说共产党内部也有两种意见,过激派的主张对蒋先生不利。叶剑英乃其中之一。另外一派主张和平解决,拥护蒋先生。周恩来自己属于这种观点。”
张学良在对日本NHK电视台记者的谈话中,也承认周恩来一度成为西安城中的“首领”。他的话无疑是对当时周恩来所处地位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所起到的历史性作用的嘉许。这对于一生都不肯服人的张学良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毕竟他才是这场震惊中外的事变的真正发动者和领导者之一。
对西安事变后带周恩来与蒋介石见面一事一直谨言慎语
2001年张学良在美国檀香山去世后,海外某些学者利用全文公布他生前所著《杂忆随想漫录》之便,公开否定他在西安事变前后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甚至利用他《同中国共产党人的交接》、《同周恩来会见于肤施》以及《对共产党的观感》等篇中的观点,达到丑化他与周恩来关系的目的。这是让人非常痛心的事情。事实上,张学良撰写这些文章时,是20世纪50年代被幽禁在台湾清泉时期,也正是蒋介石对他采取白色恐怖的日子。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张学良奉命撰写这些直接涉及中共和周恩来的文稿,无疑身受种种局限。因此,他在上述文稿中出现一些混乱的思想意识,是在所难免的。
1990年,在刚刚有了点言论自由后,张学良就对日本NHK电视台记者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是不容抹杀的。他说:“共产党最后的决定是这样的:拥护蒋先生的抗日指导权,与东北军、西北军合作,绝对遵守延安会谈的协定。于是,周恩来也参加了已经成立的委员会。当时的西安称为‘三位一体,即东北军、西北军及共产党。委员会得到共产党的加入,讨论了当时的形势,决定了以下的方针:坚持八项要求,但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要力争早日和平解决……”
由于张学良当时尚未真正走出历史的阴影,所以当日本记者问到周恩来在西安和蒋介石见面他是否在场时,他说话比较隐晦:“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尖锐的事情。我简单说一句话,就是请你不要往下问这个事情。不单是我在场,周恩来见蒋先生也是我领他去见的。”日本记者追问:“您现在能不能稍微讲讲当时谈话的内容?”张学良当即表示:“对不起,我不能往下讲。我很不愿意回答这个主要的问题。简单说,请体谅我的苦衷就是了。”
张学良于1991年4月到达美国后,在纽约接受美国之音广播电台记者采访时,采访者也提出了与日本记者相同的问题:“事变时周恩来到西安,周、蒋及您三人还单独见面。你们见面所谈的问题,对事变的结束是否产生了关键性的作用?”张学良此时仍然持谨慎的态度。他说:“此事现在我应该不应该说,你叫我想一想。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见的。那时蒋先生身上稍微有点伤。他们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实在外面很大的是谣传,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他问候蒋先生,蒋先生也见到他。他自承是蒋先生当年的部下。可(以)说三个人并没有谈什么。”
美国记者继续询问:“事变中中国共产党究竟担当什么角色?”张学良回答说:“事变共产党开始没有参加,事情起来了,我们才把周恩来先生接来,谈此事该怎么办。”美国记者又问:“中国共产党对事件发生的态度如何?是赞成还是反对?”张学良答道:“他们没有预谋。他们也很惊讶忽然出来这个事情,没有赞成或反对的意思。”记者继续问:“您觉得周恩来先生怎样?你有无和毛泽东接触?”张学良回答说:“周恩来先生我非常佩服。我们初次见面,我认为他反应很快。这人说话一针见血,没什么委曲婉转绕弯。虽然他是那么大的一个政治家,也是外交家,但是他说话直截了当。人很聪明。我俩见面感情很好。毛泽东我没见过。”
关于张学良去南京一事,许多人都认为周恩来事前不知情,但张学良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去南京的事,您和谁商量过吗”,这样说:“我自己决定的,但杨虎城想拉住我。”日本记者问:“您没和周恩来商量过吗?”张学良说:“没商量,但他知道。为了制止我,他跟到飞机场来了。周恩来是打算把我劝回去的,他恐怕我在南京会出什么事。但我认为,作为军人来说,我的行动就等于谋反。谋反就要判罪,该判死刑就判死刑。”日本记者又问:“您在飞机场见到周恩来了吗?”张学良说:“他来到飞机场时,我已经上飞机了。因此没见到周恩来,我就向南京出发了。”
若干年后,周恩来回忆起当年在西安机场上的最后一幕时,对张学良不听他劝阻飞往南京一事曾经感叹地表示:“汉卿是看《连环套》中了迷,他这是摆队送天霸啊!”
虽然天各一方,但张学良与周恩来彼此一直情深意重
张学良去世前后,海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他在谈话中的语误,刻意制造所谓“张学良批评周恩来”等种种传闻,企图混淆视听。其中有自称是“流亡海外的东北老乡”的人在文章中说:“张学良曾经在与几位客居美国的东北同乡的谈话中抱怨说,当初周恩来说捉蒋时讲得头头是道,后来说放蒋时也是头头是道。”显然这是无中生有。稍知这段史实的人都知道,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时,周恩来正在陕北保安,事前不可能知道张、杨发动事变之事。如此,周恩来又怎么能在“捉蒋时讲得头头是道”呢?
事实上,张学良从没有说过任何有损与周恩来友谊的话。诚如他1990年对日本NHK电视台记者所说:“周恩来对我有评价,我也差不多同样评价周恩来。就是反应很快,了解事情也很透彻。我对他的评价差不多也是这样。一谈话反应很快,内外不用什么啰唆……”
张学良不仅在恢复自由后的所有公开谈话中对周恩来没有微词,就是自1936年12月在南京失去自由以后,也始终与周恩来保持着良好的感情纽带。虽然处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下,他依然没有忘记远在抗战第一线的周恩来。
1937年2月17日,被蒋介石秘密囚禁在浙江奉化深山中的张学良,得以有机会往外捎信时,便冒险给周恩来寄出了第一封密信。他在这封信中写道:
恩来兄:
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犹对东北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
弟目下(闲)居读书,一切甚得,请勿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使,盼有教我。并请代为向诸同人致敬意。
此颂延安
弟良二月十七日
张学良此信,通过何柱国将军最终辗转送给远在延安的周恩来。这足以说明,直到张学良身陷囹圄之时,仍然和周恩来保持着秘密的往来。如果依前文所说,张学良对周恩来在捉蒋放蒋一事上早就心存抱怨,那么他就不可能再有这封书信捎往延安了。
在此后的艰难岁月中,张学良和周恩来天各一方。
1946年,当东北元老莫德惠获蒋介石特许前往贵州桐梓探望被幽禁了10年的张学良时,带去了周恩来的一封信。此信不知何故至今尚未公开,但张学良在收到周恩来书信后请莫德惠捎回的他的复信,则在近年得以解密。这是张学良在幽禁中第二次给周恩来写信。信的内容是: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为)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作红娘,愿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视想(者)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余不尽一。
弟良四月十九日
与前信有所不同的是,张学良给周恩来的这封信,用语稍为隐晦,而且在信前没有惯用的抬头,略去了周恩来的名字。历经幽禁十载,反倒不如当初在浙江奉化时敢于在信中直呼其名,只能说明张学良在贵州的幽禁状况不如从前。不过即使环境如此险恶,张学良怀念周恩来的情感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周恩来在世时从未对张学良在幽禁中曾有书信给他披露过只言片语,显然是为了保护张学良的安全。但这并不等于他在心里忘却了张学良这位重感情、讲义气的朋友。
1958年岁末,周恩来在北京获悉宋子文从美国来到香港,感到这是一次营救张学良的好机会,于是设法透过在香港的友人,以“一个北京的老朋友”名义向宋子文传话,要求他实现当年在西安事变期间曾经作出过的三项保证,设法实现张学良的人身自由。宋子文马上意识到“老朋友”即是周恩来。他也清楚地记得当年在西安时曾经对周恩来作出的三项许诺,其中的第一项停止内战,第二项对日抗战,当年已经兑现。唯第三项保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安全,他当年已经作过努力,然而无法改变蒋介石的主意;加之现在自己早已远居美国,且与蒋介石貌合神离,对于救助张学良更是无能为力了。于是,他遗憾地向那位传话的友人表示:“请转告北京的朋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实在无能为力。请北京的老朋友谅解!”
1961年春,日理万机的周恩来透过相关人士,巧妙地将一封密信送到了台湾,交到了仍然没有自由的张学良手中。全信只有弥足珍贵的16个字:
为国珍重,善自养心;
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这是周恩来去世后得以公开的一封密信,虽只有16个字,但足以说明周恩来生前对张学良的至深情谊。1961年12月12日,周恩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亲自主持召开“西安事变25周年纪念会”,在会上洒泪陈词:“我的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让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
即便在“文革”中,周恩来也没有忘记张学良。一次,他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一位台湾友人时,还深情地表示:“如果张学良将军的生命有个一差二错,我们就不好见面了。”对张学良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1976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病逝。去世前夕,他听闻张学良在台湾染患眼疾,很是忧愁,在病榻上叮嘱国务院主管港澳台事务的负责同志:“不要忘了台湾的老朋友。”张学良在台北惊悉周恩来去世的消息后,也曾遥望远天,洒泪为祭。但在当时两岸对峙的情势下,这两位在西安事变中结下真挚友情的爱国者,无法实现阔别聚首的夙愿,无疑是历史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