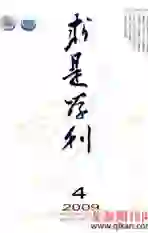从元刊杂剧重新审视元杂剧体制之原貌
2009-08-04杜海军
摘要:《元刊杂剧三十种》是现存刊刻最早的元杂剧选本,也是最早的戏曲刊本。它保留了元杂剧体制、内容、版本最原始的资料,从中可以看出元杂剧分折的不规范,题目正名使用的不规范,诸宫调形式的影响等,若以戏曲的标准衡量,某些作品在许多方面还没能达到今日戏曲史所云之规范。
关键词:《元刊杂剧三十种》; 折;出; 题目正名; 诸宫调
作者简介: 杜海军(1957—),男,河南内黄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宋元文学、古代戏曲文献与戏曲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I23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4-0107-05收稿日期:2008-03-17
杂剧进入元代后,作为戏曲看待应当说有成熟之作,但也还有不少作品并非如今人所说之圆满和规范,特别在体制方面,反映了元杂剧在元代也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元人所刊杂剧本身就可以看得很明白。这里所说的“元人所刊杂剧”就是《元刊杂剧三十种》。
《元刊杂剧三十种》 ①原无此名,无是次序,剧本亦缺属作者姓氏,据知先后由李开先、何煌、黄丕烈、罗振玉等人收藏。黄丕烈称其为“元刻古今杂剧”。王国维在京都文科大学影刊后,见其流传中土者少,又深感“原书次序先后舛错”,“本无次第及作者姓氏”,于是亲手考订时代及作品的撰人,厘定录目,方成今见之框架和名称,遂为人们广泛接受[1](P237)。以后郑蹇、徐沁君、宁希元、田中谦二等中外学者分别对其校勘,补校了许多内容,因广泛流行宇内,在元杂剧的推广和研究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成为人们认识元杂剧内容和体制的重要依据,甚至是唯一依据,而元刊杂剧的原本从此被抛掷一边。
元杂剧,若从今天所存之元刊本来看,就剧本体制而言,很多地方是不规范的,比如分折、分楔子,题目、正名,角色等问题,几无方圆可规矩。明代以后人或者说我们今人所论元杂剧之规范实多从明人选刊元杂剧说起②。《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刊刻内容和形式为我们恰当认识元杂剧的本来面目提供了可能。
一、元杂剧实未全以“折”分
关于元杂剧以“折”分的问题,学者讨论已很多。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四折、或四折加楔子。早些时候如王国维在《元剧之结构》中就说:“元剧以一宫调之曲一套为一折。普通杂剧,大抵四折,或加楔子。”[1](P87)稍近者如李春祥作《元杂剧史稿》说:“元杂剧剧本由折、楔子和题目正名构成……元杂剧以折为单位,折是剧本的情节段落,以一剧四折为通例,超过四折为变体。”[2](P28)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说“元杂剧剧本结构通常分为四折一楔子,合为一本”[3](P31)。更近者如田同旭2007年的皇皇巨著《元杂剧通论》也有是说:“一本四折加楔子,四套宫调一人主唱到底,这是元杂剧的基本构成形式,其中有许多值得探讨的文化意蕴。”[4](P62)
这里称“折”略相当于近日戏曲中的“幕”,是对杂剧以套曲为单位的情节的划分和称呼。这种以“折”分杂剧的主张,基本是依据钟嗣成《录鬼簿》、张时起的《赛花月秋千记》和《开坛阐教黄粱梦》记载的说法,如幺书仪说:“分‘折的说法起于元代,如元人钟嗣成的《录鬼簿》注张时起的《赛花月秋千记》为‘六折,注《开坛阐教黄粱梦》云:‘第一折马致远,第二折李时中,第三折花李郎学士,第四折红字李二。看来,元代即有分‘折的规矩。”[5](P94)还有些是依据明刊元杂剧立论,不必说。这些学者重视了《录鬼簿》有“折”的文字记载,是应该的,依明刊元杂剧立论虽有些牵强,也勉强可云备一说,但却不该(甚至是有意地)忽略了元刊杂剧这一人尽皆知的不曾以“折”分的事实。幺书仪的说法在此方面有代表性:“但是刊刻于元代的《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剧本中,却只是通过剧中情节形成的自然分界和人物的上下场来划分场次段落。这种与《录鬼簿》记载不符合的情况,或许是刊刻者认为没有必要标示的缘故吧?”笔者以为,这种采信一种说法,不顾(甚至直接否定)一种事实的办法,是不客观、不科学的。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除了《录鬼簿》中有“折”字之记载和明刊元杂剧的以四折分,更主要的是源于人们一种先入为主的看法,以为元杂剧的体制与生俱来就应该如此。李日星《元杂剧“折”的本意与起始》文中有一段话最具代表性,他说:“元代和明初文献出版家所刊刻的元人杂剧不分折,并不等于说元杂剧家所创作剧本没有分折,而是因为刊刻者尚处于杂剧时兴的当代,对约定俗成、众所周知的领域知识不以为然而简省了分折标目的程序,使元杂剧固有的折次没有得到彰显……根据臧懋循《元曲选》和隋树森《元曲选外编》……这说明四折结构法是元杂剧的定式、惯例、原则和方法。”[6]
其实,李日星这种“杂剧时兴”、“约定俗成”、“众所周知”,尤其是“定式”、“惯例”、“原则”等说法,多半是一相情愿而根据不充分的。一是杂剧当时并说不上“时兴”。在元代,人们对杂剧这种体裁的认可程度还不如我们今天这样高,这点学者们也是有共识的。王国维《元剧之文章》就说:“元剧关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当日未尝重视此事,故往往互相蹈袭,或草草为之。”[1](P85)王国维的“未尝重视”之说在文献中不难得到印证,主要表现在实践中,演员和作家都受尽了人的歧视,他们多是“门第卑微,职位不振”[7](P101),即使如一些名家,人拟之为杜甫、杜牧如杜善夫、白朴、关汉卿者,也一样为“庸俗者易之”,为“用世者嗤之”[8](P20)。在这种情势下,相信当时无论是杂剧作家或者演员,对于杂剧的体制思考并不一定会如今人认真而深入,也可能甚至就没有时间深入思考。再说,彼时人们作杂剧也多是以作曲视之,表现在艺人们论杂剧也常将论杂剧附在论曲之间,如元人燕南芝庵《唱论》、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论乐府等,其实多是论杂剧中曲,而于戏曲中其他问题则少有涉及。
另外,当时杂剧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还说不上成熟。元杂剧兴起从宋金到元代,它的演唱形式、体制等也应当有一个从不规范、不成熟到逐渐成熟、完善、规范而被人接受的过程,不可能进入元代便一蹴而就地定型为“惯例”。这点,我们从元杂剧作品本身保留有许多明显的说唱文学痕迹是可以看出来的(详论见本文第二部分“元杂剧多诸宫调形式之遗存”)。因此我们不能将《元刊杂剧三十种》不以“折”分强说成是人们对元杂剧以“折”分的认可。实际情况是,笔者拙见,当时杂剧应尚以套曲分场次而名暂无定说,包括各行其是的三种情况:场次无冠名的、冠以“出”或者“折”“出”杂用的、以“折”冠名的等。这些我们可在元刻、明刻元杂剧或明初人所作杂剧的刊行本中得到印证。
首先说场次无冠名的。此类情况现存元刻本《元刊杂剧三十种》全然如此,是最好的明证。其他,明人李开先选刊于嘉靖、隆庆间的《改定元贤传奇》是时间仅后于元刊本的早期杂剧刻本。这部选本共选元代和明初人杂剧16种。今全书散逸,只存有马致远《青衫泪》、《陈抟高卧》,白朴《梧桐雨》,乔吉《两世姻缘》、《扬州梦》,王子一《误入天台》等六种。这六种中,有些元刊本同样没有场次冠名,如《青衫泪》。较《改定元贤传奇》稍晚的脉望馆杂剧其中抄于小谷元杂剧更有多不冠名者,如郑廷玉《宋上皇御断金凤钗》,李寿卿《月明和尚度柳翠》,无名氏《郑月莲秋夜云窗梦》,白仁甫《董秀英花月东墙记》,高文秀的《好酒赵元遇上皇》,费唐臣《苏子瞻风雪贬黄州》,无名氏《杀狗劝夫》、《大妇小妻还牢末》、《敬德不伏老》等都是如此。还有关汉卿《单刀会》。脉望馆杂剧明丹丘先生《独步大罗天》,朱有燉的杂剧也还未分折。
其次是冠以“出”,或者“折”、“出”杂用。如明刊《古杂剧》本《杜蕊娘智赏金线池》第一套曲、《李云英风送梧桐叶》第三套曲、《汉元帝孤雁汉宫秋》第一套曲和第二套曲等标的是“出”,其他标“折”。而《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感天动地窦娥冤》全四出却不论折,早于《元曲选》本《窦娥冤》,却与《元曲选》本全然不同。
再次是以“折”冠名,这是常论,不赘。
从以上所论元杂剧的不分折、或折与出混用等情况来看,“折”的问题在元代杂剧发展中可能不如今日所说之整齐。《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全然不以“折”分,是对我们的一个明确提示,要尊重这一事实。即使是元杂剧以折分的,从杂剧作品内证也可看出以折分未成必然。元杂剧虽然在文献中有“折”之说,但何谓“折”,用法是比较混乱的。据今所见《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剧目,彼时“折”字的使用作为杂剧一幕戏之名亦非如王国维所说专指杂剧的“一宫调之曲一套”,却在更多的情况下,往往是用在一折戏的内部,任何一个角色的出场都可以称为一折,意思或许是标举一个小的场景。如《诈妮子调风月》第一折:“老孤、正末一折。正末、卜儿一折。”第二折:“外孤一折。正末、外旦郊外一折。”第三折:“外孤一折。夫人一折。正末、六儿一折。”《马丹阳三度任疯子》第一折:“等众屠户上。一折下。等马一折下。”从这些情况看,“折”的概念在元代至少是不确定的,在一本戏中一个概念不至于多种含义,否则逻辑上混乱难通。所以,我们以为其时杂剧的场次之分还没有取得一个固定的明确的名称,是有其实却无其名,或者有些是不分折,所以每套曲只有曲牌而不注明宫调。因此有些学者对元杂剧在元代的分折便表示了怀疑。郑振铎说元杂剧分折“约是始于万历时代,至早也不能过嘉靖的晚年”[9](P27)。
拙见以为,元杂剧作家在如何对场次命名方面应该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统一的意见。
还有楔子的问题。元杂剧的楔子之名在《元刊杂剧三十种》中也是没有的,或许有其实。今人所论元杂剧之楔子多是据明刊元杂剧如《元曲选》而言,徐扶明说:“从《元曲选》来看,在一百种杂剧剧本中,有楔子的,共六十九种,约占全部剧本三分之二以上。”[10](P77)所以楔子的问题,从元刊元杂剧看也是研究元杂剧者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二、元杂剧多诸宫调形式之遗存
元杂剧受宋金文学的影响,在元刊杂剧中依然显现出诸宫调的痕迹。学者多认为元杂剧作为戏曲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诸宫调的影响。关于元杂剧与诸宫调的渊源关系,郑振铎说得明确:“诸宫调的伟大影响,却在元代杂剧里……或者可以说,如果没有‘诸宫调的一个文体的产生,为元人一代光荣的‘杂剧,究竟能否出现,却还是一个不可知之数呢。”①郑振铎所说诸宫调对元杂剧的影响主要是“专一人”念唱的形式。我们要说的是,元杂剧中演员的叙述方式,也还偶然存在许多诸宫调的蛛丝马迹,即“第三身的叙述与描状”特点②,也就是“剧外人”的叙述。徐扶明把这一点看做诸宫调与北杂剧的区别点③。如《看钱奴》元刊本第一折,圣帝欲增福神加福二十年与贾弘义,贾弘义要求增加,增福神唱道:“他成家人未身安,破家人先生下。借与他个钱龙入家,有限次家私交你权把,借与你二十年不管消乏。你待告增加,祸福无差,贫富天公定论下……”这曲本是增福神唱与贾弘义的,当直接使用第二人称“你”字,然而使用的却是第三人称“他”,显然是唱说诸宫调艺人所有的腔调,且与第二人称混合使用。又如《陈抟高卧》第二折,在使臣党继恩秉圣旨的催请下,陈抟允诺下山,有向党继恩唱一段曲,元刊本[黄钟尾]:“也不索雕鞍缓缓的登程进,也不索骏马驱驱的践路尘。虽然圣旨紧,请将军勿心困。尽交山列着屏,草展着裀,鹤看着家,云锁着门,子消得顺天风驾一片白云,教他那宣使乘的紫藤兜轿稳。”这明系是陈抟叮嘱党继恩的内容,既然是有圣旨来请,就该快速下山,乘车太慢了,那就驾白云吧。元刊本他剧也多存此等失照应处,这等问题实在是诸宫调的遗制。
在叙述方式上还表现在主唱(正末或正旦)在很多情况下是由剧中次要角色甚至是与剧情毫无关联的角色来完成。《元刊杂剧三十种》中此类情形依其目录次序就有第1、3、7、11、12、13 、16、17、20、21、26、27、30 等13种杂剧(几近元刊杂剧的半数,在明刊元杂剧中也很多)如此④。当然也有主唱者为正末或正旦的。这种演唱形式所隐含的正是诸宫调演唱体制的精神。如《关大王单刀会》中主角是关羽,而正末却扮演乔国老、司马徽;《汉高皇濯足气英布》中英布为主角,第四折探子扮正末;《薛仁贵衣锦还乡》中主角是薛仁贵,而正末先后扮演杜如晦、薛仁贵父亲和拔禾等;《陈季卿悟道竹叶舟》陈季卿为主人公始终是外末,全剧正末先后扮吕岩、列御寇和渔翁。
这种由其他角色主唱的形式是不符合“代言”之戏曲定义的,许多正末演唱的曲词非关角色自己,却是述说他人行藏。如《气英布》第四折探子扮正末,所唱为英布战霸王:
【醉花阴】楚汉争锋竞寰宇,楚项籍难赢敢输。此一阵不寻俗,英布谁知,据慷慨堪推举。
【喜迁莺】多应敢会兵书,没半霎儿,嗏,出马来熬翻楚霸王。他那壁古剌剌门旗开处,楚重瞳阵上高呼。无徒,杀人可恕,情理难容,相欺负,斯耻辱。他道我看伊不轻,我负你何辜。
【出对子】咱这壁先锋前部,会支分,能对付。床床床响飕飕阵上发金錊,唦唦唦各臻臻披(徐沁君校改为“坡”)前排士卒,呀呀呀扑剌剌的垓心里骤战驹。
【刮地风】咚咚咚不待的三声索凯(徐沁君据《盛世新声》等校改为“战”)鼓,火火火古剌剌两面旗舒,脱脱脱扑剌剌二马相交处,喊振天隅。我子见一来一去,不当不睹,两匹马两个人有如星注。使火尖枪的楚项羽,是他便刺胸脯。
【四门子】九江王那些儿英雄处,火出(徐沁君校改为“火尖枪”)轻轻早放过去,两员将各自寻门路。动彪躯抡巨毒,虚里着实,实里着虚,斯过谩各自依法度。虚里着实,实里着虚,呵,连天喊举。
【山(各本作水)仙子】分分分溅土雨,霭霭霭黑气黄云遮太虚。滕滕滕马荡动征尘,隐隐隐人盘在杀雾,吁吁吁马和人都气出。道吉丁丁火枪和斧笼罩着身躯,道足吕吕忽斧迎枪数番烟焰举,道坑察察着枪和斧万道霞光注,道斯郎郎郎断凯(《元曲选》作“铠”)甲落兜鍪。
【收尾】把那坐下征猛兜住,嗔忿忿气夯破胸脯,生掿损那柄黄烘烘簸箕来大金蘸斧。
此一折从口气、用词都可见到是说唱者口吻,且完全不必增加科白,情节已甚为明了,我想这也是元刊杂剧不刻宾白的主要原因。《元曲选》本《气英布》或以其不类戏曲,因于其后特续英布为正末几曲结尾。其他,如《单刀会》第二折正末扮司马徽唱,演述关羽的性情;《竹叶舟》第三折正末扮渔翁演述陈季卿与妻子久别见面时的絮絮叨叨;《薛仁贵》中正末扮薛仁贵父亲、扮拔禾述说薛仁贵成长,《火烧介子推》第四折樵夫为正末述说介子推之死等,皆无二致。可以说对于这些杂剧,若从主人公人物的形象塑造角度言,正末所扮的人物最多可为配角,这一人物充其量只是戏剧情节中的一个旁观者,发挥作用等于诸宫调的演述者。
综合考察,在元杂剧中正末扮谁,在剧情中角色主次的决定,与今天所理解的戏曲不同。角色特别是正末(旦)色的确定通常取决于谁更适合叙述故事情节的发展,更易于揭示、形容主人公的性格成长、事业发展轨迹或展现某一个场景,以及人物的成长、场景的展现,而非鉴于角色本身在剧中地位的主次。全不同于“正末主唱的,叫做‘末本,正旦主唱的,叫做‘旦本……这两种角色,都扮演主要人物”[10](P163)的说法。就此而言确同说唱文学。这也应该看做诸宫调的影响所致。以此传统的“正末主唱”的说法似应替代为“主唱者为正末”。
三、元杂剧题目、正名使用未规范
题目和正名是戏曲中元杂剧这一体裁特有的形式,特有的称呼,人们对何为题目何为正名、题目正名是一或是二、内容为何、位置居剧前或居剧后等多有讨论。通常看法:题目、正名是放在元杂剧剧本结束之后,多用四句或两个对偶句以概括全剧之剧情,末句四字或三字为本剧剧名(海军按:《杂剧选》本《谇范叔》题目为“须大夫轻谇范雎”正名“张相君大报冤仇”恰与常说颠倒)。这些讨论的立足点实际是将题目、正名作为元杂剧体制规范的一部分来看待,其实,也是一种先入为主的看法。客观地说,题目、正名在元杂剧中的使用尚未十分规范。
试观之《元刊杂剧三十种》,其中的题目、正名的使用确实很不规范。在三十种元刊杂剧中,有八种杂剧题目、正名及其内容皆无,如《关张双赴西蜀梦》、《闺怨佳人拜月亭》、《楚昭王疏者下船》、《泰华山陈抟高卧》、《张鼎智勘魔合罗》、《李太白贬夜郎》、《晋文公火烧介子推》、《范张鸡黍》等八种。仅有正名及内容的,有《诈妮子调风月》、《赵氏孤儿》、《诸宫调风月紫云亭》、《公孙汗衫记》、《严子陵垂钓七里滩》、《岳孔目借铁拐李还魂》等六种。仅有题目及内容的,有《关大王单刀会》、《马丹阳三度任疯子》、《萧何月夜追韩信》、《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等六种。题目、正名全有者有《好酒赵元遇上皇》、《散家财天赐老生儿》、《尉迟恭三夺槊》、《汉高皇濯足气英布》、《薛仁贵衣锦还乡》、《东窗事犯》、《霍光鬼谏》、《辅成王周公摄政》、《陈季卿悟道竹叶舟》、《诸葛亮博望烧屯》、《张千替杀妻》、《小张屠焚儿救母》等十二种。
以上四个数字使我们看到,不使用题目、正名的,几近元刊杂剧的三分之一,正名、题目使用不规范的,占元刊杂剧的三分之一,而题目、正名完全的,仅占元刊杂剧的三分之一略强。
从题目、正名的句子形式上看,元刊杂剧也非常杂乱。少者一句,如《看钱奴买冤家债主》题目“疏财汉典孝子顺孙”;多者八句,如《诸宫调风月紫云亭》正名将退场诗也刻在内:“象板银锣可意娘,玉鞭骄马画眉郎。两情迷到忘形处,落絮随风上下狂。灵春马适意为功名,韩楚兰守志待前程。小秀才琴书青琐帏,诸宫调风月紫云亭。”且元刊杂剧的题目和正名其内容多不加区分:如《散家财天赐老生儿》,其题目、正名连写一行,以下两联四句连写(《杂剧选》本《吕洞宾三度城南柳》,《阳春奏》本《陶学士醉写风光好》相同,可证元刊的非偶然性),难别何为题目何为正名。
这种句式的不整齐,题目、正名的连写,或者题目、正名或有或无等现象,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元杂剧创作与演出中或许题目、正名未必皆备,如《闺怨佳人拜月亭》、《晋文公火烧介子推》等直接标明“散场”。即使备者也是十分随意,没有完全的讲究。这种情形在臧懋循以前的明刊或明抄本的元杂剧中还依然如故。如《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录于小谷本的《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好酒赵元遇上皇》,《古名家》本的《感天动地窦娥冤》、《迷青琐倩女离魂》等,皆是题目、正名不分。只是到了《元曲选》所选杂剧中,题目、正名方是每剧皆备,且句式比较讲究修饰,基本是两句或四句,再无一句或八句的现象,用词也力图整齐对仗。题目与正名的内容及先后次序,也才区分得十分清楚。往往前为题目后为正名,这大概是选曲者给予题目、正名的关注,所以对题目、正名的内容形式特别给予了一定程度修饰的原因,只是这不可以作为论元杂剧的依据。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笔者认为,今日所云元杂剧之规范或说人们对元杂剧之认识,实际上有很多问题。求是地说,要认识元杂剧体制,甚至元杂剧内容的真实面貌,《元刊杂剧三十种》是应当得到正视和重视的。《元刊杂剧三十种》不仅具有文献价值,还具有一定意义上的文物价值,较文字记载更当具备有客观性。
参 考 文 献
[1]王国维. 王国维戏曲论文集[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2]李春祥. 元杂剧史稿[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
[3]邓绍基. 元代文学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4]田同旭. 元杂剧通论[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
[5]幺书仪. 戏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6]李日星. 元杂剧“折”的本意与起始[M]. 文献,2003,(2).
[7]钟嗣成. 录鬼簿[A].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C].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
[8]邾经. 青楼集序[A]. 夏庭芝. 青楼集笺注[C].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
[9]郑振铎. 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雍熙乐府》本《西厢记》题记[A]. 郑振铎文集[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10]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杜桂萍]
On the Original Form of Zaju in Yuan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uankan Zaju
DU Hai-jun
(School of Literatur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irty Types of Yuankan Zaju is the earliest selection of zaju so far and also the earliest opera selection. It keeps the most original system, content, and version information of zaju, which shows that the non-standard form of dividing zaju into zhe, the non-standard form of the name of zaju and the influence by all kinds of Gongdiao. According to standard of opera, some zaju can not reach the standard mentioned in opera history.
Key words: Thirty Types of Yuankan Zaju; zhe; chu; non-standard form of the name of zaju; kinds of Gongd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