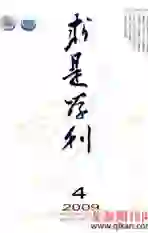试论现代文学发生期的语言嬗变与话剧创生
2009-08-04张艳华
摘要:中国现代话剧是伴随着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兴起而诞生的,是在对传统旧戏和文明戏的强力扫荡中登场的。由于早期的创作者既对剧本的“文学性”缺乏重视,又对演出的“舞台性”关注不够,导致了问题剧的渐被冷落以及观剧者的严重流失。为改变这种状况,后起的创作者开始了对话剧语言形式的各种探索,从注重“说什么”到关注“怎么说”,并注意从传统戏曲及西方现代剧中吸收养料。尽管这种探索既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但浪漫剧和现代剧的出现,无疑丰富了早期剧坛,开拓了话剧的表现领域。
关键词:白话文运动; 写实剧; 浪漫剧; 现代剧
作者简介: 张艳华(1963— ),女,山东滨州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文学在20世纪的语言选择”,项目编号:05JA750.11-44015
中图分类号:I207.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4-0092-08收稿日期:2008-08-01
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文学在20世纪初期开始了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是以语言的彻底置换为前提的:从文言到白话,新文学创造者拥有了新的感受及描述世界的思维方式、审美眼光和生命体验,在此基础上,势必引发一场旨在打破传统积淀以承载现代意识的文体革新运动。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种文体中,戏剧的变革最为突出:五四前夕,根深蒂固的旧戏与自甘堕落的文明戏所代表的戏剧文化现状令新文学倡导者深恶痛绝,他们认为这两者都无法担当起建设新文化、重塑新国民的历史重任,当务之急是引进先进的现代西洋戏剧观念,从剧本的编写入手建设中国的戏剧文学。在他们看来,西洋戏剧的长处在于其认识教育功能,它用写实的手法、自然的言语贴近万象人生,将现实生活逼真地再现出来,让观者犹如身临其境、进而感同身受,以达到启迪思想、净化心灵的目的。相比之下,中国的戏曲文化现代意识匮乏,与真实人生隔膜,凭借其虚假而僵化的表演方式培养了一代代只知赏玩娱乐、不知思考进取的“戏迷”。因此,“要建设西洋式的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底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1](P163)。出于这样一种信念,新文学倡导者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抨击旧戏和文明戏,另一方面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开始了对西洋现代话剧的输入。
作为一种“舶来”的文学艺术样式,话剧引进国门之初是经过了一个由翻译到模仿再到创造的过程的,这一成长轨迹在《新青年》上可窥见一斑。自1915年第1卷开始,《新青年》便不定期地刊登西洋话剧的翻译作品,而翻译最多的是英国王尔德的作品,如薛琪瑛女士所译的《意中人》、陈嘏所译的《弗罗连斯》、沈性仁所译的《遗扇记》等。从这些译作可以看出,初期的台词还是半文半白的,有些地方甚至是“双语并用”的:剧中的人物对话用的是白话,而作者的舞台提示则使用文言。以刘半农在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2号上所译的《天明》(P.L.Wilde著)为例:
……
男:唉!好老婆,我比皇帝多开心了!(行至炉旁)我回来了,你喜欢么?
女:那自然,迪克。
男:还是喜欢点儿的好!(脱去上衣,掷之案上。就坐,向外伸两足,以足尖点地,妇未之见)
这种现象在早期的翻译剧本中是十分常见的。尽管如此,钱玄同在该剧最后的附言中,对刘半农所翻译的人物对话甚至现代标点符号的采用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文字里的符号,是最不可少的。在小说和戏剧里,符号之用尤大;有些地方,用了符号,很能传神;改为文字,便索然寡味:像本篇中‘什么东西?如改为‘汝试观之此何物耶? ‘迪克?如改为‘汝殆迪克乎?‘我说不相干!如改为‘以予思之实与汝无涉。又像‘好—好—好一个丈夫!如不用‘—、—符号,则必于句下加注曰:‘医生言时甚愤,用力跌宕而去之。‘先生!他是我的丈夫!如不用‘!符号,则必于句下加注曰:‘言时声音凄惨,令人不忍卒听。或再加一恶滥套语曰:‘如三更鹃泣,巫峡猿啼。——如其这样做法,岂非全失说话的神气吗?”[2]通过比较,白话的简洁自然与文言的烦冗矫情一目了然。
《新青年》 1918年第4卷第6号推出了一期易卜生剧作翻译专号,刊登了《娜拉》、《国民之敌》、《小爱友夫》等剧,同时还发表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自此,易卜生的写实“问题剧”渐受国人关注。何以中国现代话剧的倡导者们偏偏选中易卜生的写实剧呢?很显然,这是由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所决定的。胡适说过:“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官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3]如果说胡适看重的是易卜生毫不粉饰的写实手法给予社会的冲击力,那么鲁迅推崇的则是易卜生敢于挑战社会、不屈不挠的人格魅力:“何以大家偏要选出Ibsen来呢?……因为要建设西洋式的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底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先以实例来刺激天下读书人的直感:这自然都确当的。但我想,也还因为Ibsen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那时的绍介者,恐怕是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现在细看墓碣,还可以觉到悲凉,然而意气是壮盛的。”[1](P163)正是这种易卜生精神,契合了处于社会新旧交替、急于从封建势力束缚下挣脱出来、急于追赶世界进步思想潮流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态,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此,从古典主义桎梏中走出来的中国戏剧选择了易卜生,选择了现实主义,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民初的中国社会,处处充满了“问题”:女子解放问题、贞操问题、礼教问题、教育改良问题、婚姻问题、父子问题……面对种种社会问题,易卜生的“问题剧” 无疑提供了最好的摹本。胡适不但在理论上倡导“易卜生主义”,认为“最重要的,以‘问题剧来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4],而且在实践上身体力行,在1919年《新青年》上发表了仿照易卜生的《娜拉》创作的剧本《终身大事》,标志着中国话剧迈出了剧本创作的第一步。“胡适的这样推崇易卜生主义,对于后来中国话剧的发展,影响是非常广大的。易卜生的戏剧,很快地有许多被译成中文;而在创作方面,有若干的作家,不仅是把易卜生剧中的思想,甚而连故事讲出的形式,一齐都摹仿了。”[5](P20)
继《终身大事》之后,“问题剧”的尝试者日益增多,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创作模式。应当看到,“问题剧”的特点并不在文体上,而在题材上,它是新文学倡导者秉承人道主义精神,承担社会改造使命的启蒙理性的反映。欧阳予倩说:“盖戏剧者,社会之雏形,而思想之影像也……一剧本之作用,必能代表一种社会或发挥一种思想,以解决人生之难题,转移误谬之思潮。”[6]洪深说:“现代话剧的重要,有价值,就是因为有主义。对于世故人情的了解与批评,对于人生的哲学,对于行为的攻击或赞成——凡是好的剧本,总是能够教导人们的。”[7]而闻一多后来则是以检讨的姿态回顾了这一现象:“第一次认识戏剧既是从思想方面认识的,而第一次的印象又永远是有威权的,所以这先入为主的‘思想便在我们脑经里,成了戏剧的灵魂。”[8](P55)反映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揭露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不良现象,以期达到教育国人、改造社会的功利目的,这是五四话剧首先关注的方面;至于戏剧的艺术价值,则相对来说被忽视了,“它们的目的是宣传,以戏剧为工具,它的艺术价值是无暇顾到的”[9]。这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下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现实主义戏剧潮流在中国绵延了几十年,其贡献与缺憾是并存的。在后来的发展历程中不断有人试图加以匡正、纠偏、提升,但始终没有彻底取代它的主流位置。
我们知道,易卜生的戏剧语言也经过了一个由诗体剧向散文剧的转变过程。他曾说:“诗体剧的形式给戏剧艺术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害。我本人在过去七八年几乎未写过一句诗, 而是用一种极为简单的、现实的真实语言从事创作, 这是一种十分困难的艺术。诗体剧的形式在最近的将来会被抛弃, 因为它与未来的创作意图水火不相容, 它将衰落下去。”[10]他解释说, 现实主义戏剧应该“写成尽可能接近现实的形式”,要制造“现实的幻觉,要在读者心中引起这样的印象:他所看到的, 在生活中确有其事”。“如果我用诗写,就跟我的意图, 跟我自己规定的任务背道而驰。”[10](P27)中国戏剧语言的嬗变轨迹与易卜生戏剧语言的转变历程有某些相似之处:传统戏曲的语言以不自然的韵白与唱词为主,由于远离实际生活而为话剧倡导者所唾弃。为了给观众制造逼真的现实幻觉,就必须运用自然而生活化的语言,如洪深所说:“写剧就是将剧中人说的话, 客观地记录下来。”[7]而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为建立散文剧的体式和采用口语化的对白奠定了基础:“白话散文用在现代‘写实剧里自然合式,因为内容和形式是一致谐和的,现实的人说现实的白话——现代的人说现代的话。”[11]
话剧是一种直接诉诸观者视觉与听觉的立体的艺术形式,要打动观众,使其感同身受,主要靠语言与动作。但五四时期创作的剧本,大都语言铺排较多,动作性却不强,对于舞台性的一面关注不够,对于人物性格的刻画也缺乏力度。过于重视功利目的的结果,往往把戏剧当成了教育的“工具”,人物成了某种概念的传声筒。写实剧本最常见的一种情形是:在关键之处,借角色之口直陈某种“思想”,以表达剧作者的立场。如陈大悲的《幽兰女士》,主人公幽兰在最后发出这样的呼喊:“我不能自杀!我不能自杀!缺乏了勇气的人才会自杀!我要奋斗!奋斗是我们青年的天职!一天不死,就得奋斗一天!我从黑暗中奋斗出光明来!从强权中奋斗出真理来!有志的青年,应当报答社会的恩!报答人类底恩!”陈大悲剧中的人物在做派上带有文明戏的遗风,像幽兰的这番呼喊,就与剧情有些游离,带有一种宣传鼓动的意味。洪深在探究早期文明戏受欢迎的原因时说:“在一个政治和社会大变动之后,人民正是极愿听指导,极愿受训练的时候。他们走入剧场里,不只是看戏,并且喜欢多晓得一点新的事实,多听见一点新的议论。”[5](P14)同样,在五四那个百废待兴、畅言革命的时代,文化启蒙者试图将他们的“精英意识”借助话剧语言这一媒介教育民众,所以形成了那种“教诲”式、讲演式的言语方式。
对于“话剧”,洪深是这样界定的:“话剧, 是用那成片段的, 剧中人的谈话, 所组成的戏剧(这类谈话术语叫做对话)……凡预备登场的话剧, 其事实情节, 人物个性, 空气情调, 意义问题等一切, 统须间接的借剧中人在台上的对话, 传达出来的。话剧的生命, 就是对话。”[7]没有了歌舞音乐,对白成为话剧的核心因素,剧情的展开,动作的推动,个性的展现,内心的表露,都要靠人物的语言去实施。能否成功地驾驭“对话”,成为剧本成败的关键。初期的话剧作品大都语言缺少加工,用意过于直白,人物缺乏性格。具体到作者个人,由于人生阅历与知识素养的不同,作者的语言功力也是各不相同的:陈大悲、汪仲贤熟悉城市市民阶层的生活,因而他们剧中人物的语言具有浓郁的市民气息;胡适、丁西林拥有较为优裕的身份地位,因而他们剧中人物的语言处处流露着贵族气质与文人智慧;至于田汉、欧阳予倩剧中散发出的乡土气息,蒲伯英、熊佛西剧中含有的讽刺味道,以及侯曜、濮舜卿剧中弥漫着的学生腔调……都表现了开创期的话剧作者在语言运用上所初显的个人风格,这其中最有特色的当推丁西林。
与其他写实派剧作家不同,丁西林的剧作尽管也是写实的,但并不着力描写民生的苦难与新旧的冲突,他的剧情往往因人性的流露而透着温情,人物因对话的机智而显得知性。在激越沉郁的悲剧时代氛围中,能以达观幽默的喜剧心态面对世相百态的,丁西林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作于1923年的《一只马蜂》,是丁西林的处女作。剧中的吉先生与余小姐不得不利用“说反话”、“说谎”互相表达爱慕之情,人物的机智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得淋漓尽致:
余:喔,一个人可以随便说谎吗?
吉:自然不能“随便”。不过我们处在这个不自然的社会里面,不应该问的话,人家要问,可以讲的话,我们不能讲,所以只有说谎的一个方法,可以把许多丑事遮盖起来。
……
吉:……说谎,说得好的人很多,不过我最佩服的是你。
余:我向来不说谎,你说我说谎,你有什么证据?
吉:对呀! 所以佩服你的缘故,就是因为拿不出证据来。
赵景深曾这样评价说:“在五四以后不久,看到好几种初期的通俗剧和闹剧,浅显易晓,忽然看到丁西林的《一只马蜂》,便觉得突出同侪,耳目为之一新。”[12](P47)乔羽十分赞赏丁西林的喜剧风格,他这样评价此剧:“明明是颇费匠心的经营,却又出之自然,自然到象生活本身那样;明明是极为谨严的笔墨,却又那样游刃有余,挥洒自如。”[13]与初期话剧作品语言的稚拙和青涩相比,丁西林驾驭话剧语言要熟练而老道得多。他的剧作尽管数量不多,却起点颇高、引人瞩目。如果说闹剧主要靠人物夸张的外在形体取悦观众,那么喜剧则主要以睿智的人物语言征服观众,可以说丁西林的喜剧为中国话剧语言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话剧从西洋舶来之初,实践者主要致力于“仿制”,即从戏剧体式到戏剧精神都着力模仿西洋剧。尽管异域之苗移入中土难免先天不足,但是对于民族文化的虚无态度,使他们不屑于从传统戏曲中吸取营养;白话文学的提倡使他们迫切想尝试走白话新剧的道路,但同初期的新诗一样,剧作者只注意了白话的实用价值,却忽视了白话的审美功能,以为把生活中的口语直接搬上舞台就是话剧,却没有意识到剧本毕竟是一种文学体裁,它需要将生活中的日常白话升华、提炼,进而带给人以美的享受。由效仿西剧所形成的话剧语言的欧化特点,限制了话剧的受众范围;而缺乏美感的口语化台词,也为旧戏的捍卫者攻击白话剧留下口实。于是,一些继起的话剧实践者开始思考话剧的民族化问题,开始从本体角度关注话剧语言的内在价值。借用田本相评价曹禺剧作时所说的话:“戏剧语言的转化,是最深刻、最细微、最内在地体现着对外来戏剧形式的把握,也意味着朝话剧民族化的创造性转化。”[14](P92)
杨振声的《中国语言与中国戏剧》一文,开始重视汉语的特性与话剧的民族化问题。他说,“要增进戏剧介体的功能,你只能在中国语言的本身想法子,绝对不能求助于外援的。然则我们讲起中国戏剧,不能不注意于中国的语言了。语言与戏剧关系最切的,要算是语言的个性了”;“我们不敢说不同的语言就会发生不同的文学;我们却不能不说不同的语言会发生文学上不同的表现”。汉语是个性鲜明的语言,“我们不能不承认它在介绍欧洲文学上有相当的阻力,可是也不能不承认它这阻力正是防止中国的文学纯粹欧化的一道长堤”。他认为,“惟其语言有个性,然后我们的文学才有个性,文学有个性,然后才配得上在世界文学上占个地位”;“总之中国语言的特性,造成中国文学的特性”[15](P111-116)。从语言角度探讨戏剧的发展,是杨振声高于他人之处。的确,中国的话剧要想闯出一条新路,就要尽早摆脱模仿的痕迹,努力建造自己的话剧体制,培养独有的艺术个性。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不从语言上下工夫。筚路蓝缕、跋涉前行的五四话剧,经历了无数次舞台实践的挫折之后,写实问题剧逐渐进入低迷状态。这时,被洪深称为“从文学走向戏剧”的田汉、郭沫若等人,以带有文人浪漫气质的话剧作品,给剧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洪深评价说:“在那时他们虽也写作戏剧,但目的似乎注重在给人家阅读,而并不是准备自己实演给人家看的。”但是,“这是无害于他们的功绩的。在那个年代,戏剧在中国,还没有被一般人视为文学的一部门。自从田、郭等写出了他们底那样富有诗意的词句美丽的戏剧,即不在舞台上演出,也可供人们当做小说诗歌一样捧在书房里诵读,而后戏剧在文学上的地位,总算是固定建立了”[5](P44,45,48)。应当说,田、郭的剧本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是与他们对汉语诗性特征的挖掘及对戏剧诗化传统的借鉴分不开的。
田本相曾经说过,“话剧与诗的结合,或者说话剧诗化的美学倾向,是‘五四话剧在艺术上的最突出的特色”,这一特色由田汉及郭沫若所开创,“一方面表现出他们开放的艺术精神,一方面把民族的艺术精神、民族戏曲的质素融入其中”[16]。的确,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艺术的精华是诗,由诗而词,由词而曲,戏曲不过是诗的衍化物,因此郭沫若说:“诗是文学的本质,小说和戏剧是诗的分化。”[17](P223)他还形象地比喻说:“小说和戏剧中如果没有诗,等于是啤酒和荷兰水走掉了气,等于是没有灵魂的木乃伊。”[18](P6)同五四初期倡导西洋剧、鄙视传统戏曲的新文学诸先贤不同,田汉和郭沫若在接受外来戏剧的同时,对传统戏曲并不排斥。田汉曾说:“我不否认欧洲形式对我们的巨大影响,但我主要是由传统戏曲吸引到戏剧世界的,也从传统戏曲得到很多的学习。”[19]郭沫若由作诗到写剧,最初影响尽管来自西洋诗剧(如歌德的影响),但后来传统戏曲给他的启发也是不容忽视的:“西洋的诗剧,据我看来,恐怕是很值得考虑的一种文学形式,对话都用韵文表现,实在是太不自然……我觉得元代杂剧,和以后的中国戏曲,唱与白分开,唱用韵文以抒情,白用散文以叙事,比之纯用韵文的西洋诗剧似乎是较近情理的。”[20](P66)因此,对早期创作的《棠棣之花》等诗剧作品,他评价说:“这些与其说是剧,不如说是诗。”而对《卓文君》、《王昭君》等话剧作品,他自认为“它们比较具备有一些戏剧的风格,虽然渐渐在从歌德的影响下脱离, 但是文言的桎梏并未十分解脱, 而且很鲜明的又有易卜生和王尔德的摹仿”[21](P118)。可以说,田、郭自觉地将西洋戏剧与中国戏曲结合起来,努力吸收各自的精华所在,摒弃各自的陈规陋习,试图创造既有世界意识、又有民族风范的戏剧文学。至于郭剧中“文言的桎梏”,也可以看出一种对传统难以割舍的情感:或许是由历史剧创作的特点使然,或许是作者为使语言雅化、诗化而有意为之。
陆炜在《试论戏剧文体》一文中,曾将戏剧语言的四个要素“动作性”、“口语化”、“个性化”、“诗化”进行了阐发:“动作性之必要”因为它“是戏剧语言最根本的性质。判断一句语言是否具有动作性,看这句话是否具有改变现状——从移动物体到改变人的心情、改变人物关系,从任何角度改变现状——的意义。口语化的必要性,在于戏剧是演出的艺术,戏剧语言是有声的,要让观众当场听懂的语言,所以不仅人物的话,就是剧本中叙述性的话都要采用口头语言。个性化的必要性,在于戏剧的代言性质。诗化的必要性,在于戏剧是聚众观看的艺术,要使大批观众集中注意,激动、感动,就必须采用高于生活语言水准的语言。具有这四种性质的一段话,会让人感觉到它像戏剧语言”。他认为“戏剧语言的风貌就主要决定于它偏于诗化还是偏于口语化的程度”[22]。作为白话文学运动的成果之一,五四早期话剧抛弃了不自然的剧诗传统,在西洋写实戏剧的参照下,追求戏剧语言的通俗化、生活化,因此呈现为“偏于口语化” 的语言风貌。其优点是强化了话剧的真实性及现实感,缺点则是过于琐碎、直白,缺乏艺术的提炼,忽视了“诗化”这一要求,对语言审美层面的开掘远远不够。可以说,随着田汉、郭沫若的出现,这一缺憾得到了弥补。他们在审视戏曲传统的同时,借鉴了以言抒情的表达方式,以诗化的语言风貌,不仅为话剧寻找到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而且提升了话剧的文学价值。
田汉与郭沫若早期剧作中语言的诗化特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对白与独白。
在写实派戏剧中,对白的主要作用是传递信息(交代背景)、实现交际(推动剧情发展);而在浪漫派戏剧中,对白也可以成为饶有诗意的情感交流的纽带。田汉的早期作品尽管不乏写实描写,但在创作手法上更多地借鉴了浪漫派的抒情风格。
作于1921年的《获虎之夜》,被洪深誉为新文学在第一个十年收获的话剧作品中“最优秀的一个”,一波三折的戏剧构思,富有神秘色彩的猎虎故事,充满乡土气息的环境氛围,都表现出了作者高超的编剧才能。洪深评价说:“在题材的选择,在材料的处理,在个性的描写,在对话,在预期的舞台空气与效果,没有一样不是令人满意的。”[5](P51)在这部剧中,田汉一方面善于利用对话渲染人物处境,交代人物关系,铺垫人物命运,另一方面,也很热衷采用大段的独白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从中可以领略作者诗情澎湃的语言特色。如流浪儿黄大傻遭枪伤之后面对心上人所抒发的幽怨心声,就是一段带有诗意的语言:
少年:我寂寞得没有法子。每到太阳落了,山上的鸟儿都归到巢里去了的时候,便一个人慢慢的踱到这后面的山上来望这个屋子里的灯光,尤其是莲姑娘窗上的灯光,我一看了这窗上的灯光,好像我还是五六年前在爹爹妈妈膝下做幸福的孩子,每天到这边山上来喊莲妹出来同顽,我拼命摘些山花给莲妹戴的时候一样,真不知道多么欢喜,多么安慰!尤其是落霏霏细雨的晚上,那窗上的灯光远远望起来越显得朦朦胧胧的,又好像秋天里我捉得许多荧火虫儿,莲妹把它装在蛋壳里一样,真是好看……
我们在欣赏田汉剧作的语言所带给我们美感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在塑造人物性格方面所具有的缺憾:田汉有时因过于追求语言的唯美和诗情而使他的人物都带上了“小资”的情调。如从侍女、流浪儿这样的人物口中说出那样带有诗意葱茏的话语,就显得不够真实。有时人物独白过长,那种滔滔不绝的恣意抒情显然也是违背舞台演出要求的。
创造社同人有个共同的信念,那便是郁达夫所说的:“我们更想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23]这里的“真”,更多的是情感的真挚;这里的“美”,更多的是词句的华美。同田汉一样,郭沫若的剧作也常利用对白或独白展示他浪漫的诗情。作为新诗的领军人物,郭沫若的语言很能表现他自由不拘的个性;而作为一个同样深受古典诗词浸濡的文人,郭沫若的语言又能表现得优美而富有节奏。以《卓文君》为例,卓文君与丫鬟红箫深夜等候司马相如琴声的时候就有一段诗意充沛的对话:
文(君):你听,不是琴音吗?
红(箫):……不是,是风吹得竹叶儿玲珑呢。
文:是从下方来的。
红:……是水摇得月影儿叮咚呢。
文:是从远方来的。
红:……不是,不是,甚么音息也没有呢。啼饥的鸮声也没有,吠月的犬声也没有。
这样的对话,不仅富有诗的韵律和乐感,而且烘托出诗的意境和情调,把卓文君思念司马相如那恍惚而急切的心情表现得摇曳生姿。
白话文学兴起之初,倡导者对白话本身的缺点是有清醒认识的。俞平伯曾经感叹白话作诗的艰难:“我总时时感用现今白话做诗的苦痛”,因为它“缺乏美术的培养”,“有干枯浅露的毛病”[24]。傅斯年也曾深感用白话写散文的不易:“现在我们使用白话做文,第一件感觉苦痛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国语,异常质直,异常干枯”,“我们使用的白话,仍然是浑身赤条条的,没有美术的培养”[25]。以对话为主的话剧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同样的缺点,所以杨振声甚至呼吁中国需要诗剧,希望借助白话诗的成功来改革话剧的缺憾:“对话戏又在初探,说的语言,内容不丰富,又太没有相当的训练了,将来能美丽说的语言,同时又对于对话戏有帮助的,一定是白话诗。”[15](P117)为改善白话的贫弱与不足,五四初期新文学力倡走“欧化”之路,但“新文艺的实质和社会的嗜好不能调和”,“东西语言太远”[24](P355),因此,随着五四退潮期的到来,新文学“民族化”的回归趋势便在所难免了,这一点在话剧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诗、散文、小说的受众是个体行为,戏剧的受众却主要是群体行为,“你在说中国话的听众之前表演,要得他们充分的赏识,你就不能不用纯粹的中国语言为介体”[15](P111),因此话剧民族化是一条不得不走的道路。而且,从文人本身来说,再偏激的反传统态度也不可能完全割断与传统千丝万缕的“血缘”联系。就像田本相所概括的那样:“这种改变也并非偶然,恰好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文化西方戏剧的矛盾心理。他们出自一种理性批判精神否定传统文化传统戏曲,然而在骨子里却依恋着传统的东西,这种‘情结是颇难割舍的。”[14](P154)“中国人对外来话剧艺术的认识和把握,由潜在的审美精神到表层的艺术形式手段,都带着民族的审美眼光,为其固有的民族审美意识所支配,这几乎是一个天然的审视角度。”[14](P111)话剧语言诗意的回归,既是对剧诗传统的寻觅,也是对汉语诗性魅力的彰显。从关注外部世界的真实反映,到注重内心世界的真情流露,田、郭的作品开拓了话剧的表现领域,增添了浓厚的文人情调,增强了话剧的文学底蕴。
五四初期激进、昂扬的时代氛围,决定了早期中国话剧对易卜生一派的选择。在剧本创作中,无论是现实题材的,还是历史题材的;无论是写实的,还是浪漫的,都或多或少可以看到易卜生剧中人的影子。但在五四那个对外来思潮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时代风气影响下,兼有写实手法与现代派风格的剧作者不在少数。
随着五四退潮期的到来,新文学呈现出一种低迷、消沉的氛围。“我们自有文学革新运动以来,已有四五年了。其初,也颇有些新鲜气象,到了四五年后的今日,早已暮气深沉,日渐衰运。一种萎靡不振的空气重重地压在方兴未艾的新文坛上。”“新文学的兴衰,实在与新思想是相关连的,而现在的思想界是消沉极了。”[26]对现实的失望,使易卜生昂扬进取的写实“问题剧”由热趋冷,而理想的幻灭,则使充满“世纪末”苦味的现代派剧作受到推崇。“心理之得以具象化”是现代派惯常采用的手法,而表现派那种“支离灭裂的表现”尤其能打动试图尝试新路的中国现代话剧创作者。一时间,出现了一批郁达夫所说的“不以事件、性格或观念的展开为目的”,“专欲暗示一种情念的葛滕或情调的流动”[27](P39)的心理抒情剧。 就像时人所说的那样:“近代人底心里,尤其有一种说不出的幽忧哀怨;要传达出这种隐微底消息,势不能不用神秘象征底笔法;先把读者拉到空灵缥渺底境界,使他们尤沉醉战慄底片刻之内,得到极深切的感应。而且把所有惯习、权威、理想、信仰,一切破坏,进于虚无之境;喧嚣的议论,切实的行为,早已没有;最后归着底地方,就是梅特林克(Maeterlinck)所谓‘沉默,只剩下一种幽忧哀怨底情调罢了。但是近代人心最深的意义,正存在这个‘沉默里。到了这个境地,向来底直接经验,全无用处,神秘底色彩,超自然底材料,便成为必不可缺的了。”[28]象征、神秘、心灵的外化,成为中国现代派剧作尝试者的主要手段。他们的剧作格调大都是沉郁的、压抑的,语言是反逻辑的、情绪化的,甚至是神经质的,从中可以感觉到人物意识的流动与心理的纠结。
洪深的《赵阎王》,是较早尝试现代派手法的一部作品。他一方面用易卜生批判现实的精神揭露和控诉了旧军队的黑暗现实(他曾说过他写这个剧本的初衷缘于一起在直奉战争中受伤士兵被活埋的真实惨剧,心灵受到刺激的他试图用话剧形式加以反映);另一方面,他又借鉴美国表现派剧作家奥尼尔的《琼斯皇》手法,展现了主人公赵大(人称“赵阎王”)“灵肉交战”直至沉沦的悲剧下场。《赵阎王》得以搬上舞台,主要得益于洪深本人的表演及导演才能。但是,上演这种过于“前卫”的、带有现代派风格的话剧,在那个时代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这次表演的结果,对大多数观众是失败的。”当时的报纸评论说:“前夜实演时,观者颇不明瞭,甚至有谓此人系有精神病者。”[5](P61)尽管该剧的失败是注定的,但作者对现代派创作手法的借鉴还是有益的。
洪深的心理剧仍是以写实精神为依托的,故而人物的独白看似胡言乱语,意识跳跃不定,却仍有着清晰的逻辑脉络可寻。相比之下,一些受现代派影响更深,走得更远的剧作者,则以他们的尝试展现了现代派剧作更为光怪陆离的“另类”风格。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真正称得上“现代派”的剧作者寥寥无几,且集中活跃在20世纪20年代。研究者一般将陶晶孙、向培良、高长虹等人的某些作品归入此类。
作为创造社一员的陶晶孙,代表作是《黑衣人》和《尼庵》。这两部作品明显地带有表现派、象征派戏剧观念的影响。陶晶孙的作品给人的感受是格调黑暗而阴冷,人物偏执而病态,语言晦涩而沉郁。作者似乎对黑色情有独钟,不仅《黑衣人》中的哥哥一袭黑衣,而且《尼庵》中的兄长也是身着黑色僧衣,作者有意要从视觉上给人以压抑和沉闷之感。《黑衣人》中那萧瑟的秋风、寂寞的别墅、冰冷的湖水,一切都在预示着死神的降临。作为有精神病家族史的一员,哥哥对自己的现实人生感到绝望:“啊,我受了伤的灵魂哟……(哽咽欲哭)我可诉与谁人呢?”他想反抗,却看不清对手;他爱弟弟,却在神志错乱之中亲手将其杀死。“死神来了。不然,我自己便是死神!我的肉体是死了的。我自从成了绝对的黑色,死是已经入了我的魂髓了。”作者以“黑衣人”的悲剧性结局,说明了社会的没有出路,表达了对“现实之苛酷”的愤懑。同样,《尼庵》中那崎岖的山路,孤独的庵堂,萧萧的落叶,也处处给人以寂寥苦闷的感觉。冒充僧人的兄长前来看望出家为尼的妹妹,但是妹妹拒绝相见。原来兄妹曾经相恋,为斩断情缘,避开纷扰的情事,妹妹躲到庵堂里,谁知兄长执意邀妹妹逃走,妹妹最终投湖自尽。“啊,死是高贵,死是华美,同生一样的程度!”“我是在这世间上没有生存的目的的人哟”……对兄妹之间畸形恋的描写,对死的憧憬与赞颂,都使该剧带有浓重的颓废情绪和唯美风格。陶晶孙的作品没有什么故事情节,似乎只为表达某种情绪,大段意识流的独白毫不顾及舞台演出的要求,不但缺乏思想深度,而且艺术含量也十分稀薄。
中国的现代派剧作家似乎特别钟情于“病者”,“病”成为一种意象,是孤独、受伤、悲苦的象征。向培良的《沉闷的戏剧》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剧集。“这个集子里面,只充满着疲倦,忿怒,爱之牺牲,迷惘矛盾,性底苦闷,以及所追求着的理想底破灭。”[29]在《生的留恋与死的诱惑》一剧中,主人公“病者”这样感叹道:“我从前好像不羁的野马,在平原中奔驰。那时候,我是生的力,能动的力,跳跃的力。我们的生活是奋斗,我的事业是破坏:我想要创造一些炸弹似的雷电似的东西,我曾经是光荣同希望的对象,后来我却被打倒了”,因为这事业“究竟不是民众所能了解的”。在《冬天》与《暗嫩》中,作者同样表达了“寒冷、黑暗而且残酷”的冬天对青春生命扼杀、窒息的绝望心情以及对“美”从孜孜追求到理想幻灭的痛苦历程。
与上述剧作相比,高长虹的《一个神秘的悲剧》现代派的味道更浓一些。此剧写于1926年,受表现派戏剧的影响,全剧带有荒诞色彩与神秘意味,出场人物只用大写英文字母ABCDE表示,抽象化、符号化特点十分明显。该剧一共分九幕,剧中人物A是先生,BCD是他的学生,E则是他的女儿。学生们追随先生,先生自己却理想幻灭,最终死去。该剧只有人物梦呓般的对白,没有性格的刻画与行动的展示。就像时人评价梅特林克的剧本语言“对话和人物也都是叙情诗的,不自然的”[28]一样,《一个神秘的悲剧》对白中的言语同样与日常用语拉开了距离:
C: 祝福我们,一个新的战士将要来到了!
D: 我相信我只能看见一个尸体!
C: 一个更强的新的战士,他会比我们能干到一千倍。
D: 我还没有知道过世间有更强的那么个东西。
C: 当太阳走近白云的身边的时候,白云会变做红霞,那将要来到的,便是我们的太阳。
D: 但是什么是我们呢?
C: 那些看见我们便要跑掉的敌人,到他来的时候,他们将要像那广袤的冰洋,但是,在热带上,你不会看见他们的一点影子。
……
高长虹的语言欧化的痕迹十分明显,这特别表现在他的舞台提示语中,喜用叠床架屋的长定语,是他的一个语言特色。其实,呓语般的、晦涩的言语表达,正是为了表现剧中人或剧作者本人曲折隐秘的精神世界,因而也是现代派剧作家所追求的风格。
余上沅曾将以表现派为代表的现代戏剧称为“最年轻的戏剧”,认为它是作为写实派的反动而出现的进步的戏剧思潮:“现实的生活,把它描写出来已经不够了,已经不够艺术家充分发挥他们的意象。”认为现代派戏剧是主观的戏剧、个人的戏剧,它不求为别人所理解,但求自我心灵的释放[30]。现代主义戏剧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一度受到青睐,反映了启蒙理想陷入低谷之际,一些看不到前途的知识者对社会现实所产生的悲观情绪。他们咀嚼着个人的悲哀,经受着灵魂的煎熬,试图以形式的花样翻新和语言的扭曲变形,发泄自己隐秘的内心世界,发掘话剧多样的表现可能。他们的探索精神是不应一概抹杀的,但是当时的中国缺乏现代戏剧生存的土壤,那些表现灵肉挣扎的梦呓般的人物语言无法引起广大民众的共鸣,人们需要的不是这种远离实际生活的虚幻作品。因此,现代派戏剧受到冷落也是必然的结果。
参 考 文 献
[1]鲁迅. 鲁迅《奔流》编校后记[A]. 鲁迅全集,第7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钱玄同. 天明·附言[J]. 新青年,第4卷,(2).
[3]胡适. 易卜生主义[J]. 新青年,第4卷,(6).
[4]胡适.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J]. 新青年,第4卷,(4).
[5]洪深. 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M]. 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6]欧阳予倩. 予之戏剧改良观[J]. 新青年,第5卷,(4).
[7]洪深. 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J]. 现代戏剧,第1卷,(1).
[8]闻一多. 戏剧的歧途[A]. 余上沅编. 国剧运动[C]. 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本.
[9]顾仲彝. 中国新剧运动的命运[J]. 新月月刊,第4卷,(1).
[10]奥托·布拉姆, 亨利克·易卜生[A]. 易卜生评论集[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11]余上沅. 历史剧的语言[J]. 新月月刊,第4卷,(3).
[12]赵景深. 文坛忆旧[M]. 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本.
[13]乔羽. 橄榄——读《压迫》札记[J]. 剧本,1957,(9).
[14]田本相. 现当代戏剧论[M].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
[15]杨振声. 中国语言与中国戏剧[A]. 余上沅编. 国剧运动[C]. 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本.
[16]田本相. 继承和发扬话剧的宝贵传统[J]. 光明日报,2007-04-06.
[17]郭沫若. 文学的本质[A]. 沫若文集,第10卷[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18]郭沫若. 诗歌国防[A]. 沫若文集,第2卷[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19]田汉. 答《小剧本》读者问[J]. 小剧本,1959,(7).
[20]郭沫若. 创造十年[A]. 沫若文集,第7卷[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21]郭沫若. 作剧经验[A]. 王锦厚等编. 郭沫若佚文集,下册[C].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8.
[22]陆炜.试论戏剧文体[J]. 文艺理论研究,2001,(6).
[23]郁达夫. 《创造社》宣言[J]. 中华新报,创造日,(1).1923-07-21.
[24]俞平伯. 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A].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C]. 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25]傅斯年. 怎样做白话文[A].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C].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26]郑伯奇. 国民文学论[J]. 创造周报,第33号,1923-12-23.
[27]郁达夫. 戏剧论[M].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28]昔尘. 现代文学上底新浪漫主义[J]. 东方杂志,第17卷,(12).
[29]王光东. 美的诱惑与变异——中国新文学中的唯美主义[J]. 东岳论丛,1997, (6).
[30]余上沅. 最年轻的戏剧[J]. 新月月刊,创刊号.
[责任编辑杜桂萍]
On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Drama in the Formation Period of Modern Literature
ZHANG Yan-hu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01, China)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Drama originates with movement of writing in the vernacular of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it comes onto the stage by smashing tradition drama and civil drama. Due to the lack of attention to literariness of drama of some early dramatists, and that of “stageableness”, problem drama is neglected and audience is less and less. In order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later dramatists begin explorations into the language of drama, paying attention not to “what to say” but to “how to say”. They also learn from traditional opera and western modern drama. The appearance of romantic drama and modern drama enriches the stage and enlarges the representation area of drama in spite of some failure.
Key words: movement of writing in the vernacular; reality drama; romantic drama; modern dra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