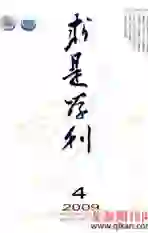现代东北文学中的俄罗斯人形象
2009-08-04金钢
金 钢
摘要:现代东北文学中出现了众多的俄罗斯人形象,东北作家们对俄罗斯人形象的描摹,一方面显示了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历史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俄罗斯文化对现代东北文学的深刻影响,为现代东北文学增添了几许异国风味,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生活在东北这块黑土地上的人们所演绎的独特的社会人生景观。现代东北文学中的俄罗斯人形象反映了近代以来东北地区战乱频仍的历史现实和多元文化杂糅、儒家文化传统薄弱的文化状态。
关键词:现代东北文学;俄罗斯人形象;地域文化
作者简介: 金钢(1978—),男,黑龙江绥化人,文学博士,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2008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现代东北文学与俄罗斯文化”,项目编号:08C056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4-0100-07收稿日期:2008-06-10
在现代东北作家的作品中,真实地表现和描绘了广泛出现于东北地区各个生活领域中众多的俄罗斯人形象,并且由形象展现出俄罗斯人的性格及积淀于其中的丰富文化内涵。就作品中出现的俄罗斯人形象之多、描绘之普遍而言,东北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没有其他地域的文学可与其相提并论。归纳和分析现代东北文学中的俄罗斯人形象,不但可以了解俄罗斯文化对现代东北文学的深刻影响,而且能够更好地认识现代东北文学自身。
一、俄罗斯人形象的类型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俄国侨民构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此之前,活动于这里的俄罗斯侨民主要是中东铁路工作人员及其眷属,以及一些商人和传教士等。而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大批从俄国逃亡的白军和难民涌入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北地区,俄罗斯侨民的数量达到了高峰期,许多人在这块土地上滞留了相当一段时期后才陆续散去,还有一少部分俄罗斯人在这里生根、终老、留下后代。流落于异乡的生活总是充满了苦痛,来到东北的俄罗斯人大多有着悲惨的命运。或许正因为他们这悲惨的命运,在现代东北文学中,俄罗斯人较少被当做侵略者、殖民者看待,更多地被视为流亡者,与基本是反面角色的日本人不同,俄罗斯人似乎能够与本土的人们更好地相处。
骆宾基在《混沌初开》中描写的故乡边境小城就接纳了这些被“赶出国来”的俄罗斯人。小主人公“我”去看“老毛子”,看到的是“有山羊眼睛的俄国孩子”、“眼睛全是琥珀色或是蓝色的”男人和女人,他们衣着破乱、脸上脏污、饥饿不堪,显露出逃亡的苦涩和艰辛。大部分流亡的俄国士兵、平民、破落贵族的生活都比较困苦,其中不少人沦为了乞丐。阿成的散文《洋乞丐》中写道:“洋乞丐也是早年哈尔滨城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景观。”文中描写了一个俄国老乞丐,“战争使他的手指都不全了,但他却能灵活地演奏手风琴,几根手指像小松鼠一样在琴盘上跳来跳去。我很熟悉他所演奏的每一首曲子,像《瓦夏瓦夏,好瓦夏》,像《黑龙江的波浪》等等……这个俄国乞丐的样子像一个圣诞老人,有一双迷惘的灰眼睛。许许多多的老哈尔滨人都认识他,甚至把他当成哈尔滨街头固定的一景,当成朋友了,见了面,也像洋人那样,摘一下帽子向他致敬,说‘得拉斯基(你好)”[1](P7)。如作家所说,这个俄国老乞丐是一处“耐人寻味”的风景,被战争摧残了肉体、赶出了家园的老人,在异乡的街头靠拉琴乞讨度日,虽然他拉得充满激情,虽然他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但是他的眼神中却有掩饰不住的“迷惘”。
在现代东北文学中的俄罗斯人形象里,俄罗斯女性形象可说是最为丰富多姿的一类。她们那异族的美丽、多情放浪的性格,善良、勤劳而又勇敢的品质,她们在东北地区的现实生活、多舛的命运,为现代东北文学增添了一抹奇异的色彩。朱媞的短篇小说《大黑龙江的忧郁》演出了一场人生的悲剧,卢丽的母亲亚娜年轻时被一个中国人诱惑,离开了她的爱人来到中国,十几年后,这个中国人死掉了,同族的攻讦迫使这个“异族血系的女人”带着16岁的卢丽离开了这个家族,在黑龙江的江轮上,她又遇到了她从前的爱人莫托夫,莫托夫与卢丽父女相认,但亚娜终究不能原谅自己,投江自尽了。杨利民、王立纯合著的《北方故事》中描写了一个颇具魅力的俄罗斯姑娘叶莲娜,她“那白皙的皮肤,金色的头发,挺秀的鼻子,深凹的浅蓝色眼睛”,“掺杂在人群里,有一种扎眼的漂亮,那么暴露,那么逼人”,显示了一种“无法融合”又楚楚可怜的异类的美。她苦难的身世与遭遇,她的美丽、善良、勤劳,无不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她充满了同情和喜爱。她与金铁匠、二江的婚姻爱情交织着浪漫与凄美的情愫。可悲的是,她和她深爱的二江都没能逃过日寇的屠杀,她带着她唯一的奶牛在草地上采花的时候,被日寇罪恶的子弹击中,永久地融入了这块土地。这一异常美丽的生命的陨灭,也是对日寇罪恶的血泪控诉。
现代东北文学中的俄罗斯人大多属于社会下层的弱势群体,他们流落到东北地区,就像一群迷途的羔羊,尝尽了人生的辛酸。对这一群异族人的描摹,从侧面折射出东北作家们的创作意绪。舒群的短篇小说《无国籍的人们》描写了“我”在狱中所见到的白俄穆果夫宁以及两个穷苦的俄国儿童果里和力士的形象。穆果夫宁时常独自唱道:“白云下,/有我的祖国,/有我的家。//风雨中,/有我的一颗心,/有我的一朵花。//花落了,/心伤了,/在这天涯”,“这种悲哀的调子,常常打动我的心,使我记起了一些悲哀的回忆”[2](P298-299)。对于家园沦丧、处于政治与文化边缘的东北作家们,尤其是那一群流亡作家来说,对这些俄罗斯人的关注和描写,有一种同命相连的意味在其中。这个俄罗斯人的孤独、内省、愤世嫉俗,其心灵负载的不堪忍受的感伤,都在去国离乡的历史背景上得到表现,极易在东北沦陷后的时空中激起读者的共鸣。
这些俄罗斯人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滞留在东北,他们中的一部分在这里留下了后代,这是一群血统和文化的混血儿。在现代东北文学中,也有对他们的这些混血儿的关注。在阿成的作品中,对这些混血儿的关注尤多。长篇小说《马尸的冬雨》中,有众多的混血儿形象:邮递员达尼、小胡木匠、电车司机果力……他们每个人的身世都是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短篇小说《间谍》、《马兹阔夫生平》,中篇小说《闲话》等篇什中也有对混血儿形象的描写。
此外,在现代东北文学中还有对苏联人,主要是苏联军人的描写。舒群的短篇小说《舰上》记述了“我”和战友马斌元与苏联士兵苏斯洛夫的友谊。这个短篇通过“我”这个江防海军的视角叙写出东北地区那几十年政局的变化及与苏联的关系,作家的创作倾向是明显的,把苏联作为一个善良、宽厚而又强大的朋友,表达了对红色苏联的亲近和向往。苏斯洛夫的形象就是苏联的象征,战舰取名“红星”更是暗喻了苏联的红色政权。
二、俄罗斯人形象的性格特征
乞丐、妇女、混血儿是现代东北文学中的俄罗斯人形象里比较突出的三类,从对这些异族血统的人的描写来看,他们的生存状况大多很艰难,东北人对他们虽然有嘲弄、排斥的一面,但主要还是显示出了一种同情的态度,能够包容他们的存在,与这些异族人和谐相处。这一方面是因为这块曾经荒凉的土地本身就是由无数移民者共同开发的,这使得生活于此处的人们对外来者具有先天的同情心;另一方面,地理位置的毗邻使东北人对俄罗斯人较为熟悉,一部分东北人还到过俄国,例如《第三代》中的林荣曾在俄国闯荡多年,《混沌初开》中“我”的父亲也曾闯过崴子(海参崴),而且自然环境的相似也使得俄罗斯人与东北人的性格中具有某些可以沟通的层面,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便指出了自然环境对精神状态的重要影响。在现代东北文学中,对俄罗斯人的性格特征也有多方面的表现。而这些俄罗斯人的性格,也或多或少地融入了东北人的性格之中,给东北人的性格中加入了一些斯拉夫民族的因素。
在极北苦寒的自然环境中,酒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北方人喜欢饮酒是人们的一个共识,俄罗斯人的好酒更是举世闻名。俄罗斯人喜欢烈性酒,把白酒称做“伏特加”,“伏特加”一词是对水的爱称,含有“心爱的水”之意,足见他们对白酒的偏爱。对滞留在东北地区的俄罗斯人来说,酒不仅可以驱寒,而且是一种精神麻醉剂,可以稍稍减缓一点流亡异乡的内心苦痛。爵青的短篇小说《哈尔滨》中描写道:“一个喝得舌根都硬了的白俄摆过来,向窗橱里深深地看了一眼,长叹了一声,又用破皮鞋在水门汀上怏怏地走了过去。穆麦心里想:这个棕色的异国流浪者,也许还怀念着莫斯科的豪华的往日,也许悲伤着自己流亡的忧郁和离开温柔的家的情景,可是这大都市的存在,就连这么一个人的简单的需要和安慰都不能给他吗?”[3](P1490)流浪是现代东北文学中俄罗斯人形象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原本拥有的家庭和社会财富等由于种种原因而失去了,这种流浪的无根状态促使他们更加借酒浇愁、及时行乐。而寄居他域异乡的俄罗斯流亡者这种非正常生活状态中的醉态苦情,有时反倒更浓烈地流露出了作者对家园沦陷、民族危亡的忧患意识。
在现代东北文学中,俄罗斯人不仅喜欢饮酒,而且似乎善于开酒馆,俄国酒馆是现代东北文学中一个很突出的意象。萧军的短篇小说《下等人》里“一个跛了脚的退伍的铁路工人”开了一个“地窖酒馆”,“他是一个高加索人,在一九一四年,他参加过欧洲大战。因为他杀了他的长官,他逃到了西伯利亚,又逃到×××”。这里是“下等人”们经常聚集的地方,在这里每人喝一杯“唔德克”(俄国下级劳动者常饮的酒名),吃几片肠子,便是疲惫的精神和身体的“酬报和慰安”。这些酒馆大多是比较低档的,是普通劳动者聚集的地方,现代东北文学中也有对“华梅西餐厅”等高级俄式餐馆的描写,但远不如这些小酒馆那么热闹、那么有生气。这些小酒馆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劳动者、流亡者休闲、发泄的场所,在严寒的自然环境和严酷的社会环境中,酒精既给予了他们短暂的身体舒展和精神放松,也促进了他们之间的彼此交流,从而生发出一个个曲折悲凉的故事,这些故事真切地表现了活动于此处的流亡者与本地人的生存境况和精神状态。从时间段来看,这些故事大多发生于俄国十月革命到东北解放之间。在这一时期里,流亡的俄罗斯人处于无国籍状态,而东北地区的政局则是跌宕起伏、战乱频仍。经历了日俄战争的东北地区,又相继落入了军阀、日伪的黑暗统治之中,东北地区的人民“就像麦草似的被这些杀人的滚子辗来辗去”[4](P292)。东北人民的生活与这些流亡的俄罗斯人一样处于危难之中,朝不保夕,酒这种麻醉剂也是他们聊以自慰的良药,于是好酒也就变成了东北人的性格特色之一,而酒馆也成为文学作品中事件的多发场所。
在很多人看来,俄罗斯人的情爱观是较为自由随意的,不像中国人有那么多礼法的约束,与西方文化的情爱观更为接近。有人说西方文化是“性文化”,东方(尤其中国)文化是“食文化”,此论虽然偏颇,却也有一定的道理。在两性关系方面,俄罗斯人要比东北人开放得多。在现代东北文学中,对这些滞留在东北地区的俄罗斯人的情爱纠葛也有较多的描述。《第三代》中的佛民娜对赫列斯达可夫似乎存在着“一种不能够和解似的憎恶”,说:“我一小就不喜欢兵,不喜欢乞丐,不喜欢那些不靠自己的力量赚面包的人。我的父亲第一句话教训我的就是:‘不靠自己手脚挣面包吃的人,是人类中最卑贱的臭虫!他们不是上帝创造的属于人类的真正的子孙!他是个兵,又自吹是个贵族,他就是个不靠自己的手脚挣面包吃的那种人……”[4](P591)可是慢慢的这种憎恶发生了转变,赫列斯达可夫的花言巧语打动了她,她竟然抛弃了林荣,置两个孩子的情感于不顾,委身于这个“流氓、乞丐、不靠自己的劳力挣面包吃的卑贱的臭虫”,这从东方人的情爱观出发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而对佛民娜这个生活于异国他乡的俄罗斯女人来说,虽然家庭的温暖让她难以舍弃,但离乡的苦楚、民族的差异和对性爱的自由观念使她无法抵挡她的同族人赫列斯达可夫的诱惑,失身于他,从而造成了她与林荣的决裂。
不过,俄罗斯人的情爱观并不都是那样随意的,也有一些人物形象表现出了对爱情的坚贞不渝。《马尸的冬雨》中的小胡木匠是一个流亡到马尸的俄国寡妇与一个姓胡的中国木匠所生,在小胡木匠长到十岁的时候,老胡木匠突然不辞而别了。不久,大家知道老胡木匠在他的山东老家还有一个老婆和两个儿子,而且他的两个儿子都很大了。从关里闯关东的男人,在关东找一个女人“结婚”,组成一个临时的家庭,在当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那个俄国女人认为,“这个厚道的中国老人回自己的老家去看望原配的老伴儿,就说明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小胡木匠的母亲坚信,那个中国老人也一定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她每天的清晨和傍晚,无论风霜雨雪,都要去马尸那条通往外地的大路口那儿张望。十几年后,一个大雪之夜后的清晨,老胡木匠终于回到了她的身边。这个俄罗斯贵族女人的坚持获得了回报,她的“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在现代东北文学中,这些流亡的俄罗斯人的情爱故事与他们的流亡生活、与他们周围的人们紧密结合在一起。事实上,作家们对这些异国人形象的描写不可能是任意的,这些形象承载了许多信息,无论是放荡还是坚贞都只是表象,在其深层体现出来的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此处人们的深远的人生悲凉。从对娜达莎的放荡生活的描写来看,作家所持的并不是批判的笔调,而是蕴涵着深深的同情与悲悯。在东北这块苦寒之地,冬季非常漫长,且滴水成冰,哈气成霜,自然生存条件十分恶劣。生活在这里的大量的移民和侨民,都有很强的生命意识,加之儒家文化土壤的贫瘠使他们对俄罗斯人自由的情爱观并没有过多的苛责,而是宽容的理解和接纳。在这些东北作家的笔下,道德礼法的批判已经退居次席,对艰难的生存环境中人物的生命意识,情感的丰富性、复杂性的透视占据主位,进而勾勒出了一幅幅富有地域风情的人生画卷。
在这种艰难的生存环境中,流亡到这里的俄罗斯人所表现出来的勤劳与善良、乐观与勇敢、骄傲与自尊也成为东北作家们所着力渲染的一个部分。欢快地唱着歌、跳着舞、拉着手风琴的俄罗斯人给多灾多难的、沉重的东北大地带来了鲜活跳跃的生命律动。《第三代》中的林青就表达出了对手风琴声的赞赏:“我是在听那些琴!它们比我的胡琴要好多了!我的胡琴它只会使我伤心,这琴……它却让人有力量……”[4](P576)阿成的散文《洋乞丐》中那个俄国老乞丐“从不像中国乞丐那样,向行人伸出一截枯干的手臂,说:‘可怜可怜我吧……”,他一声不吱,不管有没有行人,有无施舍,总是“充满激情,充满活力,像一个小伙子”一样拉着琴,这场景让人感动。
杨利民、王立纯合著的长篇小说《北方故事》中的俄罗斯姑娘叶莲娜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她一出场便以“她奇异的美貌”震动了整个放马营,而她这异族的美丽中却蕴涵着多灾多难的身世。她的苦难经历与俄国的政治变动和现代东北地区的战乱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她的父亲是邓尼金部队的士兵,十月革命的风暴摧毁了一个腐朽的政权,也把她恬静的童年生活打破了。他们全家逃往东北,父亲在渡河的时候溺水而死,她和妈妈流落到哈尔滨。妈妈在异乡生病使她们背上了高利贷,债主要把叶莲娜卖到桃花巷去,正好被金铁匠遇到搭救下来。为了报答金铁匠的搭救之恩,叶莲娜硬跟着金铁匠来到放马营,做了他的女人。叶莲娜一来,金铁匠的生活便焕然一新了。在叶莲娜的张罗下,金铁匠的铁匠炉旁又修了个面包炉,接着又修了房子,两个人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金铁匠虽然年老,但忠厚善良,可以看出,这时的叶莲娜是幸福而又快乐的。然而这幸福是短暂的,命运再一次苛待了这个美丽的姑娘,金铁匠被翻倒的牛车压伤,变成了残废。在这个时候,一直暗恋叶莲娜的二江走进了她的生活,他不顾母亲的反对和乡亲的嘲讽,和叶莲娜结成了夫妻,与金铁匠一起经营起一个拉帮套式的家庭。在经历了起初的冷眼之后,叶莲娜的勤劳和善良、健康的美貌打动了洪嫂的心,也赢得了乡亲们的喜爱。事实证明,她和二江的结合是洪家三兄弟中最为幸福的一对,而另两对洪嫂极力撮合的婚姻却充满了苦涩。
值得一提的是,在现代东北文学中,有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诗歌等小篇幅的作品专门描写了俄罗斯人形象,而在长篇小说中,俄罗斯人形象大多是作为点缀和陪衬出现的,描写较为简单,叶莲娜是少见的一个作为主要人物出现的俄罗斯人形象,作家倾尽笔力把这位异族女性描写得异常生动美丽。这个形象的塑造根源于作家对本地域历史的深入观照和反思,小说题为《北方故事》,却有书写地域风情史诗的架构和野心,文中洪氏三兄弟分别代表了身为伪满官员的知识青年、生活在民间的普通农民、啸傲山林的侠义胡匪三种人群,而三个女性形象则代表了具有文化知识却又冲不破传统礼法的新女性、流亡东北的俄罗斯人和闯关东的关里人的后代,这六条线共同编织出一幅色彩斑斓、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展现出了从20世纪初到日伪统治那一段时间里东北地区的民俗风情和百姓的生存状态。叶莲娜作为流亡东北的俄罗斯人的代表,是认真考察那一段历史的作家必然要触及的人物形象,是绘制那巨幅历史画卷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颜色。而作家在描写这一形象时所表现出来的特有的偏爱,则显示了作家通过这一异族形象对那种善良、纯真、豁达、乐观而又坚强的民族性格的高扬,这种性格就像文中描写的矢车菊,它“抗冻,几场霜都打不死。它蓝得干干净净,开得遍地都是,就像被雨水擦过的星星那样”[5](P206)。
三、俄罗斯人形象的文化内涵
法国学者巴柔在他的论文《形象学理论研究:从文学史到诗学》中指出:历史和政治因素对于文学中的异国形象的形成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形象并不是,至少并非绝对是与当时的政治、历史及文化现实相吻合的,但它却和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6](P197)。可以肯定,现代东北文学中俄罗斯人形象的出现和丰富与东北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和政治变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上看,东北地区处于中国的边疆位置,与俄、日为邻,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从战略上讲是良好的后方基地和物资储备库,近代以来就是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以及之后的国共两党的必争之地。从帝俄入侵到日俄对峙,再到日伪全面控制东北,以及之后的国共战争,可以说东北地区从近代以来就弥漫在战火硝烟之中,甚至到建国后在边境上还有与苏联的军事摩擦。连年的战乱,受害最大的自然还是生活在这里的平民百姓,尤其是帝国主义之间争夺利益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更是只有灾难。东北作家们对这种罪恶的战争也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蔡天心的中篇小说《东北之谷》中的朱龙老丈清楚记得他21岁的时候,他和父亲住在山外一个叫松岗堡的村庄。“六七月,正落着暑雨的天气,俄大鼻子从北边反上来,不多久就和日本人打起仗来了。两下到处激战着,烧房子,杀人,奸淫妇女……他们的村庄,遭一夜炮火的洗劫便完全破灭:房子烧净了;人,死的死,流荡的流荡。”[7](P542-543)
日俄战争的失败也加速了沙皇俄国的覆灭,而帝俄的覆灭和苏联政权的建立使滞留在或流亡到东北地区的俄罗斯人的身份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他们也曾是侵略者,是殖民者,在他们的殖民地上过着闲适的生活,可转瞬之间他们就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亡者,就像萧红在她的散文《索非亚的愁苦》中所写的那样,“现在那骂着穷党的,他们做了‘穷党了”[8](P948)。也许此时这些俄罗斯人才能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给他们带来的伤害,在《第三代》中,林荣曾拍着他那条受伤的腿对佛民娜说:“我是一个中国人,却也为你们俄国流过血了……”佛民娜的回答可说是真正的人民的声音:“你的血和那个流氓的腿全是应该到俄国的沙皇那里去报功,他会赏你们的。你们打仗是为了沙皇,并不是为了俄国的人民。我知道,俄国的人民从来也不需要这样的战争的……”[4](P591)佛民娜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俄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也抱着深切的恨,这说明作家在处理俄罗斯人形象时是将他们放置在与东北人民同样的受害者一边。纵观现代东北文学,其中的俄罗斯人形象大多被处理成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处理成可以与东北人民友好共处的朋友,这与日俄战争中俄国的失败和之后日寇控制东北地区时期对俄罗斯人的迫害有着密切的联系。
当年曾目睹日军暴行的万斯白(Amleto Vespa)在其著述中写道,“从俄国革命爆发后,整千整万的俄国人逃难到满洲,他们到了那里是一律遇之宾客以礼的。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三二年间,没有一天不是一大批一大批的俄国难民逃到满洲的。不管他们中间是有护照的或没有护照的,犯罪的或守法的,一律都受到热忱的招待,个个都帮着他们安置下来了”。然而“日寇到后不上几个星期,成千成千的俄国难民逃出满洲,又有成千成千的下了牢狱,成百成百的给枪杀或谋杀了。事实上又有成百成百的俄国女孩子给日军奸淫了。和中国人交易而得来的钱财产业转到日本人的手里去了”[9](P22)。俄国的政治变革使这些俄罗斯人流亡到东北,幸运的是这里有东北人热情而又宽容地接纳他们,但日寇的入侵把这块流亡地的生活也击得粉碎,不堪忍受的他们不得不经历再一次的流亡,这种流亡的心境与那些流亡的东北作家又何其相似!日寇的入侵和奴化统治使东北人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和民族独立性,变成了阶下囚,大批东北的仁人志士流亡关内。“从异乡奔向异乡”,既是这些流亡的俄罗斯人,又是流亡的东北人的真实写照。东北作家对这些俄罗斯人形象的描写既反映了这些异族流亡者的生存现实,也从侧面反映了东北地区的社会状况和人民的苦难生活。这些俄罗斯人形象的悲伤和忧郁也弥漫到东北文学之中,与存在于现代东北文学中的那种广大的忧郁融合在一起,东北这块土地的沦陷以及这块土地上人民的屈辱和苦难的记忆是每一个东北作家都不能忘却的。
从历史文化的发展来看,东北地区也处在中国文化的边缘,在中国文化的版图上缺少自己独立的位置。王富仁先生认为:我们可以从尘封的历史资料上找到许多东北出身的文人,找到他们创作的许多作品,但这些文人及其作品却只是关内文化的复制品,他们没有体现出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独立的生活体验和精神特征,没有把他们的独立的世界感受、人生感受、审美体验注入到中国文化的精神之中去。能征善战的满族人进了关,成了中国社会的统治者,但他们的文化却丢失在关外那块广袤的土地上。他们在关内学会了温文尔雅,学会了忠孝节义,学会了讲“道”论“理”,但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他们在东北大地上自然形成的世界感受、人生感受和审美体验,这样一个剽悍的民族当面对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的时候,不但早已失去了征服汉民族政权时候的剽悍的力量,甚至连直面西方列强的勇气也丧失了[10]。可以说,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后的东北文化陷入了一种邯郸学步的尴尬。虽然将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软弱归罪于满族人有失偏颇,但对于东北文化来说,民族性格弱化的同时却没有积累起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种儒家文化传统的贫瘠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是使东北文化更具有包容性和可塑性,更容易接纳外来文化;人民的性格较为豪爽旷达、不拘礼法,更注重生命的自然状态。从现代东北文学中对俄罗斯人形象的塑造来看,这些异族人大都能和本地人友好相处,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自由的情爱观等也为东北人所接受,而没有引起过多的反感或指责。《马尸的冬雨》中的流亡者们来到“中国的小西伯利亚”,当地的政府允许他们在那片荒无人烟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园,而且不收一切赋税,让他们在这里安静而自由地生活。《北方故事》中的叶莲娜与金铁匠和二江结成拉帮套式的家庭,这丝毫没有影响乡亲们对她的喜爱。当他们面对洪嫂的时候,叶莲娜说:“这不怨二江,都是我不好,是我勾引他的!”二江则说:“是我心甘情愿的!”围观的乡亲们都“认为他们很仗义”。金铁匠的话可说是从人性的角度对封建礼教的反驳:“我和叶莲娜根本就不配,这谁都能看出来,她嫁给我为的是报恩;其实她和二江一见面就互相爱上了。是二江救了我的命,他要是不救我呢?他和叶莲娜就是快快乐乐的一对了,可他救了我,还愿意拉扯着我这个瘫巴活下去。我……我咋就觉不出来他下做呢?我看他都够高尚的了!”[5](P131)当无话可说的洪嫂让他们“糊涂着过”的时候,金铁匠则针锋相对地说:“这事儿我可是一点儿都不糊涂!”对这种拉帮套的生活方式来说,能糊涂着过已属不易,这里的“不糊涂”标示着这种民间淳朴的是非观对封建礼教的胜利。这块土地上人们的宽容和善良让叶莲娜深深爱上了这里,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
而从消极的方面看,文化底蕴的不足,缺乏理性思维的能力和习惯,决定了东北文化更容易接受那些表层的物质技术层面的文化,而对高层次的精神方面的文化则不敏感,缺乏理性的文化思考能力和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东北地区民众的性格也存在着懒惰、贪图物质利益、不思进取、玩世不恭、缺乏自尊心等缺陷。而现代东北文学中俄罗斯人形象的描写,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对这些缺陷的反讽作用。俄罗斯人形象所表现出来的勤劳、自尊和虔诚的信仰是很多东北人所缺少的。《洋乞丐》中的俄国老乞丐不像中国乞丐那样伸手乞讨,而总是充满激情地拉着手风琴,虽然身为乞丐,却不失风度和自尊。在《第三代》中,萧军通过那个断腿的俄国兵之口讽刺了中国士兵:“做那样一些灰老鼠似的中国兵吗?就是那些像流氓、土匪,把皮带斜在肩头上,或者提拎在手里,满街跑,坐马车、坐人力车……全不给钱的中国兵吗?”显然,家园沦陷的东北作家对这些旧中国的士兵是怀着蔑视和愤恨的。这些旧的社会制度的武装机器是民族劣根性的集中代表。在阿成的作品中,经常会描写到教堂的钟声,作家认为这钟声意味着爱、仁慈与和平,具有永恒的魅力。不过这钟声并不能真正进入生活于此处的中国人的心灵。在《马尸的冬雨》中作家写道:“遗憾的是,生活在流亡地马尸的少数中国人,到教堂做礼拜的,却寥寥无几。偶尔有三两个中国人探头探脑地走进去,那不过是出于对洋教堂的好奇心而已。——中国人的好奇心,在世界上可居榜首。”面对庄严而又神圣的教堂,中国人没有忏悔和祈祷,而只是表现出看热闹式的好奇,“探头探脑”地看西洋景,而没有敬畏,这都说明了生活于此处的中国人对精神信仰的冷漠,他们更关注的是那种实用的、物质方面的文化。
另外,从混血儿这种独特的人物形象来看,本地文化底蕴的薄弱让他们很难找到文化归属感。他们已经远离了俄罗斯文化中心,却很少能真正地从精神层面融入到本地文化之中。混血儿是一类颇有意味的文学形象,他们的出现本身就与那一时期的历史文化状况密切相关,他们的身世中大多包含着战乱和流亡。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都有一种不确定性,在两种文化背景的血脉之间摇摆,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阿成的短篇小说《马兹阔夫生平》就叙写了混血儿马兹阔夫一生的故事,他的母亲是本地人,他的父亲是流亡到这里的俄国人。马兹阔夫的经历并无特异之处,但他的混血儿身份却使他不能确定自己的精神归属。文中东正教堂和极乐寺的描写象征着两种精神世界的分立,教堂是父亲国度的信仰,寺庙是母亲国度的信仰,而马兹阔夫自己的信仰又是什么呢?他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很多年,中苏边贸兴盛的时候,他也去过俄罗斯大地,然而这两块土地都没有留住这个混血儿,有人说他“去了澳大利亚”,或许那个移民的国度更适合他这个混血儿的生存。远离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向往,对大多数生活在东北的混血儿来说,他们在精神上更倾向于俄罗斯文化,而难以与本地文化真正融合在一起。虽然这些混血儿的身体里有一半中国人的血液,但在内心中却把俄罗斯当做他们的祖国。东北地区虽然有肥沃的自然土层,却没有深厚的文化土层使这些流亡者的后代扎下根来。在中国的版图上,东北一直是经济文化落后地区,虽然它以它的富饶和宽容成为战乱、饥荒年代人们的避难所,但是到了和平时期这些流亡者和他们的后代便大多返回他们的文化中心地区。
总之,俄罗斯人形象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了形象塑造者的影子,它是一种言说自我的表征。现代东北文学中的俄罗斯人形象反映了近代以来东北地区战乱频仍的历史现实和多元文化杂糅、儒家文化传统薄弱的文化状态。东北作家们对这种异国形象的塑造,主要不是对异国社会文化(缺席的客体)的表现,而是对本土社会状况(在场的主体)的表现。近代以来东北地区复杂多变的历史文化状况通过这些俄罗斯人形象可见一斑。法国学者巴柔认为:一个社会在审视和想象着“他者”的同时,也进行着自我审视和反思。毫无疑义,异国形象事实上同样能够说出对本土文化(审视者文化)有时难以感受、表述、想象到的某些东西。因而异国形象(被审视者文化)就能将未被明确说出、定义的,因此也就隶属于“意识形态”的各个“国别”的现实,置换为一种隐喻的形式[11](P156)。东北作家们对俄罗斯人形象的描摹,一方面显示了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历史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俄罗斯文化对现代东北文学的深刻影响,为现代东北文学增添了几许异国风味,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生活在东北这块黑土地上的人们所演绎的独特的社会人生景观。
参 考 文 献
[1]阿成. 哈尔滨人·洋乞丐[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2]舒群. 舒群文集(一)[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
[3]张毓茂主编. 东北现代文学大系·短篇小说卷,下卷[M]. 沈阳:沈阳出版社,1996.
[4]萧军. 第三代[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5]杨利民,王立纯. 北方故事[M].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
[6]孟华主编. 比较文学形象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7]张毓茂主编. 东北现代文学大系·中篇小说卷[M]. 沈阳:沈阳出版社,1996.
[8]萧红. 萧红全集[M].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
[9]万斯白. 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M]. 上海:国光印书馆,1945.
[10]王富仁. 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之二)[J]. 文艺争鸣,2003,(2).
[11]巴柔. 形象[A]. 孟华主编. 比较文学形象学[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杜桂萍]
Image of Russian in Modern North-Eastern Literature
JIN Gang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Heilong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18,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Russian images in modern north-eastern literature and these descriptions show Russian cultural influence on north-eastern literature due to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reasons since modern time, which adds some foreign flavor to the literature; on the other hand, it reflects the unique social panorama of people living on this land. Russian images demonstrate the cultural state which combines historical reality with successive wars and multi-cultural elements and in which Confucian cultural tradition is very weak.
Key words: modern north-eastern literature; Russian images; regional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