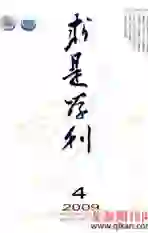游荡与现代性经验
2009-08-04汪民安
摘要:在本雅明的笔下,现代都市中的游荡者既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是现代性的观察者。游荡者漫无目的地在都市中游逛,行走在店铺林立的街头,穿梭于熙攘的人群中,欣赏着商品经济制造的琳琅满目的文化形象,但却脱离于现代都市生活的节奏。游荡者被现代都市生活所遗弃,但又深处都市生活的中心地带,以冷眼旁观的姿态观察着都市生活,他的视角是那些忙忙碌碌的都市男女所不具备的,正是这个视角使他能够洞悉都市生活的本质。
关键词:本雅明;游荡者;现代性
作者简介: 汪民安(1969—),男,湖北武汉人,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从事批评理论、后现代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565.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4-0022-06收稿日期:2009-03-18
或许,在本雅明的丰富遗产中,最有意思的是他的“游荡者”(flaneur)概念。在巴黎的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一个被步履匆匆的人群包裹的身影却在缓缓地徘徊,这个人在人群中既孤独又自在。这样一个经典形象就是游荡者的形象。这个游荡者的最初雏形是波德莱尔笔下的居伊——他是现代生活的画家,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是现代生活的观察家。居伊在巴黎街头忙忙碌碌,马不停蹄,充满激情,但是这种激情完全是观看的激情,他全神贯注地沉浸在自己的观看之中。“在任何闪动着光亮、回响着诗意、跃动着生命、震颤着音乐的地方滞留到最后。”[1](P483)并且,在芸芸众生之中,在反复无常和变动不居的生活场景中,他获得巨大的快乐。居伊寻找的和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现代性”。什么是现代性?“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现代性是被目击和体验到的,它是大都市的生活风格。现代性的目击者是个游荡者,这是本雅明的一个决定性经验。本雅明就是借助于游荡者来发现现代大都市的生活风格的。不过,游荡者是现代性的目击者,同时也是现代性的产物。
在一个什么意义上,游荡者是现代性的产物呢?游荡,并不是一个现代的概念,但是在大都市中游荡获得了自己的特殊表意。游荡是一个中介,将游荡者和城市结合起来,城市和游荡者位于游荡的两端,谁都不能甩掉对方。游荡者寄生于城市之中。只有在城市中,游荡者才能获得自己的意义和生存,同样,城市也只有在游荡者的眼中,才能展开自身的秘密。事实上,在乡村,到处都是游荡者,但是在空旷寂寥的乡村,游荡者被建构为唯一的中心形象。乡村是游荡者的背景,乡村并不是一个充满了技术的地理场所,它是一个自然景观,现代性还没有在乡村萌芽。乡村单调而且缺乏变化。乡村的游荡者并没有被丰富性培植出发达的视力,与其说他们将目光投身于周遭,不如说他们将目光投向于地平线的另外一端。在此,游荡的意义就在于游荡者本身,他的孑然一身,他的纯粹性在乡村的广袤旷野中勾勒了他的孤独。乡村的游荡者,将自己的背影淹没于无限之中。人们正是在这里发现了一种哲学人生,一种有限性和无限性暧昧交织的人生。游荡,通向了意义的无限。而集镇则天生是和游荡格格不入的,集镇如此之小,脚步刚刚启动,集镇就到了它的尽头。有限的集镇,埋没了游荡者的兴致,再也没有比集镇中的游荡更加乏味的了:没有兴奋,没有刺激,没有热情,重复,熟悉,单调。集镇是游荡者的坟墓,在这里,游荡总是和挑衅结盟,集镇中的游荡者无非是惹是生非的无赖:游荡者最终总是演变为一个滋事者。
本雅明敏锐地发现,只有大城市,才是游荡者的温床。他可以百看不厌。而巴黎是游荡的最佳去处。没有比巴黎更适于步行的城市了。本雅明初次来到巴黎就发现,巴黎更像是他曾失去的故园。这是他想象的都市。事实上,柏林对于本雅明与其说是一个喧嚣的大都市,不如说是一个静谧的乡村。本雅明关于柏林的童年回忆,总是自我的和内省的,并且总是在树丛和密林之中嗡嗡低语。而巴黎则更容易让人忘却自身,人们会陶醉于外在于自身的街道世界而心神涣散,正如观众在电影银幕前心神涣散一样。巴黎充分体现了街道的活力,这个活力既来自城市的构造本身,也来自街道上的人流,同样还来自巴黎街头的各种新式物品。在这个城市中,步行并不会令人们感到无聊和乏味,街道上一个店面接着一个店面,一个咖啡馆接着一个咖啡馆,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一个时尚接着一个时尚,没有丝毫的空隙,让人目不暇接。巴黎养育了游荡者,而游荡者也发现了巴黎。游荡者和巴黎相互创造,它们一体两面。只有在巴黎才能发现如此之多的游荡者,也只有游荡者才能发现如此之深邃的巴黎。因此,本雅明的拱廊计划不得不也是一种游荡者计划。只有借助于游荡者的目光和脚步,拱廊街的每一道褶皱才能悄悄地铺展开。
那么,这些游荡者是些什么人?游荡者通常是些无所事事的人,他们具有波西米亚人风格,居无定所,被偶然事件所决定,在小酒馆中充满醉意地打发时光,这是些密谋家、文人、妓女、赌徒、拾垃圾者、业余侦探。他们有相似的生活态度,“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模糊地反抗着社会,面对着飘忽不定的未来”。因为没有固定而紧张的职业,经常无所事事,但是,“他把悠闲表现为一种个性,是他对劳动分工把人变成片面技工的抗议”[2](P116)。在所有人都被现代社会职业化的时候,这些人就只能作为多余人出现了,他们并不跟着机器的节奏挥动手臂,而是在街头随意地迈动自己的双脚。这种游荡者溢出了社会分工的范畴,溢出了现代性的规范范畴。在这个意义上,游荡者既是现代性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性的抗议者。现代性锻造了游荡者来抵制自身。一旦放弃了城市机器的节奏,游荡者就有自己的特殊步伐,他喜欢“跟着乌龟的速度散步,如果他们能够随心所欲,社会进步就不得不来适应这种节奏了”[2](P116),有时候,他走走停停,完全没有效率和时间的概念。这同步履匆匆的过路人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泰勒主义的苛刻效率在现代社会取得了上风,游荡者,只要他在游荡,他就注定是要被现代性所排挤——他们注定是城市的剩余者。这就是游荡者的命运,这种命运也是他的诗意所在:游荡成为一个笼罩着其形象的光晕。
现代性正是被现代社会的格格不入者所打量——这些格格不入的游荡者使得自己从现代都市日益井然有序的生活风格中脱离出来,不过,这种脱离并不是归隐,归隐者与世隔绝,他闭上双眼,他厌倦了城市和人生。但是,游荡者慵懒的目光不乏警觉和好奇。他害怕孤独,因此一次次地置身于人群中。但是,为了躲避孤独而被抛进了人群的深渊使他变得更加孤独。游荡者并不是对城市本身的脱离,而是对金钱魔咒的脱离。游荡者并非不眷念生活,而是讨厌宰制现代生活的种种法则和秩序。所谓现代社会,按照西美尔的说法,不过是以金钱和数字为尺度来权衡的社会。为此,游荡者同所有以金钱为目标的人保持距离,并不时地报以冷漠的嘲讽。
他首先感受到的是瞬息万变。这转瞬即逝的现代生活有时候煽动了他的热情,有时候令他忧郁。新奇在刺激着他,令他眩晕,但一切又往事如烟,“没有任何慰藉可言”。这使他陷入忧郁。热情和忧郁交织于一身,游荡者本身就是一个辩证意象。一方面,他是对都市的摆脱,另一方面,他如此之深地卷入了都市。或者说,他和都市保持距离,恰恰是对都市的更进一步的探秘。反过来同样如此,游荡者深入到城市的内部,却是为了摆脱城市的控制节奏,就如同他总是在人群中晃荡但却总是为了和这些人群保持距离一样。现代都市存在着这样一个奇怪的悖论:在都市中安身的大众,却总是对这个城市视而不见,相反,被都市排斥的游荡者,却反倒能深入到这个城市的肌理之中。这正是布莱希特的“间离”效应:人只有摆脱自身的环境并同它保持距离,才能看清这一环境事实。这个游荡者正是一个使自己从城市中抽身而出的都市戏剧的“观众”。他置身于城市中,但并没有被这个城市吞没。正如布莱希特的理想观众,他在观戏,却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射于舞台。这样,闲逛者既是离城市最远的人,也是离城市最近的人:他既远离城市,又摸索在城市的层层晦涩之中。
本雅明发现了这个游荡者,正如这个游荡者发现了巴黎。这是双重的发现。本雅明通过游荡者的目光来发现历史,游荡者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本身。在这里,有一个双重的观看方式:对观看的观看。游荡者在观看巴黎,本雅明在观看游荡者。事实上,这再一次是布莱希特的方式:观众(游荡者)在观戏,而我们在看整个剧场。游荡者徘徊于其中的巴黎,构成了本雅明的史诗剧。对于本雅明来说,历史,一定要以一个活生生的戏剧的方式演出。本雅明是这个戏剧的撰稿人,他将主角和摄影师的双重角色分配给了游荡者,因为他的游手好闲,这个主角就成为现代主义舞台上的孤独英雄:他不仅指出了历史的真相,而且它本身就是真相。
因为不被大城市的机器节奏所控制,游荡者是漫游性的,他没有目标。他的步伐是偶然的,因此,他的目光可能停留在街道的任何一个角落,在此,时间似乎暂停了,游荡者驻足不前。游荡正是展现了滞留和运动的辩证法,或者说,运动总是以反复滞留的方式进行的。游荡,只有通过滞留才能发现它的真谛。正是借助于游逛,连续的空洞的时间打开了各种各样的缺口,时间总是以并置的空间的方式来展开,并由此形成了一个饱和而丰富的星座,而不是一串连贯而空洞的历史念珠。历史就此在空间的维度被爆破,也可以反过来说,空间的爆破不得不展现为历史的纷繁的此时此刻。滞留,意味着对“当下”而非未来的强调,而这正好符合本雅明的信念,“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不准研究未来的”,“他就建立了一个‘当下的现在概念。这个概念贯穿于整个救世主时代的种种微小事物之中”[3](P276)。微小事物是“当下”这个概念的必然归宿,正如游荡者的停滞的目光总是自然而然地飘至巴黎的细节上面一样。“在这个当下里,时间是静止而停顿的。”[3](P274)细节,具体之物,就是在这个静止的时间中,纷纷从历史的尘埃中被拖出来,它们以一种当下性暴露自身。在此,运动和前行搁浅了,细节和具体之物获得了自己的深度。这也迫使本雅明的行文充满着滞留感。在他的那些关于游荡者的著述中,读者的思路一再被打断,被分叉,被拐到了另外一个地点。人们在这些著作中总是弄得晕头转向。显然,这不是一个前进的坦途,而是一个四处播撒的纷繁场景,人们很难在这里抓住一个主干道,正如他笔下的游荡者没有一个明确的行踪路线一样。对于读者来说,埋头于本雅明的著作之中,犹如游逛者置身于繁复的巴黎一样。而要理解这些著作,就必须采用游荡者的视角,读者必须作为一个游荡者,在任何一个地方流连忘返,左盼右顾,而不是匆匆忙忙地要抵达一个最终的目标。唯有如此,人们方可以体验到其中的美妙和风光。那些希望在一般哲学推论的康庄大道上获得最终目标的读者,总是在本雅明这些纷乱的细节里遭受挫折,总体性的欲望迷失于碎片之中。不仅如此,本雅明的那些单个的句子同样要符合这种运动和静止的辩证法。“要理解本雅明,我们必须在他每个句子后面感觉到剧烈的震动转化为一种静止,实际上就是以一种滞留的观点来思考运动。”[3](P32)运动和滞留是相互依赖的,它们相互凭借对方而自我暴露。具体的意象就将运动和滞留囊括一身,有时候,它也将梦幻和现实囊括一身,这样的意象,就是本雅明所说的辩证意象。无论是巴黎,游荡者,还是本雅明的句子本身,都是如此。
游荡者的步伐因为被街道的细节所扰乱而停滞,但是,他还被人群所推搡而运动,运动和滞留在游荡者身上相碰撞。不过,这是另一个历史意义上的滞留:“这里既有被人群推来搡去的行人,也有要求保留一臂间隔的空间、不愿放弃悠闲绅士生活的闲逛者。让多数人去关心他们的日常事物吧!悠闲的人能沉溺于那种闲逛者的漫游,只要他本身已经无所归依。他在彻底悠闲的环境中如同在城市的喧嚣躁动中一样无所归依。”[2](P205-206)即便被运动的旋涡所携裹,回身和滞留的欲望仍旧强烈,游荡者并不愿意被人群携裹而去。这个人群,当然是匿名的大众,这也是19世纪的特有产物,个别的人居然形成了一种如森林般汇聚的人群,“市场经济的偶然性把他们聚集到一起——就像‘命运把一个‘种族再次聚集起来一样。而这些当事人则把这种偶然性加以合理化”[2](P127)。结果就是,人群没有任何怀疑地被市场的力量推动前行。大街上的聚集的人群缘自现代的生产和消费体制。除了游荡者敢于从这个市场化的人群中脱身之外,人们纷纷地涌到了这条不可逆转的历史的单向街上,这个单向街的标志就是现代性的进步,是纷纷扰扰的人们的坚定前行。但是,游荡者在抵制这个历史的单向街,这已经不单纯是对空洞时间的抵抗,它还包括着一种特殊的历史境遇的洞见:现代性的残垣断壁。回身,既要让单薄的时间绽开丰富而多样的缺口,也是个人抵御现代的姿态。这个姿态,正如舒勒姆写下的:“我的双翅已振作欲飞/我的心却徘徊不前。”当然,滞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左右为难的取舍。“沉沦在这个不光彩的世界里,被人群推来搡去,我就像一个饱经风霜的人:他的眼睛总是向后看,一眼看到岁月的底蕴,只看到幻灭和艰辛;在他前面也只有一如既往的狂风暴雨,既不能给出新的教训,也不会引起新的痛苦。”[2](P233-234)那么,就只好徘徊不前了。不过,这也驱除了启蒙者眼中对未来充满向往的神秘感。被人群推搡,这是个街道经验,也是个历史经验,或者说,历史经验现在就体现为一种街道经验。为什么不愿意被推搡着前行?那是因为,前方看到的是狂风暴雨,是越堆越高直逼天际的残垣断壁,历史的尽头,或许是一连串的灾难。这同样也是克利的新天使的形象,它被进步的风暴猛烈地刮向未来,尽管“他的脸朝着过去”,“想停下来唤醒死者”[3](P270)。这也是波德莱尔的形象,“流动的、具有自己灵魂的人群闪烁着令闲逛者感到眩惑的光芒,但这种光芒对于波德莱尔来说则显得越来越黯然”[2](P234)。
滞留终于有了它的理由,它是对灾难的警觉。事实上,运动、前行和进步最终是被幻灭这一目标所把控,不幸的是,这正好是现代的气质,所有的现代人都沿着这一虚幻目标前行,都彼此推搡着前行。现代,总是意味着要向前行。这种前行如此之快捷,这也意味着,此时此地的东西转瞬即逝。而本雅明清楚地发现了这一点,“现代性自身始终是过时的衰落,它在其强劲的开端中证明了自己崩溃的特点”。拱廊街刚一建成就被拆毁了。游荡者卷入人群中,“但完全是为了用轻蔑的一瞥把他们送进忘川”[2](P205)。“销魂的瞬间恰好是永别的时刻。”[2](P210)在巴黎的街头,陌生人频繁地偶遇,但在目光交接的一刹那,人们也彼此在对方的目光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瞬间的美妙总是淹没在人群的深处。所有这一切,用马克思的说法就是,“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尽管光怪陆离,但瞬间即逝,那些丰盛的物品的展示不过是废墟的频繁堆积。因此,对本雅明而言,滞留也是抵抗消逝的方式,它尽可能让瞬间获得短暂的永恒,尽可能让破碎之物有一个临时性的哪怕是不完满的缝合。当下,这是唯一能够抓住的东西;目光和脚步这类身体感官,也是唯一能够信赖的东西。尽管这类感官经验也一再被快速地改变,也一再遭到速度的电击而引发震惊。这种速度如此之快速,震惊如此之频繁,人们不断地撞入新奇的王国,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怀疑这个现实就是一个梦境。巴黎,与其说是一个历史,不如说是一个幻觉。“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在另一面镜子里那样,这种新奇幻觉也反映在循环往复的幻觉中。”[2](P22)
同游荡者的滞留相反,人群总是步履匆匆地奔向一个终点而对周遭视而不见,这个终点既可能是上班场所,也可能是家园,在更广义的层面上,这个终点是一个进步的梦想,一个乌托邦幻境,一个幸福的未来承诺。现代人的步伐被这个承诺牢牢地束缚而失去了闲荡的自在天性。相反,游荡者抓住的是此时此刻的街头,家园不在别处,就在于街道本身,家园本身就是过道,而不是终点和目标。“如果说闲逛者把街道视为室内,拱廊是室内的古典的形式,那么百货商店体现的是室内的败落。市场是闲逛者的最后去处。如果说最初他把街道变成了室内,那么现在这个室内变成了街道。”[2](P117)游荡者抓住的是眼前的实在之物,是可感触之物。人群最后发现,家园或许就是一个梦想的幻灭地带,一个乌托邦破碎之地;而置身于街头的游荡者,事实上,在这个现代世界中,也还是备感孤独,他的家或许并非虚幻之地,但是,他也只能在“商品的迷宫中转来转去,就像他在城市的迷宫中转来转去”。对未来的抵制,只能是停留在一种姿态上面,而并不能从“市场”和商品的包围中全身而退。他陷入困境,既无法向前,也无法后退,因此,本雅明“像一个沉船中爬上遥遥欲坠的桅杆的人,在那里……发出求救信号”[4](P11)。
显然,游荡者被商品包围。大城市正是围绕着商品而展开,商品是巴黎这样新兴的大都市的魂灵。本雅明对马克思的商品概念谙熟于心。商品的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衡量: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本雅明发现,在现代巴黎,“商品戴上了王冠,焕发着诱人的光彩”。这样一来,马克思津津乐道的使用价值退到了幕后,商品的交换价值大放异彩。实际上,本雅明在这里所说的交换价值,与其说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交换价值,不如说是后来鲍德里亚更加明确地界定的符号价值。商品首先是以一个形象的面目出现的。形象将商品的使用功能完全压制住了,从而“为人们打开了一个幻境,让人们进来寻求开心”。更重要的是,商品几乎无一例外是一种生产式的发明——它是全新的,并以不断翻新的时尚所驱动而被求新的欲望所再一次驱动。作为一个新奇的充满幻觉的意象,商品里面凝结着人类的梦想——尽管这是资产阶级的虚幻梦想。因此,它是现代人的膜拜对象。当然,商品编织的海洋可以淹没包括游荡者在内的所有人,这也是游荡者能在百货商店反复地消磨一整天的原因。
这样一个商品概念再一次同马克思的商品概念有所区分,在后者这里,商品凝结的不是人类的梦想而是工人的血汗。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概念力图将商品背后的血淋淋故事叙述出来。与马克思不同,本雅明对商品背后的欺诈和剥削并不感兴趣。商品毫无疑问是一个经济现象,但本雅明感兴趣的是,商品将经济和文化勾联在一起。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见,经济当然潜伏在文化之下,并且对文化有一种决定性的支配权。但本雅明发现,单纯的经济必须借助于文化形象表达出来,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文化生产。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就变成了经济,文化生产就是经济生产。本雅明最先考察了“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作家生产的是商品,而不单纯是小说。文化首先是作为商品而出现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隐秘回应:经济和文化具有同质性。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并非文化的基础,文化也非经济的产物。对于本雅明来说,“所要展现的不是文化的经济本源,而是经济在文化中的表达。换言之,所涉及的问题是努力把握作为可感知的原初现象的经济过程”[5](P312)。广告、报纸、建筑,它们是商品,同时也是一个可感知的文化形象。经济就是借助于这样的文化现象得以表达的。就此,经济和文化并不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区域,它们并非各自为政。相反,经济和文化彼此埋藏在各自的形象中。一个商品基于经济事实要出售的时候,它同时出售的也是一个文化形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生产。
商品正是形象生产的典范,形象和经济在此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由于商品在它的形象上反复地锤炼,巴黎最终变成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巨大的视觉机器。而在这一形象化过程中,商品当然成为中心。如果说,经济总是要被形象化的话,那么历史——即便是经济决定论的历史——难道不是可以通过形象的汇聚而发现自身吗?不是可以从形象中来发现经济的规律吗?马克思从商品中窥见了历史的奥秘,本雅明同样如此,不过,这个商品是以将经济形象化的方式暴露出来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理解历史就必然要求以牺牲历史的直观性为代价吗?或者,怎样才能将一种高度的形象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实施相结合?这个项目的第一步就是把蒙太奇的原则搬进历史,即用小的、精确的结构因素来构造出大的结构。也即是,在分析小的、个别的因素时,发现总体事件的结晶。”[5](P313)每一个小的蒙太奇的形象,每一个商品,每一个细节,都是总的生产方式的暴露。“正像一片树叶从自身展示出整个经验的植物王国的全部财富一样。”本雅明抛弃了康德而转向了歌德。哲学让位于诗学,历史被电影所替代。巴黎,像一个个分镜头一样被播放出来。本雅明对具体形象的强调,既偏离了哲学的抽象性质,也放弃了历史的编年纪事,然而,它既包裹了哲学的深邃,也拥有史学的精确。在本雅明这里,哲学获得了形象,史学被钉入了辩证的锲子,而文学的下面则涌动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波澜。本雅明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风格,这种风格就是用形象作为炸药去将各种既定文类的壁垒轰毁。
如果说商品是巴黎这样的大都市创造的时尚的话,那么,垃圾则是这种时尚的最后归宿。商品总是有它的历史命运,熠熠发光的商品最后无不沦落为马路上的被遗弃的垃圾。不过,商品在成为废弃物之后可以被再一次利用:有时候是穷人的直接利用,有时候可以被工业机器再次加工。这就直接促发了拾垃圾者的诞生。垃圾同商品一样,仍旧是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在大城市之外,垃圾形不成自己的规模。只有在人群和生产大规模聚集的场所,垃圾才可以以令人瞩目的体积和数量出现,它也才会形成一个场景——尽管这个场景被大多数人所回避。垃圾是光怪陆离的城市的一个剩余物,就像游荡者也是城市的剩余物一样。游荡者,在循规蹈矩者的眼光中,同样是“垃圾”。游荡者和垃圾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如果说,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城市的五光十色的形象所深深地吸引进去了的话,那么,垃圾只能得到少数游荡者的抚慰。垃圾堆砌于城市的偏僻角落,它执意地将城市一分为二:在辉煌的城市的背面有一个肮脏的城市;在一个富足的城市后面还有一个贫困的城市。垃圾是现代工业噩梦的最早预告者:城市最大的困惑和烦恼之一就是垃圾。因此,现代城市的规划和设计,通常是围绕着垃圾而展开的。城市首先是一个掩盖和处理垃圾的机器。事实上,有多少商品的生产,就有多少垃圾的剩余。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商品是它的精心打扮的容颜,而垃圾则令人生厌地不断地毁坏这种容颜。垃圾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城市的公敌。于是,拾垃圾者出现了,在本雅明关于巴黎的研究中,最有意味的话题之一是重新激活了波德莱尔笔下的拾垃圾者的形象。
不过,有一种职业化的拾垃圾者,这是一个保持街道清洁的职业工人。比如,伦敦在17世纪就有了一种付费的清扫街道的人,在19世纪,这些清洁工的权利被写入了《伦敦市道路交通法》[6](P259)。这样的清洁工人如今在所有的城市中都大量地存在,他们在夜晚和清晨中出没。但是,在波德莱尔和本雅明这里,拾垃圾者不是职业化的,他是自发的,他像一个收藏家一样在搜集垃圾:“凡是这个大城市抛弃的东西,凡是它丢失的东西,凡是它唾弃的东西,凡是它践踏的东西,他都加以编目和搜集。他对所有的东西分门别类并作出明智的选择。就像一个吝啬鬼守护着一个宝库那样,他搜集着各种垃圾。”[2](P148)同职业化的清扫街道的垃圾工人不一样,这些垃圾对他有用,而不是要完全将它清扫掉。这样的搜集垃圾的人,有自己特殊的步伐和身影,而这却和城市中的诗人接近,“拾垃圾者和诗人——二者都对垃圾感兴趣,二者都是在市民们酣然沉睡时孤独地忙活自己的行当”。诗人犹如拾垃圾者。拾垃圾者翻翻拣拣,试图在垃圾中寻求真理,寻求“价值”,抒情诗人则在街道的两旁守候灵感,为他的诗歌意象寻章摘句。波德莱尔希望将自己的诗人形象和拾垃圾者形象联系起来,同样,作为试图揭示19世纪的巴黎风貌的本雅明又何尝不是?本雅明也是个收藏家,他搜集的是“历史的垃圾”,这些历史垃圾正是正统历史学家不屑一顾的历史废料。他们所遗漏的历史垃圾,恰恰是本雅明需要的素材。问题是,搜集这些垃圾干什么?对本雅明来说,“那些破布、废品——这些我将不会将之盘存,而是允许它们,以唯一可能的方式,合理地取得属于自己的地位,途径是对之加以利用”[5](P312)。这完全是拾垃圾者的方式。
本雅明似乎相信,偏僻的城市角落中的垃圾废墟中蕴涵着城市的整个秘密,就如大海中打捞起来的珍珠蕴涵着整个大海的秘密一样。事实上,他的拱廊计划正是这样一大堆历史垃圾的大全,是它们的分门别类。如果说一般历史学家看到的是巴黎的显赫地位的话,那么巴黎在本雅明的眼中则是以一个废墟的形象出现的,这座废墟就围绕着垃圾和它的另一面——商品组成了一个盛宴。垃圾和商品相互补充,这是巴黎的两端,也是现代社会的两端。如果说商品是人们梦幻的凝结,那么,垃圾中或许包含着记忆散落的珍珠。人们发明和拥有了商品,在它上面铭刻了时间的痕迹,然后将它转化为废物并且弃置一旁,这就是垃圾的诞生,它们堆积在一起,同琳琅满目的商品遥相呼应。一种奇特的景观就此出现了:最时尚的和最过时的、最耀眼的和最肮脏的、最富裕的和最贫穷的、最梦幻的和最现实的,它们在一个并置的时间内拼贴和重叠起来——这难道不是从巴黎这个废墟中升腾起来的巨大的历史讽寓?这个讽寓难道不是表明了,梦想的归宿就是废墟?
参 考 文 献
[1]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本雅明. 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汉娜·阿伦特编. 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M]. 北京:三联书店,2008.
[4]郭军,曹雷雨编. 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与语言的种子[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5]本雅明. 拱廊计划:N,郭军译[A]. 生产,第一辑[C].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编. 城市文化读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李小娟付洪泉]
Wandering and Modern Experience
WANG Min-an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In the description of Walter Benjamin, the flaneur in modern metropolis is the product as well as the observer of it. They are wandering aimlessly in the metropolis, walking on the street lined up with stores and observing all kinds of cultural images created by commercial economics. They are shuttling among people but isolated from the pace of modern city life. They are deserted by modern life, but observe this life as an on-looker in the heart of city. They have a unique perspective, different from those busy citizens, which enables them to perceive the nature of city life.
Key words:Walter Benjamin; flaneur; moder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