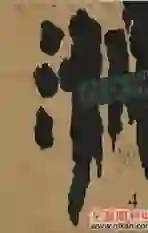想念《百花洲》
2009-07-30赵丽宏
我对南昌有一种亲切亲近的感情,因为那里有一本和我有特殊缘分的文学刊物《百花洲》。
大概是在二十八年前了吧,那时我还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发表了一些诗歌和散文,小有名气,但还少有外地的刊物专门来上海向我约稿。一天,从南昌来了一位编辑跑到学校里找我。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这是一位清瘦文雅的编辑,年纪比我大一点,说话轻声轻气,似乎还有一点腼腆,但态度非常诚恳。我们在校园里见面,在学生宿舍的走廊里互相介绍。他自我介绍是《百花洲》的编辑,名叫洪宜宾。他说他一直关注我的诗歌和散文,希望我为《百花洲》写稿。说实话,我有点受宠若惊,没想到我的文字会这样被人注意,还这么老远地专门赶到上海来约稿。对这样的诚意和盛情,怎能轻慢应付呢?我很认真地写了文章寄给洪宜宾,他收到后马上回信,鼓励称赞我的文字,很快编排发表。后来我才知道,洪宜宾也是诗人,笔名洪亮,诗风典雅,讲究意蕴和音律,情感深挚,一如他的为人。他是上海人,“文革”前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作家和文学编辑。此后,洪宜宾经常来信约我写稿。记忆中,我为《百花洲》写过诗,也写过其他文章。每次洪宜宾都热情地回信,从不耽搁,并以最快的速度发稿。后来他又来上海找我约稿,我很想请他吃一顿饭表示感谢,但他却怎么也不肯吃我的饭。他说,你还是穷学生,吃什么饭,还是我来请客。我当然也不答应他请客。结果,是他到我家里来看我,还带了礼物送给我父母。他是那种认真奉献却不求回报甚至拒绝回报的人,这样的人实在不多。而这一切,对他来说是那么自然。一个作家和一家刊物的关系,其实就是和一位熟悉的编辑的关系,而这位编辑的风格,就成了作者心目中这家刊物的风格。在我的记忆中,《百花洲》是美好的,我发自内心地感觉到她的亲切和慷慨无私。
大学毕业后,我成为《萌芽》的编辑,负责编辑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仍然和《百花洲》继续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有一个事件,值得一提。那是在1983年,我看到叶永烈发表在《福建文学》上的短篇小说《爱国的“叛国者”》,写一位流落国外的音乐家爱国思乡的故事。我觉得这是以钢琴家傅聪为原型创作的。当时傅雷的《家书抵万金》已经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他和儿子傅聪的通信,感动了无数人。我想,如果写一篇傅雷和傅聪的报告文学,一定能引起无数中国人的兴趣。我找到叶永烈,请他为《萌芽》写报告文学。叶永烈一口答应,并雷厉风行,马上到处找人采访,很快就写成一篇有分量的报告文学《家书抵万金——傅雷和傅聪》,其中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情节。我也以最快速度编发,准备在年末的刊物上头题推出。但在刊物付印之前,却横生枝节,因为主编认为内容可能犯忌,将此文送审,结果被搁置,没有了下文。我当时非常愤懑,但又无奈。情急之中,想起了《百花洲》。我和洪宜宾通电话,谈了这篇报告文学的大致情况,问他是否能发。洪宜宾给了我简短的回答:“你快寄来,我们力争发。”我把《家属抵万金》的清样寄给了洪宜宾,很快,此文就在《百花洲》以头条位置刊出。这篇报告文学,当时曾引起强烈反响,很多报刊转载,傅雷和傅聪的故事被广为流传,而叶永烈也从此开始了他的纪实文学的创作之路。
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在我的记忆中,《百花洲》是一个正直仗义的朋友,是一个有勇气也有智慧的朋友。
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百花洲》经常在庐山举办笔会,招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作者。我曾经被邀请参加《百花洲》的笔会,上过庐山,同行的还有肖复兴和罗达成。洪宜宾和《百花洲》的其他编辑们,陪着我们跋山涉水,欣赏美景,那是一些难忘的美好记忆。
我想,我的文字,在《百花洲》发表的作品中大概并不显眼,但这本刊物对我来说却非同一般,我觉得她是我的知己,是我的挚友,尽管最近几年很少为《百花洲》写稿,但情谊是不会消失的。现在,《百花洲》迎来了她的三十岁生日,我衷心地祝愿她在而立之年重振雄风,集聚更多作家,吸引更多读者,在中国文坛赢得她应有的一席之地。
赵丽宏,散文家,诗人。1952年生,上海崇明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著有散文集、诗集、报告文学集等各种专著共六十余部,有四卷本《赵丽宏自选集》行世。
责任编辑 许 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