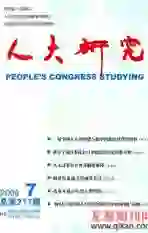生态补偿机制是民族地区实践科学发展的重要支撑
2009-07-30葛少芸马占元
葛少芸 马占元
一、甘肃民族地区生态补偿主体架构渐趋形成
根据“生态功能服务付费”理论,生态补偿实际上就是要求社会各阶层对生态环境承担社会责任的一项制度。它要求政府在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个人在追求自身发展空间的过程中,强调人类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要通过补偿的形式,确保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明确指出了生态补偿机制构建主体,即国家、区域和产业。这一规定为我们勾勒出了生态补偿机制补偿主体的基本框架。
根据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所设定的内容,由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的甘南藏族自治州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与建设项目,于2007年12月20日正式启动。这是甘南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生态补偿工程,预算总投资44.51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农牧民生活生产设施建设、生态保护支撑体系建设等。此项主要由国家通过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实施的生态补偿,体现了国家作为全民利益的集中代表而在生态补偿机制中的主导性地位和最重要的义务主体。
实践中,国家早已在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许多地区启动了诸多生态建设项目,如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防沙治沙工程、自然保护区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三化”草地治理工程、湿地资源恢复和保护工程,等等。这些项目本身也都是对民族地区的生态补偿形式,并充分彰显了政府不容置疑的主导作用。
鉴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具有地域性和跨域性的特点,以及资源产权的难以界定等原因,政府在组织和协调区域间合理的利益转移方面,同样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从2007年12月1日起,甘肃省率先在全国试行征收草原植被恢复费制度。规定对在省境内草原上从事地质勘察、修路、探矿、影视拍摄等活动,以及采挖野生植物的企业或个人,将收取植被恢复费。这意味着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将为履行生态环境社会责任承担所必需的成本。今后,根据生态补偿客体的特点和要求,诸如此类的生态补偿制度和明细化规定,都应该逐步得到建立和完善。
二、充分把握民族地区生态补偿契机,以科学发展理念实现生态治理与改善民生同步
甘肃少数民族总人口虽只占全省总人口的9.3%,但民族自治地方国土面积却占全省总面积的40%。全省民族自治地方草原面积占全省草原面积的63%;有林地面积占全省有林地面积的近一半。全省天然林资源主要集中在民族地区,其中甘南州占全省的30%,森林蓄积量占全省的45%。民族地区水电资源理论蕴藏量占全省水电资源总量的62%。
根据《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和祁连山麓的甘肃民族地区,许多区域被列为国家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其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调节功能,维系着区域或全国的生态安全。这一主体功能的科学定位,决定了甘肃民族地区有提供生态服务功能的重要义务和应当获得生态补偿的必然权利。但是,民族地区大多地处高寒阴湿山区和荒漠戈壁地区,多变而极端的气候、高海拔、土壤瘠薄、植物生长缓慢以及日益发展的气候暖干化趋势,再加诸多人文因素的影响,使其又是极其脆弱的生态区域,极易受到破坏并且很难恢复。由于资源承载能力较弱,生存环境恶劣,生存空间狭窄,加之为了保护生态功能区而丧失了部分发展机会和自身利益,因而民族地区目前贫困面较大。全省21个民族县(市)中,有14个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2006年民族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省的5.6%,地方财政收入仅占全省的4.2%。在全省86个县(市)综合经济实力排序中,有15个民族县排在50位以后,排在最后的6个县全是民族县。在全国30个民族自治州中,临夏州、甘南州综合经济实力排在最末两位。
研究资料和大量实践表明,贫困是招致生态恶化的首要原因,而生态环境恶化又是造成贫困的主要根源。为此,必须充分把握生态补偿契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理念,这是促使生态治理与改善民生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大力发展资源优势产业
根据民族地区资源特点和产品优势,科学地构建起生态经济发展的支撑点。在草原牧区,要在落实和完善草原家庭承包的基础上,普遍推行保护草原和提高草原生产力的适用技术配套系统,主要是:人工草地建设,草原围栏,划区轮牧,禁牧、休牧制度,草原水利设施建设,病虫害和毒害草的防治等。与此同时,应积极推广以提高家畜生产转化效率为核心的生产经营方式。例如,占甘南州牲畜总数90%以上的藏绵羊和藏牦牛,它们能适应当地高寒严酷的生存环境,在生长性能方面又具有较好的弹跳力和爆发力。现有的技术路线完全可以实现肉羔羊当年育成出栏、藏牦牛商品牛两年育成出栏的目标。这不仅大量节约了饲草料资源,减轻了对草原生态的压力,还能大大提高产品质量,显著增加经济效益。在其他农区或农牧交错区,要在发展生态农牧业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农牧结合、农牧互补的优势,重点开发肉牛、肉羊育肥产业,并与牧区紧密结合,走“牧区繁殖,农区育肥”的易地育肥路子。
要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并发展与之相应的产品加工业,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高寒阴湿山区的绿色食品、中药材、油料、蚕豆、水产、山珍等;其他农牧区的油菜、蚕豆、马铃薯、蔬菜、水果、花卉、食用菌、水产、中药材、牛羊肉、皮革、羊毛等,都是极具特色的产品,具有广阔的发展和提升空间。
(二)积极示范并推广“六化”家庭牧场
近年来,在广大牧区发展起来的“六化”家庭牧场,即牲畜良种化、圈舍暖棚化、草场围栏化、饲草料基地化、防疫规范化、牧民定居化,已成为保护草原生态和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并具有组织成本低、适应市场波动变化能力强,还有可能向规模化经营转型提升等优势。据报道,甘南州的碌曲县,已有不同规模的家庭牧场2434户,占牧户总数的75%。有条件的牧区都应得到发展。
(三)重视林业生态保护和建设,不断发展壮大林业产业
鉴于天然林的重要生态功能,要在“天保”工程取得初步成绩的基础上,争取继续实施第二期天保工程。通过严格封护,保护好天然林的生境条件、物种资源,并使残次林尽快恢复成林。要不断完善政策,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抓紧宜林荒山荒地造林和低产林的改造,提高森林覆盖率。
要积极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断发展壮大林业产业。民族地区发展花卉、经济林木、林下经济、林木种苗、林木林副产品加工等林业产业的潜力巨大。应合理利用生态补偿资金,予以重点扶持。
(四)不断提升生态旅游的产业地位
充分利用民族地区独特的原生态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优势,积极开展森林旅游、草原旅游、湿地旅游、荒漠旅游等,让它们在发挥自身生态功能的同时,又能与发展当地经济相结合。目前,甘肃民族地区生态旅游尚处于起步阶段,管理上也无成型的体系,现行的体制和管理法规又较滞后,政府、企业、本地社区还未形成多方的积极参与和合作,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备,等等,距离生态旅游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应该得到改善。
三、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支撑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在继续明确和规范生态补偿主体的情况下,笔者以为,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从法律关系视角来看,还需完善以下其他几个方面的核心内容。
(一)生态补偿对象应尽力实现直接补贴
生态补偿的最终受益者肯定是生态系统,但生态系统的最终受益,必须经过中间受益人才能实现。即生态补偿的补贴,只有体现到生态系统所在地的居民,最终通过他们对生态环境影响行为的变化,才能体现到生态系统。此外,在我国民族地区生态补偿中还有一个“因环境保护和建设而致财政收入减少的地方政府”,也是生态补偿的重要对象。
值得借鉴的是,西部地区在退耕还林还草的立法中,对退耕农户改间接补贴为直接补贴,大大减少了中间环节,减少了腐败,提高了整体效率。民族地区的生态补偿,在补偿对象明确的情况下,也应尽力实现直接补贴,可以具体到一个县、乡或更小的村社和个人。
(二)生态补偿标准,既要考虑受偿地区的生态贡献,又要顾及补偿者的承受能力
如果按照环境经济学测算出来的“生态价值”,那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对“外部性溢出”的数量化研究,目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形成实际操作还面临一系列困难。当前,有些研究机械照搬国外标准,评估指标选取的任意性、计算方法的无序性和重复计算问题,非市场价值评估的不确定性,理论计算与实际应用相脱节,等等,都需要认真解决。并要通过加强科学研究的力度、特别是生态功能基础研究的力度,逐步解决若干亟待解决的理论和方法等问题。
(三)生态补偿机制的实现形式应具有多元化特征
国内外曾创造了名目繁多的生态补偿形式,归纳起来主要有:资金补偿、实物补偿、项目补偿、政策补偿、智力补偿。前两种可以看做是输血型的补偿形式,后三种是造血型的补偿形式。从现实情况看,输血型的补偿形式自然是很直接、很实惠的选择。但从长远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应该更加重视造血型的补偿形式,因为这可以使受偿者充分发挥其发展经济的潜能,所形成的造血机能,最后能转化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四)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的法制化问题
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生态补偿行为的实施等,都需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来实现,这是建设法制社会的客观要求。同时,生态补偿法制化也是生态补偿本质的内在要求。因为生态补偿的本质,实际上是在生态保护的实施者和受益者之间重新分配利益的问题。根据博弈理论分析,对于实施生态保护并且使受益方对实施方进行补偿,只有无穷次地重复博弈内容,才可以使帕累托改进成为纳什均衡。这表明,只有建立起长效运行机制,才能保证生态补偿的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和自然公平。而建立长效机制的根本保证就是法律保证。
我国迄今还没有一部生态补偿的基本法律或行政法规,以对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补偿主体、对象、范围、标准、方式、资金来源、监督管理等作出总体性规定。已有的生态补偿规定都是散见于一些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之中,对生态补偿的规定也太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尽早实现生态补偿领域的国家层面立法或区域立法,对于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的长效运行机制将是极为重要的。
(作者分别系西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民侨办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