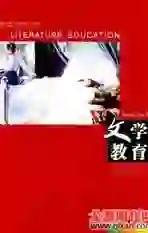以《雷雨》为例分析封建传统对人的毒害
2009-07-24吴莉斯
曹禺先生的《雷雨》演绎着人对“不公平”的社会的控诉和抗争,是受压抑的人性向天空的一声呐喊,也是一出被怜悯的爱情悲剧。封建资本家周朴园无奈放弃爱情的悲剧,下层妇女(侍萍)被离弃的悲剧,上层妇女(繁漪)错爱个性受压抑的悲剧,青年男女(周萍、四凤)得不到正常的爱情的悲剧,这些爱情幻梦的破灭,向人们诉说着人类最真实的人性惨遭扭曲、压抑的痛苦。《雷雨》中周朴园、周萍和侍萍、繁漪之间的爱情,在那个背负着沉重的民族悲情与历史沧桑的时代中显得弥足珍贵,却又不堪一击,他们在爱情的纠葛中挣扎,向封建伦理观念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深层意识发出最悲壮的控诉。
《雷雨》中,在封建大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周朴园和周萍,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最终还是无力挣脱封建传统的束缚,选择了“回归”社会。周朴园是个有着浓厚封建气息的资本家,他既尊崇旧道德,又接受了国外的新思想。三十年前,他与女仆相爱了,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他迈出了遵从自己意愿的一步。可是周朴园最后还是“回归”了社会,在爱情和地位之间放弃了爱情。但是,这并不是说周朴园不爱侍萍,正如曹禺先生说:“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感情是真的,绝对是真的。”因为周朴园的“抛弃”侍萍并不是他自愿的,而是被逼的,被周老太太逼的,被封建传统逼的。
年少的周朴园应该是想娶侍萍的,否则也不会跟侍萍生下两个儿子。可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并不是因爱而婚,而是有目的的,一是为两个异性家族缔结“亲缘”,二是为男方家族继承“血统”。因此,把一男一女结为夫妻,只是形式;把两个家族结为亲家,才是内容。婚姻只是旧家族的延续,而不是新家庭的开始;是男方家族多了个成员,女方家族多了门亲戚,而不是男女双方当事人得了个伴侣。所以周朴园是无法决定自己的婚姻的,结婚不是他个人的事,而是周家的事。既然是周家的事,周老太太自然要为儿子娶个“有钱有门第的小姐”,这样“强强联合”的婚姻,才是“门当户对”。
所以,侍萍虽为周家生了两个儿子,可是身分阶级的限制使周朴园无法在周家为她争得一席之地。正所谓“聘则为妻奔是妾”〔1〕,也就是说通过正规手续的,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婚的女子才能有名分,是妻。而私定终身的女子将永世不得翻身,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有名分。而侍萍本就是周家的下人,下人本就是周家的东西,是可以被周家的老爷、少爷玩弄的,生了儿子,儿子也要认妻为母亲,其生母还是下人。因此,年少的周朴园虽然出过国,留过洋,却仍然无法挣脱那有着几千年积蕴的封建传统意识,无法走出自己的身份阶级限制,在那个婚姻被看作交易,爱情被当作筹码的时代,他的婚姻是注定要为周家的家族服务的,他的责任则是把周家“发展壮大”。这样看来,三十年后周朴园再见侍萍时开始的绝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他的绝情不等于无情,年少时的他不能脱离自己的阶级限制,三十年后这些阶级属性更是在他的内心生长茁壮了,他的表现应该是他那个阶级的“正常表现”。于是等他冷静下来,他那被铭记的爱情又开始占上风,先是寄钱,在第四幕的开头他三次不自觉地拿起侍萍当年的像片观看,在剧本的结尾又向侍萍认了错。
因此,周朴园对侍萍的感情,可以说是伤害与悔恨交接,恐惧与思念相杂,冷漠与真诚同在,在他不得不“自愿”地放弃爱情,“回归”了社会之后,他只能把那份爱深深地埋在心里,在漫长的时间中经历着“伤害——怀念——忏悔”的嬗变,承受着刻骨铭心的疼痛。
与周朴园不得不“自愿”地放弃爱情相比,他的儿子周萍对爱情就是怯懦和逃避了。周萍虽受过“五四”时期民主思想的洗礼,不满于父亲的专横与不尊重女性,但是作为周朴园的衣钵传人,他连站起来反抗的精神都没有,反而竭力想做周朴园所代表的那个社会和阶级的忠臣孝子。阴郁而不得志的他,与同样也是倍受压抑的后母繁漪走在了一起,从此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十字架。他怯懦了,繁漪带给他的只是无尽的悔恨,他害怕与繁漪的关系张扬开去,不容于父亲,不容于社会舆论,不容于整个统治势力。就在他苦闷不堪时,开朗单纯的四凤闯进了他的视线,如一缕阳光般给了他生活的希望。他爱上了四凤,竭力想逃出周公馆,中断与繁漪的关系,重新开始他的生活。但对于他和四凤的未来,却没有认真考虑过。
作为“长子”的周萍“一方面勇于自我牺牲为齐家而奉献个人的一切,另一方面又卑柔软弱”〔2〕,他就是鲁迅所说的“甘做封建传统文化的奴隶而缺乏挑战反抗之力”这类人,这样的人无法背负两个女人的爱恋,他的怯懦负了繁漪,害了四凤,他在人性和伦理道德、本性和传统意识中挣扎沉浮,最终还是屈服于男权社会的强大统治,驶向“回归”社会的港湾。
封建传统社会中的女人,追求爱情的道路更加艰难,她们摆脱不了封建传统意识的阴影的纠缠,就无法逃脱社会传统的藩篱,沦为封建传统的牺牲品。
《雷雨》中对爱最宽容的是侍萍,她对爱情的态度表现了中国下层劳动妇女对生活逆来顺受的屈辱生存状态,她们纯洁、善良,向不公平的社会坚韧而倔强的抗争着,却仍逃不开封建传统意识的禁锢,成为男权社会中最圣洁的祭祀品。侍萍是个有着巨大精神力量的女子,三十年前怀着少女对爱情的憧憬她去爱了,当周朴园为了自己的前途抛弃她时,面对社会上的指责与漫骂,她勇敢的活下来了,顶着椎心刺骨的煎熬,用自己瘦弱的双肩抵抗着不公平的遭遇。
尽管如此,女人多情和心软的天性决定了她无法完全恨起周朴园来,三十年后,当她在那间映照着前尘旧梦的屋子里看到那个三十年前爱过、三十年来恨着的冤家时,恍然又回到了三十年前的情境,其情感是迷离的、感伤的。当大海要去周家报复时,侍萍说:“你要是伤害了周家的人,不管是那里的老爷或是少爷,你只要伤害了他们,我是一辈子也不认你的。”可见她对周朴园是一种怎样的“恨”。她对四凤说:“人的心都靠不住,我并不是说人坏,我就是恨人性太弱,太易变了。”这也正是经历磨难后的她对人性弱点的顿悟。于此,她也便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原谅了周朴园。
这就是侍萍的爱情,不同于铁腕女子的刚毅,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对生活的宽容。在封建传统意识强大的社会里,她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处处隐忍退让,然而三十年后她再次面对滴血的选择,她的灵魂仍无法逃脱封建传统那高垒的祭台。正如作者所说:“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3〕
《雷雨》中对爱最执着、最极端的当属繁漪。繁漪被周朴园软禁在这个仿佛与世隔绝的周公馆里,寂寞枯淡的生活,闷得她透不过气。封建社会的权势,周朴园家庭绝对权威独裁,使得她的生存理想与现实相悖,人性的本能追求被压抑的生活使得她已不存在什么希望,只安安静静等待死亡到来。
就在这时从乡间跑来的年轻人周萍,以他的热情使繁漪这株即将枯死的奇花得到了点滴雨露的滋润,逐渐有了生气。她把生命、名誉整个交给了周萍,却不知道周萍不是一个可以指望的男人。于是,当周萍爱上四凤,要跟繁漪停止之前的不自然关系时,繁漪的爱变成了恨,倔强变成了疯狂。“一个女子,不能受两代的欺侮。”怀着这样的思想她为了自己的“爱情”不择手段,连自己的儿子都被拉出来借以破坏周萍和四凤的结合。她像战神一样充满勇气,以夸父追日般的热情索求虚无缥缈的真爱,却在寻爱的路上迷失了自我,她是罪人,也是受害者,越希望摆脱被压制、被玩弄的地位,却失去的越多,最终沦为封建传统的牺牲品。
情是人类亘古追求的最美好的情感,可是中国传统社会却偏偏绝不容许男人和女人恋爱,婚姻只是传宗接代的必须过程。被封建传统禁锢着的男人和女人,被这些所谓的“传统”压抑的喘不过气,不断地扭曲自己的“心愿”,造成人性的缺陷。他们无法打开几千年的封建心狱枷锁,使自己作为“人”的存在得到社会认可,就只能受控于一瞬间的无意识冲动、直觉和神秘体验,最终只能在一边吞咽着自己的爱情苦酒,迷失在对自我的追求中。
正因如此,才有了弃爱回归的男人和为爱悲伤的女人,才产生了“雷雨之夜”的悲剧。在这最浓缩的时间与空间里,所有的人都在纠缠着,挣扎着,或为了实现救赎,或为了追求梦想,或为了保持一点眼前的平静,然而没有挣脱封建传统束缚的一切努力都是无力的,最终的毁灭无可避免。
注释:
〔1〕易中天:《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3月第3版,210页
〔2〕赵德利:《长子情结与人格悲剧》,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79页
〔3〕曹禺:《〈雷雨〉序》,《曹禺文集》1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213页。
吴莉斯,湖北省机械工业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