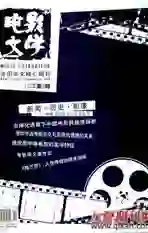新闻·历史·影像
2009-07-20王伟
王 伟
[摘要]发生在图像时代下的“9·11”,深刻改变了世界,经由大众传媒之强势介入,使不少已经被反复讨论且尘埃落定的传播议题,有了重新审视的必要。本文从主体间性的交往视阈出发,在建构文本意义的层面上,沟通新闻传播、历史传承、影像再现的辩证关系,在意义论的哲学基础上创构“解释”和“传播”的相互联系,进而在图像时代的现实语境,来重新审视二者的内在关联,最终提出“传播作为解释的世界”的命题,从而走出影像之“镜式反映现实,被动忠于历史”的理论迷思。
[关键词]影像文本;主体间性;解释学
一、从《华氏9·11》谈起
“9·11”事件距今7年有余,由于时间距离,由新闻文本沉淀为历史文本;因为岁月流逝,人类逐渐退却情感的冲击震撼,转向理性的认知检视,从而催生影像文本的视听演绎。发生在图像时代下的“9·11”,深刻改变了世界,经由大众传媒之强势介入,使不少已经被反复讨论且尘埃落定的传播议题,有了重新审视的必要。
第一,在暴力美学成为时尚的影像时代下,多元文明、不同世界的平等对话、和谐交往如何可能。不逊色于好莱坞大片的恐怖袭击,以及随后发动的“反恐战争”与“反‘反恐战争”,陷入相互报复的循环怪圈。第二,如果新闻和历史作为文本是“客观的”,那为什么出现“一个事件,多种故事”之新闻报道的影像奇观?西方国家(内部又划分为英美、旧欧洲、新欧洲等),中国(包含内地、台湾、港澳)、阿拉伯世界(界分不同派别)的主要媒体在第一时间所作的现场报道,没错都是“事实的陈述”,但却又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不完整的真实。显然这触及新闻从业人员理解事件的角度,和受众究竞选择何种视阂来二度诠释,以及双方通过媒介进行的循坏互动。交流的“偏见”能否克服,“权威”专家的解读能否信赖,“传统”能否在转换中传承、传承中转换,阐释“视阈”的差异能否完美融合、向前延伸,封闭的怪圈能否转化为开放的循环,文明间对话的障碍壁垒和清除之道又在何方?第三,影像作为现实的镜像,能“真实”地诠释事件、再现现实吗?迈克尔·摩尔的《华氏9·11》和奥列弗斯通的《世贸中心》,虽取材于此,却基于不同的视阈来建构文本的意义,从而为不同的观众群体,显现同一事件的诸种面向,体现了影像文本与其他艺术一样,具有对现实的批判作用和超越功能。那么影像是否有必要“真实”地再现现实和被动地忠于历史,以便观众获取同一性地认知吗?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全球化成为话语时尚的现实语境中,伽达默尔的主体间性解释学,或许能为上述发问,提供一种相对满意的理论解释。
二、解释学视阈下的历史文本
昨天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正如张法先生所言,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的第二部分《真理问题扩大到精神科学里的理解问题》中,关于历史文本之意义建构的论述是其“最辉煌的部分”。不错伽氏正是以“主体间性”这根红线,将诸多如宝石般的概念串成一条光彩夺目、熠熠生辉的项链,浑然天成、不落痕迹,集中体现哲学解释学在文本诠释之维的出色运用。下文就是顺着这一线索,采用关键词的分析方法,阐发他的主体间性接受理论。
首先,“偏见”的柔性正名,这是其历史观的创见所在。伽达默尔直言不讳,之所以选择“偏见”这一饱受非议的概念作为意义理解的起点,是受其恩师海德格尔“先在结构”(Vor-struktur)的影响。按照海氏在《存在与时间》中的论述,“解释一向奠基在一种先行具有(Vorhabe)之中”,即我们要想理解某物,就必须先行具有此物,理由是人无法理解在其整体世界之外的事物。而且“解释向来奠基在先行视见(Vorsicht)之中,它瞄准着某种可解释状态,拿在先有中摄取的东西‘开刀”,即我们在解释活动中,总是会对先有之物采取某种观点,此为理解进程的起始点。总之,“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及先行掌握构成了筹划的何所向。意义就是这个筹划的何所向,从筹划的何所向方面出发,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得到领会”。可见,作为理解之始基的前理解,本身是先于主体与客体意识的区分,所以理解的起点不是大写的主体。
伽达默尔坦率地承认,“偏见”(praeiudicium/pr éjudice/Vorurteil/prejudice)这一概念,在西文中(拉丁语、法语、德语和英语),具有强烈的负面色彩。他惊世骇俗地将启蒙运动之克服偏见的口号,描述为一种似是而非的偏见,“启蒙运动的基本前见就是反对前见本身的前见,因而就是对流传物的剥夺”。在他看来,启蒙主义对前判断、偏见、权威、传统的决绝否定,导致启蒙运动和随之起舞的历史意识,对偏见的作用充耳不闻,也就对构成人类生存之历史现实的置之不理。他用心良苦地写道,“早在我们通过自我反思理解我们自己之前,我们就以某种明显的方式在我们所生活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理解了我们自己。主体性的焦点乃是哈哈镜。因此个人的自我思考只是历史生命封闭电路中的一次闪光。因此个人的前见比起个人的判断来说,更是个人存在的历史实在。”总之,他认为,偏见远非个人的主观判断,而是人类理解的生发之源,没有先见谈何理解,在构成我们存在的过程之中,偏见的影响远远胜过判断的作用。他还不失时机地用偏见来表明人类的历史属性,“我们存在的历时性包含着从词义上所说的偏见,它为我们整个经验的能力构造了最初的方向性,偏见就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倾向性”。
第二,在为“偏见”拨乱反正的同时,伽达默尔还意犹未尽地附带讨论了两个相关的概念,“权威”与“传统”对文本理解的影响。他毫不含糊地反对“理性和权威作为绝对的对立面的论断”,并极为反感将权威的本质与现代专制主义的用语盲目挂钩。他试图强调权威的本质“最终不是基于某种服从或抛弃理性的行动,而是基于某种承认和认可的行动——即承认和认可他人在判断和见解方面超出自己,因而他的判断领先,即他的判断对我们自己的判断具有优先性”,是“理性知觉到它自己的局限性,因而承认他人具有更好的见解”。他在《论解释学反思的范围和作用》中,也反复重申权威“并非总是错误的”,而是建立在知识之上、值得信赖之正确的信息源。他认为,“对与权威的关系来说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接受或承认”,权威并不依赖教条的力量而是依靠教条的接受生存。”
为强化自己的观点,他再接再厉对“传统”做出别开生面的诠释,从而一步步地卸下主体性哲学的皇冠。他指出。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而要被认为是一种置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Einrncken),在这过程中过去和现在经常地得以中介”。即传统并非与人相疏远。成对峙的外在之物。人们天然地生存在传统之中,未来尚未确实来临,过去从未真正过去,而是在传统中复现在场。传统通过人类交往活动,过滤消极因素、保留积极方面,在人们身上实现而生气永驻。更进一步讲,历史意识不仅在事件中,还在其自我的理解中。文本理解
不是个体主体的任性而为,而是往昔和当下之生生不息的交融化合,脱离传统谈理解无异于缘木求鱼。
第三,“时间距离”(Zeitenabstand)不是文本理解的障碍壕沟而是“传释”意义的畅达途径。他认为,“时间距离并不是某种必须克服的东西。……事实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时间距离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时间距离不是一个张着大口的鸿沟,而是由习惯和传统的连续性所填满,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一切流传物才向我们呈现了出来”。他进一步指出“时间距离”是在运动中扩展,于开放中延伸,因而具有非封闭性。更为重要的是,在伽氏眼中,经由时间距离的过滤,能够区分“产生理解的真成见和产生误解的假前见”,解决了解释学的真正批判性问题。
第四。他就转入探讨“效果历史意识”与文本意义的交互建构。他对“效果历史意识”做出如下描述:“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他在《真理与方法》的第二版序言中写道,“理解(Verstehen)从来就不是一种对于某个被给定的‘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属于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这就是说,理解是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Sein)。”总而言之,“效果历史”是指能够对当前之建构意义的接受活动,产生影响、发挥作用的历史;“效果历史意识”就是指意识到接受主体自身是有限的历史性的存在物。根据效果历史的观念,历史文本(包括其他媒体文本)既不是客观的对象,也不是主体(如绝对精神、生命、心灵等等)的自我表现,而是主客体汇融同一的动态过程。
最后,为方便阐明在接受活动中,处于特定情境的接受主体所拥有“前见”的性质和作用,伽氏使用“视域”这一隐喻来表征。他意味深长地指出:“一切有限的现在都有它的局限。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阈(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视阈就是看视的区域(Gesichtskeis),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把这运用于思维着的意识,我们可以讲到视闽的狭窄、视阀的可能扩展以及新视阈的开辟等等。这个词自尼采和胡塞尔以来特别明显的被用于哲学的术语里,以此来标示思想与其有限规定性的联系以及扩展看视范围的步骤规则。一个根本没有视阈的人。就是一个不能充分登高远望的人,从而就是过高估价近在咫尺的东西的人。反之,‘具有视闯,就意味着,不局限于近在咫尺的东西的人,而能够超出这种东西向外去观看。谁具有视阈,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阈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笔者以为,视阈更为准确的翻译,应为地平线(天与地的相交之界)。在他的传播哲学中,其既能表明主体视力所能臻至的界限和最大幅度,又喻指主体目力所及的界限范围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主体的正反运动,持续的向前延展,抑或往后不断退却。也就是说,主体视阈“有界无边”可望而不可及,反映有限与无限的辩证统一。主体视阈的开放性本质正是主体间性的应有之义。他强调理解“既不是一个个性移入另一个个性中,也不是使另一个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标准,而总是意味着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的提升,这种普遍性不仅克服了我们自己的个别性,而且也克服了那个他人的个别性。”。“视域融合”(Horizbntverschraelzung)充分表明,“理解”既不是由传播内容(“历史流传物”等信息)所单向决定,也不是由所谓的接受主体来投射建构,而是二者的和谐交往来共同协商。视阈融合突出信息接受、意义生成的时间性,解析传统形而上学所强调的空间性和对象性的“永恒在场”。这一概念还否定了主客二分的意义考古,作别存在有超然于文化历史之外的接受主体,在反对单向度之信息接受论的同时,主张在积极参与或交互作用中去建构意义,典型的体现其传播哲学的主体间性。
三、新闻/历史,影像作为文本的意义建构
今天的历史就是昨天的新闻。正如蔡尚伟先生所论,“理解新闻事实与理解历史其实有太多的相通之处。历史因为理解的历史性因为偏见因为理解的视界差异而必然地是‘效果历史,新闻何尝不同样地因为理解的历史性因为偏见因为理解的视界差异而必然地是‘效果新闻”。进而言之,影像作为对现实的诠释。绝非是机械的镜式反映,而是不同视域的交往融合。
下面,就对其文本阐释理论的意义,略作评析。
第一,如果将新闻解读、历史诠释、影像再现作为文本理解的一类,在逻辑上就否定其具有客观性的学术公设。伽氏对“解释学问题之父”狄尔泰的历史客观主义的诉求不以为然,认为其是缺乏历史性反思而带有素朴性。他说,“一种真正的历史思维必须同时想到它自己的历史性。只有这样,它才不会追求某个历史对象(历史对象乃是我们不断研究的对象)的幽灵,而将学会在对象中认识它自己的他者,并因而认识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由此他否认历史作为客体对象而存在,并引申出“效果历史意识”,在更深层次上批判所谓的客观性理解。他对客观性的否认,本与新闻报道无甚联系,但引用在此,却可恰到好处地解释新闻客观性的局限,为纪录片的倾向性,提供强有力的哲学论证。按其逻辑,不偏不倚、不群不私之公正客观的纪实文本,只是教科书之迂腐不堪的陈词滥调,甚至是后政党媒介时代,西方业界说服受众消费的广告策略,至多也不过是向往的终极理想,而不是现实的可行目标。
第二,新闻、历史、影像作为文本是动态开放的,而非静态封闭的,不是自足完整的实体,而是循环往复、永未完成的辩证过程。伽氏在谈艺术时,曾利用黑格尔哲学浓厚的历史感,集中火力批判“美学之父”康德的先验主体性美学。但在论历史时,他显然不能容忍黑格尔体系的失误,即过于迷恋大一统的终极体系,而刻意压抑主体间性的交往思想。伽达默尔显然不满黑格尔对“恶无限”的诋毁,于是又搬出海德格尔关于“解释学循环”的论证,还击黑格尔及其传人的完整闭合历史观。他还发人深省地指出,“这种循环在本质上就不是形式的,它既不是主观的,又不是客观的,而是把理解活动描述为流传物的运动和解释者的运动的一种内在相互作用……是由那种把我们与流传物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性所规定的。”不错,在具体的接受活动中,文本的意义,特别是经典之作,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被悉数挖掘出来,每次照面都生发新的经验,在原有理解的基础上,交融形成更高更具普遍性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又沉淀为下次理解的“前理解”,如此往
复循环,直至无穷。这就是传播主体间性的辩证法。时下媒介所热炒的重新演绎“某某经典”,翻拍“某某片”,其内在驱力即源于此。
第三,新闻、历史、影像作为文本,既然是在生成中解释,又在解释中生成,意味着其是主体间意义的建构。他写道,“我们必须理解作者‘在他的意思中意指的东西,这样说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在他的意思中并不是指‘他本人打算说的。它毋宁是指,理解还可以超越作者主观的意义活动,而且很可能必然地并且总是超越作者主观的意义活动。”由是观之,伽氏在拒斥意义的确定性和将解释的目的定格在“维持话语继续进行”之后,指出意义的生成是文本与阐释者相互之间的对话、交流、重构,是二者间的相互从属、包容、融合,体现意义交互建构并传递共享的动力学原理。
第四,文本阐释者形象的转换,即从无理性、非主动的接受者到积极、能动的参与方。伽达默尔的法兰克福同事普遍将“大众受众”作为贬义词使用,在他们想当然的理论叙述中,可怜的大众被锚定为“像一盘散沙一样孤立无助、被动消极的个体”,成为单向的、非人格(impersonal)的传播接受端,是中弹伏地的目标对象和任人操纵、毫无主体意识的“乌合之众”。如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就毫不客气地说,大众无力为自己辩解,听任传媒将“心理无知”强加于己身。追本溯源,上述诸种过激言论,显然是建立在行为主义的“刺激一反应”(S-R)模式之上,是基于主客二分的认知逻辑。而伽氏的哲学解释学,就是在学理上正本清源,挑战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论调。他深深相信,阅听人在解释活动(文本的传播过程)中,从来就不是绝对被动的,而是具有选择能力和自我意识,能够从主体的视闽出发、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解读媒介文本,并积极参与本文意义的建构。有意思的是,他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被文化研究学派的头面人物所借镜并发扬光大,而且在实践的激荡中被主流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所验证肯定,彰显出元理论的前瞻性与普适性。
第五,“大众”的消融,“分众”的走向。早期大众社会理论(Mass media theory)之所以为人所诟病,就在于其传媒批判理论的逻辑演绎,或多或少是建立在“大众”这一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概念假定上。社会所的第一代学人想象的所谓大众,似乎是消除任何差别的整齐划一之群体。在激进批判主义者眼中,“虽然在任何社会的实际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等级差别,但是对于大众传播媒介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时都一视同仁”。如果借用解释学理论来透视,这只不过是臆想而已。每一个人受教育的或高或低、程度不一,受传统的熏染不仅深浅有别而且所属迥异,立足点不同必然导致视阈千差万别,所生成的意义自然大相径庭,岂能用一个包罗万象的名词笼而统之、一概而论呢?准确地说,“事实上并没有大众,有的只是把人们看成是大众的方法”。
四、传播作为解释的世界
斗转星移,从美国引进传播学,历经二十余载,但国内的传播学研究基本上都沿袭美国主流模式,即限于经验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只是将‘大众传媒作为工具、作为‘它,但是对‘大众传媒作为世界、作为‘他甚至作为‘你的一面却往往视而不见”。笔者认为,不妨将解释学思想作为传播哲学研究的新进路,恢复解释作为“传播之延伸”的本义,以文本意义为桥梁,来沟通传播和解释,在本体论的层次上将“传播看作解释的世界”。如此这般,我们便能够在文本意义之交互主观性的建构中,重新测绘新闻、历史、影像的分殊和关联,走出影像必须“镜式反映现实、被动忠于历史”的理论迷思,真正赋予受众之理解的充分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