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新视界
2009-06-24吕文翠

王韬(1828—1897)的欧游记行《漫游随录》早经公认为近代文化史重量型著作。王氏之盛名及其在中国现代报业史上的先驱地位为这部书加持的光环自不待言,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不管从出洋的时间先后、在国外居停之长短或从事的工作属性来看,王韬这趟欧陆之旅,确可誉为创举。1867年王韬受香港英华书院的院长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之邀,从香港出发前往苏格兰,一直到1870年期间他就居住在理雅各的家乡翻译中国经典。当时比王韬更早踏上欧陆的仅有斌椿父子一行人,站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来看,鸦片战争后、甲午之战以前非官方或半官方派遣的出洋团体中,王韬以一介布衣儒生的身份在英国长达28阅月佐译五经,实为晚清众多为公为私的游历者中所仅见。
新媒体与新视域:
晚清文人域外旅游书与现代报刊
同治十二年下旬(1870)王韬结束欧游之旅回到香港后,有感于普法战争(1870—1871)中法国的惨败与欧陆诸国的转型,遂参据西文报刊资料着手完成了近代第一部记述海外战争的著作《普法战纪》。自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初,《申报》上开始连载录自香港《华字日报》的《普法战纪》,一直到同治十二年的六月十二日(1873年8月4日)为止,刊出长达11个月之久,总计25篇长文,几可视为草创初期的《申报》上持续连载最久的专题论说。这段期间读者只要翻阅《申报》,很难忽略王韬的《普法战纪》。有感于百年来称霸欧陆的法国竟在普法战争中一蹶不振,遂由香港英文报社主笔张芝轩口译,王韬润述编纂,共同将外文报刊的战争消息与国际情势的分析进行编译。为了兼顾新闻时效性,“午夜一灯,迅笔瞑写,积同束笋,篇帙遂多” [1],夹叙夹议之际,《战纪》更采取中西历史对照的视野,评论战争起源、经过与法国战败之由,以为国人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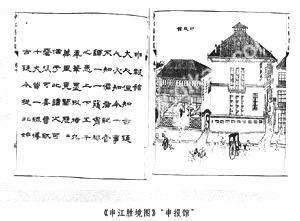
追究起来,王韬在香江撰成这部首次“由中国人所写的史实确凿的欧洲战争史” [2]并在《申报》上连载,实由王氏早年与上海文坛的渊源关系匪浅。作为第一代“洋场才子”的代表人物的王韬,率先在上海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创办的墨海书局助译圣经历时13年,与当时最现代化的出版机构渊源甚深。1862年虽因上书太平天国事件遭清廷通缉,避祸至香港的王韬仍与上海文坛往来密切,《申报》创立后的第9天(1872年5月8日)就曾介绍王韬与黄平甫在香港报业的成绩,视为启发《申报》创办机缘并引领沪上报业潮流的典型人物。出于这样的视野,加上与主编钱徵的深厚交情,王韬《战纪》成为《申报》创办初期最重要的系列连载文章,早有脉络可循。也可见当时从沪地逃亡遁居香江十载有余的他,在上海报界与出版业已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故沪地读者屡屡可在《申报》上见到转载自《香港华字日报》的王氏笔墨,申报馆亦以上海为中心,在全国各地的报社据点寄售他在香港出版的各类书籍。
《普法战纪》刊行后引起陆续回响,奠定了王氏鼓吹思想启蒙与社会变革的知识领袖地位。此书流传至东瀛,也在日本知识圈掀起热烈讨论,一时洛阳纸贵,有压倒魏默深《海国图志》之势。光绪五年(1879),在日本已被誉为“当世伟人”的王韬应邀赴东瀛游历,也享受到大师级贵宾的礼遇,回港后,王韬将他4个月的所见所闻写成《扶桑记游》,为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西化成就与政治社会实况,留下可贵的“当代”见证。
历来学者都将王韬这趟为期两年多深入了解当地民情风俗的欧洲之行,视为《普法战纪》成书的重要因缘,五十余岁的这趟扶桑之旅,自然也是三万里漫汗之行的连锁效应。东西洋见闻的亲身经历,直接造就了这位眼界开阔、极具变革前瞻意识,跨越中西文化隔阂的开明知识分子,足见泰西之旅在王氏个人生命史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的关键角色。
重新检视过去一向被忽略的出版史料与报刊资料,重构王氏《漫游随录》其人其文和彼时上海报章界的紧密关系,藉由文化语境的追索,这不仅可以为《漫游随录》的接受史补上最初的一页,更有助于拼凑王氏晚年作为一个最早的上海职业作家之完整面貌,并藉此一窥此部欧游见闻录所描绘的泰西城市景观与政治社会的新视野,为晚清中国文化界注入崭新的世界想像。

从报章资料推究《漫游随录》刊行的时间与王氏生平经历作一对照,我们会讶异于这部书是在作者游欧后约20年(1887),方于上海《申报》馆发行的通俗刊物《点石斋画报》上按月以一文一图的篇幅登出,直至1889年才连载告终。因此严格说来,《漫游随录》几乎是一部作家晚年追想廿年前西土壮游的回忆录。这个认识有助于我们梳理王韬的生命史,更深入理解该书面世的波折历程。
相较于多数在太平天国后来沪的江南文人,王韬为了维持生计,乃于当时仍颇具争议的洋人传教士麦都思开设的墨海书馆任职,担任的主要是翻译《圣经》的“秉笔华士”工作。这段期间,心中未卸下夷夏大防的他虽然仍觉得郁郁不得志,权且栖身在洋人处求得温饱,却也因缘际会地结识了影响他一生命运、友谊甚笃的几位“麦家圈”西儒传教士:美魏茶(William Milne, 1815-1863)、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魏雒颉(William Lockart, 1811-1896)等人,虽都属神职工作者,但因他们渊博的人文或科学知识,也同时为鸦片战争后的上海文化圈注入第一波现代性思潮,间接地传播了西方思想文化与格致之学。与洋人走得近,以及最主要是对清廷政治腐败与社会乱象的不满,1862年回乡(苏州)探亲时,王韬化名黄畹向太平天国的苏福省民政长官刘肇献策 [3],详述攻克上海的具体谋略,未料此书中途为清军截获,朝廷以通贼的嫌疑犯通缉王韬。王韬最后只得避祸至香港,此去一别就是二十二年,57岁时(1884)王韬终于得到默许回到睽违已久的申江。
照这样看来,再次返回曾度过生命精华期(21-34岁)的上海,王韬于此陆续发表他多年累积的文稿,自属必然。可耐人寻味的是,若细致比对著作出版的时间先后,就会发现王韬返沪后首次在刚创刊不久的《点石斋画报》上刊出的作品其实是“聊斋体”的文言小说集《淞隐漫录》,过了三年,《淞隐漫录》登毕,才由《漫游随录》走马上阵,并逐期连载至1889年底。因此可以说从1884到1889年长达五年的时间,王韬的作品一直以一个月三期、图文对照的方式,持续在沪上最畅销的通俗画报上曝光,这固然透露了1880年代上海已逐渐形成相应的文艺环境,容许王韬这样的“期刊专栏”职业文人存在,更说明了沪地的报章界成功地透过图像挂帅的通俗刊物打造市民的阅读口味,使大众媒体的竞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通俗《画报》老幼白丁皆解的普及性,以及不乏“猎奇”趣味地从图像中遥望泰西世界的新鲜感,这是王韬的《漫游随录》得以在画报上连续刊登两年以上最主要的原因。《点石斋画报》不仅宣告了图像为主的阅读即将在文字挂帅的报刊界中占据一席之地,也让1880年代上海的文艺圈开始兴起一股以“图像”捕捉上海这个新兴城市的风潮,如《海上繁华图》、《飞影阁画报》(吴友如创办)、《申江胜景图》(申报馆出版)、以及1890年代的《申江时下胜景图说》等等。这样的环境,使睽违申江22年后的王韬在《点石斋画报》逐期登出图文相配的《淞隐漫录》成为可能。刊出后,因为反应热烈,申报馆还将之结集成册,以《后聊斋志异》的名目重新印行。更值得注意的是,《点石斋画报》立下一个报刊史上的创举:即每幅图画酬资两元的稿酬, [4]这是目前仅见的“最早投稿报刊有润的现象”。推算王韬在画报上连载文章,每月也有“四十佛饼”的稿酬,名副其实的职业作家身影已逐渐浮现。
据此可知,时移事往20余载后,当年的海角羁人如今风光返沪。在香港也曾出版过东瀛游记《扶桑记游》(1879),一向不忘经营笔墨事业的王韬在1887于《点石斋画报》推出廿载前游欧的《漫游随录》,除了迎合阅读市场对此类游记的青睐,更有画报主编打铁趁热的成分。从该书自1887年10月起一直连载于通俗画报直至1889年2月来看,《漫游随录》经得起市场考验逮无疑义,通俗刊物《点石斋画报》的大量发行,更使王韬这位“文坛健将,墨海闻人” [5]成为名副其实沟通东西洋文化的欧西经师、日东诗祖。
从作品的流通性以及读者的回响来评估《漫游随录》与清廷的外交史与官方出洋纪录的差异,会发现,固然自同治五年(1875)起,清廷迫于局势与外来压力不得不派遣常驻使节,已开始有了晚清帝国与泰西各国官方的往来纪录,但使节团的“日记”或“闻见录”多少都被归类为官方外交档案,仅有历届钦差大臣及使节团才能读阅,实际刊行者寥寥可数。何况第一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郭嵩焘在被派往英国(1875)途中写下的日记《使西纪程》在光绪三年(1877)出版刊行后引起极大的争议,六月一刊行就“有诏毁版”,在国内招致弹核与物议,郭的黯然去职与此书有直接关系。

郭嵩焘的日记被后来的钦差大臣奉为圭臬,但出版日记一事引起的负面效应却也让人望而生畏。勉强算得上曾经在书市流通的是曾担任郭之翻译官的张德彝所刊行的《航海述奇》。但这八本题名为“述奇”的出使日记就有五本从未刊行,迟至1980年代才被重新挖掘出,予以重视。 [6]皆可说明晚清此类官方使节的记闻不易流传,士人或一般读者没有机会阅见的原因。
缘此,方显得1887年开始在上海报刊出版业与文艺圈流传的《漫游随录》不可取代的重要性。王韬在畅销的通俗画报上连载《漫游随录》反映出“图像叙述”冲击了沪地的文化生产与传统的知识接收模式,这帮助我们贴近历史语境:彼时上海作为远东第一大港埠,《漫游随录》与沪地文化思潮互相形塑,为彼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新型文化人的实践模型,允为19世纪末传统士大夫阶层吸纳引渡现代文明、内化现代性感知结构与文化行为之重要管道。王韬的泰西游记相映成趣地折射出沪上一地都市文化的转变轨迹,为晚清上海社会风貌的递嬗推移留下了珍贵的纪录。
想象世界:图像中的泰西文明
1867年前后一游伦敦的王韬,曾对富丽堂皇的邮电总局印象深刻:
偶过电信总局,入而纵观。是局楼阁崇宏,栋宇高敞,左为邮部,右为电房,室各数百椽。局中植奇花异草,有子母树,其叶如艾似榕,叶上生叶,为远地携来。总办师蔑导览各处,堂中字盘纵横排列,电线千条,头绪纷错,司收发者千余人,皆绮年玉貌之女子。(第96页)
即使是20年前的伦敦印象,迟至1880年代末才在《点石斋画报》上连载刊出,这段文字置诸彼时的文化场域,仍让还未开设国营邮电企业的上海市民读者充满新奇想像。特别是接在这段描写之后,王韬详述了“电学”在泰西发展的来龙去脉:

按电学创于明季,虽经哲人求得其理,鲜有知用者。道光末年,民间试行私制,而电线之妙用,始被于英、美、德、法诸国,其利甚溥,其效甚捷,凡属商民荟萃之区,书柬纷驰,即路遥时逼,顷刻可达,济急传音,人咸称便。同治七年,英议院以电线获资甚巨,遂禁私设,悉归于官而征税焉。通国设局五所,以京都为总汇,内外分局五千五百四十所,岁税金钱百数十万,可云盛矣。余至英时,盖属于国家犹未数月也。(第96页)
这段话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采用“明季”、“道光末年”、“同治七年”等中国王朝的断代纪年而非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来描述电学发展如何融入大众日常生活。除了让当时读者知晓英国政府将“获资甚巨”的电信收归国家对整体民生经济的裨益外,还清楚地呈现出比较文化的观点,一方面诱发了海上文人反思当前社会文化环境的视野,另一方面更从泰西庶民文化图景的描绘,触动上海读者形构现代性时空概念。
正如王韬笔下所述:电信的便捷在泰西行之有年,不仅成为欧洲强国每岁税收的来源,也反馈在民生经济上,深入民间,已为泰西诸国大众日常生活之不可或缺。同样的,新闻报刊作为传播事业的一环,更是促使民众告别传统的时空观念,与现代生活感知模式不断进行协商、交融的枢纽。作为海上文人中第一代报人,以及长期接触外国传教士、对洋人采取现代化印刷技术印制书籍报刊的手法 [7]认识匪浅的王韬来说,一旦踏上报章杂志等新闻事业已行之有年、具有深厚传播文化的西欧洲先进国家,比传统文人感受更敏锐的他就有了如下的细腻观察:
往一印书馆,其馆屋宇堂皇,规模宏敞,推为都中巨擘,为信宜父子所开设,其中男女作工者约一千五百余人,各有所司,勤于厥职,浇字铸版,印刷装订,无不纯以机器行事。其浇字盖用化学新法,事半功倍,一日中可成数千百字,联邦教士江君曾行之于上海。其铸版先捣细泥土作模,而以排就字版印其上,后浇以铅,笔画清晰,即印万本亦不稍讹,此诚足以补活字版之所不逮。苟中国能仿而为之,则书籍之富可甲天下,而镌刻手民,咸束手而无所得食矣。(第120页)

除了爱丁堡的大型印书厂,王韬1870年回程由苏格兰前往伦敦时,也特别拜访了理雅各的老友士排赛的制纸厂:
士君以机器造纸,一日出数百万番,大小百样咸备,设四铺于英京,贩诸远方,获利无算。香港日报馆咸需其所制,称价廉而物美焉。导观其造纸之室,皆溶化碎布以为纸质,自化浆以至成纸,不过顷刻间耳,裁剪整齐,即可使用,亦神矣哉。(第156页)
造纸厂不仅供应本国需求,也销售至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香港,间接让我们明了香港一地为何拥有全中国最早而且蓬勃发展的中英文报刊:廉价的纸,即是日报与刊物得以降低成本,成为大众消费得起的通俗读物之关键元素。
这些在《漫游随录》中错落的关于制纸、印书与日报主笔备受各界敬重的叙述,著实埋下了王韬自欧洲返回香港,隔几年后即与留美归国学生黄平甫合作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的种子,此报为香港第一份中国人自办的中文日报,极具开创意义。 [8]
除此之外,王韬也提到他在苏格兰为曾国藩辟谣的一则轶事,此事乃因爱丁堡的行政首长得到由“中国邮筒递至”的日报上刊出曾国藩保守封闭的对外政策与外交谕令之信息,当时“都中官民阅此报者,疑中外必因此不和,遂来问余”,经过王韬将之斥为传闻讹语的澄清,“于是浮议以息”(第122页),可见报纸作为舆论公器对社会立竿见影的影响。
相较于王韬对于电信、印刷与传播媒体这整套环环相扣的知识系统,及其作为舆论公器促使社会观念产生变革的掌握,稍早(1884)出版欧游杂记《谈瀛录》的另一个沪上文坛大老袁祖志较关注的毋宁是“新闻纸”在泰西城市生活流布层面的广泛:
新闻纸分售于街头巷尾小亭中,或持于手中沿街叫卖,至于客寓饭店咖啡馆中,则设有专看新闻纸之房间,堆积横陈任人坐阅。 [9]
新闻纸按日分送各户,凡客寓饭店咖啡馆,无处不备,以供人目。故随在可以索观,且不需钱。……分售新闻纸之法,沿街皆有大铺,大率皆属女流,亦有擎于手中逢人求售者,倘至暮夜不能销售净尽,亦准将所余送还馆中。 [10]
这些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描述,如果放在当时虽有几个大型报馆发行日报、但“新闻纸”种类不多且尚未普及于各阶层、遑论免费阅看 [11]的上海报业流通网,袁祖志的观察恰恰为新旧交接、中西掺杂的社会语境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文化指标。
上面的分析,都说明了19世纪末叶上海新闻纸的流通与专门类型的刊物的出现,除了洋行或外商的雄厚投资外,相当大的程度取决于报社编辑与主笔群的文化视野与创造活力。王韬与袁祖志笔下,欧洲名城公共舆论成熟、资讯相对流通,报人地位崇高与新闻纸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凸显出报纸媒体不仅仅作为一种跨文化讯息流通的载体,更是文化传译与思想启蒙的便捷渠道,为晚清报人群体提供了广阔的实践空间,亦悄悄地带领上海市民形构出与时俱进、有机生成的公共舆论意识与现代性时空感知。
与庶民大众息息相关的交通运输,及左右日常生活节奏的各种民营企业,也具体而微地出现在王韬的游记中。诚然,海禁开放后40年的岁月,开埠通商后迅速发展的上海城也已有了第一波现代化的傲人成果。经过规划的公共设施、便捷的交通工具与为了接驳中、短程航运而设置的轮船企业(如轮船招商局等官督商办的大型企业),或民用企业的出现——银行、西式街道、煤气灯、电话、电力设备、自来水等等, [12]似乎说明了上海洋场这个巨型的“国际村”已有足够的文明条件堪与西方世界接轨。
然而,此现代生活环境──器物的革新或局部的现代化设施──毕竟只集中在洋人主事的“夷场”(租界),相对于华界,它们固然带头示范了规章井然、秩序分明的先进城市图像,但也往往停留在予人窥看炫异西洋景、域外奇观的模式,无法促成群体思维模式的转变,进一步打破因袭传统的思考惯性,形成文化变革的动力。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1876年中国第一条在上海营运的铁路──吴淞铁路──正式通车后仅三个月就被拆除的风波:当时囿于观念未开而导致的强大反对声浪,不久就由清廷向英商买回,将其拆毁任其锈蚀。
铁路被“妖魔化” [13]的事件具体展现了近代中西文化融合过程的缓慢与艰辛,即使到了1880年代中叶,翻开当时的报纸,从许多创设公共设施的议题:诸如华界是否独立兴建自来水工程的社论文章所引起的争议 [14],就透露出沪地各界新旧各派不同立场与舆论角力的激烈程度,侧面反映了保守势力的顽强。
也因此,王韬混合了传统文人与开明人士的特殊身份,让《漫游随录》呈现的欧洲城市生活之具体样貌,一来不乏提供读者“域外猎奇”的阅读乐趣,二来更扮演了文化斡旋与协商中介的重要角色。叙述者亲履异国城市且参与其中,肤触实有的逼真感受,更屡屡在书中流露。如《制度略述》一篇详细描述1860年代末叶的火轮车,更透露了在洋人圈子长达17年,对泰西事物已相当熟稔的王韬,仍然对伦敦利捷的轮车交通有“百闻不如一见”的惊叹:
泰西利捷之至,莫如舟车,虽都中往来,无不赖轮车之迅便。其制略如巨柜,左右启门以通出入。中可安坐数十人,下置四轮或六轮不等。行时数车联络,连以铁钩,前车置火箱,火发机动,轮转如飞,数车互相牵率以行。车分三等,上者其中宽绰,几席帷褥光洁华美,坐客安舒;中者位置次之;下者无蓬帐蔽遮,日曝雨飘,仅可载粗重货物或栖息仆役而已。其行,每时约二百里或三百余里。辙道铸铁为渠,起凸线安轮,分寸合轨,平坦兼整,以利驰驱,无高低凹凸、奇欠斜倾侧之患,遇山石则辟凿通衢大道,平直如砥。车道之旁,贯接铁线千万里不断,以电气秘机传达言语,有所欲言,则电气运线,如雷电之迅,猝不及避,有撞裂倾覆之虞,故凡往来起止预有定期,其当车路要,置驿吏邮役昼夜守立,严谨值班,须臾不懈。余居英商士排赛家,每至李泰国家晚餐,车必由地道中行,阅刻许始睹天光,或言地中两旁设有,灯光辉煌,居然成市集。(第96页)
火车通讯以“电气”传达、一丝不苟的严谨铁道管理,以及地铁中商机无限的隧道市肆都给王韬留下深刻印象。
文中提到上海也曾有过铁路与火车,只是“未一载即毁去”,王韬虽然没有说明火轮车未能行于中土的来龙去脉,但文末的“虽起古人于九原,亦当惊为奇绝”这段话,却颇有引古人为自己的论点作注脚,并说服读者大众的言外之意,这段话置诸当时还未有铁路营运通行的中国,自有提供文化参照座标的积极意涵。这也让人想起王韬在《制造精奇》一文所云,他在伦敦结识一位卖酒女子的父亲,此人乃“司理轮车铁路者”,提到英国初创轮车时,“国人莫不腾谤,蜂起阻挠,谓举国牧御由此废业,妨民恐多”,也曾有过巨大的抵制声浪。但车子通行后,“岂知轮车既兴,贸易更盛,商旅络绎于途”(第106-107页),方始获得民众的接纳与认同。甚且有阿士贝创造“凉油”,使火轮车“行久而轮不热”因而获得巨利,由一介平民成为富甲一方的名流,侧面呈显此新兴交通利器带来的财富冲击了旧有的社会阶级观念。至于王韬在文中列举火轮车有助于迅速平定国内变乱,也可避免征夫骑行荒野遭遇强盗劫匪意外的好处,也说明了迅捷的火轮车带来“时间观”的巨变,将促成国家军卫脱胎换骨,彻底贯彻施行公权力。
王韬在游记书写中自然流露的评论与感触,对照彼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现状,饶具意义。当王韬1887年在通俗画报上强调火轮车对欧西诸国民生社稷的诸般贡献时,自有间接诱导庶民大众接受先进国家业已普及的新兴交通工具,与世界思维接轨的积极意义。
固然早先几个熟悉洋务的名臣名士著作已提到了外国的铁路与火车造就的社会政治变革,但他们皆不曾越洋履足欧美诸国,未若王韬眼见耳闻身试的临场感受;更从现代媒体与出版业革新信息的接收与传达的角度而言,《漫游随录》这部在上海书市与全国报刊网络中通行的旅游书,就不仅提供了未能出洋或即将出洋的读者第一手的导游指南或旅行资讯,还是启迪读者大众接受新型态的城市想像,扮演创造新文明视域、成就文化变革之契机的重要推手。
上述分析皆清楚说明,作为现代化启程第一站的器物、科技文明与生活环境的改善,此可触可感、充塞在食衣住行各方面的具体成效,将点点滴滴地酝酿成新思维,造成文化启蒙与思想观念的变革。王韬在《漫游随录》中描绘泰西诸国物质条件或日常生活所见所闻,看似片断琐碎而非脉络化的抽象哲思论述,在“报章媒体”与大众出版品的扩散效应中,实为晚清上海读者最易接受的文化信息,它们所释放的新文明气氛,连带地为19世纪末叶众多或以沪地为本位的“上海学”著作或通俗读物,开辟出向外眺望或从他者的凝视中反思内视的深刻视野。王韬的域外见闻录为彼时沪上那些徘徊在接受或抵御新文明视域的社会中坚份子,提供了可资追寻、或不复朦胧的现代性世界图像,在缓慢而复杂的文化转接磨合期中,也投映出近代海派文人立体明晰的历史造像。
注释
[1]王韬:《普法战记》,大阪:明治廿年九月大馆印行1887年版,凡例。
[2]忻平:《王韬评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页。
[3]王韬撰,王稼句点校:《漫游随录图记》,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以下引文仅在括号内标注页码,不再作注。
[4] 见1884年6月6日《申报》头版登出的《请各处名手专画新闻启》,其中注明“每幅酬资洋两元”。
[5]1887年12月28日《申报》。
[6]见钟叔河《航海述奇序》一文,收入钟叔河《从西方到东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408页。
[7]王韬曾描述1849年他在墨海书馆见到的以兽力牵动机具、半自动化的印书景象:“墨海书馆以活字版机器印书。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翻,诚捷巧也”。见《漫游随录》,第23页。
[8]老冠祥《王韬与<循环日报>》。见林起彦、黄文江主编《王韬与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5-358页。
[9]袁祖志《西俗杂志》,收入《谈瀛录》,上海:同文书局1884年出版,第2页。
[10]袁祖志《西俗杂志》,第19-20页。
[11] 1870年租界茶馆曾有提供茶客阅看《上海新报》(字林洋行的本地新闻)招揽生意,如福仙茶园在报上打出的广告(1870年4月12日)。但这个例子却恰恰证明了新闻纸仍属于有闲阶级的消费,而非庶民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12] 见上海通社编《旧上海史料汇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13] 李岳瑞记载1860年代北京最早的铁路引起民众恐慌的事实:“同治四年七月,英人杜兰德,以小铁路一条,长可里许,敷於京师永定门外平地,以小汽车驶其上,迅疾如飞。京师人诧所未闻,骇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至大变。旋经步军统领衙门饬令拆卸,群疑始息。”可以想见修建铁路与火车运行在当时遭到的强烈抵制。见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卷下,台北:文海书局1967年版,第56页。
[14] 见1883年3月29日《申报》《论沪城改用自来水》;1883年4月15日《论自来水工程》。
吕文翠: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
栏目策划、责任编辑:唐宏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