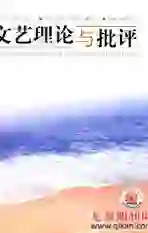“女性文学”:繁荣背后的危机
2009-06-18刘卫东
刘卫东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从无到有,并且以令人咋舌的速度发展壮大。一套套丛书不断问世,各种研究协会活动频繁,“女性文学”从作家作品到理论研究都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这无疑显示了“女性文学”的巨大的影响力和未来发展空间,但是,“盛世”之下,也存在着一些隐忧,如果能够得到较好解决,相信“女性文学”可以进入新阶段,否则,可能因无路可走而偃旗息鼓。
1、“女性文学”存在的合法性
“女性文学”为什么能够存在,而且能够具有独立性,是“女性文学”理论首先需要关注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合理解释,整个“女性文学”理论根基就不稳定,而就目前来看,对此问题的回答尚存在诸多不完满之处。如果要标举“女性文学”的话,不仅要说明文学需要分性别,而且要说明“男性文学”为什么不存在,这是一个具有相当理论难度的命题。在“女性文学”理论家看来,作为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文化”也是有性别的,有论者就这样说:“人类文化并不是没有性别的东西,绝对不存在超越男人和女人的纯粹客观性的文化。”强硬地给文化贴上性别的标签,不仅令人哑然失笑,也暴露了“女性文学”理论先天的不足乃至新的“性别暴力”,除了祭起性别的“上方宝剑”,“女性文学”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束手无策。然而,“性别论”可以是一个观察问题的视角,但是若被当作“真理”,就会抹杀文化创造过程中的各种复杂因素,犯形而上学的错误。举例来说,一座建筑中的“文化”不全是男性的,就如同一条锦缎中的“文化”不全是女性的一样。显然,按照“文化有性别”的逻辑去证明“女性文学”的存在并不能取得预想的目标。退一步说,即使上述结论成立,对“男性文学”如何理解,也是一个问题。当然可以解释说,由于男性在社会历史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整个文学就是“男性文学”,而“女性文学”就是与之对立不同的文学。从理论上来讲也许没有破绽,但是看看所谓的“女Jl生文学”就可以知道,“女性文学”并不能推出与“男性文学”完全不同的作品,如同女性不可能建立一个没有男性的世界,因此,并不存在完全属于女性而不属于男性的文学。从这一点看,“女性文学”是建立在“怨恨政治学”平台上的写作,立场、态度实际要大于写作的内容。
在“女性文学”理论中,“女性意识”是一个关键词;是否触及“女性意识”,也是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女性文学”的重要标准。关于“女性意识”的定义,基本没有分歧。女性意识到自己的性别和在性别结构中的被压迫地位,并予以讨论,便是“女性意识”。有论者在谈到“女性文学”的基本内涵的时候说:“在本学科领域内,‘女性这一概念的质的规定性是女人性别意识的自觉,是女人的主体性。而女性文学概念的质的规定性,是女性作为创作主体和言说主体在文学中对自己主体位置的探寻和实现。所以,并非凡女作家所写的就是女性文学。”这段表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般来说,“女性意识”被作为“女性文学”的主要特征。在一些理论家看来,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女性写作”是一片空白,一直到“女性意识”觉醒,才开始有了所谓的“女性写作”。拿“女性意识”来界定女性文学必然会遇到一个问题:“女性意识”并非理论家设想的那样,是一个稳定的女,陛群体的诉求,而是根据不同情况,呈现出千差万别的景观。比如,在黑人女性理论家看来,女性主义运动只不过是白人女性的诉求,甚至是某些白领女性的事情,而与她们并无关系。说到底,“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同社会历史发展紧密相连的,没有第三次工业浪潮带来的新的不需要性别区分的岗位(坐在写字楼办公)和一定数量可以经济独立自食其力的女性,“女性意识”便无从谈起,而用某个历史阶段、某些女性群体才出现的“意识”去统摄人类历史中的女性写作,无疑是以偏概全,且漠视了大多数女性的诉求。
女性主义理论认为,作为“第二性”,女性长期生活在“黑暗大陆”之中,成为沉默的一群,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李银河的说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长期以来妇女所面临的选择或者是被排除在权力机制之外,或者是被同化在男性的阴影里,妇女独特的价值一直难以实现。”女性能够改变这一状况的途径,惟有通过写作。在女性主义批评者的视野中,“女性写作”是女性的自我救赎,也是女性表达自我的惟一手段。正如理论家西苏倡导的那样:“只有通过写作,通过出自妇女并且面向妇女的写作,通过接受一直由男性崇拜统治的言论的挑战,妇女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她主张,女性通过写作,从潜在状态中“飞翔”出来,从而获得真正的自我解放。这是“女性写作”存在的根基。这种理论不仅在西方大行其道,也被中国的女性主义理论家接受和发挥。孟悦、戴锦华的观点是:“对那些毫不隐讳自己的女性身份的作家而言,写作与其说是‘创造,毋宁说是‘拯救。是对那个还不就是‘无但行将成为‘无的‘自我的拯救,是对淹没在‘他人话语之下的女性之真的拯救。”女性通过写作,能够获得一定的话语空间,更重要的是获得表达自我的权力,是“女性写作”被女性主义理论高度重视的原因。虽然福柯的“话语即权力”的说法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的女性认为这样就可以拯救自己,恐怕还是一厢情愿,因为“女性说话”与女性真正的“女性独立”毕竟是相去甚远的两回事。女性能够拿起笔书写自我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这是毋庸质疑的,但是这并不能代表胜利,“女性写作”仅是女性通往自由之路的条件之一,远远不能作为女性解放的终结和目的。
“女性文学”的存在,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又是一个实践问题,而后者可能更为重要,我们有时候对“女性写作”之所以失望,也是由于“女性写作”理论指出的道路过于飘渺,镜花水月般缺乏现实的实践功能。
2、“女性写作”写什么
如果“女性写作”提供的“女性文学”与“非女性写作”并没有什么不同的话,就可以宣告这个所谓“女性文学”只不过是概念游戏,这种结果显然是该理论的倡导者所不愿意看到的。女陛主义理论家在论及“女性写作”的时候,总是要标举出一些作家和作品来验证理论的正确性,而通过考察这些作家作品,往往可以发现“女性文学”进退两难的尴尬之处。
对于“女性写作”的题材,理论家给出过毫不含糊的回答。西苏认为,女性写作是“反叛”性的,“她必须写自己”,而这个理想只能通过“写身体”实现:“通过写她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女性的身体在传统(男性)文学史中确实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曲解,而这一切并没有获得女性的首肯;女性要求书写自己的身体,并没有问题。实际上,女性的身体经验是男性永远关心却又无法涉足的,也注定是女性写作的“独门绝技”。
当“身体”成为“女性文学”的突破口和主要阵地时,不能不说,文学确实经历了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革命”。女性尽情挥洒自己的笔墨,展示了自己身体成长的各个阶段,将从未暴露过的“经验”曝光于众目睽睽之下。或许女性认为这是一种勇敢的“革命”,一次冲决男性垄断的努力(他们占据了书写人类共同经验的统治地位),但始料未及的是,她们的“身体”并没有带领女性走向独立,却成了满足男性窥视欲望的对象。非常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当波伏娃的名作《女性——第二性》被引入国内时,出版社把原书第一部分女性主义理论历史删掉了,只保留了第二部分女性身体和心理的发育演变史。一部女性主义的“圣经”竟然变成了打性擦边球的通俗读物,女性主义者自然可以对这种现象表示愤慨,但是却不能阻止类似现象的发生,有时候甚至还不得不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这也是写“身体”无法躲避的怪圈。这样,“女性文学”就成了极其尴尬的写作:女作家试图通过写身体获得女性表达的权力,引来的看客却只对女性身体感兴趣,至于女性地位,几乎没有改变。
就当前我国“女性文学”写作的现状而言,上述问题已经到了必须面对的时候,是否能够从“写身体”的怪圈中摆脱出来,直接决定着“女性文学”的生死存亡。在谈到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时候,陈染、林白是不能不被提及的,尽管引来不少非议,但还是作为“女性写作”的标志性成果被载入文学史。有人认为,陈染等作家“把女性个体生命成长过程中极隐蔽的甚至被视为文化禁忌的私人经验带进文本……并不是哗众取宠,更多的是表现女性在男权中心社会里创伤性的生存体验,生命被压抑的愤怒,具有尖锐的挑战男权文化和女性文化自我建构的意义”。这段评论旗帜鲜明、态度明确,显然从躯体修辞学的角度对“女性文学”的“写身体”倾向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果陈染等的写作具有“挑战男权文化”和“女性文化自我建构”的意义的话,紧随其后的卫慧、棉棉的作品在“身体写作”方面要走得更远,私人经验暴露得也更多。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卫慧和棉棉的作品却遭到了否定,理由是“写身体”。有论者认为卫慧们“放逐”了“精神”,“利用‘身体写作的幌子去美化自己那个已经被污染了的身体”,是“中国大地上疯狂上演的一出令人难堪的‘丑剧”。同样是女性写作和“写身体”,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评价?说到底,女性写身体有一个尺度的问题,卫慧、棉棉作品中的性描写以及同时带来的炒作风潮,在捧红二位主角的同时也彻底葬送了“女性文学”,最终使“女性文学”由反抗变为撒娇。随着卫慧、棉棉相继停笔和出走异国,喧嚣一时的“身体写作”也走向终结,木子美、九丹似乎仍想在这块土地继续耕耘,然而却颗粒无收,甚至折了本钱。女性从“身体”试图取得突破,寻找到自我,但是最终也由于过度写“身体”而迷失,可见,“身体写作”仅仅是“女性写作”的入口,而不是目的地。
3、“女性文学”的“理想”和“未来”
女性问题不是女性自身的问题,而是两性或整个社会政治、结构的问题,经过了单纯的“批判”与“反抗”,女性主义者的态度已经由愤激转变为平和,也希望从“对话”而不是“对抗”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这是女性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变化。
似乎是国情的原因,中国的“女性文学”对所谓“男权社会”的反对并不那么激烈,也罕有明确执此立场的理论家,绝大多数女作家甚至不愿意自己被归为“女性写作”的行列。不少女性作家曾表态,希望自己在写作中采取一种“超性别”的视角,既与传统的“花木兰”式写作区别,也不采取纯粹的女性立场,而是以超越性的“人”的关怀来考察社会和历史。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出了“雌雄同体”的概念,指能够同时具有男性与女性思维能力的人,并且提倡集男女性别长处的思维方式。她说:“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性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能够从男性与女性和谐发展的视角看待问题,脱离“性政治”思维模式,是解决“性别战争”问题的关键。刘慧英说:“我比较欣赏西方某些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建立和发展‘双性文化特征的设想,它是拯救和完善人类文化的一条比较切实可性的道路。”无论是对男性还是女性,这个理论都有强烈的诱惑力,尤其是对于试图走出男女对抗模式的“女性文学”来说,无疑是一个值得试验的主张。在中国,也有一些女作家对此理论进行了发挥和阐释,并且进行了具有探索意义的实验。铁凝说:“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叫做‘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在铁凝看来,“第三性”的视角超越了男/女性别对立,直接面对人性深层、本质的东西,关注“人”共同需要面对的问题。毫无疑问,这样的设想是没有问题的,似乎也有着光辉的前景,但仔细分析后可以发现,这不过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女性不可能找到“第三性”视角,即使再客观,也不能超越本身的局限性,就像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超性别”视角与其说是女性写作理论的发展,不如说是对女性过度强调性别倾向的反拨。
从创作本身来看,“超性别”视角所带来的,更多是对女性自我的审视以及对男女关系的重新考量。在陈染和林白的许多作品中,几乎没有男性出现,他们被作者放逐到了文本深处,成了不能发出声音的群体。陈染和林白营造了一个没有亚当的伊甸园,女性在其中自得其乐,自给自足,甚至不再需要男性的爱情,这与以往女性等待男性唤醒的“睡美人”情结大异其趣。虽然陈染宣称自己不是一个同性恋者,但是她认为同性间的爱才是真正的爱情,而异性间只有欲望和罪恶。女性当然不可能造一个可以性别独立的“女儿国”,而陈染所设想的完全抛弃男性的世界也不可能存在,不过,女性希望掌控命运的努力在这里得到了彰显。跳出传统文化所规定的贤妻良母的老路,获得自身的意义,是女性主义对“新女性”的要求,也是女性的理想,但这不过是女性的幻觉而已,正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提出的,女性的出走如果不是伴随自身的经济独立,结局只能是“堕落”或者“回来”。徐小斌的《羽蛇》是女性对自身命运的书写的一个寓言。主人公羽一直在试图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与陈染、林白小说中的女性不同,羽做了脑叶胚手术,变成了一个无欲无求的普通人,她反抗的性格也随着她身体的“修正”而消失了。小说如此叙述羽的挣扎:“脱离了翅膀的羽毛不是飞翔,而是飘零,因为它的命运,掌握在风的手中。”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反抗之后,徐小斌已经看到,女,陛的悲剧命运是被注定的,无论做什么努力去抗争,都无济于事。虽然她的结论可能过于悲观,但是也不能否认,多年的女J陛独立的口号喊过之后,女性的命运和地位都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改变。
从接受的角度考虑,“女性文学”应该听取男性的意见。“女性文学”虽然圈出了自己的地盘,但也设置了路障,让男性逡巡徘徊在圈子之外,授受不亲。对于红红火火的“女性文学”,男性理论家普遍反映冷淡,私下里有非议的不在少数,但是却没有公开直接批评,因此,“女性文学”基本上处于自娱自乐的状态,只在自己的圈子里热闹。实际上,出自异性相吸的原因,男性对女性的观察和揣摩并不比女性少,文学中的伟大女性,也多出自男作家笔下,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苔丝等女性的形象生动鲜活,丝毫不输于女作家塑造的简·爱、郝思嘉。如果把女性形象全都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妖魔化”,无法否认,男性对女性的爱与关怀虽然出自本能的要求,却构成了人类精神史上可歌可泣的感情中一个重要的部分,这也是伟大文学的来源之一,正如王富仁所说:“不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都存在一个思想境界和艺术境界的问题,都存在一个艺术创造的问题,都不能仅仅依靠自己现实生活中那点狭隘的、零碎的直感经验的记录式书写,就能创造出真正杰出的作品来。”无论怎么说,像《红楼梦》、《哈姆雷特》这样的作品,在接受的时候,是不用考虑作者的性别的,当然,读者也不用考虑自己的性别。
“女性文学”仅停留在理论上,而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文本,说明该理论尚有缺陷,需要进行弥补和缝合。不过,这样似乎仍然难以脱离“男/女”二元思维框架,也许,消弭了“女性”的视角,摘掉“女性文学”的有色眼镜,使写作重新回到写作,焕发出书写本身的光彩,才是女性真正拯救之路。进入到“当代”社会中,展示出“新女性”的诉求,帮助更多女性和男性认识到这种诉求,进而推动社会生活的变化,不仅是“女性文学”,也应该是当代文学的理想。从这个角度说,当“女性文学”可以休矣的一天,也是“女性文学”真正获得胜利的一天,而这一天或许已经不太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