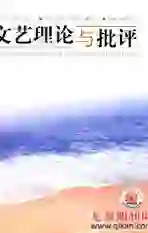俄罗斯文学界关于新现实主义的讨论
2009-06-18张捷
张 捷
众所周知,在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现实主义曾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流派。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现实主义,或称批判现实主义,曾创造过辉煌的业绩,它的许多作品后来作为经典,不仅载入俄罗斯文学的史册,而且进入世界文学宝库。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革命运动的兴起,出现了一批革命作家,他们在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有所创新,这使得他们的作品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学的萌芽。另一方面,这时的现实主义文学也受当时各种现代主义流派的影响,某些作家在其创作中吸收了现代主义的某些手法,结果他们的作品与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有着明显的不同。当时有人曾试图用“新现实主义”这一术语来表示这种现象。
十月革命胜利后,现代主义文学逐渐退潮,到1930年代初基本已终结,而社会主义新文学得到迅猛发展,开始占有主导地位。于是出现了如何对它进行理论概括和命名的问题。当时有多种建议,最后决定将其定名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1950年代上半期,社会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股批判主义浪潮,同时沉寂多年的现代主义以及其他文学流派重新抬头,西方新的文学思潮开始得到传播,这不能不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艺术表现手法变得十分多样。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已不能完全说明新文学现象。于是1970年代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体系”的理论,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艺术形式的历史地开放的、不断丰富的体系”,可吸收其他体系的诗学成分。这一理论曾得到文学理论界不少人的赞同。
“改革”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遭到攻击,旧有的文学思想和文学观点完全复活,西方的文学思潮大量涌入。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原有的和从西方引进的各种非现实主义的理论和观点曾一度占有主导地位,甚至出现过一股“后现代主义热”。不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遭到彻底否定,而且一般的现实主义也受到了冲击。尽管许多传统派作家仍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一段时间内,现实主义被一些人看作过时的、落后的东西,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和挤压,处境比较困难。有人甚至宣布现实主义已经死亡。与此同时,各种非现实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诗学成分开始渗入传统的现实主义,使它发生了某些变化。从而引发了理论界关于新现实主义的讨论。
一
批评家斯捷潘尼扬早在1992年就指出这种现象。他在《现实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结束阶段》一文中分析了这种现象,把那种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某些诗学成分,然而其作者仍相信“最高的精神本质的实际存在”并努力使读者注意这些本质、试图把对世界的传统看法和主观的看法综合起来的作品称为“新现实主义”1996年他在《现实主义是孤独的克服》一文里重新提到这个问题,说他在四年前就指出“文学中的新现实主义时代”正在到来。
批评家莱德尔曼和利波韦茨基父子在他们合写的题为《死后之生,或关于现实主义的新情况》一文中分析了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又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现象,把它称为“后现实主义”。他们指出,20世纪的许多艺术家既认为人生有意义,又不认为人生无意义,既不肯定,又不否定,只提出“人生有意义吗”的问题。这些艺术家改变了“创作构思”、“中心思想”等概念的内容本身,他们的创作构思成为提出问题,而创作过程成为“紧张地逐个查看各种答案,在这样做时,肯定同怀疑和否定相互交替,而发现往往为新材料所推翻”。他们认为,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性范式”,其基础是“可作多种理解的相对性原则、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的对话性认识和作者对他们采取的立场的开放性原则”。而在这样的“艺术性范式”的基础上形成的创作方法,可称之为后现实主义。这种后现实主义的基础是一种新的诗学,而首先发现这种新的诗学的是巴赫金。在另一处,他们强调后现实主义的人和世界的概念“要求对文化的道德的和本体论的坐标作根本的改变”。显然,他们所说的“后现实主义”已不是发生了某种变化的现实主义,而是对现实主义的超越和克服。利波韦茨基在《死亡的摆脱——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的特点》一文里赞同一位论者关于“后现代主义者当中最杰出的人不由自主地走上了后现实主义的道路”的说法,说它特别重要,因为“‘后现实主义同时是后现代主义的克服和继续”,“它是以一般的后现代主义、同时也是以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哲学逻辑为基础的”。这种说法与上一篇文章里的说法是有矛盾的。按照一般的逻辑,这种文学现象不应叫做“后现实主义”,而应叫做“后后现代主义”。不过无论用哪个术语来表示,他所说的文学现象已不是现实主义的某种变体了。
批评家巴辛斯基在《回归》一文里就现实主义的演变问题,与莱德尔曼和利波韦茨基进行商榷。他认为两人的文章的基础是关于“现实主义的终结”的思想,这个思想并不新鲜,过去在俄罗斯和西方已有人说过了。在他看来,两人的文章的新颖之处在于他们在“新现实主义”中,或在“后现实主义”中,或在“存在主义现实主义”中看列了“死后之生”的可能性。接着他提出这样的看法:以普拉东诺夫在卫国战争结束后写的小说《归来》为标志,俄罗斯文学“经过本世纪的痛苦的考验回到了自己的家——俄罗斯现实主义”,并列举一批作品来加以说明。他在《谢谢!谢谢!》一文里用肯定的语气说:“俄罗斯现实主义将要复兴。它也许会像《战争与和平》里描写的百年橡树那样最后一次获得新生……”他又写了《什么是俄罗斯现实主义》一文,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说,对这个问题“我已试图在《回归》一文中做某种回答,这篇文章的主要思想是这样的:我们在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基础中发现的主要不是诗学原则,而是本体论原则,它在于作家相信神圣的世界是一种创造”。他接着说:“我们还需要回答俄罗斯现实主义在二十世纪发生了什么事的问题。已经很清楚,它作为世界文化的现象现在处于遭到毁损和破坏的状态。这说明除了创作外,需要制订某种保护和发展这种现象的非常具体的纲领。”他对《文学学习》杂志和年轻作家帕夫洛夫试图把采用现实主义体裁的当代作家组织起来的做法表示欢迎。
巴辛斯基提到的帕夫洛夫主张发扬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不仅在创作上遵循现实主义原则,而且发表文章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在《根本问题一(俄罗斯传统主义者宣言)》一文里对“传统”作了解释,他说,这“不是一成不变的条文构成的章程”,“传统为了使自己能够继承和发展,不由自主地拓宽自己的边界,把许多独特的创作世界纳入自己的范围,不过这些世界应当与俄罗斯的信仰、文化和生活具有血缘关系并联成一体”。他不同意某些人提出的文学的艺术原则本来应当革新的意见。他说:“这种
革新就其实质来说不是革新而是否定。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是不承认肖洛霍夫的创作,而漠视《静静的顿河》,就是否定俄罗斯的艺术现实主义。”后来他又在题为《俄罗斯小说的玄学》的长文中进一步说明他对现实主义的看法。他说:“现实主义的根本问题是所描绘的事物的可信性问题……以其实际的形式描绘现实,是可信性所要求的一个艺术原则。”他特别重视现实主义精神,认为“现实主义的丰富性在于它的精神的表现,而不在于流派的多少”。
另一位年轻作家瓦尔拉莫夫也宣称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他这样说过:“我的倾向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也就是说,俄罗斯文学一直崇尚的价值观念就是我的价值观念。我从来没有想推翻它。”他登上文坛后不久,巴辛斯基就注意到他,发表了评论他的作品的文章。1995年瓦尔拉莫夫的小说《诞生》获首届反布克奖,帕夫洛夫的小说《公家的故事》也在评布克奖时入了围,于是两人名声大振。他们和巴辛斯基被看作坚持现实主义的新一代作家的代表人物。有人开始用“新现实主义”这个术语来表示他们的观点和创作。
二
到1990年代中期,后现代主义开始失势,现实主义重整旗鼓,在创作上取得显著的成就。到这时,谈论现实主义不再惹人耻笑,相反,它开始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有人试图把近年来失去联系的新老现实主义作家团结起来。例如波利亚科夫就作了这样的尝试。在他的努力下,1995年2月成立了“现实主义者联盟”,并出版了文集《现实主义》。在文集的作者当中既有传统派人士,也有自由派作家;既有文坛老将,也有初出茅庐的年轻人。
在这之后不久,传统派的莫斯科作家组织的一些成员和在高尔基文学院任教的一些批评家以及在《莫斯科通报》杂志工作的一些人于1997年举行了首次关于新现实主义的研讨会。发起人为卡兹纳切耶夫、米哈依尔·波波夫和帕拉马尔丘克等人。事后卡兹纳切耶夫这样回忆他们当时如何决定使用“新现实主义”这一名称的过程。他说:“‘新现实主义流派是自然产生的。米哈依尔·波波夫提议把这两个词作为1997年3月召开的研讨会的口号。开头我一般说来比较喜欢‘新的俄罗斯小说这一术语,但是围绕‘新现实主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是什么?给一个定义吧!争得不可开交,需要对这问题好好想一想。我就着手重新分析同时代人当中主要是中青年作家的作品,发现他们在遵循古典文学传统的同时,写法有些不一样。‘新的现实——新的现实主义这个口号的提出如同火上加油,争论更激烈了,但是这个口号被接受了,虽然直到现在对它的理解并不一致。”他根据他提出“新的现实一新的现实主义”的口号这一点,认为自己是第一个用“新现实主义”这个术语来表示当代新文学的人。在2000年初举行的另一次研讨会上,卡兹纳切耶夫在他的报告中把后现代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做了比较,多数发言者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批判,也有个别人替它辩护。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会上有人针对新现实主义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请说说,它有什么新东西?
上面提到过,“新现实主义”这个术语早在20世纪初就出现了,后来有人不断使用过。卡兹纳切耶夫也承认这一点。他说,“类似的术语已在文学中浮现过几十次”,例如“二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曾多次被称为‘新现实主义等等”,因此,“文化的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相应的现实主义”。既然如此,在重新使用“新现实主义”这个术语时,应该对它的新的特点作出具体说明。根据现在所能见到的材料,卡兹纳切耶夫曾在一篇文章里做过这样的尝试。首先,他强调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因为第一,就是对一般现实主义的理解还有不清楚和不一致的地方,第二,对任何定义都可从作家创作实践的角度提出质疑,这是由于大艺术家很少能够完全纳入具体的流派之中。在讲到目前的新现实主义时,他特别指出它在运用语言上的特点。同时他发现新现实主义作家运用的艺术手法非常广泛,有的人在采用后现代的美学原则方面取得了成功。由此可见,他把吸收后现代主义的某些诗学成分作为现时的新现实主义的特征之一。
为了认清今天的现实主义的特殊面貌,传统派的《莫斯科》杂志编辑部于1998年下半年召开了主题为“现实主义:是时尚还是世界观的基础”的座谈会,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有瓦西连科、瓦尔拉莫夫、奥特罗申科:帕夫洛夫、米哈依尔·波波夫等五人。他们在发言中表明了自己对现实主义的看法和态度。奥特罗申科认为反映外部生活的能力是第一位的,人物及其性格情节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等术语,都是外部的东西,实际上只是布景,是供那种内部的、自古以来的现实进行活动的舞台。波波夫在发言中说,现实主义的含义很多,但它不是一切,确定它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反证法,说现实主义不是后现代主义,不是感伤主义,不是浪漫主义等,那么是否其余一切都是现实主义?也不是。其实他这样说,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帕夫洛夫认为“新现实主义”、“后现实主义”、“严峻的现实主义”等术语都是批评家发明出来的,这就是说,现在已有某种他们想要界定的艺术经验。但是问题不在于现实主义,换句话说,当代小说不产生于“现实主义”而出自新的生活经验,出自时代和人的活的心灵。瓦尔拉莫夫说他对谈论现实主义不大感兴趣,认为这不是作家的事,他说,让别的人来决定你该属于哪个部门吧。瓦西连科则相反,认为谈论今天的现实主义很有意思。她说,她信奉的不是19世纪僵死的、“古典的”现实主义,而是“另一种现实主义”,一种经常不断地发展着的和作为一个开放体系吸收着20世纪所有其他流派——先锋派、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所创造的手法和做出的发现的现实主义,一个同其他派别和流派同时存在的现实主义。参加座谈的都是在创作中坚持现实主义的作家,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对自己属于什么主义并不十分关心,不过他们提出的某些具体看法,例如当代文学出自新的生活经验,反映时代特点和当代人的思想感情,它可以吸收其他流派的艺术经验和手法等,表达了他们对现时的新的现实主义的认识。
2000年1月,沃罗涅日的《高潮》杂志出专刊介绍新现实主义作品。收入该专刊的作品包括戈洛瓦诺夫、瓦西连科、基利亚科夫、奥特罗申科、帕夫洛娃、帕夫洛夫、塔尔科夫斯基、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等人的小说以及巴辛斯基、帕夫洛夫、柳特等人的文章。该专刊出版后,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当代俄罗斯文学和国外俄罗斯文学研究室的学者曾邀请在上述专刊上发表作品的作者进行座谈,讨论现实主义的现状问题。学者们纷纷就这一代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发表意见。他们的看法并不一致。研究当代文学的萨瓦捷耶夫觉得新现实主义作家们的创作并无特别的创新之处,但是多数人认为还是可以从中发现不少新东西的。座谈中提出了许多问题,例如现实主义是否“疲惫”的问题,
现实主义吸收现代主义手法问题,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之间的界限问题等。为了对新现实主义作出明确的界定,这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在现实主义逐渐升温,关心和讨论它的人不断增多,“新现实主义”这一术语为许多人所接受并迅速流传开来时,发生了一场关于谁首先使用这个术语的争论。1998年初,巴辛斯基在一篇文章里提起这样一件事:他听人说在某编辑部里一位文学家几乎是挥着拳头扑向另一位文学家,喊道,是他,而不是巴辛斯基第一个讲“新现实主义”的。于是巴辛斯基对此事作了澄清,他说,“新现实主义”一词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20世纪初“只有懒汉才不讲它”,而他不止一次地谈到的是“俄罗斯现实主义”。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在这之后,卡兹纳切耶夫在《独立报》上发表文章,指责巴辛斯基“窃取了他的‘新现实主义的思想”。巴辛斯基再次发表声明说,他“从来没有宣布‘新现实主义是一个当代文学流派”。从巴辛斯基发表的言论来看,他确实没有提出和宣扬过“新现实主义”,他想要加以说明的是“俄罗斯现实主义”。至于说到现阶段是谁第一个使用“薪现实主义”这一术语的问题,那么事实证明,那也不是卡兹纳切耶夫。上面已经说过,早在1992年,在他提出“新的现实——新的现实主义”的公式前,斯捷潘尼扬就已使用了“新现实主义”这一术语,并且在1996年重申了这一点。对此卡兹纳切耶夫应该是知道的。再说,他自己也承认“新现实主义”并不是新词,而是一个用熟了的术语,那么他争夺“发明权”之举就更显得无聊了。
三
到两个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坛上出现了一批信奉现实主义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沙尔古诺夫、先钦等人。沙尔古诺夫在学生时代写的长篇小说《一个男孩受到了惩罚》于2001年获得了处女作奖。同年发表了题为《不同意送葬》的文章,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点。他在文章里在给后现代主义致悼词的同时,宣布“新现实主义正在到来”。他说:“现实主义不会完结。现实主义与现实一起,连续不断地更新着,它要比后现代主义神话般地年轻”。他接着说,出现了新的情况,作家不再抱某种成见和不再认为思想有绝对权利,这就使得文学有可能不受倾向性挤压而获得真正的自由。他由此得出结论说:“正是在新的思想条件下,散文创作除了走向现实主义,此外无处可去”。沙尔古诺夫在文章结尾说:“让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在盛开的百花中有现实主义的花蕾。现实主义是艺术的花园里的玫瑰。我重复一下我的祈求:新现实主义!”沙尔古诺夫主要讲在当前的思想条件下走向现实主义是唯一的选择,讲他深信现实主义有光明的前途,至于这种新的现实主义有什么样的主要特点,在这篇文章里未作具体说明。不过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主张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不回避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因此他所描绘的生活画面比较阴暗。他笔下的主人公通常是一些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浑浑噩噩地过日子的年轻人。这大概是他所代表的年轻的新现实主义作家创作的共同特点。
先钦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他既写小说,又从事文学批评,观点与沙尔古诺夫相近。2003年他发表了《新现实主义者们》一文,着重介绍和分析了新一代年轻作家的创作。他说,这一代作家“年龄在三十上下和更小一些,也就是说,他们是在改革年代和俄罗斯野蛮的资本主义年代长大的。对他们来说,国内发生的变化是极大的震撼。不过今天二三十岁的人受到的震撼是与年长的几代人不同的,——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可用来与今天的生活相对比,过去没什么可以认真‘怀念,也没有什么可诅咒的。这些青年在刚开始走上生活道路时,似乎到了一个很深的峡谷前,或者需要跳过去,或者会滚到谷底,——这个说法可用来说明最近十年到十五年俄罗斯的现实。”这里他讲到新一代作家成长的环境和思想状态是与他们的前辈不同的。他接着说:“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的许多作家选择了现实主义方法,几乎选择了自然主义,选择了纪实笔法。在文体上不标新立异,不讲究辞藻,有时甚至语言不作加工,情节简单,人物有时有意写得与作者近似,直至姓名完全相同,这使得文学批评家们有理由重新争论作者与其人物等同的问题。”他列举这些现象,似乎想说明新一代现实主义作家创作的艺术特点。他对现实主义充满信心地说:“‘新现实主义是今天俄罗斯文学的许多流派之一。但是它是最年轻的,而且似乎是最有希望的流派。”他还说,读者读腻了后现代主义、超级隐喻、低级趣味的读物,读腻了怪诞和乖谬的东西,没有从大做广告的新作品中找到特殊的意义,便回过头来读反映现实生活并把玩弄辞藻降到最低限度的文学作品,这是一个好兆头。
四
上面讲了各种类型的被人们称为和自称为“新现实主义者”的作家。批评家邦达连科在他的一篇题为《新现实主义》的文章里,把这些作家分为三个群体。照他的说法,第一个群体的作家聚集在《十月》和《新世界》两本杂志和《文学报》周围,其中包括小说家帕夫洛夫、瓦尔拉莫夫、斯韦特拉娜·瓦西连科、塔尔科夫斯基和批评家巴辛斯基。他把他们称为“自由派内部的独特的反抗者”,说他们的现实主义“就手法的总和来说,与弗拉基莫夫、别洛夫或者与阿斯塔菲耶夫毫无区别”,因此这些作家“完全可以称为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承俄罗斯主流文学的传统派”。他们之所以成为新现实主义者“不是因为形式,而是因为他们在统一的自由派框架内向主导地位的后现代主义提出了挑战”。邦达连科在讲到第二个群体时说,这个群体存在于传统派的莫斯科作家组织内部,理论家是卡兹纳切耶夫,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有米哈依尔·波波夫、焦格切夫、阿尔焦莫夫、科兹洛夫等。他说,这些人被称为“新现实主义者”,是“相对于在《我们的同时代人》、《莫斯科》杂志里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的现实主义,相对于博罗金、克鲁平、利丘京和叶基莫夫的作品而言的”,他们“最大限度地把后现代主义手法吸收到现实主义中来,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游戏的现实主义”。最后邦达连科谈到第三个群体,他说,这是一些20到25岁的男女青年,其中包括沙尔古诺夫、先钦、斯维里坚科、杰涅日金娜等。他们被称为“新现实主义者”完全由于另外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非常细致地描写他们周围的‘新的现实”,“在描写当代青年肮脏的现实世界时,不进行美化,不用各种象征,用的是风俗随笔的写法”。
邦达连科把“新现实主义者”分为三个群体是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的。他所说的第一个群体即后现代主义一时占有优势的自由派阵营内部的“反抗者”,他们的现实主义既与后现代主义相对立,又与该派的一些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作家的现实主义有所区别,他们的“新现实主义”大概就“新”在这里。第二个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可
说是在总体上对后现代主义持抵制和反对态度的传统派阵营内部的“离经叛道者”,他们的“新现实主义”新就新在吸纳后现代主义的手法为己所用。这么说来,卡兹纳切耶夫提出的“新的现实——新的现实主义”的口号并不完全反映它的特点。这一群体中的某些作家因为未能把握好采用后现代主义手法的分寸和限度,他们的某些作品已很难归入现实主义的范围,如科兹洛夫这样的作家,有人甚至把他归入后现代主义阵营,称他为“爱国派的佩列文”(佩列文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真正照“新的现实——新的现实主义”口号行事的,恐怕是第三个群体的年轻人。他们的作品新就新在反映当前的现实生活,主要是年轻人的生活遭遇,而在艺术上有时不免带有自然主义的一些特点。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先钦甚至把新现实主义说成发端于“黑色文学”。其实两者只是笔法上有相似之处,而在反映现实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在现实生活中既有光明面又有阴暗面的情况下专门写阴暗面,而后者面对苏联解体后缺乏光明的现实别无选择,它描绘的比较阴暗的生活画面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两个世纪之交一批年轻作家和批评家的涌现,给俄罗斯文学界增添了活力,受到了文学家的欢迎和重视。大型文学杂志和报刊为他们敞开了大门,欢迎他们投稿,不断发表他们的作品和文章。有关方面举办各种研讨会,为他们发表意见提供论坛;同时设立各种专门的奖金,肯定他们的创作成就并加以鼓励。有的年轻作家确实写出了一些有分量的作品,其中有的作品获得了全国性文学大奖。这样一来,他们在整个文学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有所增加。人们在谈到新现实主义时,开始把很大一部分注意力集中到他们身上。
五
俄罗斯文学界关于“新现实主义”的讨论和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近年来,随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作家和批评家登上文坛,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讨论和争论的重点逐渐转移到如何看待新一代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上。
不过在最近几年的讨论和争论过程中,仍有人提出“新现实主义”这一术语是否合适的问题。有一位名叫加尼耶娃的女批评家说,有人根据“新现实主义”利用当代生活的材料因而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这一点来说明它的“新”,如果是这样,那么“每一个接踵而至的时代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新—新的和新一新—新的现实主义”。她问道:“这岂不是毫无意义的吗?”
从以上所述来看,不能说没有人对“新现实主义”作过分析和界定,不过他们在谈到它的新的特点时说法不一,这就使得“新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具有不确定性和多义性。最近几年不断有人试图对“新现实主义”的特点作出概括和说明,如年轻女批评家普斯托瓦娃说:“新现实主义越出了岸,冲击着一般现实主义的古老的堡垒,侵占着创新的礁石,淹没着所谓的年轻作家的一个个岛屿,——新现实主义像什么也不是的东西一样,是无边无际的。”这位被称为“新的浪潮”的“主要理论家”用形象的语言发表的高论,不仅没有说清“新现实主义”究竟是什么,反而使之更加糊涂了。
比较年长的批评家叶尔莫林把作家朝着“艺术自古以来的使命——认识和表达真实情况”的方向的“偏移”称为新现实主义,他同时指出,新现实主义在审美上吸收古典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新浪漫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20世纪后半期的反文化和现代主义的巨大的经验。显然,叶尔莫林所说的“新现实主义”是一种在艺术方法上兼收并蓄的现实主义。这里就出现一个老问题,如何区分它与当年法国理论家加罗蒂提出的“无边的现实主义”?
对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情况(尤其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及其影响和作用,也有不同的估计和评价。有的人大概是由于对新现实主义理解得比较宽泛,而且有意想肯定它在今天整个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因而把较多的作家和作品归到新现实主义中来;有的人则相反,认为新现实主义文学至今还是无定形的东西,采取鄙视态度。这在年轻作家和批评家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上面说过,沙尔古诺夫和先钦等人认为新现实主义是发展方向,肯定它取得的创作成果。普斯托瓦娅、奥尔洛娃、普里列平等基本上也持这样的观点。而有的年轻批评家的看法完全相反,如女批评家马尔科娃认为,新现实主义是“老一套”,戈连科把新现实主义称为“文学的模拟”。有的人虽然看法与他们相近,但是说话语气比较缓和,如鲁达廖夫。他认为,把“新现实主义”作为已经存在的现象来谈论还为时过早,“新现实主义还远不是文学过程的事实。而只是某种正在出现的东西,没有成形,还只是形成中的东西。”在散文创作中“新现实主义”暂时还有争议,但是在文学批评中已完全形成了。言外之意是,关于“新现实主义”只是批评家谈论得比较热闹,而在创作上并不完全是这样。
如果对最近一段时间的整个文学创作情况作一个考察,那么应该承认,随着后现代主义的退潮,现实主义的信奉者明显增加,其中包括一批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创作才能的年轻人,他们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创作成就。尽管一些批评家在谈论他们的创作时,有时有点言过其实(这是应该避免的),但是采取讽刺和嘲笑的态度则是不对的。
从目前情况来看,关于“新现实主义”的讨论和争论远没有结束,还将继续进行下去。为了使讨论进一步深入,一方面,对一些基本概念,特别是关于现实主义的概念,要有正确的和比较一致的认识;另一方面,要遵循一切从事实出发的原则,对创作的实际情况作全面深入的研究,在掌握大量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理论概括,不作抽象的推论,不单纯在使用术语概念上做文章,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能站得住脚的结论,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能逐步取得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