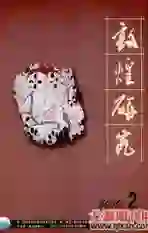西凉刘昞注《黄石公三略》的发现
2009-06-15刘景云
刘景云
内容摘要:《俄藏敦煌文献》x17449《黄石公三略》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手抄夹注残卷孤本,是史书所载北魏、西凉刘晒注《黄石公三略》注本,较之传世的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本早800余年。为我国古代军事文献史上的重大发现。
关键词:发现;《黄石公三略》;西凉刘晒注
中图分类号:G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2-0082-06
《俄藏敦煌文献》且x17449《黄石公三略》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手抄夹注残卷孤本(图版18),是史书所载北魏、西凉刘瞒《黄石公三略》注本,较之传世的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本早800余年,为我国古代军事文献史上的重大发现。
该卷子为一纸,质地细麻纸,棕褐色。长52.49厘米,高23.76厘米,书写版心高21.18厘米。乌丝栏,残存26行,行大字12至14字不等。该残卷存大字236字,夹注小字167字,为《三略·上略》残文。墨色清新浓郁,宛如新墨。字体为秦隶,篆意较浓。
据纸质、纸色及书法、款式判断,该卷子时代较早,为隋以前北朝文物,大致为5世纪抄本。
卷背为朱批收支历。
现今学术界认为《黄石公三略》是后人托名之作,真实作者已无可考证。成书年代也纷争不一,多数认为是西汉末年。
《三略》不同于其他军事著作,它侧重于从政治策略上阐明治国用兵之道,糅合诸子各家思想,论说兵家战略。正因为它的特殊性,历来受到政治家、军事家和学术界文人的重视,是治国治军、平定天下的重要著作,影响极大。南宋晁公武(1105—1180)称其“论用兵机之妙,严明之决,军可以死易生,国可以存易亡”,其意义何其重大。晁公武在《读书志》说:“元丰中,以《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颁武学,号日‘七书。”此即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黄石公三略》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该书先后传人日本、朝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三略》分上略、中略、下略3卷,3800字。现存最早的为南宋孝宗、光宗年间(1163—1194)《武经七书》刻本,后人亦多注释,金人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等,《黄石公三略》亦编列在其中。
出自敦煌石窟的Ⅱx17449《黄石公三略》的时代,比南宋《武经七书》要早600至700年。《汉书·艺文志》没有记载,而《史记》、《汉书》却有下邳圯上老人传张良《太公兵法》的故事,文稍异。
《史记》卷55《留侯世家》: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目:“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
子房始所见下邳圯上老父与太公书者,后十三年从高帝过济北,果见谷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黄石(冢)。每上冢伏腊,祠黄石。《汉书》卷40《张良传》:
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欧之。为其老,乃强忍,下取履,因跪进。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惊。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期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后五日蚤会。”五日,鸡鸣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后五日复蚤来。”五日,良夜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日;“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是则为王者师。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已。”遂去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良因异之,常习(读)诵。
良始所见下邳圯上老父与书者,后十三岁从高帝过济北,果得谷城山下黄石,取而宝祠之。及良死,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腊祠黄石。
根据这些传说,三国时代魏李康在《文选·运命论》说:“张良受黄石之符,通《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唐李善注:“《黄石公记序》曰:‘黄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隋书》卷34《经籍志》三:“《黄石公三略》三卷。”下注:“下邳神人撰,成氏注。梁又有《黄石公记》三卷、《黄石公略注》三卷。”又有“《黄石公三奇法》一卷。,下注:“梁有《兵书》一卷,《张良经》与《三略》往往同。亡。”其中《黄石公记》、《黄石公略注》均指《黄石公三略》,“下邳神人”即黄石公,作《三略》,为张良所传。故《隋书》又称《张良经》,“与《三略》往往同”。这是说《三略》成书于东汉末年的。
《新唐书》卷59《艺文志》三“成氏《三略训》三卷”、《宋史》卷270<<艺文志》六“成氏注《三略》”,连同《隋书·经籍志》所载“成氏注《三略》均亡佚无考,“成氏”亦无从考知。
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有圯上老人授张良《太公兵法》,唐张守节《正义》引梁阮孝绪《七录》:“《太公兵法》一帙三卷。太公,姜子牙,周文王师,封齐侯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申、吕肖矣,尚父侧微,卒归西伯,文武是师;功冠群公,缪权于幽;番番黄发,爰餐营丘。”《正义》:“吕尚之祖封于申。申、吕后痛微,故尚父微贱也。”《正义》又言:“言吕尚绸缪于幽权之策,谓《六韬》、《三略》、《阴符》、《七术》之属也。”张守节的观点说,《三略》为吕尚所作,由黄石公授张良。
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认为《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三略》,判断为后人所伪托。
我们暂且不去争论《三略》的作者是谁,就《三略》的注本作一分析。
据史书记载,最早为《黄石公三略》作注的,是东晋末年西凉的刘晒,见《魏书》卷52《刘晒传》,言凉武昭王李禺(400—416)时,刘晒有《三略》注传世:
刘晒,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宝,字子玉,以儒学称。晒年十四,就博士郭瑶学。时踽弟子五百余人,通经业者八十余人。瑶有女始笄,妙选良偶,有心于晒。遂别设一席于坐前,谓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长,欲觅一快女婿,谁坐此席者,吾当婚焉。”晒遂奋衣来坐,神志肃然,曰:“向闻先生肃求快女婿,晒其人也。”踽遂以女妻之。
晒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弟子
受业者五百余人。李嵩私署,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罱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晒时侍侧,前请代罱。昔曰:“躬自执者,欲人重此典籍。吾与卿相值,何异孔明之会玄德?”迁抚夷护军,虽有政务,手不释卷。罱曰:“卿注记篇籍,以烛继昼。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晒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将至,孔圣称焉。晒何人,斯敢不如此?”晒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北史》卷14《刘延明列传》:
刘延明,墩煌人也。父宝,字子玉,以儒学称。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瑶。璃弟子五百余人,通经业者八十余人。踽有女始笄,妙选良偶,有心于延明。遂别设一席,谓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觅一快女婿,谁坐此席者,吾当婚焉。”延明遂奋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璃遂以女妻之。延明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命,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
凉武昭王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昭王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葺。延明时侍侧,请代其事。王曰:“躬白执者,欲人重此典籍。吾与卿相遇,何异孔明之会玄德?”迁抚夷护军,虽有政务,手不释卷。昭王曰:“卿注记篇籍,以烛继昼,白日且然,夜可休息。”延明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将至,孔圣称焉。延明何人,斯敢不如此?”延明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墩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行于世。
敦煌出土的《黄石公三略》夹注本,时代当在隋以前的北朝。刘日丙时为北魏武昭王(400一416)李鼍私署儒林祭酒、从事中郎。二者时代极相近,故《俄藏敦煌文献》且x17449夹注抄本,应该是北魏、西凉刘晒的注本。
现将《俄藏敦煌文献》且x17449{(黄石公三略》残叶全文录于下:
[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牧其半,则政行而不[怨]。政行以理,故不怨也。
用兵之要,在于崇礼而重禄。礼崇则士至,禄重则戎士轻其死。口口敌也。故禄贤不爱财,赏功不遇时,登口口其有功口口口以劝将口也。则下力并而敌国消。
将之所以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
据《俄藏敦煌文献》Ⅱx17449,残存《三略·上略》部分,现将传世的《三略》最早本子,即南宋孝宗、光宗年间(1163—1194)《三略》刻本(即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本《武经七书》,原版框高20.1cm、宽13.7cm)相应部分辑录,以作文字考订。
世能祖祖,鲜能下下。祖祖为亲,下下为君。下下者,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则国富而家娱。然后选士,以司牧之。夫所谓士者,英雄也。故曰:罗其英雄,则敌国穷。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则政行而无怨。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故禄贤不爱财,赏功不逾时,则下力并而敌国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赡以财,则士自来。接以礼,励以义,则士死之。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因。昔者,良将之用兵,有馈箪醪者,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而饮。夫一箪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军之士思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军谶》曰: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辨,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谋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万。《军谶》曰: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
敦煌本:“夫将率者,必同滋味,共安危,敌乃可加,是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囚。”
这其中的“囚”字,是考订《三略》各本源流的根本。敦煌本夹注作:“囚,拘也。全,为己于拘制也。”
景宋本《三略》作“因”,形近。
明刘寅《三略直解》亦据宋本,这句话作:“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因。”注:“夫为将帅者,必与士卒同食滋味而共处安危,然后士卒感激奋发,而敌乃可加。‘因字未详,或日当作‘湮言。吾兵有全胜,则敌有全没者,未知是否?”“加”字亦未作解释,敦煌本“加”字夹注:“加兵诛伐之也。“‘伐”字误作“代”。
清朱墉《三略汇解》“囚”字亦作“因”:“可加,加兵于敌也。全胜,以全取胜也。全因,言敌之所有,皆为我资也。”《纂序》:“……故兵有完全取胜,无一之损伤,敌有前徒倒戈,无一不为我资也。”
可知宋本、明刘寅《直解》本、清朱墉《汇解》本均出一脉,或言“不详”,或臆会杜撰,离本字相去甚远,均因传刻致误。
而今所见《施氏七书讲义》,金人施子美于《三略讲义》言:“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囚。”《讲义》:“法曰:
勤劳之师,将必先已。故为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既与之共,斯可以得其死力。故敌可得而加。穰苴唯与士卒平分粮食,故能使病者求行争奋,以却燕晋之师。田单惟身操版插,与士卒分功,故能使怒自十倍,以克燕师。大抵驭象有术,则可以必胜。志在爱人,则可以安人。兵有全胜,此言驭人有术,而可以必胜也。敌有全囚,此言心乎爱人,而可以安人也。昔者吴起全胜六十四,充国欲以全取胜,此兵之全胜也。穆子入鼓,不戮一人;李想入蔡,不杀一人,此敌之全囚也。”
施氏叙述十分明白,全胜全囚,全胜指己全胜,全囚则指拘敌不杀一人。施氏的这一关键词同敦煌本,然这段文字其他均同宋本。
关于施子美及时代背景,以下文字可作参考。
施子美,正史无传,生平不详。江伯虎在《施氏七书讲义》序言中作过简单介绍:“三山施公子美,为儒者流。谈兵家事,年少而升右庠,不数载而取高第,为吴孙之学者多宗师之。”国内地名为三山者有多处,在史籍中,均未见有关施氏的记载,故其里籍不好确定。日本文久三年(1683)刊本之江序后署“贞韦占壬午”(贞韦占为金宣宗年号,其实贞祐仅四年,壬午年为元光元年),即宋嘉定十五年(1222)。如果江序作于此年,该书成书当在此之前,故有人认为施氏为金人。
《施氏七书讲义》为施子美在朝廷武学授课之讲义,内容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六韬》、《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七部兵书的原文和注释。每部子书前均有解题,概述作者、成书、存佚等情况,对正文则分段阐释,后引史实相参证,史论结合,通俗易懂,在兵书
编纂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自宋代以来,著名军事家、学者对《武经七书》的学习、研究和译注,均将它作为重要依据。诚如江序所云:“古人成败之迹,奇正之用,皆得以鉴观焉。”可见其在中外军事思想上也很有影响。
《施氏七书讲义》被江伯虎得到后,“于是锓木以广其传”。这说明此书曾有宋刊本问世。可惜在我国不仅宋刊本早已不得见,而且全书失传。该书传到日本以后,日本建治二年(1276)武将北条实时曾命其子北条显时抄录,即所谓“金泽文库”抄本。此后,在日本多种抄本、活字本和刊本相继问世。其中日本孝明天皇文久三年(1863)刊本反传到我国。
现所见施氏《三略讲义》,实为日本孝明天皇文久三年(1863),据传入日本的金刻本的抄本翻刻,然它多少保留了金以前《三略》的原貌,至少传人日本的施氏《三略讲义》,较今所见影宋本要早。
最近本人在研习西夏文献时,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发现以"HHB"编号的第578和第715合号的译自汉文的《黄石公三略》(图版19)。其中和敦煌本对应的文字,尤其是“夫将率者,必同滋味,共安危,敌乃可加,是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囚”句,其文意与汉文《三略》相当,并于“擒陷”下夹注:“得胜。囚,擒陷。”
《俄藏黑水城文献》所收《黄石公三略》本,为册叶装,配补而成。该《三略》首缺一叶半,末残缺半叶,《下略》至“伤智(者)则三世取祸,蔽智(者)则[殃]身”。下缺“嫉贤者其名不全,进贤者福流子孙,故君子急于进贤而美名彰焉。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万,国乃思敬。去一利百,人乃慕泽,去一利万,政乃不乱。黄石公三略卷下竟。”
西夏,是11世纪初我国西北地区由党项羌建立的封建王朝,建都兴庆府(即今宁夏银川)。西夏文是由野利仁荣等创制的记录党项羌民族语言的文字,时称“番字”、“番书”、“番文”。
由于西夏王朝所处时代,前期与北宋、辽鼎立,后期与南宋、金对峙,它的文化受汉文化影响极深,西夏人从汉、吐蕃翻译了大量文献,《黄石公三略》亦在其中,多少保留了那个时代的文献特点。
十分肯定,“全囚”的“囚”字,误作“因”字,说明影刻的宋本,或依景宋本传承的明刘寅《直解》本、清朱墉《汇解》本均因字形相近致讹,可以断定为后续本,解释亦牵强附会。
对应敦煌残卷的西夏文《黄石公三略》文,直译如下作参考:
勇者国之干,民者国之本。得干治民,法行无怨。用兵之要者,禀崇礼施重禄。如禀崇礼,智人自来,赐重禄,勇人斗强。故举智不惜财,授赏不失时,下同力合斗非友。招人道者重其禄位,口口口实智[人]自来。礼以致敬,柔以语言,则不避死难。惟为将者,与兵共承凶残,共食苦甜。故朋友共得利,敌仇全擒陷。昔智将用兵,人有奉一瓶酒更投河源,令民饮水尾。以一瓶酒岂能味江,军士因共尝甘甜以夺命。军书中说,井不俱掘,帅不言渴。军舍未定,将不说疲。[冬]不穿裘,夏不执扇,雨不张盖。此谓将礼是也。同受安凶,与众和合,当不分离,用时不说疲。以昔养恩,言计成也。故行恩不厌,故因一得万。军书中说,将威仪者,军政是也。
很显然,西夏本《太公三略》与其同时代的金本施子美《三略讲义》,由于时代接近,故在传抄、刻印时更保留了《三略》的原本原貌,故敦煌本,作为北朝抄本,它要比西夏本更早五六百年,所以它的军事文献价值极高。
又因景宋本为白文本,无注。敦煌本、西夏本均有夹注,敦煌本注文稍略,而西夏本注文详尽,亦知为二的不同注本。
西夏文夹注本《黄石公三略》,是西夏朝(1038—1227)的早期译本,基本完整,于《上略》前佚去二叶半,木刻。由于西夏文的特点,于《三略》多意译,更多地保留了早期《三略》本的原意,完全不同于敦煌本,更多更详尽,是研究《三略》源流很重要的本子。尤其于敦煌本的关键词“囚”字,西夏本作了诠释,这一点很重要,可依据考定今本致误的原因。由于它不同于敦煌本,又与金施子美本和景宋本不同,它是否就是《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所提到的失佚“成氏注《三略》”,抑或就是一个西夏注本?然“成氏”离西夏朝去远,可能性较小。西夏注本于夹注中,如《上略》“智人自至”下,有引《周易》语,这些均值得研究。西夏文刻本有残缺和注文笔划模糊,辨认有一定难度。此次仅译释和敦煌本残叶相应的句子,以作考定比勘。
金施子美《三略讲义》,史籍于施子美时代无考。然据《三略讲义》与敦煌本相较,亦可见敦煌本痕迹,虽《三略》多与景宋本相同,然诠释仍保留了《三略》原意。金施子美本于我国却已失传,流传日本、高丽后反传回来,应该说,该本保留原作的可能较大,可据以考定施子美当时撰写《讲义》时所使用的《三略》定本,应早于景宋本,晚于西夏本。
关于宋本《黄石公三略》,现在传世的是宋孝宗、光宗年间(1163—1194)的刻本,并认为是《三略》传世的最早本子。北宋元丰三年(1080),神宗赵项诏国子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定《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书,至元丰六年(1083)完成,并将此七书颁定为“武经”,镂版行于世。
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印的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刻本《武经七书》,为白文,无注文。校之敦煌本、西夏本、金施子美本,其中有“兵有全胜,敌有全因”之“因”为“囚”之误,则知宋本已误。西夏本和金施子美本,从时代上分析,可能使用的是北宋以前或神宗元丰年间的《武经》本。
据西夏本和金施子美本对勘,参照敦煌本,金本又晚于西夏本,此据“军灶未炊,将不言饥”而下的结论。
至于明刘寅《三略直解》、清朱墉《三略汇解》及《四库全书》白文本、《续古逸丛书》白文本《黄石公三略》,均同中华学艺社景宋本。
这样分析下来,可得出这样的结论:
敦煌夹注本《三略》,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三略》本,时为北朝。《魏书·刘晒传》、《北史·刘延明传》载刘氏注《三略》,此前史籍均未载有人注《三略》的,那么刘氏注《三略》,应该是《三略》唯一的最早注本。其后《隋书·经籍志》于“《黄石公三略》三卷”下注:“下邳神人撰,成氏注。”成氏注失传,成氏无考。由于隋(581—619)去西凉武昭王李禺(400—416)甚远,因此敦煌本不为成氏注本。又该卷子出自敦煌莫高窟,从卷子外观判断为北朝卷子,刘晒又为敦煌人,故敦煌夹注本为西凉李鼍朝,刘晒《黄石公三略》即公元416年前的注本,而卷子上校订批改之语,抑或为刘晒真迹。
当今史学界,普遍认为传世的《三略》最早本子为宋孝宗、光宗(1163—1194)的刻本,敦煌夹注本《三略》的发现,将时间足足提前800年,这是我国古代军事文献的重大发现,亦是史籍记载的重大实证材料的发现。
西夏文夹注本《黄石公三略》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文献也同样意义重大。汉文史籍均未载有这么一个西夏译本,即便是《隋书》、《新唐书》、《宋史》亦只提到有成氏注《黄石公三略》,且亡佚。西夏译本不仅仅是翻译汉文《三略》,亦是一注本,且注释详尽,它比传世的宋本更接近于《三略》原貌。它的注文不同于敦煌本,如果这些注文也是从汉文著作译出的,那它是不是佚失的成氏《黄石公三略》注本?《宋史·艺文志六》:“成氏注《三略》三卷。”说明宋时成氏注本尚存世,那么西夏朝据以翻译,仍是可能的。
如果确定西夏本为成氏注本,那么它和敦煌本的发现,不是同样令人振奋吗?居然两个佚失的本子都被发现,意义何等重大!
如果西夏本不是成氏注本,那它也一定是哪位卓越的军事理论家的述作,这在我国古代军事史上也同样是占有显赫地位的。
金施子美《三略讲义》,国内已失传,从日本、高丽反传回来,意义亦不可抹。今所见施氏刻本,有明显的刻本特征,于字句左边都有标示汉字的声调符号。然施子美将《三略》以讲义形式串讲,则不知他依据的是何种注本,也就无从考订《三略讲义》的祖本。然从“兵有全胜,敌有全囚”句,亦可考知它依据的《三略》本要早于宋孝宗、光宗时的本子,从时代上分析,和西夏本较为接近,可能都是北宋时期的《三略》本。
至于景宋本、《四库全书》本、《续古逸丛书》本及明刘寅本、清朱墉本,实质上是《三略》同一底本的不同刻本,均祖宋孝宗、光宗朝之《三略》,也就是今天存世的通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