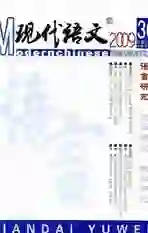定州汉简本《论语》校读札记
2009-06-13韦扬
韦 扬
摘 要:1973年出土于河北定县的《论语》残简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论语》白文抄本,也是《论语》出土文献的代表。定州本《论语》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对于进一步探明《论语》的编纂、成书、版本变迁具有重大的意义。将简本与传世本的文字进行对校,发现简本保留了大量的古文字形。我们认为,简本《论语》是在三家《论语》形成之前的各家融合过程中的产物。
关键词:定州汉简 《论语》 校勘
1973年,在河北定县城关西南十公里的八角廊村第40号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论语》残简,共计620余枚,录成释文的共7576字,将近传世本《论语》的二分之一。其中保存最少的为《学而》,只有20字;最多的《卫灵公》有694字,可达今本的百分之七十七。定州本《论语》是现存已知最早的《论语》白文抄本,其年代比熹平石经残片的石刻本《论语》也要早两百余年。作为为数不多的《论语》出土文献的代表,定州本《论语》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其出土对于进一步研究《论语》的编纂、成书、版本变迁以及孔子的思想具有重大的意义。近年来,学者们围绕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性质、文献价值以及与传世本《论语》的关系展开了研究和讨论,并取得了众多的研究成果。本文总结了诸位学者对于简本《论语》性质的讨论,并通过对《十三经注疏》本与简本进行对校,对文字相异之处进行考证,展现了简本与三家《论》尤其是《鲁论》的关系,以使定州简本《论语》的性质进一步得以明确。由于笔者学力有限,文中定多舛误之处,望诸位老师不吝指正。
一、定州汉简本《论语》的性质
(一)关于简本《论语》性质的众说纷纭
定州本《论语》的性质问题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至今尚无定论。这部《论语》出土于西汉中山怀王刘修之墓。李学勤先生认为,在竹简所处的年代,张禹刚刚以其经学著称,《张侯论》彼时则尚未形成,且简本与传世本文字差异颇多,考虑到《古论》流传不广,因而认为其属于《齐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1]单承彬先生曾多次撰文讨论简本《论语》的性质问题,通过将简本与《说文》中所载《古论》残篇以及郑玄的注本进行比对后得出结论,认为简本属于《鲁论》系统,是一部重要的《鲁论》抄本。[2]陈东先生通过统计对照简文的避讳用字,认定简本是汉高祖刘邦时期的抄本。他指出,《古论》是汉武帝时期纔出现的,《齐论》和《鲁论》又晚于《古论》,则简本《论语》不属于一般意义上汉代三论中的任何一种,它与《古论》一样是战国的遗存。《古论》隐匿于鲁壁,而简本则是当时口诵《论语》的记载,它不属于《齐论》和《鲁论》,却是齐学和鲁学传习《论语》的基础和源头。[3]李若晖先生认为,简本《论语》是与古、齐、鲁三家并行而互有同异的一种文本。他指出,西汉武帝时经学出现了由齐传鲁的倾向,简本《论语》则体现了这一倾向,是齐、鲁融合而更多反映《鲁论》特点的本子。[4]郑春汛女士通过研究简本的用字情况、字形和避讳,认为简本属于汉初的今文隶写系统,较多用古字形,保留了古文的一些面貌。她也认为,简本《论语》不属于三论中的任何一论,而是在三论之前的一个本子。[5]
笔者认为,李若晖先生所宣导的“融合说”具有其合理性,因为今人对于古、齐、鲁三家的传习情况和相互关系的了解缺乏真正的文献依据和实物证据,多根据前人对于三家《论语》关系的描述来进行猜测和推断。余嘉锡曾在其《古书通例》中指出,《汉书艺文志》并未着录当时存世的所有书籍;胡平生、韩自强也曾指出,《汉志》并未将汉初所有治《诗经》之家囊括。因而我们也可以大胆地假设,在西汉初年,治《论语》绝不仅仅有《汉志》所着录的三家,还应有与此三家互有异同的其它各家。此外,治《论语》虽有齐、鲁之分,但随着学人的传习、发展和交流,肯定也无法保持泾渭分明的状态,齐、鲁出现了融合趋势而更以《鲁论》为主要的传习依据。定州简本《论语》作为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实物依据,恰恰反应了《论语》在流传的过程中各家相互借鉴和融合的状态。
竹简整理小组在《介绍》中另外指出的一点是,在定州汉墓中与《论语》同时出土的,还有写有确切时间的西汉名臣萧望之的奏议。萧望之是传授《鲁论》的大师,是当时皇太子的老师。而简本《论语》与萧望之的奏议放在一起,应不是偶然的,起码说明了墓主人生前的喜好和当时《论语》传习的倾向。笔者在校勘的过程中也发现了简本多处文字不同于传世本但与《鲁论》相同之处,证明了简本与《鲁论》密切的渊源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萧望之本为齐人,原治《齐诗》,后师从夏侯胜才开始治《鲁论》并成为了《鲁论》大师。另外,张禹也是先学《齐论》、后治《鲁论》的。我们在研究定州简本《论语》性质的同时,应当结合西汉时期这一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时期中经学所发生的嬗变。当然,嬗变的过程绝非一蹴而就,针对简本所处的特定年代,在论定它的性质时,我们大可以跳出“三家”之说的藩篱,而更多地关注西汉《论语》各家分流并融合的传习过程。
(二)简本年代的问题
经考古发掘者考证,八角廊墓的墓主人为西汉中山怀王刘修,据《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记载:“中山靖王胜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四十三年薨。子哀王昌嗣,一年薨。子糠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子顷王辅嗣,四年薨。子宪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怀王修嗣,十五年薨,无子,绝四十五岁。”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在《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介绍》中指出:“因中山怀王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所以它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本子。”李学勤先生也指出:“八角廊墓的墓主中山怀王卒于宣帝五凤三年(前55)。”而单承彬先生则指出:“刘修死时当汉宣帝五凤四年丁卯(前54)。”关于这一小分歧,笔者重新进行了推算:汉景帝前三年为公元前154年(丁亥年)[6],按照次第顺序和年数往下推,则怀王刘修的卒年实际上应为汉宣帝五凤四年,即前54年。纵观有关定州简本《论语》的论文,多沿袭整理小组在《介绍》中的说法,认为刘修的卒年为五凤四年,但根据《汉书》记载的年数进行推定,则整理小组的说法未必确切。
二、简本《论语》异文选释
本文以《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为底本,以阮元《十三经注疏》本为主要校本(以下简称阮本),皇侃疏本为参校本(以下简称皇本),于简本异文中选择了有心得体会的26处进行了考证,在简本整理小组注释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异文。
体例说明:
1.在录简文时,只录异文所在的能表达相对完整意思的词组或句子,以及其中的标点符号。文中单称“校勘记”的即为整理小组在简文后的校勘记,文中称“注释”为整理小组对简文进行的注释。
2.简文后面的括号内标明的是其所在的简号。简号以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中所标为准。
3.《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中,外加[ ]表示因唐山地震扰动残损的简文,用□表示原简中残泐不能辨识的字,用“○”表示原简刮去某字而形成的空格,用……号表示残缺或不能辨识字形又不能确定字数的简文。[7]本文引简文时遵循整理小组的体例。
4.整理小组在校勘记中提到的“高丽本”实为“正平本”。“正平”并非高丽国王的年号,而是日本一个天皇的年号,因而正平本并非高丽的本子。关于这一错误,孙钦善先生已在其文章中有详细的说明[8],本文据此将整理小组校勘记中的“高丽本”改称为“正平本”。但阮元校勘记中亦称“高丽本”,本文则未对阮记进行改动。
(一)为正以德(第二号简)
正,阮本作“政”。校勘记:正、政可通,古多以正为政。
按:古籍中以正为政的例子颇多,如《尚书·大禹谟》“罔或干予正”,蔡沉《集传》曰:“正,政也。”《礼记·文王世子》“庶子之正于公族者”,郑玄注曰:“正者,政也。”《汉书·陆贾传》“夫秦失其正”,颜师古注曰:“正,亦政也。”《墨子·兼爱下》“古者文武为正均分”,孙诒让间诂:“正,与政同。”《经义述闻·诗·无俾正败》“小雅正月篇:今兹之政”王引之按:“古政事之政或通作正。”
简本中,政事的“政”多作“正”,但也存在例外的情况,《子路》篇第三二九号简中便有“受之政”,而在《雍也》篇第一一五、一一六号简存在“正”“政”并存的现象。
(二)吾十有五而志乎学(第四号简)
乎,阮本作“于”,皇本作“于”,汉石经、正平本均作“乎”。
按:疑此处阮本和皇本均误,此处实际应为“志乎学”。在古汉语中,“乎”可以作为介词,其用法相当于“于”。例如屈原《九章·涉江》:“吾又何怨乎今之人。”《荀子·劝学》:“学至乎没而后止也。”而“乎”与“于”字形相近,尤其在文字材料发生残泐的情况下,二字容易混淆。简本与汉石经、正平本作为年代较早的本子,可以相为左证。另外,据笔者初步统计,在全部定州简本《论语》可以辨识的文字中,绝大多数情况都使用“于”字共74处。而“于”字的使用极少,仅在《微子》篇第五七一号简中存在。这更加说明了此处“志乎学”为“志于学”的可能性不大。
在经典中,“于”“于”通用、混用是十分常见的情况。《广雅·释言》:“于,于也。”《说文·亏部》:“于,于也。”段玉裁注:“今音于羽俱切,于央居切,古无是分别也。”阮元在《礼记》校勘记中称:“唐石经于字一千四百四十三,于字一百四十二,莫详其义例。诸刻注疏无参差不一,各依旧本可也。”
(三)(三家者以雍)彻(第三七号简)
阮元校勘记云:“《释文》出‘撤字,云‘本作彻。案《五经文字》云:撤,去也。案字书无此字,见《论语》。”《经典释文汇校》黄焯案语云:“卢云:皇、邢本皆作彻。严云:《五经文字》撤。……《说文》、汉碑皆无撤字。”
按:经典中存在大量“撤”与“彻”通用的例子:如《论语·乡党》“不撤姜食”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撤,去也。”刘宝楠《正义》:“撤,九经本作彻。”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三引慧苑《音义》“撤睡盖”注引字书:“撤,去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损肉撤酒”,孙星衍音义:“撤,当作彻。”《广韵·薛韵》:“撤,经典通用彻。”而“彻”除了训为“通也”“达也”,也训为“去也”“除也”:如《诗经·豳风·鸱鸮》:“彻彼桑土”,马瑞辰《传笺通释》:“彻,与撤通。”《孟子·公孙丑上》:“彻彼桑土”,焦循《正义》:“撤,彻字通。”
(四)曰:“荑狄之有君也,不若诸夏之亡也。”(第四○号简)
校勘记:“荑,今本作‘夷。荑为夷之误。”
按:此处“荑”并非误字,而与“夷”是同音通假字。《广韵·脂韵》中有“荑”和“夷”二字,其注音皆为“以脂切”。并且“荑”与“夷”通假并非仅此一例,如《周礼·地官·稻人》“凡稼泽,夏以水殄草而芟荑之。”《经典释文》出“荑之”曰“音夷”,《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勘记云:“宋本同。唐石经、余本、嘉靖本、闽监本、毛本‘夷作‘荑。《释文》作‘荑,音夷。宋本注无。案:《秋官·薙氏》经注皆作‘夷。《汉制考》引此经‘芟夷注为‘夷,皆与宋本同。”因此“荑”为“夷”的同音通假字,而并非注释中所说的“夷之误”。
(四)与其媚于窖(第四八号简)
按:窖,阮本作“奥”。“窖”与“奥”音义相近,疑此处原应为“窖”字。窖、奥古音近(窖,古音见母幽部。奥,古音影母幽部)可以通假。《说文解字·宀部》:“奥,宛也,室之西南隅。”段玉裁注:“奥,室之西南隅,宛然深藏,室之尊处也。”关于此句的文义,孔安国曰:“王孙贾,卫大夫。奥,内也,以喻近臣。灶以喻执政。贾执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关于如何将“奥”与近臣联系起来,邢昺疏曰:“奥,内也,谓室内西南隅也。以其隐奥,故尊者居之。其处虽尊而间静无事,以喻近臣虽尊不执政柄,无益于人也。”如此一来,需要将“奥”字进行多次引申才能使其义与本句的句意相符合,略显牵强。
但是,如果按照简本中的“窖”字来解释,便更直接一些。《说文解字·穴部》:“窖,地藏也。”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二十“坑窖”注:“窖,穿地为室,藏五谷者也。”窖,为藏粮食的地方;而灶,则为烧火做饭菜的地方。相对于吃饭问题,窖与灶哪一个与人的关系更为密切呢?一般来说应该是灶。因而,窖与灶便引申为“县官”和“现管”之义,与公孙贾所要表达的意思也更加吻合了。
(六)哀公问主于宰我(第五五号简)
主,阮本、皇本作“社”,《经典释文》:“郑本作‘主。”黄焯案:“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正义》云:《论语》‘问主于宰我,《古论语》及孔、郑皆以为社主,张、包、周等并为庙主。”
按:关于究竟是“问社”还是“问主”的争论古已有之。《说文·示部》:“社,地主也。”《周礼》:“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陈侯免,拥社。”陆德明《经典释文》:“社,社主也。”《汉书·眭弘传》“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颜师古注:“社木,社主之树也。”因此,若此处为“问社”,便解释为哀公向宰我询问关于社主之木的事宜。关于“主”字,《文选·张衡〈东京赋〉》:“咸用纪宗存主。”薛综注:“主,木主。言刻木为人主神,置庙中而祭之。”《公羊传·文公二年》:“为僖公作主也。”何休注:“主,为僖公庙作主也。主状正方,穿中央达四方。天子长尺二寸,诸侯长一尺。”如果此处为“问主”,其意便为哀公向宰我询问关于社中牌位所用之木的事宜。吐鲁番阿斯塔纳墓363号墓唐写本《论语》郑玄注本中此句作“问主”,定州简本《论语》中“问主于宰我”,又为‘问主提供了左证,证明此处询问的的确为社中牌位之木而非社旁所植之树木。
(七)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未为可知也”(第七一号简)
未,阮本作“求”。观察此句的句型“不患……,患……。不患……,患……”今本“求为可知”,邢昺疏:“求为可知也,言求善道而学行之,使己才学有可知重,则人知己也。”但如此一来,就与本句的句型不相符合了。简本作“未为可知”,本句即意为“不担心他人不知道自己,只怕自己没有值得别人知重的才学”,如此句意恰好与邢昺的疏相符合,句型也实现了一致。
(八)子曰:“君子逾于义,小人逾于利。”(第七三号简)
校勘记:踰,今本做“喻”。《说文》无“喻”。
按:此处何晏注:“孔曰喻犹晓也。”邢昺疏:“《正义》曰:此章明君子小人所晓不同也。”一般将“喻”解释为“通晓、明晓”。但简本作“踰”,《说文·足部》:“踰,越也。从足,俞声。”此外,“踰”又可以训为“过也”“越过也”。例如:《史记·汲郑列传》“无以逾人”,司马贞《史记索隐》:“逾,谓越过人也。”《孟子·梁惠王下》“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朱熹《集注》:“逾,过也。”《淮南子·道应》“踰之”,高诱注:“逾,越,胜之也。”如此一来,本句就可以解释为:君子在对义的追求方面有过人之处,而小人在对利的追求方面有过人之处。
(九)道不行,乘泡浮于海(第八零号简)
校勘记:“泡,今本作‘桴,泡误。古桴、枹同通,枹、泡形近。”
按:简本此处“桴”作“泡”,“泡”不一定是误字。泡,古音滂母幽部;桴,古音并母幽部。两字叠韵,又属邻母,音近实可通假。“桴”字之意为木筏,而《经典释文》黄焯案:“敦煌写本作‘乘,注云:“字亦作桴,桴,抚于反。《说文》云:,木筏。”字的本字是“泭”,《国语·齐语》:“方舟设泭,乘桴济河。”韦昭注曰:“编木曰泭,小泭曰桴。”泭从水,泡亦从水,两字不但音近而且义同。所以,“泡”与“泭”“桴”等字为通假字,而并非是误字。
(十)友信之(第一○五号简)
按:,阮本作“朋”。又见《子路》篇,阮本“朋友切切偲偲”中的“朋”字,第三六○号简中作“倗”。朋、倗、傰、音近形近义同,是可以通假的,而注释中称:“为‘傰之省,‘傰字读为‘朋。”傰,古音帮母登韵;倗,古音并母登韵。两字是叠韵,又是清浊对转的关系。《说文解字·人部》:“倗,辅也。”段玉裁注:“朋党字正作倗,而朋其假借字。”《周礼·秋官·士师》:“七日为邦朋。”郑玄注:“故书朋作傰,郑司农云:读如朋友之朋。”孙诒让《周礼正义》:“傰,即朋之俗。”《管子·幼官》:“练之以散群傰署。”《管子集校》引何如璋引刘绩云:“傰,即朋字。”
由此可得出这几个字的关系:“朋”是“倗”的假借字,“傰”是“朋”的俗字,而“”是“傰”的省文。
(十一)末之,命矣夫!(第一一八号简)
阮本中“末”作“亡”。
按:“末”字可训为“衰也”“弱也”“终也”等,依照字义和句意,在此处用“末之”较“亡之”更为合理。《广韵·末韵》:“末,弱也。”《广雅·释言》:“末,衰也。”《书·召诰》:“王末有成命。”蔡沉集传:“末,终也。”《逸周书·皇门》“万子孙用末”,孔晁注:“末,终也。”而《说文·亡部》训“亡”为“逃也”,段玉裁注曰:“亡之本义为逃。引申之则谓失为亡,亦谓死为亡。”“亡”既被训为“逃亡”,又被训为“失也”“灭也”“丧也”“死也”,如《公羊传·桓公十五年》“祭仲亡矣”,何休注:“亡,死亡也。”伯牛有疾,孔子握着他的手哀叹:“你渐渐地衰弱下去了,这就是命啊!”
(十二)贲而殿(第一二三号简)
阮本中“贲”作“奔”。
按:两字形近音同义近,为通假字。“奔”字和“贲”字均在《广韵·魂韵》中:博昆切,平魂帮。谆部。《说文·夭部》:“奔,走也。”《尔雅·释宫》:“室中谓之时,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易·涣》“泱泱其机”,焦循章句:“奔,犹贲也。”《集韵·问韵》:“奔,通作贲。”《读书杂志·汉书第十三·翟方进传》:“奔走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王念孙按:“奔与贲,傅与敷,古字通用。”而《诗经·小雅·白驹》“贲然来思”,马瑞辰《传笺通释》:“贲、奔古通用。”《尚书·太诰》“敷贲”,孙星衍《今古文注疏》:“贲者,《风俗通》云:虎贲,犹言虎之贲。是贲与奔通。”由此可见,“奔”与“贲”自古可通。
(十三)黑而职(第一三九号)
阮本“黑”作“默”,阮元校勘记:“《释文》出‘默云:俗作嘿。《五经文字》云:默与嘿同,经典通为语默字。”
按:默、墨、嘿、黑在经典中是可以通用的。《广雅·释器》:“默,黑也。”王念孙疏证:“默,亦墨字也。《韩诗外传》云:默然而黑。”《集韵·德韵》:“嘿,通作默。”《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嘿而逃去,遂不复会。”《后汉书·梁统列传》:“冀嘿然不悦。”《墨子·贵义》“嘿则思”,孙诒让间诂引毕云:“嘿,默字俗写从口。”综上所引,“嘿”为“默”的俗体,“默”“墨”“黑”同义且“默”与“黑”同属德韵,为叠韵的关系。所以,“默”字实际上是简本《论语》中出现的“黑”字的后起之字,“黑”通假为“默”。
(十四)以学,亦可以毋大过矣(第一五七号简)
按:阮本“亦”作“易”,“易”字属上读,即此句意为“五十岁的时候去学习《易经》”。《经典释文》云:“鲁读易为亦。”黄焯案:“《鲁论》作亦,连下句读。惠云,《外黄令高彪碑》云,虚括守约,五十亦学。此从《鲁论》亦字连下读也。学音效,约音要。”由此可见,一般的通行本作“易”,而《鲁论》作“亦”,使其成为下句句首的一个连词。此句引起诸家争议已久,而简本《论语》与《鲁论》同,也成为了简本与《鲁论》具有密切渊源关系的一个证明。笔者认为,《论语》全篇所记载的孔子言行中可以看出,孔子强调一个“学”字(据笔者统计,《论语》全篇共出现“学”字66次),并且从不同的方面阐述之:学习的目的、时机、方法、对象、内容以及所要达到的效果等等。朱熹在《论语集注》中云:“学易,则明乎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故可以无大过。盖圣人深见易道之无穷,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学,而又不可以易而学也。”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也指出,《易》中的《卦辞》和《爻辞》是孔子的作品。但是,孔子并没有在其言论中提及《易经》以及学习《易经》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在这里孔子仍然在强调学习,此句的句意可理解为“五十岁的时候学习,也可以使自己的言行没有大的错误”。
(十五)印为之不厌(第一八三号简)
校勘记:印,今本作“抑”。《说文》云:“抑从反印”,作印误。
按:在小篆字体中,“印”字字形上部是手状,下部是一个跪着的人形,此字实际上就是以手压人之状。因此“印”与“抑”在字义上是十分相近的。《诗经·齐风·猗嗟》“抑若扬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韩作卬若扬兮。”此例更加证明了“抑”“印”“卬”由于字形上的相近之处,是可以通假的。注释中称“作印误”,实际上是十分不妥的。
(十六)诚唯弟子弗能学也(第一八四号简)
校勘记:阮本作“正”,郑注云:“鲁读‘正为‘诚,今从古。”则“诚”从鲁。
按:“诚”字可以训为“信也”“实也”,例如《尔雅·释诂上》:“诚,信也。”《助字辨略》卷二:“魏文帝与吴质书: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此诚字,信也,实也。”《孟子·公孙丑上》“子诚齐人也”,赵岐注:“诚,实也。”如此句意便为“这实在是我们做弟子的所不能学到的”,比解释为“这正是……”更为合理。此处也是简本与《鲁论》关系的左证,单承彬先生在其文章中证明“简本与郑玄所注《古论》不同,而与《鲁论》多同”时,也举此为证例。[9]
(十七)絻,卑宫室而……(第二一一号简)
按:絻,阮本作“冕”。“絻”是“冕”的古字,《广韵·狝韵》:“絻,同冕。”《文选·任昉〈为萧扬州荐士表〉》“伏惟陛下道瘾旒纩”,李善注:“絻,古冕字。”《逸周书·命训》“有绋絻”,朱右曾《集训校释》:“絻者,冕之或体。”简本中“冕”字皆作“絻”。
(十八)然善牖人(第二二三号简)
按:牖,阮本作“诱”。两字是可以通用的,《诗经·大雅·板》“天之牖民”,毛传:“牖,道也。”孔颖达疏:“牖与诱古字通用,故以为导也。”朱熹《诗集传》:“牖,开明也。”《说文·片部》段玉裁注云:“牖所以通明,故叚为诱。”
(十九)逝者如此夫(第二三一号简)
按:此,阮本作“斯”,皇侃疏曰“斯,此也。”“斯”与“此”字义相同,《易·系辞上》“上衍之数五是”,韩康伯注“斯易之太极也”,孔颖达疏斯为此。《诗经·小雅·采薇》“彼路斯何”,郑玄笺:“斯,此也。”《文选·鹦鹉赋》“故每言而称斯”,李善注:“斯,此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义府》“斯与”中称“《论语》中有斯字,无此字。斯者,此字之转音而借用者也。”而简本中出现了“此”字,证明了《义府》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二十)衍衍如也(第二七四号简)
衍衍,阮本作“侃侃”。
按:疑此处“衍衍”为“衎衎”。侃字在《说文解字·川部》被释为“刚直也”,且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侃,叚借为衎。”“衎衎”在字义上与“侃侃”相同,可被训为和乐的样子,还可被训为刚直耿直的样子,《易·渐》:“鸿渐于盘,饮食衎衎。”尚秉和注:“衎衎,和乐也。”《汉书·张敞传赞》:“张敞衎衎,履忠进言。”颜师古注曰:“衎衎,强敏之貌也。”《尔雅·释诂上》:“衎,乐也。”郝懿行《尔雅义疏》:“衎,通作侃。”《经籍籑诂·旱韵》:“《唐扶颂》:衎衎。《袁良碑》:其节衎然,忠义之臣。《孙根碑》:衎謇不挠。侃并作衎。”
由此可知,衎衎与侃侃常可相通。而简本中“衍”与“衎”字形十分相近,且经典中亦有衍衎相通的例子:《榖梁春秋·襄公十六年》“卫侯衎复归于卫”,陆德明《经典释文》:“衎,本作衍。”因而笔者认为简本中的“衍”原应为“衎”,关于此处的定论还应去核对原简的文字。
(二十一)何足数也(第三五○号简)
按:数,阮本作“算”,何晏注曰“算,数也”,正平本作“筭”。《说文解字·竹部》:“筭,长六寸,计历数者。从竹从弄,言常弄乃不误也。”“算,数也。从竹从具,读若筭。”段玉裁注云:“筭为算之器,算为筭之用。”可见这两个字的意义是不同的,筭是一种计数用的工具,而算才是指计算这一活动,可见此处作“筭”在意义上是不确切的,阮元校勘记中亦云:“案郑君注:算,数也,不当作筭字。《汉书·公孙贺传赞》及《盐铁论·大论》并引作‘选,乃算之假借字。”《尔雅·释诂下》《玉篇·竹部》《集韵·韵》皆云:“算,数也。”《说文解字·攴部》:“算,计也。”因而在表示“计数”这一行为时,“算”可训为“数”,用“数”则更为贴切。简本作“何足数也”,应该是保留了《论语》古本的原貌。
(二十二)耕也,饥在其中○,学矣,食在(第四四五号简)其中○。君子忧道不忧贫。(第四四六号简)
饥,阮本作“馁”;食,阮本作“禄”。两“○”处,今本作“矣”,简本原有字后刮去。
按:(1)“饥”与“馁”字义相近。《说文解字·食部》:“饥,饿也。”《诗经·陈风·衡门》“可以乐饥”,郑玄笺:“饥者,不足于食也。”《说文解字》中无“馁”字,《玉篇·食部》:“饥,饿也。”《左传·桓公六年》“今民饥而君逞欲”,陆德明《经典释文》:“饥,饿也。”这说明“馁”后起于“饥”,两字意义差别不大。并且经典中两字常通用,《管子·小匡》“使臣不冻饥”,戴望《管子校正》:“《左氏·庄九年正义》引‘饥作‘馁。”《广雅·释诂四》:“馁,饥也。”
(2)“禄”一般被训为“食”。《荀子·强国》:“官人益秩,庶人益禄。”杨倞注:“秩、禄皆谓禀食也。”《吕氏春秋·怀宠》“皆益其禄”,高诱注:“禄,食。”《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郑玄注:“禄,所受食。”
由此可见,“饥”可通为“馁”,“食”可通为“禄”。简本用“饥”“食”,保留了古本的原貌。
(二十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第五二四号简)
钟,阮本作“钟”,阮元校勘记云:“皇本、闽本、北监本、毛本‘钟作‘钟,注疏并同。”
按:从确切的字义上来讲,此处应为“钟”,简本的文字也为此提供了依据。“钟”与“钟”形近音同,但字义完全不同。钟是一种乐器,《说文解字·金部》:“钟,乐钟也。秋分之音,物种成。从金童声,古者垂作钟。”《尔雅·释乐》“大钟谓之镛”,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字林》:“钟,乐器也。”而钟是一种酒器,《说文解字·金部》:“钟,酒器也。”《孟子·告子上》“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赵岐注:“钟,量器也。”钟常与鼓连用表示乐器,本句中“乐云”“钟鼓”,显然表示的是乐器,应用“钟”字。
当然,经典中两者的区别并非泾渭分明,“钟”字常假借为“钟”,如《韩非子·解老》“鼓竽先则钟瑟皆随”,王先慎集解:“钟,古通用钟。”《庄子·天地》“以二缶钟惑而适不得矣”,陆德明《经典释文》:“钟,应作钟。”
(二十四)三年不为乐,乐必项(第五四○号简)
注释:“项,今本作‘崩。作项误。”
按:此处孙钦善先生指出,“项”或为与之形近的“顷”字,而倾与顷相通。[10]《诗经·大雅·瞻卬》“哲妇倾城”,朱熹《诗集传》:“倾,覆也。”《文选·干宝〈晋纪总论〉》“基广则难倾”,李周翰注:“倾,崩也。”因而,可以看出“倾”与“崩”意义相同,简本中“项”原为“顷”的可能性极大。
(二十五)三人焉(第五五三号简)
按:人,今本作“仁”,何晏注曰:“仁者爱人,三人行异而同称仁,以其俱在夏乱宁民。”但此处若为“仁”,还须增字为训,简本作“人”则更容易解释。
(二十六)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第五九九号简)
阮本文字与简本同,但阮元校勘记云:“汉石经、皇本、高丽本不重‘罪字。案《书·汤诰》云:‘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国语·周语》引《汤释》云:‘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墨子·兼爱篇下》亦云:‘万方有罪,即当朕身。《吕氏春秋·季秋纪》云:‘万夫有罪,在余一人。《说苑·贵德篇》云:“‘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与此并大同而小异,核其文义俱不重‘罪字。”
按:阮元的说法恐误,因为此处汤的话均为四字一句,单从句式上来看,此处就应该重“罪”字,意为“如果天下万方有罪,罪责都在我一人之身”。并且阮元所引的“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并非与此句同,而是同下句中周武王所说的“百姓有过”相同。因而无论从句式还是从文义来看,此处都应为“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简本的文字更提供了证据。
三、结语
在校勘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了简本《论语》有以下特点:第一,保留了大量的古字形,并且往往会在简本与传世本相异之处发现其与《鲁论》的渊源关系;第二,避汉高祖刘邦之讳;第三,简本文字中有大量“不规范”的文字,如文字的简省、叠加、偏旁的错位等。这些特点说明:在简本所处的时代,各家治《论语》正处在由齐转鲁的过程中,在齐鲁融合的同时更多的反映了鲁论的特点。简本出土于中山怀王之墓,说明此本肯定反映的是墓主人所钟爱的《论语》流派。简本中出现的文字的“不规范”的用法,一方面体现了汉字字形字义演变的过程,同时也说明了定州简本并非当时官方所定的、各家所统一遵循的《论语》版本,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初年治《论语》的诸家纷呈的状态。本文认为,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所保留的《论语》古本原貌,是先于三家论的、各家融合而更多体现《鲁论》特点的《论语》版本。随着学者对于定州简本《论语》研究的不断拓宽和深入,相信我们对于《论语》的传习和流变过程会有一个更加明晰的思路和理解。
注 释:
[1]李学勤:《八角廊汉简儒书小议》,收于《简帛佚籍与学术史》
中,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单承彬:《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性质考辨》,《孔子研究》,
2002年第2期,第29-38、124页。
[3]陈东:《关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几个问题》,《孔子研
究》,2003年第2期,第4-13页。
[4]李若晖:《定州〈论语〉分章考》,《齐鲁学刊》,2006年第2
期,第20-23页。
[5]郑春汛:《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性质看汉初〈论语〉的面
貌》,《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第38-40页。
[6]陈垣《二十史朔闰表》第14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7]单承彬:《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性质考辨》,《孔子研究》,
2002年第2期,第33页。
[8]孙钦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校勘指瑕》,《文献》,2007
年第2期,第152页。
[9]单承彬:《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性质考辨》,《孔子研究》,
2002年第2期,第33页。
[10]参见孙钦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校勘指瑕》,《文献》,
2007年第2期,第152页。
参考文献:
[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M].北京:文物
出版社,1997.
[2]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皇侃.论语集解义疏[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5册) .
[4]陆德明.经典释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5]黄焯.经典释文汇校[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7]宋本广韵[M].北京:中国书店,1982.
[8]丁度.集韵[M].北京:中国书店,1983.
[9]王念孙.广雅疏证[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0.
[10]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故训汇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3]陈垣.二十史朔闰表[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14]杨伯峻.论语译注(第二版)[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韦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