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科迪
2009-05-25朱贤杰
朱贤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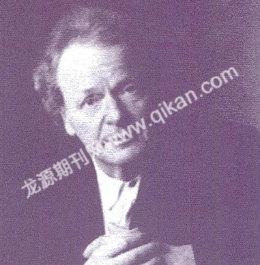
“音乐整个是一体的,为了能够美妙地表达音乐,你必须具备技术。伟大的演奏家所做的是,在可能与不可能的界线之间。如果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就不可能让人信服。”
——安东·科迪
2008年10月2日晚,上海音乐厅。加拿大钢琴家安东•科迪(AntonKuerti)正在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贝多芬的《G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与《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 》。
穿一件深蓝色上装的科迪,演奏手势相当简洁,而他的琴声如此感人,充满内在的激情。他将这两部音乐会中常见的协奏曲演绎得新颖而富有想象力,让人觉得似乎是第一次听到它们一样,在他指下,贝多芬音乐中的内在张力伸展到了极限,营造出近乎白热化的气氛。音乐厅的一千多名听众,听得聚精会神,当最后一个和弦响起时,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鼓掌叫好,久久不愿散去,直到音乐厅的灯光全部亮起。
这是科迪连续第三年参加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的国际钢琴大师班。在前两届的音乐会中他精彩地演奏了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奏鸣曲,因而早已在上海的听众中享有盛誉。当晚的音乐厅几乎爆满,楼厅还加了临时座位,可谓盛况空前。但是,听众中或许没有人知道,这位钢琴家是坐地铁来音乐厅排练和演出的,他坚持不肯坐大师班主办方给他派的车,让陪同的人员大为不解。
尽管《CD评论》杂志称誉科迪为“本世纪真正伟大的钢琴家”,《号角》杂志则称他为“当下最好的钢琴家”,但是他自己宁可置身于名利场外。在美国与加拿大的音乐圈内,科迪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是他并不是名闻天下的那一类,如果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问老师,“谁是北美洲最有名的钢琴家”,答案不一定是科迪;但是如果学生问老师,“谁是最好的钢琴家”,那么老师的回答常常是科迪,尤其是他演奏的贝多芬。《美国录音指南》赞叹道:“很难说人们是惊异于贝多芬还是科迪,因为他们几乎合为一体。这是一种令人激动的体验:让我们瞥见了永恒。”
加拿大这个人口三千万的国家为国际乐坛贡献了相当多的钢琴家,从人口比例上来说,可能比任何地方都高。而且——也许是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使然——他们大都极有个性。当然,凡是艺术家都具有强烈的个性,但是像科迪这样特立独行到乖张的地步的,还不多见。他的种种反常规的行事方式可以追溯到1975年。当时的《加拿大表演艺术》杂志刊登过一篇题为“安东•科迪挑战名声”的评论文章。今天,他已经赢得了这种挑战:不管媒体如何冷嘲热讽,他就是不与大牌的唱片公司签约。并且,他宁可在加拿大北方的小型音乐节演奏,也不愿去参加萨尔斯堡音乐节或者英国的“逍遥”音乐节(Proms)。
他我行我素的个性使得他有时到了旁若无人的境界。几年前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一次演出中,他突然在乐章中间停了下来,离开舞台,再回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把螺丝起子。他一边抱怨钢琴机芯里一个零件不好,一边若无其事地将键盘移出来,调整了榔头的位置,再把它装回去。这一切都在几分钟之内完成。然后,再从方才中断的地方开始演奏。评论家认为他在舞台内外的作风,无助于提高他的专业形象,而让人想起加拿大另一位怪才古尔德。
音乐会的第二天晚上,当我们与科迪在“香樟花园”饭店落座之后,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何你不愿意与大唱片公司签约?”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因为他们要限制我的自主权。他们规定你必须录什么,而我不喜欢。”
“那么你不考虑名声?”
“我想,古典音乐家不需要跟摇滚乐手、流行明星,或者足球、冰球手去竞争。”他解释道,“我们宣称我们不是为了钱财而干这一行的,这不是商业,这是一种精神需求。如果我们能够挣很多钱,当然很好,但是我发现这很难,如果我在一场协奏曲的演出中挣到七万五千美金,那么看看乐队中小提琴手的眼神吧,他们一年也没有挣这么多。经济的考虑使得音乐演出的场地越来越大,变成一种‘追星行为,你去‘看阿什肯纳齐演奏,去‘看马友友拉琴,当然,最大的马戏团,是三大男高音。”
科迪1938年生于维也纳。父母是科学家,业余音乐家。但是他并没有在那里呆很久。“我是犹太人”,他说:“但是我的父姓科迪是源自匈牙利。”他出生的那年,因为希特勒的反犹行为,迫使他们一家避难到了英国,从那里,一家人又分头寻找落脚之处。母亲与孩子去了土耳其,父亲去了美国。那时似乎美国的前景好一些,他与母亲经过长途旅行,在二次大战爆发前到了美国。他父亲,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后来的航天专家,凭着爱因斯坦的一封推荐信,在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大学找到了一个研究助理的职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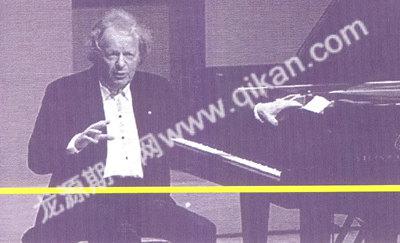
音乐天赋极高的科迪在四岁半时,没有征询他父母的意见,就要求幼儿园的老师教他钢琴。他跟过许多老师,其中有塞尔金、霍尔佐夫斯基。他首次登台演出是在9岁,与波士顿乐队合作。他还学过小号与法国号,16岁那年他作为音乐家拿到了平生第一笔报酬,他记得是25美元。19岁那年,他赢得费城乐队比赛奖和威望极高的“列文特里特”(Leventritt)比赛奖,使得他有机会在卡内基音乐厅与纽约爱乐乐团,以及克里夫兰交响乐团、底特律和匹兹堡乐团合作演出。《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对他有相当高的评价。他成了美国的明日之星。
但是事情的发展常常出乎意料。科迪于1961年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了他第一场音乐会,据他自己说,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不是音乐上的关系,使他打起行李,往北方进发。
我问他:“听说你是因为反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而迁居到加拿大?”
他一脸严肃地说:“我反对许多事情……比如,我不能生活在一个有原子弹的国家。”与巴伦博伊姆一样,他是犹太人,但是反对以色列的政策。他敬佩与巴伦博伊姆对话的已经去世的阿拉伯作家萨义德。“有一次他来出席我的音乐会,当时我并不知道,是音乐会之后有人告诉我的,我觉得非常荣幸。”
科迪自1965年起,一直住在多伦多,并于1984年入籍加拿大。他的大提琴家妻子克莉丝汀,已经在去年去世,目前他居住在市中心林登街一栋不起眼的红砖房子里。他告诉我,他有两儿子,“一个拉大提琴,但拉得不怎么样,另一个在波士顿交响乐团当助理指挥”。
2008年3月11日,他去波士顿听他儿子朱利安(Julian)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会,著名钢琴家莱昂•弗莱舍将在音乐会演奏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就在演出之前,获知弗莱舍因病不能上台,科迪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就答应救场——离开演仅仅两小时!听众与评论的反响极其热烈,最后一个和弦刚结束,全场听众像一个人一样,“唰”地站起来鼓掌。关于这场没有排练过的父子音乐会,《波士顿环球报》的乐评写道:“科迪是最优秀的贝多芬演奏家……称得上是加拿大的国宝。”而科迪觉得在他儿子的指挥下演奏非常愉快:“当你在最后一刻被叫去演奏的时候,你会感到压力更小。你对你自己说,如果万一弹得不太好,人们会谅解的。因此你弹得更加放松,更加直率。”他不认为有完美的音乐会,但是,“当你整个地沉浸于音乐的表情与含义之中时,当你对乐器没有不适应的问题,周围没有恼人的噪音的时候,一旦你忘却了舞台上的脆弱感,你能够将自己升华至完全沉浸于音乐之美的境地”。
我告诉他,前晚的音乐会,他演奏的贝多芬的两部协奏曲,就把听众带到了那样的境地,当时我甚至有一种幻觉,似乎是贝多芬再世了,好像是作曲家本人在演奏(舞台上的科迪看起来真的有些像贝多芬)。听我这么一说,他露出一副老顽童的神情,笑着把头凑近我,用肩膀顶着我的肩膀说:“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我想听。”

科迪不是那种深藏不露的人,据说,那天音乐会上半场,他刚刚弹完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在后台就为演出的成功而喜形于色,高兴得像个小孩。
提起《“皇帝”协奏曲》,我问他,第一乐章开头的那段十六分音符的华彩乐段,没有一位钢琴家完全遵照贝多芬在乐谱上的记号去弹,即一个四连音,一个三连音,然后一个五连音,除了古尔德,而古尔德的录音听起来反而有些古怪。他说:“是吗?我得去查一查,”然后,他开玩笑说:“你知道,我很久没有弹它了。”
他吃得不多,夹了一些素菜和很少的鱼,就放下筷子了。我说,吃这么少,要在一场音乐会中演奏两部协奏曲,他的精力从何而来?“我服用许多维他命丸。” 他如是回答。
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有着火爆的脾气,说话相当直率。听我提到经常在多伦多的一个古典音乐电台听到他的演奏,特别欣赏他弹的舒曼协奏曲,他说:“那是个坏电台,因为它在音乐之后很少播放演奏家的名字,只忙着播放广告。”他对大公司与广告有种天然的反感。每次看到为他担任翻译的李老师,拿着一罐可乐进课堂,他总忍不住遗憾地说:“真是罪过。”
他抱怨与他前晚合作的乐队:“那是个相当奇怪的乐队,有不错的素质,但是不会奏轻声。最令人不解的,是当我在《皇帝》的慢乐章,为乐队伴奏的那一段时,我试图与乐队交流,我看着他们,可是没有一个队员看我,所有队员都低头看乐谱。”
但他又是宽厚温情,总是想到别人的。在音乐会的上半场和下半场,他出来谢幕时,都是首先把大钢琴的盖子放下来,为的是让听众可以看到后排的乐队队员。他认为演出成功是大家的功劳。他说:“我一直这样做的。”在大师班上课时,有时候他会为学员去搬椅子。
他的脾气禀性在上课时更显露无遗。有个学生问他,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七奏鸣曲,是弹第二还是第三乐章?他说:“我非常不喜欢第二乐章,如果你一定要弹第二乐章,那么我就从这扇门走出去,等你弹完了再进来。”
针对一个学生弹的贝多芬奏鸣曲,他指出许多问题是因为版本不好引起的;“你是这个差版本的受害者。有些乐谱版本糟糕透了。有一个钢琴家鲍尔(Bauer)修订的舒曼的《花纹》版,在乐谱中鲍尔几乎修改了每一样东西。我看到这个版本,就把它撕了,贴在我的琴房门上示众。”他一面说,一面配以手势,好像恨得咬牙切齿一般。
无论是大师班,还是在平时吃饭聊天的时候,据星海音乐学院的孙鹏杰老师说,如果刚好跟科迪在聊到某一部作品(大多数都是贝多芬)的某一处处理的时候,科迪觉得,一听有些学生,就知道他们是听完录音在模仿某某钢琴家的处理,然后他就会说:“我知道许多大钢琴家这样弹,但是他们错了(I know many great pianists do that, but they arewrong)。”而且每次说:“错了!”的时候都会做同一个动作:一挥手,然后皱起眉头,作出恶作剧般的神情。
上海大师班活动的最后一天中午,科迪上完最后一堂课,就被学生们团团围住了,他们争着与他合影,要他签名。走出课堂,一路上仍然被许多学生围堵。他像一个慈祥的长者,耐心而且高兴地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三年来,他无疑已经成为学员们心目中最喜爱的大师之一。他带来的贝多芬的录音总是被抢购一空。然后他就带着得到的人民币,拿着一幅地图去云游四海。这次他要去安徽。他给我一张他的名片,告诉我他10月20日之后回多伦多。
在多伦多住了四十多年之后,科迪似乎比大多数加拿大人更加拿大化。不仅是他对户外生活的热爱:他尽量不开车,他骑自行车或者跑步。而且还有其他方面。对政治与社会活动,他一直持有很大的兴趣。他经常为报纸写读者来信,表达他的观点,他支持绿色和平组织等团体,1983年,他倡议出版保护鲸鱼的书籍。他征求以鲸鱼为主题的短曲,收到了伯恩斯坦、武满彻、谢德林等作曲家的新作品,他将它们收进这本书里。他告诉我:“谢德林还寄来了他作的一幅画,几乎可以当作乐谱演奏。”他自己也是一位作曲家,他目前演奏的五十多部协奏曲中,有一部就是他自己作曲的。“音乐家如果不能作曲,是很奇怪的”,他若有所思地说道:“这是音乐中最具创意的部分,就算是只为你自己,它可以使得你更加懂得欣赏伟大作曲家的作品。”
除作曲之外,科迪还热心于室内乐,《纽约时报》称他为“一位理想的室内乐演奏家”。与他合作过的有马友友,吉顿•克莱默和东京四重奏组等等。科迪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大提琴家勃劳特说:“我认识科迪三四十年了。他是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我认为他是现今最伟大的音乐家。作为一个人和一个艺术家,我都对他极为尊崇。”
对科迪来说,行动比说话更有力。为了更直接地参与政治,科迪在1988年代表左翼的新民党竞选国会议员,可惜功败垂成。如果说,他在政治上的努力没有得到承认,那么他作为一位音乐家,在加拿大却大受欢迎。除了在大城市演出,他还在许多小镇上享有盛名,在那些地方,他收费很低。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他在150个大厅演奏过。在他演奏事业顶峰时期的80年代,他每年举办80场音乐会,时常用他的货运小卡车,装上他的钢琴,穿越千山万水,到加拿大那些偏远地区去演出。我有他那个年代去农村演出的照片。他高兴地回忆起,在曼尼托巴的一个只有1500人口的小镇上,有750人出席了他的音乐会。还有一次,他去查罗德皇后岛演奏,只是因为那里有一位老太太写信给他,说她是多么喜爱他的录音,请求他去她的小镇演奏。
当然,科迪并没有将他的演奏范围局限于加拿大。他在全世界31个国家演奏过,包括大部分欧洲国家。今年来上海之前,他刚刚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挤满了两千多名听众的音乐厅里,临时代替不能上场的默里•普拉亚(Murray Perahia)演奏。
他的演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演奏的贝多芬作品—— 《告别》与《热情》奏鸣曲以及《迪亚贝里变奏曲》好评如潮。当地报纸评论道:“当科迪演奏《迪亚贝利变奏曲》的时候,奇迹发生了……这部作品对于许多钢琴家来说,是一个不可能攻克的堡垒。然而科迪,他的演奏是那样地毫无瑕疵,令人目眩神迷,鲜活而透彻,无与伦比地将33个变奏整合在一起……在这次首演之后,他在此地与其他地方一样,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科迪这种对政治的热衷,对大人物的反抗和对小人物甚至动物的关爱;这种愤世嫉俗,直言不讳的性格与大爱无疆的胸怀,是非常贝多芬的,难怪他演奏的贝多芬这样出色,他对贝多芬的音乐有种发自内心的认同与共鸣。
尽管他挑战或者甚至远离名声,但是名声还是找上门来了。欧洲顶级的演出经纪公司Riaskoff已经为科迪代理了好几个国家的演出。而加拿大政府最近授予他代表国家艺术最高荣誉的“总督奖” 。
科迪今年夏天度过了70岁的生日。其他人在这个年龄已经退休。但是对科迪来说,这只是另一个生日而已。他继续专注于他终生的事业,演奏、创作、研究音乐。谈到音乐演奏,他认为,技术、乐句或者音乐的意向等等音乐“整个是一体的,为了能够美妙地表达音乐,你必须具备技术。伟大的演奏家所做的是,在可能与不可能的界线之间。如果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就不可能让人信服” 。
在被问到他希望人们将会怎样铭记他的艺术使命,他停顿了一下说:“我觉得,一方面是一个真正尊重作曲家的表演者所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更个性化、更浪漫的途径,不那么把人束缚在一种传统的演奏方式上,我愿意认为我是在尝试把这二者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