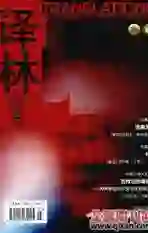巴赫曼文学创作中的历史意识
2009-05-07刘文杰
摘要:短篇小说《在杀人犯与疯子之中》是巴赫曼的一部重要作品,本文根据小说主人公即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叙事过程,探讨他从最初彷徨无力到最后明确自身定位、并敢于质疑当时主流精神的变化过程,阐述巴赫曼对奥地利20世纪50年代纳粹社会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揭露。同时,通过对主人公身边不同角色的分析,探讨作家对于战后奥地利社会在反思二战问题上的态度及其文学创作中的历史意识。
关键词:战争反思杀人犯受害者历史意识
奥地利女作家英格博格·巴赫曼历来重视历史意识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她在1973年的一次采访中强调:“对于作家来说,历史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一个人看不到我们当今时代背后的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关联,那么他就无法写作。”从巴赫曼的生活年代看,她经历了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创伤在她的生活中乃至在她以后的文学创作中是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由此可见,巴赫曼的历史意识明显集中于对二战历史的记忆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注,而对战争的反思则是她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表现主题之一。
1961年,巴赫曼发表了短篇小说《在杀人犯与疯子之中》,收入到她的短篇小说集《三十岁》中。这部小说在她的短篇小说集中是最富有批评精神、揭露现实社会最为尖锐、在奥地利当代现实批判性文学中最具有先导作用和影响的一部作品。
一、社会文化结构的“混淆状态”
巴赫曼在小说一开始就揭示了战后奥地利社会人们的心态,并以讽刺的语调对此加以描述。“男人们都在逐渐找回自我”,然而他们寻找自我的方式是不同的。他们不是在新的时代里对过去进行反思,重新定位,而是逃避到一个与日常生活相脱离的封闭空间,沉浸在回忆中寻找安慰。
50年代初期,以美国为首的占领国出于对欧洲军事策略的考虑,逐渐减少了奥地利非纳粹化的各项措施,并在1957年3月14日以所谓的“纳粹赦免令”终止了清算纳粹的计划。这项措施所带来的后果是,奥地利人没有从自身内部进行战后反省和致力社会良性秩序的重建。虽然战后国家政治机构的外部框架很快被构筑起来,但是要想从各社会阶层与民众心态上完成相应的转变,显然不是在短时期内可以实现的。许多纳粹时期的参与者如法官、教授、医生、记者以及政府公务员又迅速回到从前的职位并重新占据了社会的重要地位,而流亡者和大批饱受战争迫害的人们则必须历尽艰难才可能重新融入社会或进入主流,甚至仍然不得不为生存而抗争。这种不平等的共处局面对于他们来说是难以接受而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这种现实状况意味着,过去的纳粹分子在战后能够依然得势,而战争的受害者面对过去的历史则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巴赫曼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社会现状,其小说的标题《在杀人犯与疯子之中》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她对战后奥地利社会中凶手与受害者“同桌共饮”的现实问题的观察,也暗示了战后国家的纳粹势力依然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一事实。
小说《在杀人犯与疯子之中》里每周聚会的男人明显地分成两类,一类是前纳粹军官哈德勒、胡特、拉尼兹基和纳粹士兵贝尔托尼等人。他们过去曾积极地拥护纳粹,参与大屠杀的罪行,如今依旧是时代的宠儿,成为社会的主流。另一类则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荷尔兹和弗里德尔,属于战争受害者的犹太人身份。在此,巴赫曼还刻意通过一位卖画老人为前一类成功人士所作的画像,揭示其内心潜藏的法西斯本质。虽然他们已经从外部适应了政治和社会局势的变化,但他们的内心实际上并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他们对于战争采取淡化和回避的态度,从未想到真诚地对过去进行反省。当然,他们也谈到战争,如作品中所表现的,仅仅是以插科打诨的方式来谈论战术、决策的错误、进军秩序以及战败的原因等等,但绝不去关心战争的受害者,甚至对其采取完全漠视的态度,将他们排斥在谈论的话题之外。这些所谓的文化名人认为,只有通过战争才会产生文化和经验,因为对于文化来说,战争是必需的。“难道不能说,只有通过战争、战斗和压力才能有文化?”于是,战争便在这种荒谬的文化意识支配下被合法化了,被理所当然地解释为不可避免的历史经验,甚至还得到了积极的评价。由此,纳粹的战争罪责不但没有得到清算,反而变得不值一提了。显而易见,正是有了这种所谓受害国身份的掩护,这些“昨日的刽子手们”才更容易重新回到往日的权力秩序。
在这部小说中,巴赫曼没有像纳粹统治时期那样,简单地把人划分为好人和坏人,而是以写实的手法表现出一种“混淆状态”,以此来揭示当时社会的复杂状况。如同小说主人公“我”原以为“世界已经、而且永远地被分化成了好与坏”,但是现在无论好人还是坏人“又混在了一起”。巴赫曼曾于1966年在一次作品朗读会上把纳粹罪恶产生的根源描述为一种病毒,并严正指出这种病毒即使战争过后还仍在蔓延“不仅我自己,相信在座的各位也都时常会思考,这个罪恶病毒去了哪里——它不可能在20年前从我们的世界里突然消失,就因为谋杀在我们这里不再受到奖励、要求、获得勋章、得到支持。大屠杀虽然已经过去,但刽子手还在我们当中”。这段话无疑点明了小说《在杀人犯和疯子之中》的表现主题。
二、“受害者”身份的尴尬与无奈
作品主人公“我”是一个年轻男子,和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一样,希望人们都能在纳粹统治垮台之后理性地认识过去,勇于承担历史责任,并致力于重建新的社会政治秩序。但是,他从周围人身上看不到这样的希望。因此,他彷徨失措,不知该如何适应这个社会。
在每周聚会者的另一类人中,荷尔兹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他深受纳粹的迫害,妻子和母亲都被纳粹士兵杀害了。然而,他现在却和那些从前的刽子手混迹在一起,甚至还帮助拉尼兹基获得历史教授的职位。他生活艰辛,有求于他们,因而不得不妥协,曲意逢迎这些人。可以说,荷尔兹过去是受害者,现在依然别无选择,还是社会的弱者。显然,在巴赫曼看来,这个人物形象身上体现了历史的悲剧。
另一个人物弗里德尔与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都处于复杂的矛盾心理之中,其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被称为犹太人,尽管事实并非如此。然而,被称为犹太人,也就等于被划归到了弱者一边。弗里德尔是个悲观的角色,他厌恶战争,却看不到任何前景。当哈德勒表示庆幸没有错过战争的经历时,他还敢于对抗,执拗地说道:“可我不想经历战争。我不要这种经历。”他认为“这个世界根本无法行得通”,在他看来,不论是杀人犯还是受害者都没有出路,因为对于杀人犯来说,时代已经不同了,但变化的只是时间。而“受害者还是受害者,就是这样”。在巴赫曼的思想里,“受害者”的概念已经在战后变得毫无意义了。为此,她曾经指出:“不可以有受害者,把人作为受害者,因为受害的人不能带来任何结果。如果说受害者可以起到警示、见证、提供证据的作用,那都是不真实的,而是最可怕、最无知和最虚
弱的诗化之一。”
当然,弗里德尔深感绝望,也想极力摆脱战争的阴影。对他来说,忘记是最好的出路。在洗手间里,他希望自己能把一切带给他“胃痛”和良心折磨的东西统统忘记,“我听到他在呕吐、漱口,喉咙呼噜作响,其间还在说:‘要是所有东西都能涌上来,要是能把所有东西都吐出去多好,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东西!。”显然,弗里德尔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摆脱这种尴尬无奈的局面。但是,他的处境、妻子和三个孩子,迫使他不得不向这些刽子手妥协,以便为自己谋得相应的社会地位,为家庭提供保障。为此,他必须伪装自己,尤其要讨好哈德勒。他直言不讳地对叙述者“我”说道:“我还要有求于他,你说得倒轻松,你又没有妻子和三个孩子。”因此,大家坐在一起时,弗里德尔也会和别人一样,“突然笑得前仰后合”,甚至“努力表现出一副对军事行动、军衔和重大事件很在行的样子”。在此,作品揭示了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尤其是战争受害者在战后社会的矛盾心理。他们经历了战争,成了战败者,虽然参与战争是非自愿的,而且深受战争经历的折磨和痛苦,但他们最终没有勇气面对过去,没有勇气承担历史责任。他们尽管厌恶身边那些往日的凶手,但还是出于无奈跟随他们,违背良心与现实妥协。
三、纳粹的疯狂与病态
在这部作品中,最富有戏剧性、最能震撼人心的一幕是作家对另一位人物形象——陌生人——出现以后的情节描写。可见,巴赫曼在作品中安插了一位陌生人的形象,其表现意图是显而易见的。随着陌生人的出现,作品的情节被推向了高潮,同时作家也把对纳粹的疯狂与病态的描写推向了极端,集中表现了这部作品的现实批判性以及作家对战争的深刻反思。
作品中的陌生人形象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他曾经既是纳粹的一员,又是一个战争受害者。他在作品中一出现就声称自己是杀人犯、刽子手,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实际上从未杀过任何人,而是战争的惨剧摧残了他的心灵,在他的精神上制造了大屠杀的幻觉,以致出现了精神病态。巴赫曼的意图在于告诫社会:虽然那场残酷的甚至罪恶的战争已经结束,但是战争给人们造成的创伤还未痊愈,战争的乌云依旧没有散去,依旧笼罩着人的精神和记忆,因为纳粹势力并没有消亡,其病态与疯狂在战后依然甚嚣尘上。巴赫曼正是利用陌生人这一形象集中表现了她对战后社会现实的观察与思考。当陌生人陷入痛苦的回忆中时,他突然听到隔壁传来退伍老兵唱起当年的歌曲,便情绪激动,不由自主地冲了出去,与那些老兵发生打斗,被当场打死。陌生人的死终于唤醒了叙述者“我”强烈的情感认同。在此,作品第一次把视角从“我”对外部世界的观察转到了自身的内心感受,致使主人公从内心的绝望和无奈转向愤怒和复仇的欲望,进而找到真实的自我,明确自己的定位。
这部作品是以一个富有矛盾意味的描述结尾的,既没有表达出陌生人对待战争的严肃态度,也没有描写出战争受害者强烈的抗拒行为。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作家描写出了战争受害者苟且附和纳粹势力的无奈与悲哀。此外,结尾通过时态和情态的转换,把描写的焦点从人物所经历的感知层面转移到了意识层面。巴赫曼认为,与其说纳粹或法西斯主义指的是一种特定的国家形式或社会制度,不如说它是一种带有普遍民族性格的总和。这种普遍性格存在于每一个人的精神之中,不论现在还是过去都同样明显。巴赫曼在1973年有这样的表述:“纳粹始于哪里?不是始于投掷下的第一批炸弹,也不是始于人们写在报纸上的那些恐怖行为。它始于人们的关系当中,最早从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之中就已开始。”她认为,纳粹势力之所以能抬头,是当时的社会现状把人们变得病态和疯狂:“这些人为什么会如此病态,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什么会半疯半狂?[……]他们的疯狂不过是对于一些无法忍受的事情的心理和生理表现,也就是与现实抗争失败的表现。但同时这又是现实与精神抗争失败的表现,那种精神宁愿陷入疯狂也不愿妥协。”因此,疯狂与病态就是人们在与杀人犯为伍的“混淆状态”下的无奈选择。
正如小说开头所言:“男人们会逐渐找回自我。”主人公从寻找到找到,经历了一段痛苦的认识过程,最后在血的教训面前幡然醒悟。虽然他此时处于一种失常的状态,几近于疯狂和幻觉:“夜晚在我心里回响,而我沉浸在幻觉里。”但是,如果所谓正常的状态所包含的是虚假的东西的话,那么这种非正常的疯狂与病态就恰恰能够说明真相。巴赫曼正是要通过作品的表现主题来揭露奥地利战后的社会现实,正是要尖锐地批判当时人们对于战争与历史的冷漠态度。如作品中所描写的,受害者在战后社会既没有发言权,又受到无情的漠视,最终无奈地选择了苟且附和之路。然而令人深思的是,战后社会中一切反省的、自责的情绪则显得与时代发展不相称,更有甚之,对战争灾难的痛苦记忆反而变成了与社会繁荣的步伐格格不入的东西……这一切,在巴赫曼看来,才是真正的荒诞与病态,才是她要揭露的真实的社会现实。
(刘文杰: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邮编: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