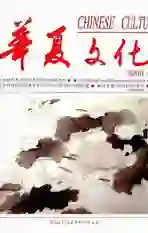略论任继愈先生的学术研究与唯物史观
2009-04-29张岂之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20世纪中国学术史,这是重要的历史课题,需要加以研究。本文拟探讨任继愈先生(1916.4.15—2009.7.11)学术研究的唯物史观特色,向读者朋友们请教。
一、任先生对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评价
任先生与侯外庐先生(1903,2.6~1987.9.14)健在时,由于各忙各的工作,很少直接交谈,只是在有关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见面,有过短时间的交流。1957年至1960年外庐先生主持《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编著工作,隋唐佛学部分写成后,外庐先生叮嘱:“此稿一定清任继愈先生审阅,他在这方面有深入的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任先生看了稿件后,评价很好,但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外庐先生很高兴,要他的助手杨超同志(这一部分的文字起稿者)按照任先生的意见进行修改。任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史及宗教史,在《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一文中,他说:“我过去一直是儒家的信奉者。新旧中国相比较,逐渐对儒家的格致诚正之学,修齐治平之道,发生了怀疑。对马列主义的认识,逐渐明确。在1956年,我与熊先生写信说明,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是任先生在1988年熊十力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稿,详见任继愈著《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11月出版,第523—536页)
2003年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西北大学为纪念这位老校长和著名历史学家,在百年校庆(2D02年)的金秋十月,举办了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西北大学特别邀请任继愈先生光临指导。2002年10月13日上午,在西安止园饭店举行学术研讨,我主持大会发言。第一位发言的就是尊敬的任继愈先生,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专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第20-24页)。他一身深蓝色西服,系蓝灰色领带,温文尔雅,庄严而不矜持。因为对外庐先生学术研究很了解,并作了长时间的思考,任先生不用讲稿,侃侃而谈,言辞自然恳切,引人入胜。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他一开始便提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样回答:
“马克思主义是过去一百年中最有影响的时代思潮。马克思主义方法是观察社会、研究历史的一种崭新的工具。以前国内没有,它是从近代西方引进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用在政治上就引起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思潮。……马克思影响新中国,靠的是他的学说的真理性,靠的是辩证法。这用在史学上作用也很明显,自从有了唯物史观这一观察社会的新的工具,史学(研究)面貌就大不一样了。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出现了一批改变了中国历史学术的杰出人物。……”(任继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载《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第21页)
任先生认为,侯外庐先生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长期学术研究实践中他创立了一个学派。关于这个学派任先生作出这样的评价:“它的主要特点是从文化的整体、社会的整体看问题,而不是孤零零地看一个问题,从整体、全局看局部,跟站在局部看局部不一样。”(任继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载《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第21-22页)在任先生看来,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历史不是从思想到思想,而是从社会史人手进行思想史研究,这二者相结合,就使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任先生还指出,这样的贡献不是偶然的,“侯外庐先生展早翻译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对马恩著作下过功夫,他是从源头上接受马克思主义较早的一位史学家。他的学术优势是从第一手原著人手,他所受联共(布)党史教科书的影响较迟,也较少。因此,他的著作中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缺点也较少。”(任继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载《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第22—23页)
可以看出,任先生2002年的这个讲话,准确地评价了外庐先生的史学研究成就。这个讲话的记录稿整理毕,曾交任先生亲自审阅,他又作了一些修改,才公开发表的。任先生的这篇讲话,学界的朋友们大约很少有人读过,因此在这里我多作了一些引证。
我还想提到,1999年我写了一篇《五十年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论文,在该年度《中国史研究》第4期发表,此文开始我介绍了外庐先生等著《中国思想通史》是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思想通史。拙文发表后寄给任先生,他很快给我回了信:
岂之同志:
《五十年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看过了,这是您很费心思、总揽全局的一篇大文章,我想这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为今后写历史的人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对有些质量差的著作,不免太宽容了。
侯外庐先生对中国思想史,对中国学术史,对文化史、通史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年来学术界对他逐渐淡忘了,有的饮水忘源,很不应该。您的文章做得很对,也看出您的治学文品有古风,也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学术界如果任凭逢蒙射羿之风滋长,就是学术界的悲哀。新年将至,祝好
任继愈
1999.12.14
这封信对我有所鼓励,认为《五十年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性,也是对建国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有助于把握这个时期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进展脉络和主要成果。后来,学者朋友在研究时,注意到了这种参考价值,这是令我略感欣慰的。同时,任先生也委婉地提出了一些批评,主要是认为选择的作品可能存在标准不高的欠缺,这对我是有教益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里,任先生扼要地对外庐先生进行了全方位的评价,不仅看到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贡献,而且注意到他对中国学术史、文化史、通史等方面研究的成就。关于中国社会史,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史学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任先生认为不能饮水忘源,应尊重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断推进学术的发展和创新。同时任先生也对某种“逢蒙射羿”之风感到痛心,希望学术界能矫正不良风气,这已经超出了拙文的范围,提出了新问题。我之所以介绍任继愈先生对外庐先生的评价,是想说明,用唯物史观来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文化史,前辈学者做出的成绩应当予以充分肯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任先生对唯物史观创造性地运用充满赞誉之情。
二、任先生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学术研究的特色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在这里我只是把自己学习、研究任先生著作,特别是他在改革
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的著述,写一些笔记式的体会,还不能称之为系统深入的研究。
任先生研究中国哲学史、宗教史、文化史,总是把研究的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观察、思考,力求加以具体:分析,从而得出应有的评论。这就是说,这种研究紧扣中国古代历史的特点。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以前的历史,任先生没有精力和时间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是从秦汉时起至清朝末年,这一长时段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任先生作了多年的研究,形成他自己的独特视野。他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特色,用他自己的语言文字风格加以论述,将社会史的表述与哲学史、宗教史、文化史的研究对象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所写的一些论文,如《朱熹与宗教》、《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唐宋以后的三教合一思潮》、《武则天与宗教》、《佛教向儒教的靠拢》、《南北朝佛教经学的中心议题——心性论》等都是如此。
这里对《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中华书局2006年10月出版)中第一篇文章《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作些分析(文末没有注明具体的写作年月),其中第一节的题目是“出发点和落脚点”,论述了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一个特点,任先生是这样表述的:
“‘多民族的统一大国是中国的国情。从二千多年前奠定这种格局,就被全国各族人民所接受。古代没有民意测验,从人民默认它,安于这种制度的行为中即可以看出,人民是愿意接受的。二千多年前曾有几度民族不统一的时期,但人们不喜欢这种分裂,因为分裂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灾难,生活不安定,战争频繁。即使在分裂时期,有识之士都主张统一,认为分裂是不正常的。多民族和平共处和要求全国统一一样,得到各族人民的支持、认可。”(任继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第3页)
又说:“‘多民族统一大国是两千年来的国情。这个国情显示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生活准则、宗教信仰、伦理规范、风俗习惯、政治制度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决定着中国哲学的全部内容。”(任继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第4页)由此做出这样的论断:“观察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哲学,都不能不以这个国情为出发点,又落脚到这个出发点。中国哲学必然带有中国的民族时代、历史文化特点,反映它的祈向和理想。”(任继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第4页)
在关于中国哲学史、宗教史的研究中,任先生有一个独特的学术观点:儒家演变为儒教,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完成这个演变的,是南宋时期的大思想家朱熹(1130~1200)。为什么会有这个演变?任先生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和政治、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展开分析。他说:
“自然经济的特点是封闭型,分散经营,不希望政府过分的干预。中国秦汉以后是统一的大国,从政治上要求集中权力,多民族,地区广大,如果政令不一,就难以达到统一的目的。中国中原地区进入封建社会比较早,生产也比较发达,周围的地区有些民族还处在奴隶制甚至原始社会,双方难免发生掠夺性战争。为了保证国家的生产正常进行,客观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维持安全繁荣的局面。政治上的高度统一是客观需要,经济上的极端分散又是客观现实,它是自然经济的本性。政治的集中与经济的分散,这一对矛盾如何协调,不使它畸轻畸重,便成了历代统治者关心的大问题。儒教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任继愈:《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第33页)
作为人文学科的哲学和宗教!学,不像自然科学中的某些实证学科,通过应有的实验手段使研究中的假设得到证实,成为站得住脚的理论。因此,人们便要求人文学者阐述他们研究课题的本身意义,以便从这里判断出基本论点的科学性。中国哲学史、宗教史就是这样的人文学科。按照任先生的说法,哲学史、宗教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就哲学史而言,其意义在于:“哲学史作为认识史,无疑将为人们提供可贵的借鉴。看到前人如何克服错误,我们从中受到启发;看到后人重犯前人已经犯过的错误,我们从中得到警惕。百年前恩格斯就指出:训练思维能力,迄今为止,还没有比学习哲学史更有效的方法。今天看来,它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任继愈:《从中华民族文化看中国哲学的未来》,《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第12页)
那么,任继愈先生研究儒学演变为儒教这个课题是为了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任先生于1982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第5期上的论文《朱熹与宗教》是一篇很重要的学术论文,不论人们是否同意其中的论点,但大家都承认它提出了新问题,促使大家去研究,去思考;而且这种思考是与中国的现实密切相关的。为什么要写这篇论文?任先生在该文的第四节“朱熹与新中国”中有明确的说明:
“中国社会几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就由半封建半殖民地而一步跨进社会主义了。由于缺乏西方约四百年的反对中世纪教会神权的统治势力的斗争的传统,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不少麻烦。‘五四时期提出两大口号‘科学与‘民主。三年前纪念‘五四六十周年,人们还提到‘五四两大任务,还要继续完成。欧洲反封建反了几百年,我们才几十年。中国的封建文化、思想,与封建制度结合得很紧密的宗教(儒教)十分顽强,过去我们对此估计不足。衡量一下,近百年中国走过的道路,再上溯到朱熹,以后九百年走过的道路,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不能无所感受。哲学、宗教,看起来,高高在上,讲的问题,提出的范畴,好像远离人间,实际上它是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任继愈:《朱熹与宗教》,《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第26页)
从以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任继愈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思考了一个重要问题。当时,“文革”动乱刚过去不久,人文社会科学家们都在思考:为什么会出现“文革”这样的恶梦?为什么出现难以理解的“造神”运动?这些问题我国现在年轻一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也许不感兴趣,但是,对于像任继愈先生这样饱经忧患的前辈学者,不能不思考,并力求找到问题的答案;也许答案并非人们都同意,但是前辈学者在关于这个重大问题的思索中,给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也许并不在于答案本身,而在于前辈学者关注祖国与民族前途的执著精神。
这里不能不提到任先生在《(中国儒教论)序》中的话:
“今天50岁以上的人们,对20世纪60年代的造神运动记忆犹新,当时社会上掀起一股如醉如狂的造神运动。这种种不来源于佛教也不来源于道教,而是儒教回光返照。”(任继愈:《(中国儒教论)序》,《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第39页)
任先生在多篇文章中阐发了上述观点,
发表于《文史知识》1988年第6期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更加通俗完整地阐述了他的观点,在该文的末尾有这样的话:
“儒教建立后,历代政府用行政命令推行它的主张,用科举考试鼓励青年人钻研诵习,耳濡目染,使宗教社会化,把俗人变成僧俗。人们记忆犹新的十年动乱期间的造神运动所以得逞,千百万群众如醉如狂的心态,它的宗教根源不是佛教,不是道教,而是中国儒教的幽灵在游荡,只不过它是以无神论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任继愈:《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第35页)
在任先生看来,从早期中国儒家的敬天法祖,到秦汉之际的“三纲”论,到西汉时的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再到东汉时期的《白虎通义》,最后到朱熹的“天理”说,便完成了儒学宗教化的过程。到20世纪60年代,这个儒学宗教化的历史传统成为当时“造神”运动的历史根源。
这里,我不想去评价自己老师的上述观点是否准确,因为这是学术观点,可以进行讨论。我想强调一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前辈学人走过太多曲折的道路,有不少痛心疾首的教训,他们思考的问题并非都是学术问题,而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关于民族复兴的重大问题。今天学人们可以对任先生的上述观点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疑问,例如,我国20世纪60年代的造神运动是否来源于儒学的传统?苏联共产党内长期流行的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没有影响中国?总之,提出问题,才便于讨论。不过,时至21世纪初,人们对20世纪60年代的“造神”运动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去进行讨论,而更加关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因此,当前人们关于中国哲学史、宗教史的研究,已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任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尽管如此,前辈学人走过的道路,呕心沥血思考过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仔细品味。从这个意义上说,任先生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今天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思考着如何使中国哲学史、宗教史的研究更加科学化、学术化、理论化,充分地显示它们的中国特色,不必仿照西方哲学的模式来剪裁中国古代哲学。除此,今天人们考虑得更多的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历史使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作为民族复兴(含文化复兴)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必须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接受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使这些融合为一个整体。我国前辈学人已经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进行过思索,留下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其中所体现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才是后来者应当继承和发扬的。
还要提到,20世纪我国人文学术史告诉我们:前辈学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在发展中去理解并加以运用的。这恰恰就是唯物史观学术研究的生命力所在。
这里我想举出一个例证。在20世纪40年代末,从苏联传来一个观点,提出哲学史的任务在于找出每个哲学家是属于哪个阵营的,是唯心论,或唯物论?因此,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划分阵营的历史,是唯物与唯心相互斗争的历史。这个观点也许是为了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思维而提出的,开始时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这个观点也影响了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们。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任继愈先生在北大哲学系培养外国留学生,为他们讲解《老子》(《道德经》),不能回避老子哲学思想是唯物还是唯心。后来,这个问题经过我国哲学史家们的多次讨论,到2006年,当任先生年届90高龄,第四次用现代汉语翻译《老子》时,他在《老子绎读》一书的“附录”中,反思关于老子哲学思想的争论,写下这样令人深思的论断:
“我一向认为老子的哲学思想比孔子、孟子都丰富,对后来的许多哲学流派影响也深远。总期望把它弄清楚。196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认为老子是中国第一个唯物主义者;197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简编》(是四卷本的缩写本),则认为老子属于唯心主义。主张前说时,没有充分的证据把主张老子属于唯心主义者的观点驳倒;主张后说时(《简编》的观点),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把主张老子属于唯物主义者的观点驳倒。好像攻一个坚城,从正面攻,背面攻,都没有攻下来。这就迫使我停下来考虑这个方法对不对。正面和背面两方面都试验过,都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来,如果说方法不对,问题出在哪里?我重新检查了关于老子辩论的文章,实际上是检查自己,如果双方的论点都错了,首先是我自己的方法错了。”(任继愈:《我对<老子>认识的转变》,载任继愈著《老子绎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第253—254页)
这个反思十分宝贵。我想,不仅对老子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简单地采用“对号入座”(是唯物的一排,还是唯心的一排),对于孔子、孟子、庄子、孙子等等都不能“对号入座”。对于丰厚的、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文化,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需要对它们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从而揭示其特点;还要向世界阐明:中国古代有深厚的哲学理论思维,这是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中华文化进行唯物史观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这就是:对具体的历史文化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这也许才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前辈学人,像任继愈先生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反思,我们在前辈学人的研究基础上应当有所前进,有所创新。离开创新,将如何表现唯物史观的生命力?
200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