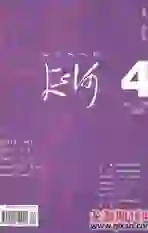松香爽净
2009-04-28鲍尔吉·原野
鲍尔吉·原野 蒙古族,国内读者最多的散文作家之一,多次获得国内大奖,出版散文集18种。主要作品有:《随感录》、《脱口而出》、《百变人生》、《酒到唇边》、《善良是一棵矮树》、《思想起》等。
人在少年,十二三岁会萌发一种无端的忧伤。这时,性还没有出来捣乱。他了解了白天和黑夜、山川和雨水、父母与孩子之后,有一种走到尽头的感受。童年的许多秘密被他窥破了,周遭现出平白,日子单调。他还没有得到了解生活的另一些秘密的钥匙。
这种可笑的忧愁与凝固的时间无关。在我们童年,一个下午有多么漫长。而所有诱人的游戏显示出无聊的时候,譬如抗马战、弹玻璃球之流,更显出一种悲哀的情绪。那时我坐在木材厂的木垛上,看太阳落山、飞鸟投林,闻到屁股下面的木板散发出更加强烈的松香气味心里便难过。如果是大型食肉动物,在相当于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早就“分窝”了,无所依靠,奔跑在密林里,斗争、夺取、流血、牺牲,无暇感伤。人在这个时候,最需要文艺作品的慰藉。《红岩》、《敌后武工队》,当年的最后一页翻完,犹如看一队人马绝尘而去,但不带你,把你孤零零地留在漫长的时间内。我之所以喜欢木材厂,是因为在都德的《最后一课》中,写到小弗郎茨逃学之后,远处传来木工厂的电锯声,还有鸟儿飞翔。这篇由胡适用白话文翻译的课文写尽了逃学的快乐。此文除了最后一句,即老师用粉笔以毕生之力写下“法兰西万岁”显得奇怪外,通篇都可爱。木垛高入云霄。松香味弥漫在空气里,伴随着小弗朗茨喜欢的电锯声。我为了这篇课文,常去那里坐。松香如一股药味,清洌滞涩,让人感到亮晶晶的爽净。那些没加工的松树昏沉沉地躲在地上,揭一片鱼鳞似的树皮,露出新鲜的浅红,像红晕,也像新生的肉芽。小弗朗茨是我心中的朋友,而老师用毕生之力在黑板上写字在我看来则是可笑的。
后来在我知道小提琴并听过琴声的时候,也想起木材厂的松香。广州的发烧友听大提琴讲究“松香味”,那是装在纸盒里卖的像透明皂一样的松香块。他们听小号或其它管乐讲究“口水”,即唾沫飞溅的演奏录音。去年夏季的一个傍晚,街上驰来一辆少见的马车。马车一般在天亮前铿锵地驶过,送菜。这辆马车斜装松木方子,像斜背三八大盖的士兵一样,它们“嗒、嗒”从我身边驶过,马蹄优雅翻盏。松香如绚烂的花朵从鼻腔钻入,在心里开放。我(骑车)追随马车一直走到柳条湖立交桥。松香啊松香,你令人迷醉。在沈阳街头,松香带来多么高贵的气息。我凝视木头的白茬,纹理如酱牛肉一样粗犷,毛茬像动物的短绒。我想当一个车老板,他的屁股下面是松木,随着马蹄“嗒嗒”起伏。那时,唐韵的《苗岭的早晨》不召自来。这个人现在不知到哪里去了,她和盛中国是文革后期广播中允许播出具有“资产阶级靡靡之音”情调的小提琴乐曲的两名演奏者之一。她的演奏比盛中国更加简约、小心和富于南国气息。而《苗岭的早晨》主要是在模仿鸟叫。小提琴的华美音色使我在雨中驻步不行。那时每个电线杆子上都有一个喇叭,由赤峰市人民广播站用聚酯唱片播出。如果走到前面的电线杆的喇叭下面接着听,中间有一段距离会失去音乐。暴雨白天而降,当时我穿着带风帽的白衣白裤,像僵尸一样站在唐韵的琴弓下面。为什么扮白?那天学校去市中心搞一个游行,我们扮作防化兵。当时的逻辑是:假如有特务偷窥这场游行,立刻屁滚尿流地向上级报告,中国的防化兵太多了。如果敌机在一万米高空拍照,得出的结论亦复如是,他们就不敢对中国使用化学武器了。高一年级的同学装扮高射炮兵,因此敌人的飞机也不敢来了。敌人为什么不认为中国的中学生在搞披麻戴孝?所以敌人总是愚蠢的。苗族适合以树叶或巴乌吹出的舞蹈旋律,在小提琴上演奏就洋溢着一点点洋味。如果此曲让顾圣婴演奏,就更洋。湿润的森林气息,苗族女人微微扭腰带动短裙的摆动,欲说还休的妩媚,使我忘记了雨和防化兵,忘记了手里拿着像洗衣机排水管一样的防毒面具。小提琴总是让人想起女人。我考虑这是文革在很长时间不允许播放小提琴音乐的理由。纤美、多情、容易触动人的内心。中央文革的领导可能忘了,即使不播小提琴曲,赤峰街头也有不少女人,在老百货公司一楼卖钮扣的柜台还有一个外号叫“蝴蝶迷”的女人向人们飞眼。
在音乐结束之后,雨仍然没有结束。我抱着冰凉的电线杆子,听,它里面是否还存有一点点琴音,像嚼吮甘蔗的残汁一样。路灯在雨水中渐渐亮了,起初钨丝桔黄,后来变成一盏冷冷的水银光。
过了很久,我听到了盛中国的《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这个旋律的竹笛版是王铁锤吹的《帕米尔的春天》。带着中亚味道的塔吉克音乐,更洋了。切分音、跳弓,十六分之一音符。总之,他们把帕格尼尼和萨拉萨蒂的玩意儿弄到这个里面,令人美不胜收。那时,我们哪知道萨拉萨蒂?此曲展示醉醺醺的漫无边际。在禁欲的时代,这首曲子甚至富于广泛的淫荡气息。它比后来出现的《梁祝》好得多。中国人如此喜欢《梁祝》,好像列入四大发明都不为过,此曲虚假的波澜起伏和戏剧性结构,越剧小调的滥情。矫饰的感伤,抽风式的动静对比,使整个曲子像一场蛆虫赛跑。盛中国好像具有少数民族血统,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一般人高,奔放。虽然他的演奏注重表演性,像胡松华唱歌,但他比别的艺术家更真挚。当然真挚和朴素相结合的时候,艺术才臻化境。如钢琴家零洛维茨,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我想过一件事情,想了好多年。声音对人而言也具有化学物理学(研究化学的物理性特性)的性质。就是说,一种频率——波长,发声位置——所传达的是一种情感反射。这在人的声音传达中更为明显。所谓轻声曼语是荷尔蒙的频率设计方式。所谓吵架是用最不和谐的频率伤害对方。我每次听到人们吵架,比如泼妇的叫嚣时,就闭着眼听,感到仅仅是这种发声方式就能引发人的焦虑。而这种频率——比如撕心裂肺式,同时我知道这种叫喊会使嗓子迅速疼痛——恰恰又是叫嚷者抒发愤怒毒素的途径。我又注意到,我和不喜欢的人说话,无意中以一种难听的频率播出,有如噪声。而我和“领导”说话的时候,竟又用另一种频率,弱而迟钝。当然这是无意识状态下的波长。我不明白,在隔肌、声音、头顶与鼻腔共鸣中,人会在无意识中设计出这么多频率程序。而古人说的“心平气和”是多么高明。心不平,频率则会组成噪声曲线。而一个人一辈子用一种口气(固定波长)说话,亲切、和蔼、圆润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而音乐,特别是大师们的音乐,是把毕生心血完成的最佳频率传达给我们。
阿根廷钢琴家阿格丽姬演奏的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让我们感到什么叫诗情画意,什么叫水晶般清澈的色泽。当我用普通物理学的“频率”一词可笑地形容这一感受时,是说心灵的,即化学的因素会统治听觉神经。而人类所具有的频率程序更多地表现不满和古怪的愿望,而这种声音本身就是古怪的。我甚至想说,你是什么声音(色彩、节奏、宽度),你就是什么人。你就是你所塑造的人格的配音演员。而大师所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种谈话或朗诵。是以无比丰富的弦乐与管乐组织的旋律和织体,是一个独立世界。心灵所需要的泉水,或者说内分泌所需要的创造快乐与宁静的化学激素的听觉资源。
我曾经说,一个人如果在早上“心机”还没有工作的时候听帕尔曼的“辛德勒名单”,这一天也别想干坏事了。人们常问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上帝?或上帝怎么会漠然于人间美好事物的毁灭,而没以人类所能知的方式,譬如冰雪地震来表达立场,以至汉代诗文常曰“天耶!”。辛德勒的名单不会是演奏给纳粹即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徒听的,而是给上帝的一封信,小心询问上帝对于暴行的态度。另一方面,犹太人崇信上帝的方式并不是“天耶!”,像烫着了一样。隐忍,自己买单,相信上帝是一种理想而不是审判官,所以犹太人揣摩到的宇宙秘密最多。从爱因斯坦到帕尔曼。帕尔曼用令人心碎的小提琴诠释与美好密不可分的悲抑。这不是疑问与思考,是在回忆血管里流出的最后几滴血时的情形。如果这支曲子在早晨出现,我想到的是,事实上我们都有可能做一个圣徒,有可能对每一个人都好一些。所谓庸俗,就是你从一天的早上开始,被一连串“庸俗”的人所激怒,与所有妨碍了你的尊严与利益的人据理力争。血管占上风的是所谓勇猛和正义的气慨。气慨使一个人大义凛然、一错再错。错就错在已经不能摆脱从一己的角度来看待周遭。庸俗还包括动用复杂的智谋程序应付所谓复杂的人生。敷衍、乡愿、谄媚、装拙守愚。还有更加低级的中伤、诽谤、愤怒、嫉妒。人生弱点的肌肉每天都在这些程序演示中锻炼的坚实有力,欲罢不能。而这一切,原本以安详、顺变与澄明的心境就能一以应之。风吹落叶,飒然入境。人的一颗心恰如某风景区绝壁上的悬石。石与石只有一线相连,形如累卵,除不可睹。心若不动,即谓看着险,它并不险,有如不动。
以撒克·帕尔曼。他的泪水已经干了,像琥珀镶嵌在心房的周围。他的心在犹太人的苦难史毒焰的煎熬下,化为羽毛,根根想飞。在他的琴声里,死亡的辗转反侧可以化为美,青春的热泪飞迸可以化为美,老人的瘦弱手臂上会长出一片片新绿的嫩叶枝。追思与弥撒低回不已,却节节充斥生机。帕尔曼和祖克曼在莫扎特的小提琴、中提琴协奏曲中,互相问候,亲切可爱。在厚实如橡木十字架的主题之下展示甜美。二人在巴哈的双小提琴协奏曲中,飞瀑一般地模仿对位,瑰丽无比。此曼与彼曼都出生于特拉维夫。同时受教于朱丽亚音乐院的葛拉米安,同气相求,天衣无缝。
责任编辑 刘羿群